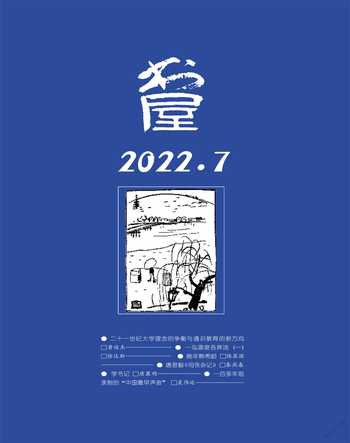二十一世紀大學理念的爭衡與通識教育的新方向
黃俊杰
二十一世紀,大國博弈,戰爭頻仍,使國際秩序輿圖換稿;病毒肆虐全球,各地封城斷航,使平民百姓生活困難、孤苦無告,在此起彼落的“脫鉤”聲中,也為“反全球化”潮流推波助瀾;氣候巨變,天災接踵,地球正處于“氣候緊急狀態”,極為危險。在高等教育領域,“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教育觀勃興,挑戰傳統的“非工具論”(non-instrumentalism)教育哲學,造成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理念激烈震蕩,使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徘徊踟躕。大學師生站在“工具論”與“非工具論”交叉的十字路口上,悵望前路遙遙,未知何去何從。
二十一世紀勃興的“工具論”大學教育觀主要表現有四:(1)綜合性大學以大量資源投入就業導向的院系,如工學院、電機學院、信息學院、管理學院、商學院、醫學院等,相對忽視理學院、文學院或藝術學院。(2)重視大學課程的“設計思維”,以產學合作、市場導向為目標。以“設計思維”為中心的教研新方向,始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而其影響及于各地。(3)強調“大學社會責任”,重視大學為社會、政治及經濟部門服務之功能。這一概念是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最早提出的,他曾分析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美國大學教育“商品化”的趨勢,提倡“大學社會責任”。但是博克校長亦有感于“大學社會責任”一詞提出以后被過度“語言膨脹”,雖然有些一流大學以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指標”作為“大學社會責任”,但是也有許多大學假“大學社會責任”之名,追逐短期的利益。所以,他在1991年哈佛第三百四十屆畢業典禮致詞特別強調:“在現代社會當中,大學有兩種重要的社會責任,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研究。雖然這個想法一點都不具有革命性,但這項使命卻沒有得到各大學的注意。”博克校長的論點確實言中當前國內外大學過度追求并扭曲“大學社會責任”,在“加強在地鏈接”或“參與地方創生”的口號之下,一些大學舍本逐末,而造成“教育主體性錯置”的問題。(4)特重“工具性技能的學習”。即通過實際操作,一方面提升學生使用這些工具之技能與效率;另一方面則經由應用,訓練學生分析、批判、邏輯和統整等能力,培養其思辨、學習,以及轉化資源的能力。這樣以培育“工具性技能”為目標的教育理念,非常鮮明地表現出“工具論”教育觀。
在“工具論”大學教育觀方興未艾之際,源遠流長的“非工具論”大學教育觀,也在呼喚著大學的靈魂。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與研究在人的培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曾參與歐洲學者所執行的2015年世界人文學科研究概況研究計量的一小部分工作,檢討世界各國人文學科研究與教學的狀況,發現人文研究在許多國家都未受到應有的重視。2013年美國人文與科學研究院提出題為The Heart of the Matter的報告,指出“人文與社會科學對于我們的開國元勛所揭示的追求生活、自由與幸福,是不可或缺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是‘事情的核心’”,這本報告書可以說代表了美國高等教育界中“非工具論”教育觀在二十一世紀的呼聲。再以日本為例,2015年6月8日,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后簡稱“文科省”)發出公文,要求設有人文社科系所的八十六所國立大學向“社會需求度高”的方向改革大學組織與業務。日本文科省這種功利取向的教育政策引起日本知識界極大批判。2015年7月23日,隸屬內閣府的“日本學術會議”干事會發表聲明,批判政府偏重自然科學而輕視人文社會科學的政策,并且重申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必須三足鼎立,在大學研究與教學中必須力求均衡。聲明又強調在“全球化人才”培育的過程中,必須重視人文社科教育所培育的跨文化視野與批判思考能力。從以上美、日兩國的例子,我們都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界以教育為工具的新潮流固然風起云涌,但是“非工具論”的大學教育觀仍然非常強勁,在風狂雨驟中重申“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含義。
所謂“非工具論”的大學之理念,在東西教育史上都源遠流長,在西方可以上溯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東方可以上溯到孔、孟。孔子說“君子不器”。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說“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以現代的話來說,“器”就是一種“技術性的能力”。朱子又解釋孔子這句話說“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朱子的解釋非常正確地闡發了孔子所謂“君子不器”的意義。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這部經典著作中區分“技藝”與“實踐的智慧”的差別:“技藝”或“技術”如建造房子等技術,是人的理智運用在制作事物之上;但“實踐的智慧”是一種理智的才能,它使人達到事實的真理,即分辨人生的善惡。亞里士多德的講法與孔子“君子不器”的說法,東西互相輝映。
以“非工具論”教育哲學為基礎的傳統大學理念,特別重視教育的目標在于喚醒學習者的心智或心靈,使他們不會成為朱子說的只有“一才一藝”的“小人”,而是體知、體會、體證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實踐的智慧”。這樣的大學之理念,注重學生的“生成”問題遠過于“存有”問題,其目標不是使學生成為達到社會、政治或經濟目標的工具,而是使學生成為頂天立地、堂堂正正、自作主宰的“人”。
“工具論”教育觀的勃興,實有其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因素,包括國際秩序重構;經濟“全球化”潮流之下,M型社會形成,貧富差距擴大;國際間強凌弱、眾暴寡、富欺貧;主要工業國家少子化趨勢嚴重,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浪潮激蕩,民族主義與政治唯我論再興;民主政治退潮(美國政治學家稱為“Democratic Recession”),經濟保護主義、強人政治與民粹主義再次興起;人工智能快速發展,沖擊著人類文明的未來;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等。這些都使人類身處危急存亡之秋,逼迫教育方法與內容必須重整。
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工具論”之勃興,與戰后世界高等教育之快速擴張也有直接關系。1950年全世界共有大學三千五百所,學生六百六十萬人;2000年,全世界共有大學三萬所,學生八千零五十萬人;2014年起全世界留學生達五百萬人;2021年,美國共有三千九百八十二所大學,中國教育部統計的全國高等學校共計三千零一十二所。在高等教育擴張、少子化成為新趨勢兩大因素相激蕩之下,大學經費拮據,辦學日益艱難,許多大學的因應之道就是特重就業導向的職業教育。例如2013年5月24日,日本文科省提出的《學校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經國會通過,從2019年4月1日起,在全日本各地創設“專門職大學院”(四年制)或“專門職短大”(兩年或三年制),將教育內容集中在就業能力的培訓,教育目標在于提升學生畢業后在職場的“即戰力”。從表面來看,“工具論”教育強化學生的工作能力,使學生畢業后有一技之長,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但從其本質來看,這種實用主義的教育觀,實為配合社會精細的分工體系而訓練所需的勞動力。而大學畢業生則淪為社會學家貝爾所說的“后工業社會”中“無臉孔的”勞力提供者。在“工具論”教育觀主宰之下,大學通識教育之日益邊緣化,實屬理所當然,事所必至。
行文至此,我們要問:二十一世紀是信息社會的新時代,是“自動化”與“工業5.0”的新時代,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激烈沖撞的新時代,通識教育對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到底有何重要性?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響應:
第一,只有優質而有思想深度的通識教育,才能培育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長程競爭力。上文所說現階段甚囂塵上的“工具論”教育觀,著眼于培育學生大學畢業后短程的競爭力,特重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以訓練學生的“工具性技能”,提升學生畢業后的“可被雇用性”。“工具論”者強調,以求職為導向的大學教育,使學生獲得一技之長,畢業后可以在二十一世紀社會分工體系中找到一個求職的立足點,不至于成為家庭與社會的負擔。以上論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正如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博克在他所著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一書中所說:“問題并非該不該廢除所有職業課程,而是要不要給予學生除了技能訓練之外更廣闊的職業視野?”優質的通識教育,正可以補“工具論”教育觀的局限,使學生成為“人”而不是被使用的“人力資源”或“對象”。
但是,“工具論”者往往未能正視學生生涯發展的一項事實:在大學時代過度追求短程的競爭力常常成為長程競爭力的限制,甚至是長程競爭力之摧毀的開始。
第二,再從大學教育的現狀來看,人文素養教育是大學師生“永恒的鄉愁”,仍然受到世界各國重要大學的重視。例如美國有一些一流的“人文學院”以極低的生師比,為學生提供極優質的基礎教育與通識教育。日本則在多數四年制大學都設有教養部或教養學部,以執行“教養教育”的教學任務,如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都設有教養學部,都極重視通識教育。所以,通識教育仍是當前世界頂尖大學教育的基礎,例如日本東京大學推行大一、大二不分系,大一、大二學生同屬“教養學部”,必修“文”“理”兩個領域共六類課程,包含基礎科目四十四至五十四學分,以及綜合科目加主題科目共十八學分;京都大學的校定畢業總學分是一百四十學分,全校共通科目五十六學分,必修兩種外語;美國斯坦福大學要求學生選修通識課程二十五學分;哥倫比亞大學則規定學生需修習通識課程四十至四十六學分,其推行超過半世紀的經典教育,更是通識教育的典范。
我以上所說大學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必然招致形形色色的批評,其中最常被提出的批評就是:在二十一世紀機器人搶走大量工作機會,疫情造成大量青年失業的苦難之中,提倡通識教育未免過于不識時務,因為它不能協助青年一代解除他們所面臨的困境,所以大學必須教導“有用”的知識。這項質疑本于悲天憫人的胸懷,著眼于青年一代當前的就業困境,確實具有極高的說服力。如果我以上所提出“短程競爭力的過度提升,常是長程競爭力的摧毀”這項論點,尚不足以說服以上這項質疑的話,我想再提出以下三點意見:
第一,許多人判斷知識之“有用”或“無用”的標準,常常著眼于這種知識能否為擁有者帶來“物質性”的利益,例如使個人獲得較高的收入、為國家創造更大的經貿利益或社會安全等,這樣的知識觀及其衍生的對待教育的態度所聚焦的是知識的“邊際效用”,而不是知識的“內在價值”,也不是知識所能創造的“精神性”的愉悅。這樣的知識觀與教育觀非常淺近而且狹隘,如果以這種力求“有用”的態度辦學,對大學教育的傷害顯而易見,其流弊比“緣木求魚”更加嚴重。正如孟子所說:“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后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后必有災。”
我想舉二十世紀上半葉偉大教育改革家弗萊克斯納的論點,進一步闡釋我以上的看法。弗萊克斯納曾調查北美地區的醫學教育現狀,在1910年將調查結果寫成《弗萊克斯納報告》,引起北美教育界極大震撼,此后北美地區的醫學教育就從招收高中畢業生施以四年醫學教育的四年制,改為大學畢業才能申請的七年制醫學教育。弗萊克斯納在1930年應邀出任世界第一所由民間捐資創立,不隸屬于大學、企業或政府的“高等研究院”創院院長,他第一個邀請的研究員就是愛因斯坦。弗萊克斯納曾在1939年發表一篇文章,題為《無用知識的有用性》,文字行云流水,內容非常深刻。弗萊克斯納歷數電子學諸大師如麥克斯韋、法拉第等人的偉大成就后,指出科學上最偉大的突破性進展源自科學家的“好奇心”,他認為“好奇”是推動近代科學最主要的動力。他進一步指出,在此時看似“無用”的知識,常常潛藏著未來發展的因子。弗萊克斯納以他領導“高等研究院”的實際經驗強調,在“高等研究院”內行政工作必須減到最低,他特別強調必須移除“用”這個字,人類精神才能獲得解放。弗萊克斯納這篇文章,可以視為對莊子所說“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這句話最佳的現代詮釋。
大學通識教育必須回歸教育的“內在價值”,而不是執著于知識的“有用性”。
第二,認為通識教育乃是“無用”的教育的人,常常認為“技術性”能力的訓練才是“有用”的教育,而“思考性”能力的培養則是“無用”的教育,通識教育正是“無用”之學。這種對于“有用”與“無用”的區分,最大的盲點在于忽視許多“技術性”知識其實以潛藏著“思考性”的因子為基礎,兩者難以涇渭分明地一分為二。因此,以通過跨領域學習而提升思考能力為目標的通識教育,并不能被視為“無用”之學。舉例言之,以“工業文明的發展”為題的通識課程,雖然講授科技的突破歷程,但是必然涉及近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基礎。
第三,知識之為“有用”或“無用”,常常決定于該知識系統所存在之脈絡或情境之中。學生從通識教育課程所習得的知識,如果放在一個小的脈絡或情境之中,可能無法發揮作用,但是如果置于較大的脈絡或情境之中,可能大放光芒,適得其所。
為了說明以上論點,我想以木材為例。一根木頭如果棄置于路旁,經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可能成為“無用”的朽木。但是,同樣一根木頭如果置于殿堂正中央,就成為“有用”的棟梁。因此,所謂“有用”或“無用”,決定于所置放的脈絡或情境。同樣地,學生從通識教育所獲得的知識或思考能力,在他們大學畢業以后,如果在適當的時間、情境或脈絡之中,極可能從表面上“無用”的知識,瞬間轉化為“有用”的學問或能力。
綜合以上所說,認為通識教育是“無用”之學,是無法成立的論點,必須予以揚棄。
那么,對于二十一世紀的大學而言,通識教育的新方向何在?
我想建議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兩個新方向:第一,新時代的通識教育應引導學生向內深思。所謂“向內深思”,指通過通識教育而引導學生追求生命的意義,尋覓價值的立足點,并培育“機器不可取代的能力”。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信息社會的時代,信息的解讀與分析能力極為重要,尤需具備“道德判斷”之能力,所以培育思辨能力的人文教育乃成為必需。二十一世紀也是一個“自動化”快速發展的新時代,大學通識教育應培育學生的“同理心”能力,也就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斯坦福大學前校長約翰·軒尼詩的回憶錄中,特別強調“培養未來領導人的同理心”;“價值”的創造力;進行道德判斷的能力;感受別人的痛苦并發自內心與別人溝通的能力,以及感恩的能力等。二十一世紀更是一個“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激烈沖撞的時代,各種文化與價值理念互相激蕩,因此我們更需要優質通識人文教育,在“自我中心心態”與“普遍關懷”之間,賦予人以一個價值的立足點,從有限的生理生命之中,創造無限的文化意義。
所謂以“向內深思”為導向的通識課程,教學目標在于引導學生面對生命的六大問題:(1)生命的有限性。(2)病苦的不可避免性。(3)死亡的必然性。(4)死后世界的不確定性。(5)生命意義之可創造性。(6)生命提升之可能性。在這種通識課程里,師生可以一起深思生命重大課題,例如:如何從“有限”創造“無限”?校正生命的方向感、節奏感與意義感。如何從“必然”(涉及規律)悟入“應然”(涉及價值)?深思生命的“所以然”,邁向生命的“所當然”(涉及“普遍性”與“規范性”)。
我之所以提出以“向內深思”作為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第一個新方向,主要是著眼于二十世紀的大學教育主要方向:追求知識的“客觀化”“數量化”“標準化”,并在以上基礎上追求知識的“商品化”,訓練學生某種特定能力,使學生在畢業后可以融入社會細密的分工體系之中,使得大學生在學校所學的“套裝知識”與自身的生命之覺醒關系較遠。
引導學生心靈向內深思的優質通識教育就切中時弊。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原鄉”,大學教學與研究最卓越的老師,都應投入通識教育的教學,像海里的鮭魚以全部生命力游回他們出生的原鄉。通識教育更是生命的學問,大學應以最優質的通識教育,送給學生一雙手工縫制的皮鞋,使他們畢業以后,可以走過生命的荊棘與磨難,使他們在生命的大船上,不會每天盯著甲板或船舷兩側的波浪,使他們可以常常仰望北斗七星,時時校正自己生命的航向。
第二,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方向在于引導學生開拓眼界。就現實而言,大學應經由通識教育而引導學生植根中華文化,宏觀世界文明。總而言之,通識教育的目標在于培育會思考的“人”。“人”是一切的根本,教育必須回歸“人”本身,在訓練學生成為專業人士之前,必須先成為“人”,因此,通識教育也可以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教育。
我提出“開拓眼界”作為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第二個新方向,主要是有感于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世界各地民族主義思潮泛起,有些國家更陷入“自我中心”之心態而不自知。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后,歐美社會常見歧視亞裔人士的“仇恨犯罪”,各地政客為獲取選票與個人利益,鼓勵“仇恨政治”。在這種“部落主義”與“自戀狂”的狂流之下,如何撥開仇恨所帶來的云山霧海,使新世代大學青年能對“他者”與異文化獲得較為健康的理解,將“仇恨”轉化為“愛心”,就極為重要。先秦孔門樊遲問“仁”,孔子說“愛人”。孔子言簡意賅的兩個字,在二十一世紀仍具有深刻的意義。二十一世紀的優質通識教育的新方向,在于引導大學生植根中華文化,并宏觀世界文明,培育新時代青年參與二十一世紀文明對話的能力。只有眼界宏闊,二十一世紀的新青年才能心平氣和地與文化的“他者”親切互動,開創世界和平的新愿景。
總而言之,如果說二十世紀高等教育的基本方向,在于訓練學生求生存的技能,那么展望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的發展,優質的通識教育就是喚醒大學靈魂不可或缺的教育。新時代通識教育在現在的職業教育基礎之上,既必須引導學生深思生命的意義與方向,又必須開拓學生的胸襟。這樣,學生才能參與二十一世紀諸多文明之間的對話,成為新時代有守有為的新青年,開展可大可久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