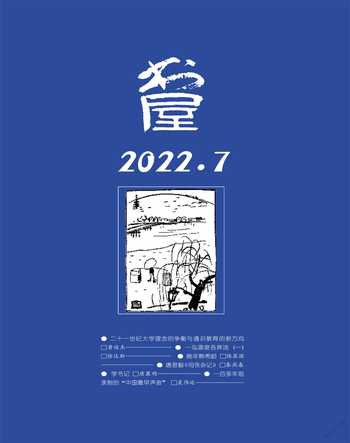短篇小說的當下困境
劉金祥
短篇小說是一種具有鮮明藝術屬性和特定人文功效的文學體裁,在中西方文學發展史上歷來自成一派、獨標一格。多年來特別是近年來,短篇小說的文壇地位每況愈下,為文學出版界所輕視的境遇似乎越發嚴重,幾乎被擠兌和逼仄到小說陣營的邊緣,這已成為無須爭辯的客觀事實。橫察縱覽當代文學出版界,不難發現很多文學期刊發表短篇小說的數量越來越少,有些文學期刊甚至取消了短篇小說的欄目和版面,而絕大多數出版機構也不愿意出版短篇小說集(選),因而,除了一些文壇大家名家之外,普通作家和一般作者撰寫的短篇小說很難發表或出版。由此可推測,屢遭怠慢與冷遇的短篇小說,其品質和數量正不同程度地下滑和縮減,美國著名作家兼詩人厄普代克曾用“緘默的年代”來概括短篇小說的這種現狀。但即便如此,我國一些幾乎專事短篇小說的作家并未氣餒和消沉,而是以極大熱忱和心血苦心經營短篇小說這塊園地,以堅執態度和堅韌毅力表現出對短篇小說的癡情與迷戀,以濃郁的短篇情結支撐自己繼續操弄擅長的文學樣式,繼續保持慣有的文學執念和姿態,如鐵凝、王祥夫、溫亞軍、裘山山、金仁順、南翔等作家,不僅依舊在短篇小說創作田野上辛勤地耕耘,而且近年分別發表了較有影響的《信使》《滑著滑板去太原》《見面禮》《一路平安》《小野先生》和《苦櫧豆腐》等佳作名篇,傳遞著歷史的回響與現實的聲音,給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不僅為當代文學書寫增添了一抹亮色,也為文壇生態注入了和諧動能。
短篇小說是一種對社會現實非常敏銳的文學體裁,所謂文學的輕騎兵,也是一種對自身發展演變反映迅捷的文學形式,在整個文學結構中占有重要分量,在小說史乃至文學史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直為中外眾多作家鐘情,契訶夫、莫泊桑、海明威、歐·亨利、福克納、茨威格、川端康成、艾麗絲·門羅、蒲松齡、魯迅、郁達夫、張愛玲、孫犁、沈從文、汪曾祺、林斤瀾等,這些文學大師都是憑借短篇小說享譽文壇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技巧性強、美學醇度高的短篇小說,要比體量龐大、字數眾多的長篇小說更接近小說藝術的內在本質,更能將文學的韻味和生活的況味表達出來,更能體現文學藝術的精致、細膩和優雅。這是由于短篇小說在選取社會生活某一斷面的同時,對斷面某些細節進行藝術上的精雕細琢,如同胡適在《論短篇小說》中所說“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而對“生活斷面說”,茅盾先生也有過精辟闡述:“短篇小說取材于生活的片段,而這一片段不但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并且使讀者由此一片段聯想到其他的生活問題,引起了反復的深思。”事實上,只要我們認真翻閱近年《中華文學選刊》《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和《小說選刊》等刊物,還是能夠讀到諸如《信使》《跳馬》《燉馬靴》《父親的長河》《晚春》《化學》《船越走越慢》等一些文質兼具的優秀短篇小說的,這些小說正是截取了新時代社會生活的某些斷面或側影進行深度文學加工,體現出藝術質地和美學風格的高超性和創新性,雖然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文壇引起巨大反響的短篇小說不可同日而語,但這些作品無論是題旨寓意還是表達技巧,均是新時期文學思潮在當今文壇的余響和賡續。這固然與當下作家文學素養提升有著一定關系,但更主要的是由新時代我國文學發展背景和演進過程決定的。筆者以為,即將評選出的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無疑還會出現一些主題新異和構思精巧的短篇力作。
即便涌現出一些有溫度、有深度、有高度的短篇力作,但總體上短篇小說依舊處于受冷待的艱窘境遇,依舊被文學出版界所不容,依舊孤默沉寂和波瀾不驚,個中原因與時下的社會心理有著內在聯系。近些年來,眾多出版機構變成了不再由財政供養的文化企業,為了在圖書市場上求得生存和生存得更好,出版機構對于長篇小說更加鐘情和青睞,對于短篇小說集(選)則加以回絕和拒斥,簡單地認為凡是長篇小說就會帶來收益遞增,凡是短篇小說就會造成效益下降,這是一種既不懂得市場法則也不知曉文學邏輯的盲目行為。“短”絕不是短篇小說的缺憾和短板,相反,這恰恰是此類文學樣式的特點和優長,短篇小說就是依靠篇幅精悍、語言簡潔、結構整飭、情節濃縮而取勝的。如果只針對“短”進行考量和審度,那么目前圖書市場上各種由短小文章輯錄而成的散文隨筆集大暢其銷則無法解釋。這種類比也許有些牽強,但在海量出版物中卻鮮見短篇小說集(選),無疑就是一種有悖常理的怪誕現象。事實上,在知識碎片化的信息社會里,大部分社會成員對于精神文化產品的需求,均喜歡“短平快”而厭棄“長冗慢”,尤其是當下讀者對于一窩蜂式的長篇出版物或者粗制濫造的長篇小說早已無法忍受、疾首蹙額,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比較精致精彩的短篇小說集(選)為大眾所接受,應符合社會心理。
當然,如上所述,短篇小說不受待見主要是出版結構變化所導致的,正如評論家李敬澤所說,“現在的文學出版基本上莫名其妙地有一種長篇崇拜”。而文學界自身愈演愈烈的“內卷化”,也是短篇小說衰落式微的一個重要原因。當下很多短篇小說的寫作高手,紛紛放棄自己的優勢和領地,競相加入長篇小說寫作隊伍中來,其結果必然是從事長篇小說寫作的作者陡然增多,而短篇小說寫作資源卻漸趨流失。許多文學青年涉足文學創作伊始就直奔長篇小說,他們的作品大都故事重復、人物僵化、語言呆板、結構混亂、主題單調,特別是很多作品的主題重復度頗高,同質化現象異常明顯,沒有展示出青年作家的個性與鋒芒,沒有表現出一種勇于挑戰和突破傳統的銳氣和勇氣。相反,他們幾乎普遍在販賣悲情、兜售苦情,異口同聲地發出青春破碎的聲音,文學創作遂成為這些青年作家“悲情苦情的角逐場”。這種一味迎合大眾心理的急功近利的畸形寫作應得到警惕和反思。客觀地講,短篇小說的勞動量、所觸及社會現實的深度以及可能的思想內蘊難以與長篇小說相提并論,但短篇小說對宏大問題的反映與關注更具張力,更有滲透性和穿透力,更能集中筆觸聚焦問題的癥結與本質。正如有的評論家所指出,“故事重要,但敘述更重要,尤其敘述中的結構力,是形成作家穩定的敘事文本風貌的保證”,所以,由于題材、容量和敘述方式等因素,短篇小說駕馭起來似乎更有難度,也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難度,短篇小說才成為小說藝術的重要更新對象,才成為體現文學創作整體水準的一個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