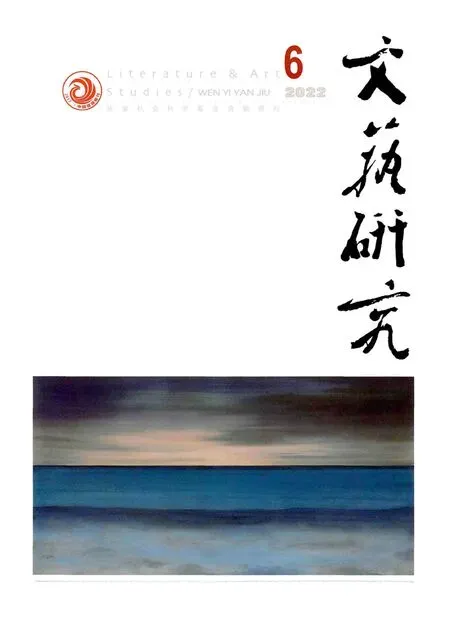麥格芬、移情機制與推拉鏡頭
——客體小a及齊澤克電影批評反思
陳林俠
從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開始,精神分析理論就認為“否定性存在”(缺席、空白)的重要性遠遠超過“肯定性存在”。拉康承續這種思路,認為存在不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是其所是”,而是根底的“匱乏”狀態。這就是后期拉康強調的實在界,其表現形式就是“客體小a”(objet petit a),即實在界或原質(the Thing)抵制象征化但又被象征化時產生的剩余。它作為一種特殊的悖論性符號(既否定/匱乏/缺席,又肯定/存在/在場),緩解了需要(demand)與需求(need)之間的對抗性僵局。齊澤克服膺于拉康理論,對這個悖論性概念自然心領神會:“拉康把我們行為的‘副產品’命名為小客體(objet petit a),即隱秘的寶藏(hidden treasure)。它‘在我們之內又不是我們’(in us more than ourselves),是神秘莫測、難以企及的未知數(X)。正是這樣的未知數,為我們的行為賦予了充滿魔力的光環,盡管我們無法把它歸于我們身上的任何實證性品質(positive qualities)。”
齊澤克通過闡釋電影案例來論述哲學觀念,其研究具有自身的特點。在分析希區柯克的電影前,他開宗明義,“我們從一開始就要剔除希區柯克電影中的敘事內容”,這是其電影批評一貫的方法與立場。然而,需要追問的是,齊澤克真的剔除了電影的敘事內容嗎?一個基本事實是,他的論述恰恰是從故事內容延伸出來的。正因如此,抽象的理性思辨與特殊語境中的形象、事件之間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抵牾。任何電影文本都難以完全對應于某種理論主張。無需贅言,“客體小a”這一拉康的重要概念,能夠借助充分的文字表達與邏輯推理獲得深入論證,然而,一旦落實在具體文本中,它就會與故事包蘊的日常經驗、人物及其社會關系糾纏在一起。筆者認為,電影的自足性幾近天然地抵御著理論的強行介入,電影闡釋存在限度。我們在激賞齊澤克電影批評的同時,有必要指出這一點。
一、什么是電影的客體小a?
吳瓊認為,“客體小a”是拉康理論中“含義最為曖昧復雜”的概念。它處于拉康理論話語的樞紐位置,成為實在界、原質、征兆、剩余快感、主人能指、主體、欲望、凝視、縫合等諸多理論、概念的交會點。齊澤克借用拉康理論,在不同場合對客體小a做出多重維度的論述:一方面,它是“意指為作為我的那種東西”(拉康語),用來解釋在一切實證性屬性之外的主體身份,構成主體最為本質的部分;另一方面,它處于主體核心的實在界點位(point of Real),是每次符指化運作的殘留。這個“作為我”的客體小a逃離了主體的掌控,不是主體的一部分。這就是“我是我”但“我不知道為什么……”的原因所在。張一兵很好地描述了這一悖論性過程:主體進入象征界后,最初是在“主人能指”(原初能指,S1)的指認中獲得穩定的身份,但在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不再簡單維系象征身份的同一性,反倒開始消解這種同一性,并以不斷暴露自己的所謂‘不體面’的‘真實’(客體小a)來確認主體的連貫性”。由此看來,客體小a既是同一性身份成功又是其失敗的剩余物,是阻礙主體完全實現的“喉中之鯁”。齊澤克多次用黑格爾的名言“精神是塊頭蓋骨”來做比喻,比如:“我們獲得了關于對象a(object a)的一個可能性的定義:實體的剩余,那塊‘頭蓋骨’(‘bone’),它拒絕主體化;對象a在與主體絕對的不相容當中與主體相關聯。”毫無疑問,從拉康式主體的維度來闡釋客體小a,是齊澤克重要的理論內涵。
在齊澤克的電影批評中,客體小a是與實在界關聯在一起的“實體”(或被稱為希區柯克式的尚未進入象征界的“客體”)。如果我們把電影視作一個符號表意體系,那么闡釋實在界的具體影像就是客體小a。因為實在界抵制象征界的符號化,只能通過剩余物回溯性地表明自身的存在,電影作為影像符號體系(象征界),也就應該只有客體小a,而沒有實在界。所謂電影中的“實在界”并不神秘,它是與其他思想觀念一樣存在于接受維度上的回溯性認知、完形、想象;它產生于鏡頭之間的斷裂與沖突,而不是呈現在銀幕上的具體影像。就其形成方式而言,它即是愛森斯坦意義上的理性蒙太奇。因此,嚴格來說,齊澤克用具體影像論述的“實在界”實例,其實都不是實在界本身,而是實在界抵制象征界的殘余,即客體小a。他認為必須區分三種客體:麥格芬是匱乏,實在界的殘余,用a表示;主體之間流通的交換客體,用S(/A)表示;原質的沉默化身,惰性存在,用Ф表示。盡管從文字闡釋來看,三者似乎涇渭分明,但在他舉出的電影案例中,這三種類型顯然混淆在一起。
比如,齊澤克認為交換客體包括希區柯克《辣手摧花》中的戒指、《火車怪客》中的打火機、《擒兇記》中的小孩、《電話謀殺案》《美人計》中的鑰匙、《貴婦失蹤記》中的老婦人,等等。“這樣的客體在主體之間循環,并把他們卷入網絡,而他們又無法控制這個網絡。”然而,一方面,電影是一個符號表意體系,意義在循環與交換的網絡中產生。齊澤克認為,客體小a是“已經成為剩余快感之化身的客體-成因界定為剩余之物,它逃避普遍交換的網絡”。作為剩余之物,客體小a“逃避”但又不得不在交換的網絡中出現,否則就無法表明自身的存在。而且,作為剩余快感之化身(欲望)的客體-成因,它一旦出現就必然處于普遍交換、流通的網絡中,與所謂的“交換客體”混淆在一起。被他歸為麥格芬的細節,如《三十九級臺階》中飛機引擎的公式、《美人計》中裝了鈾沙的酒瓶、《貴婦失蹤記》中加了密碼的樂曲等等,難道不都是在人物關系的網絡中循環流動的交換客體嗎?另一方面,既然交換客體只是一個在人物之間流通的道具,其本身的內涵顯然并不重要,它就成了啟動劇情的純粹借口即麥格芬,但這難道不應該屬于客體小a嗎?齊澤克在具體論述時也時常將二者混淆。《三妻艷史》中一直“空缺”但推動情節發展的艾迪,應當是客體小a,卻被他說成“交換客體”。他一方面認為《美人計》中的鑰匙是交換客體,另一方面又認為它是被推拉鏡頭凸顯出來的,而按照“推拉鏡頭捕捉客體小a”的說法,鑰匙其實應是客體小a。再如,他將《貴婦失蹤記》中的老婦人明確歸為交換客體,但又認為她是“欲望的客體-成因”,即客體小a。概言之,以上被歸為交換客體的細節哪一個不是欲望的客體-成因呢?它們在電影中的功能無一不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麥格芬。
齊澤克指出,第三種客體由于標志著“沉默的原質”而具有“龐大、沉重的物質存在”特征。然而,他用作例證的《群鳥》中突如其來的鳥并不“龐大”,《艷賊》中的大船殼也沒有“沉重”的意涵,這些特征究其根本是由實在界所決定的。如此,上文提到的交換客體(如戒指、打火機等)既然意味著死亡、陰謀、惡,指涉缺席但又在場的實在界,就也可以說成是“一個不可能的原樂的沉默化身”。再如希區柯克《怪尸案》中的尸體、《奪魂索》中行兇的創傷行為,大衛·林奇《我心狂野》中點燃的火柴、《藍絲絨》中被割下的耳朵,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誡》中突然爆裂的墨水瓶和牛奶瓶、《藍色》中毛茸茸的小老鼠,安南德·圖克爾《狂戀大提琴》中的大提琴,等等,這些都是標識了“一小片實在界”的“沉默化身”,但它們恰恰又被歸為客體小a。在齊澤克的闡述中,《帕西法爾》《異形》更表現出客體小a與第三種客體的相似性。安佛塔斯的傷口、雷普莉體內可怕的“異形”,都指代“在其身體中,又并非她自身”的純粹生命實體,一種無法遏制的可怖的生命體(如同隨時從雷普莉身體中跳躍而出的“器官”),一個脫離身體的“自組織的器官”,這不就是“不可能的原樂的沉默化身”嗎?
借助拉康的主體理論,齊澤克筆下的客體小a似乎有了更深刻的內涵。個體在成為主體的過程中,始終面臨“壞的父親或更糟”兩種選擇。選擇“壞的父親”意味著進入象征界的主體間網絡,受到大他者的異化;選擇“更糟”就是“面對欲望不讓步”,凸顯實在界中的死亡驅力。齊澤克在《重播》《揚帆》《獵鹿人》《羅密歐與朱麗葉》《蘇菲的選擇》中找到這樣的案例:第一次選擇父名,但在第二次選擇時則堅持客體小a,用“自殺性棄絕的姿態”償還債務,成為唯一自由的“主體”。需要明確的是,主體由于拒絕符號的認同,選擇了父名的不可能的反面,就成了被象征界排除在外的“瘋子”,這個拉康意義上的主體,就是“唯一自由的人”。但這種說法很難落實在電影案例中。從表面上看,確如齊澤克所說,他所列出的影片中的人物均存在“自殺性棄絕的姿態”,然而,這在不同故事中并非總與客體小a及其指涉的實在界相關。眾所周知,《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因誤會產生的悲劇,促使他們自殺的是愛情,很難將之說成“面對欲望不讓步”的死亡驅力導致的行為。《獵鹿人》中的尼克和《蘇菲的選擇》中的蘇菲的自殺行為雖然都出自主體選擇,然而過去的創傷性記憶令兩人“痛不欲生”,自殺恰恰是為了滿足個體的欲望。《揚帆》中夏洛特拒絕愛情的“棄絕姿態”,絕非齊澤克所說的“數年前自身處境的完全之重復”。她的創傷更多來自與母親爭吵并導致后者死亡的經歷,因此,當她看到與自己性情相似的緹娜時,就決定拒絕愛情,選擇更有道德感也更迫切的內心救贖。仔細分辨以上案例就會發現,人物所謂的“第二次選擇”都帶有強烈的倫理色彩,并不能凸顯客體小a所指向的實在界、死亡驅力,而是為了進入象征界做出的選擇;個體采取“自殺性棄絕的姿態”,恰是為了擺脫創傷性的實在界,在自我的道德救贖中建構主體性。

電影《揚帆》海報
在拉康、齊澤克這里,客體小a還具有結構主義的特征,即通過發現自己的“失位”“缺失”來推動情節發展。齊澤克認為,“麥格芬顯然就是小客體,是匱乏,是實在界的殘余”。麥格芬是可以投射任何欲望與幻象的“黑屋子”,具有純粹的形式性。在希區柯克電影中,“什么也不是”的麥格芬,只是一個用以啟動敘事的純粹借口,它的純粹性就表現在不存在任何客觀物象的空無(pure nothing)。“就其自身來說,完全無關緊要,出于結構上的必要性,它必須不在場;其意涵是純粹的自動反射性的(autoreflexive)。”也就是說,麥格芬的內涵是實在界抵制象征界的“什么也不是”的空缺。但對主要人物來說,它還是“有些意涵的”,這就在于它構成了欲望的客體-成因,即客體小a。麥格芬事實上并不神秘,簡單地說,它就是一種“對于情節重要、對于觀眾并不重要”的敘事策略,廣泛存在于類型成熟、觀念明確的電影中。在好萊塢電影中,麥格芬就是體現普適性價值的目標對象,而故事的亮點在于展示人物沖突的過程。如在西部片的探險奪寶故事中,雙方追尋、搶奪的具體對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危險環境中的冒險經歷,或雙方勢均力敵的爭奪運動。我們不妨進一步追問,電影中的麥格芬是否就是齊澤克所說的“什么也不是”的純粹的空無呢?齊澤克所歸納的“必須不在場”的純粹的空無,具有確切的能指,而“純粹的自動反射性”的意涵,也不過是內涵相對較抽象的所指。麥格芬絕非如齊澤克所說,“是啟動情節的‘秘密’,但它本身絕對無足輕重,‘一無是處’,而只是空白”,其重要性在于,它不僅是促使情節發生的結構,而且在價值觀念上就是拉康所說的“主人能指”。麥格芬的“空白”或“空洞”,不是缺乏所指,而是缺乏固定的所指,能夠被隨意替換。如《三十九級臺階》中的飛機引擎公式是公認的麥格芬,它在“記憶先生”臨終話語(能指)中出現,成為指涉捍衛國家機密(所指)的符號,以此滿足諜戰片這一類型強調維護國家權益的意識形態要求。《美人計》中的鈾瓶也是麥格芬,它是一個具有確切含義的能指,指向德國納粹分子的陰謀。《海外特派員》中的秘密條款、《貴婦失蹤記》中的樂曲等等,皆是如此。麥格芬是觀眾可以不用關心的目標,但它又恰恰是縫合敘事體的意識形態,對它的追逐、爭奪、回應,從價值觀念上支撐起敘事體。正是在這個角度上,齊澤克也不得不承認麥格芬還是“有些意涵”的。質言之,在電影的符號體系中,既沒有毫無意涵的所指,也不存在只是占據一定位置的“空位”的能指,只要在電影的符號體系中占據某個位置,就一定有相應的能指和所指。齊澤克所說的純粹空無的麥格芬,在電影中根本不存在。
二、電影如何生成客體小a?
作為悖論性概念的“客體小a”是在什么情況下產生的呢?齊澤克指出,拉康在第八期研討班“論移情”中提出“客體小a”概念,這意味著客體小a與精神分析的移情機制密切相關。“移情就是假定存在著真理,就是假定,在愚蠢的、創傷性的、缺乏一致性的律令事實(fact of the Law)后面,存在著意義(Meaning)。”換言之,精神分析師正是在移情機制中,擁有了超出自身的客體小a,成為“想必知道的主體”,而且能巧妙地操控移情的情境(不想成為大他者的父親形象),從而保證精神分析活動的順利展開。用齊澤克的話說,這是信仰的惡性循環,非理性的理由只能讓已經相信的人相信。這無疑道出了精神分析的移情機制生成客體小a的實質。
然而,使用移情機制來闡釋電影中的客體小a,造成了齊澤克電影批評的現實困境。首先,就外在關系而言,精神分析的移情機制是分析師與被分析者之間的二元關系,雙方在活動之前就已達成協議,被分析者先在地賦予分析師超出自身的客體小a。與之相比,電影批評的機制要復雜得多,它是三元關系:闡釋者始終單向地面對闡釋對象(文本);闡釋者的權威性與闡釋對象無關,而是產生于第三方的接受者(讀者)。因此,從根本上說,闡釋者的權威性來源于自身的闡釋活動。然而,齊澤克主張類似于精神分析師的“斜目而視”的闡釋方式,認為我們只有如精神分析師那樣充滿欲望地觀看,才能發現客體小a,因為客體小a本身就是由欲望設置的。這種“斜目而視”的非“客觀的”方式,無疑把理性的文本批評變成了非理性的精神分析活動,只能讓相信他的理論的人相信他的批評。
更值得注意的是,電影批評與精神分析活動存在關鍵不同:客體小a無法由被分析者直接賦予分析師,或由批評者在故事之外直接賦予人物,而只能產生于虛構的人物之間。這就決定了,電影批評所分析的客體小a始終處于人物關系的網絡之中,絕非只是自身的理論預設,批評者需要根據文本世界的人物、事件、情境深入分析。如前所述,希區柯克電影中的麥格芬之所以被齊澤克視為客體小a,是因為批評者發現這種空缺具有重要的敘事功能,但是,這顯然不是人物賦予它的“在其中又超出其外”的客體小a。它既然是抽象到純粹的空無,缺乏具體內涵與對象,又怎么能讓人物充滿欲望地賦予客體小a,使之產生超越自身的魅力?人物要把某個對象賦予客體小a,需要特殊的情境和心理。比如《三十九級臺階》中的公式、《美人計》中的鈾瓶、《貴婦失蹤記》中的樂曲、《西北偏北》中不存在的“卡普蘭”,一方面,它們確實是影片中雙方爭奪的對象;另一方面,影片又缺乏人物將之賦予客體小a的事件、場景,沒有從主觀的角度為之增添情感的可能。因此,麥格芬完全可以是觀眾不關心、敘述者也不關心的功能性道具或名稱。如《西北偏北》中的“卡普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其次,在精神分析活動中,客體小a與其他悖論性概念一樣,作為一種“不存在的存在”,都產生于欲望的回溯性指認與建構。“欲望的悖論在于,它回溯性地設置了自己的成因。即是說,小客體是這樣一種客體,只有借助于被欲望‘扭曲’的凝視,才能察覺其存在;對于純粹的‘客觀’的凝視而言,小客體是不存在的。”客體小a就是欲望回溯性地設置出來的客體。這就很好地解釋了,齊澤克為什么一再把《迷魂記》中斯考蒂第一次見到“瑪德琳”的兩個客觀鏡頭說成是“不可能主體”的主觀鏡頭(即“瑪德琳”裸背的推鏡頭和側面的靜止鏡頭)。他的解釋也是回溯性的,即用劇情的結果來追溯前因。斯考蒂后來愛上了“瑪德琳”,因此第一次見面就“應當”產生難以遏制的主觀情感,客體小a在充滿欲望的凝視中附著在“瑪德琳”身上,成為斯考蒂欲望的客體-成因(如此闡釋也可以突出另一個重要概念“死亡驅力”)。然而,這種回溯性闡釋與電影表現“第一次”的敘事機制存在根本差異。在愛森斯坦、麥茨、德勒茲看來,電影的人物、情感、思想之所以能夠使觀眾產生動態的“親臨現場”的真實感,是因為它總是通過“第一次”生成的方式展現出來。這是指在一個敘事體中,無論人物、事件,還是情感、思想,都不是給定的靜止狀態;影像從來不是復制先在的存在,而是如同“第一次”般呈現一個發生、發展的動態過程,以此吸引觀眾參與。因此,斯考蒂第一次見到“瑪德琳”時,冷靜客觀的場景效果就不可能賦予“瑪德琳”客體小a。此時兩人沒有什么言語交流,甚至沒有視線交流,僅有匆匆一瞥與躲閃的視線(表現“瑪德琳”雍容華貴的近景鏡頭并不在斯考蒂的視野中)。斯考蒂的愛情是在一個敘事體中第一次“生成”出來的。在多次跟蹤、救助的過程中,他逐漸產生憐憫、同情以及拯救弱者的“男性自大”的愛情。質言之,只有當他在與“瑪德琳”不斷交往的過程中投入了情感,她才具有了客體小a。齊澤克的闡釋顯然脫離了故事語境,忽視了電影敘事“第一次”動態生成的基本特征。
再次,精神分析的移情在本質上是幻覺。不僅真理充滿幻覺,來自誤認,而且只有添加了客體小a,產生幻覺,才能產生真理(當然,這里的“真理”并非指主客觀契合的自然真理,而是指拉康意義上的實在界)。齊澤克通過以拉康的思路重新解讀康德來說明這一點。他認為,《純粹理性批判》用“數學化”“動力學”兩個相對的概念來說明“存在”。數學化指直觀的現象的內容;動力學原則保障一些獨立于感知的意識流動,它通過增加某種雖可理解、但非感性的X(客體小a),構造出一個顛倒直觀現象的新客體。簡單地說,現象經驗層面的客體與添加觀念之后形成的新客體,構成復像關系。新客體比原來的客體多出了客體小a,因此具有觀念所賦予的幻覺。它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方面,它集中了特殊的直觀現象,集中了某個人物、類型的個性特征;另一方面,這些現象指向不依賴于它們的絕對根基,即在我之外存在的“堅硬內核”。我們認為,齊澤克用理性文字確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數學化是通過先驗綜合獲得“客觀性”的行為,動力學屬于“我自身的(主體的)‘自發的’綜合行為”。但是,他很難如此闡釋電影中的客體小a。說得極端點,它不能獨立于現象,無法僅僅通過動力學意識觀念產生。比如,齊澤克認為,《火山邊緣之戀》《一九五一年的歐洲》《游覽意大利》是從現實到實在界的運動。這里的客體小a,分別是超出小島的“火山”,超出意識形態的“圣徒身份”,“意大利當中超出意大利”的古老廢墟。然而,這些真的是被無關于現象的觀念顛倒的“新客體”嗎?小島上的火山突然爆發,天空濃煙滾滾,四處彌漫著火山灰,這些直觀的現象層面的經驗無疑是齊澤克將之闡釋為“恐怖的實在界”的關鍵;艾連尼擁有超出自身的“圣徒身份”,是因為她在喪子之后投身慈善事業,從事幫助貧苦底層群體的現實活動;凱瑟琳游覽那不勒斯和龐貝的博物館,對古羅馬的“古老廢墟”格外關注,不外乎是因為過去的那段情感。顯而易見,電影中的細節、現象、人物始終處于具體的情境、現象經驗中,背后存在因果關系,而與齊澤克所闡發的動力學保留的那種無關于現象經驗的觀念意識(如實在界)存在較大差異。
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客體小a產生于移情機制,是欲望的回溯性指認,也是獨立于現象層面(甚至悖離現實經驗)的觀念意識的改造。然而,如果要闡釋電影中人物魅力的成因,也許并不需要如此復雜的理論。《迷魂記》就形象地說明了這種闡釋的無效。齊澤克根據拉康的理論,認為愛情的真相是愛者在被愛者身上尋找自己缺乏的東西,但被愛者身上并不具備那種東西,于是只能如愛者那樣愛愛者,即,歸還愛。“愛就建立在一種幻覺的基礎上,即兩種匱乏的這一相遇可以產生并實現一種‘新的和諧’。”也就是說,愛者與被愛者的位置互換,掩蓋了雙方都缺乏客體小a以及欲望永遠無法滿足的真相。然而,如此復雜的理論闡釋,竟然也不能完全解釋《迷魂記》的現象。斯考蒂愛上了“瑪德琳”,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假扮瑪德琳的朱迪也愛上了斯考蒂,這就是拉康意義上的“歸還愛”:被愛者轉換成了愛者。然而,兩種匱乏的相遇并沒有產生“新的和諧”,朱迪沒有獲得斯考蒂的愛情。我們不妨追問,為什么他只愛作為幻象的“瑪德琳”,而不愛真實的朱迪?對此,仍然要回到影片來解釋。斯考蒂在餐廳第一次見到“瑪德琳”,隨后在花店、教堂、博物館、旅館四個場景中跟蹤、窺視。這一連串的動作指向“附在瑪德琳身上”的曾祖母卡洛塔。此后,斯考蒂獲知卡洛塔的悲慘命運(被始亂終棄,最后自殺),這構成對瑪德琳現實人生的互文暗示。此外,這四個跟蹤場景大量使用柔光制造夢幻效果(與此相似,當斯考蒂改造朱迪、復制出完全相同的“瑪德琳”時,人物似乎從夢幻的光暈中走來),“瑪德琳”就是加文為了掩蓋殺妻罪行制造出的幻象。“拯救瑪德琳”是斯考蒂欲望的客體-成因,它實則透露出希區柯克的男權意識。美國影評人羅杰·伊伯特認為,《迷魂記》是“最具自白性的一部作品”,展現了希區柯克對女性的“利用、恐懼、操控”。那么,斯考蒂為什么不愛朱迪呢?原因很簡單。朱迪被加文雇傭扮演瑪德琳,不僅參與欺騙斯考蒂,而且盜取了他的情感。追求、改造朱迪以及重返鐘樓等場景重演,只是斯考蒂擺脫創傷、救贖自我的努力,與愛情沒有關系。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電影中的客體小a既不產生于復像的對比,也不是“斜目而視”的欲望凝視,更不是無關于現實經驗的觀念的強力顛倒。它恰恰建立在經驗現實的基礎上,就是主體在特定語境中投射到他者身上的心理欲望,或者對他者一廂情愿的理想化;當主體的情感消散,因之而起的虛幻魅力也就煙消云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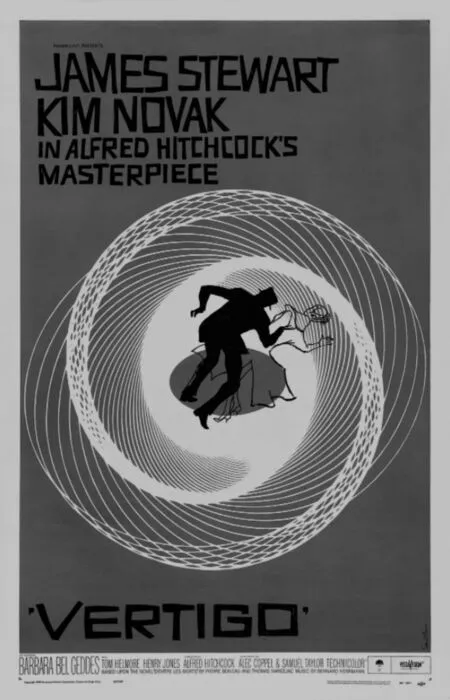
電影《迷魂記》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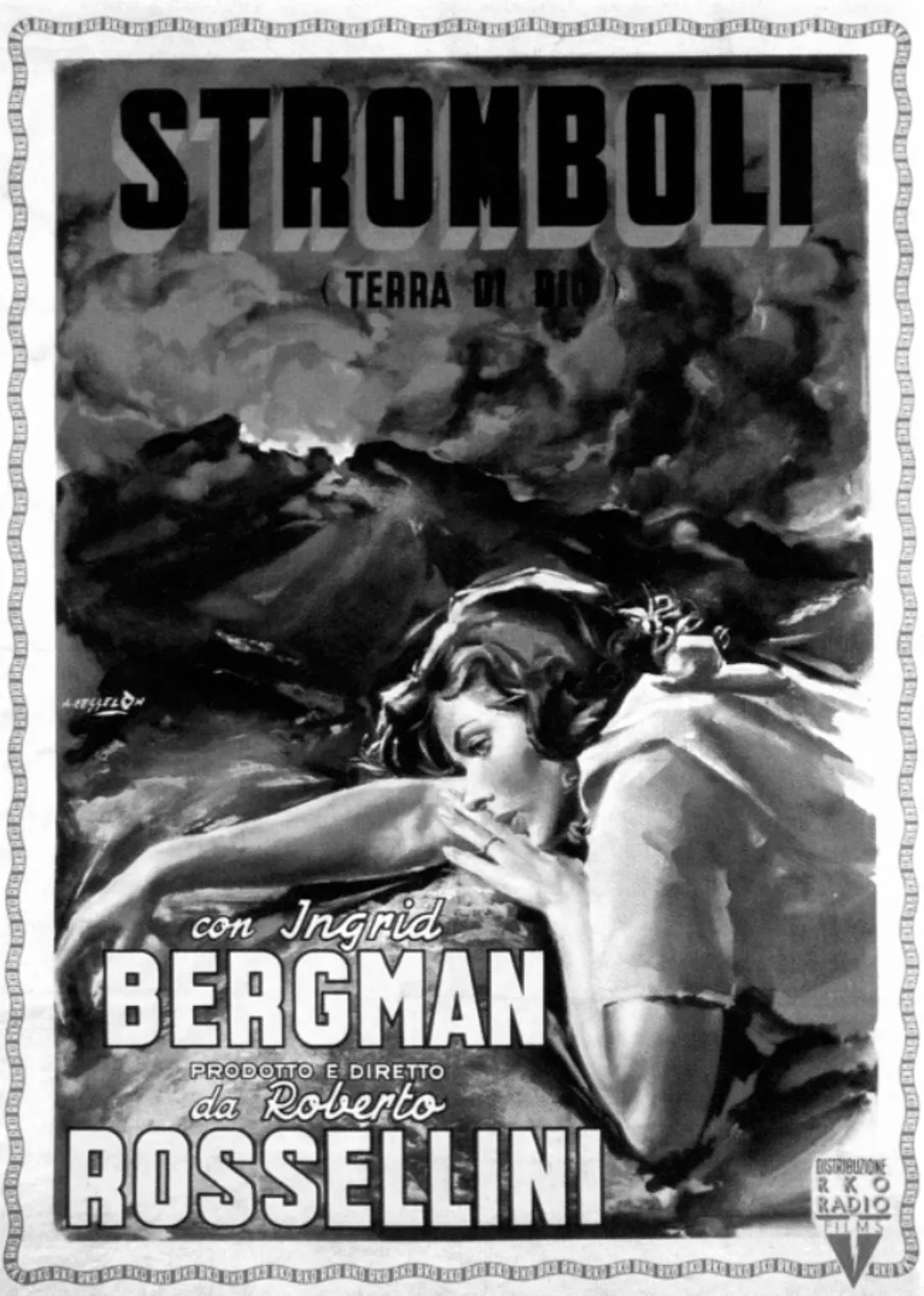
電影《火山邊緣之戀》海報
三、推拉鏡頭能否顯現客體小a?
有意思的是,齊澤克一方面認定客體小a是純粹的空無(實在界的空洞、象征界的缺口),另一方面卻為“電影如何顯現客體小a”找到了特殊的鏡頭語言。他認為,在電影中,“除了采用‘過慢’或‘過快’這兩種方式,我們無法把握它,因為就其‘正確的時間’而言,它就是空,它就是無。所以延遲或快進,是捕捉欲望的客體-成因、小客體和純粹外表之‘空無性’(nothingness)的兩種方式”。所謂“過慢”是指推拉鏡頭;所謂“過快”是指快切。在這兩種方式中,齊澤克無疑更強調第一種“延遲”的推鏡頭。他批評《群鳥》在表達“血淋淋的眼窩”時,沒有使用希區柯克式的推拉鏡頭,而是直接做了兩次“突兀的剪接”。“我們接近這樣的客體時速度太快,略過了‘理解的時間’,略過了需要‘消化’的停頓時間,因而無法整合對這一客體的殘酷感知。”在他看來,緩慢的推拉運動能夠強迫我們關注到斑點及其客體小a;它能夠隔離或者突出客體小a,并借助這個空缺的斑點建構象征界的現實符號體系。我們姑且不論齊澤克在這里的循環闡釋,另一個問題更值得追問:推拉鏡頭真能捕捉到純粹空無的客體小a嗎?答案是否定的。細究齊澤克舉出的客體小a的案例,很多并沒有使用推拉鏡頭。“在我們之內又不是我們”的恐怖或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拍攝對象,與推拉鏡頭沒有必然關聯,如《迷魂記》對準“瑪德琳”裸背的推鏡頭,就沒有所謂的“面對實在界的恐怖”。而制造恐怖效果也不一定要使用推鏡頭,《群鳥》的“血淋淋的眼窩”不就是通過跳躍式剪接凸顯出來的嗎?這顯然與齊澤克所說的情況相反,它直接訴諸視覺的恐怖效果,觀眾完全不需要“理解的時間”。快切使“血淋淋的眼窩”從全景、近景到特寫急驟放大,突如其來地顯露在麗迪亞和觀眾面前,人與死尸的距離迅速消失。特寫正是因為時間的短暫而更具有視覺沖擊力。

電影《群鳥》海報
齊澤克為了強調推拉鏡頭在希區柯克電影中的地位,將之分為四種。第一種是零度推拉鏡頭,從現實的全景推向實在界的變形,即上文所說的推鏡頭;第三種是逆向推拉鏡頭,就是常規的鏡頭向后運動的拉鏡頭。這兩種是電影語言體系中以鏡頭運動方向區分的運動鏡頭。然而,第二種和第四種卻是齊澤克臆想生造出來的,完全顛覆了已有的鏡頭分類標準,缺乏實際意義。在他看來,第二種是快速的“癔癥化”推拉鏡頭,就是“蒙太奇干預”的推拉鏡頭。《群鳥》的“血淋淋的眼窩”本來是快切,此時卻被齊澤克說成是通過跳躍性剪接過快推向斑點的推拉鏡頭。然而,這里是將三個不同景別的靜止的短鏡頭(每個鏡頭僅一秒)組織起來的剪輯,三個靜止的短鏡頭根本就沒有運動,何來推拉鏡頭?必須指出,即使這種沿著光學軸線的快切(屬于后期剪輯階段)在視線向前運動方面具有和推鏡頭(屬于現場拍攝階段)相似的視覺效果,但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容忽視。快切的美學效果是通過強調速度(快慢)與景別(大小)的疊加撞擊,產生令人震驚的、短暫而劇烈的非理性體驗;推鏡頭則是逼真地模仿認知的心理過程,不斷靠近拍攝的細節(斑點),把細節從雜亂的背景信息中凸顯出來,以強調它的重要性。因此,與齊澤克的觀點正好相反,推鏡頭的運動中存在理性主體的操控色彩,即大他者的強力介入。正因如此,希區柯克電影的推鏡頭往往引發倫理反思。第四種鏡頭更為神秘,被齊澤克稱為“不動的推拉鏡頭”。他以《群鳥》中燃燒的博德加灣來說明這種悖論性鏡頭。在鏡頭語言體系中,推鏡頭就是運動鏡頭,不可能“不動”;“不動”的鏡頭是靜止鏡頭,不可能是“運動”的推鏡頭。因此,“不動的推鏡頭”在電影中根本就不存在,它只存在于齊澤克的純粹思辨與理論假設中。這種抽象而神秘的鏡頭由于其悖論性和不可思議性,似乎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在他看來,燃燒的博德加灣就是“不動的推拉鏡頭”。齊澤克非常迷戀這個例子,在不同場合多次使用。他完全剝離這個鏡頭的物質狀態,把它抽象成哲學思辨,不僅認為它是“不動的推拉鏡頭”,而且將之視作一種既主觀又客觀的鏡頭:開始時是客觀鏡頭,然后由于鳥的出現而變成主觀鏡頭,客觀鏡頭由此經歷“徹底的主觀化”,出現既客觀又主觀的悖論性鏡頭(顯然,這也是在電影語言中不存在的鏡頭)。循著同樣的思路,齊澤克認為,這個鏡頭開始時是一個靜止鏡頭,所以稱之為“不動”;此后,鳥從鏡頭后面飛入,帶來運動的視覺感,于是原來不動的鏡頭成了“推拉鏡頭”。然而,文本的情況是,鳥從完全靜止的鏡頭后面入畫,鏡頭沒有絲毫的推拉運動。眾所周知,拍攝對象的運動與推鏡頭的攝影機運動完全是兩回事。說到底,這種“不動”的、既主觀又客觀的推拉鏡頭,其關鍵在于“鳥”,一個被齊澤克賦予了特殊內涵(如實在界、上帝視角、不可能主體、淫蕩的母性,等等)的拍攝對象。質言之,這是典型的歐陸哲學的“唯理”現象:純粹的理性思辨凌駕于客觀的經驗事實之上。
不僅如此,齊澤克更別出心裁地認為,在表現人物接近可怕的原質-客體時,推鏡頭如果是主觀鏡頭,“這個鏡頭就必須被打斷”。他舉例說,《驚魂記》中萊拉走向“諾曼母親”的房屋,《群鳥》中梅蘭妮走近米奇的家,都交替使用了主觀與客觀鏡頭。這些例子確實是用客觀鏡頭打斷了主觀鏡頭。然而,首先,表現萊拉和梅蘭妮眼中房屋的主觀鏡頭根本就不是推鏡頭。其次,這里的“用客觀鏡頭打斷主觀鏡頭”屬于典型的正反打鏡頭,目的在于實現人與物之間的視線匹配,表現的是萊拉和梅蘭妮看到了房屋,以及之后的反應、變化。換句話說,如果這個主觀鏡頭不中斷,那么它就只能表現主體“看”的是什么,而不能表現主體的“被看”。因此,正反打鏡頭建立起主客體之間的關聯互動。再次,只要我們把萊拉接近“諾曼母親”房屋的這一場景放在影片中作整體考察,就會發現原來一切都事出有因。與之相似的場景此前已出現兩次:第一次是諾曼走向遠處的房屋,影片使用大全景的靜止鏡頭,通過讓人物與房屋同時入畫來表現他走近房屋的過程;第二次是偵探走向房屋,影片也是用一個大全景的靜止鏡頭完整表現人物走入房屋的過程。這兩個場景都在冷靜 地表現某人接近房屋。如果說第一次行為屬于正常狀態,那么,在第二次中,偵探上臺階的動作明顯變得緩慢(第一次是12秒,第二次是18秒,鏡頭長度增加),已出現猶豫不定的主觀情感。第三次是萊拉走向“諾曼母親”的房屋。雖然是在白天,但她已確鑿地知道房內存在某種危險。這里頻頻出現正反打鏡頭,鏡頭越來越短,切換的節奏越來越快,這是典型的節奏蒙太奇,目的是表現人物越來越緊張的心理。相似場景三次出現,情節的緊張感、人物的主觀性逐漸增強,體現了希區柯克對敘事和視聽語言的把控能力。第三次的正反打鏡頭,正區別于前面兩次使用的靜止長鏡頭的視聽語言。

電影《驚魂記》海報
在此基礎上,齊澤克還設定了允許和禁止使用的鏡頭。允許使用的鏡頭有兩種:第一種是拍攝某人走近原質的客觀鏡頭,第二種是通過某人視點呈現原質的主觀鏡頭;禁止使用的也有兩種:第一種是拍攝原質和“離奇”客體的客觀鏡頭,第二種是從原質的角度拍攝某個正在走近的人。他的理由較為簡單:如果這樣拍攝,很容易把“原質”“實在界客體”“客體小a”等抽象概念等同于某個具體人物的主觀視點。其實,齊澤克所允許的兩種鏡頭,就是上文論及的主客觀交替的正反打鏡頭。他禁用第一類鏡頭是避免把原質客觀化,禁用第二類是避免把原質落實成人物視點。然而,這種說法同樣經不起追問。在正反打鏡頭中,其實存在大量表現原質的客觀鏡頭。如《群鳥》表現梅蘭妮走近米奇家時,就是用正反打鏡頭表現遠景中米奇與母親分別、后者開車離開、米奇隨后進入房屋。梅蘭妮看到米奇進入房屋后,才再次劃船進一步靠近岸上的紅色房屋。這里正反打鏡頭共出現九次之多,作用在于交代情節,而不是表現主觀情緒。接近房屋時,梅蘭妮充滿惡作劇般的浪漫想象,沒有任何恐懼和焦慮。因此,這里雖然是視線匹配的主觀鏡頭,但效果就是齊澤克主張禁用的關于原質的客觀鏡頭(嚴格來說,群鳥入侵才是齊澤克所說的“原質、實在界的闖入”,而米奇的家并不具有他所賦予的理論內涵)。與《群鳥》的情況完全不同,《驚魂記》的四次正反打鏡頭,無論是萊拉走近“諾曼母親”房屋的正打鏡頭,還是“諾曼母親”房屋的反打鏡頭,都有明顯的晃動。這就賦予了鏡頭主觀性:一方面極力突出萊拉眼中充滿神秘與危險的屋子,另一方面也表現出萊拉走在路上的驚懼不定。這不就是齊澤克主張禁用的從原質的角度拍攝正在走近的人的鏡頭嗎?在他的闡釋中,表現萊拉的客觀鏡頭,其實是房屋“早已透過某個點位在凝視她”的主觀鏡頭。“主體的眼睛看見房子,而房子——客體——似乎以某種方式返還凝視。”照此邏輯,這里根本就不是主客觀更替的鏡頭,而是兩個主觀鏡頭:一個是人物的主觀鏡頭,另一個是“不可能主體”也就是原質的主觀鏡頭。齊澤克的這種矛盾反映出,這種來自原質的凝視的主觀鏡頭不能拍攝(因為一旦拍攝,就意味著取消原質、實在界的恐懼),只能想象(我們只能在“不存在”的鏡頭中想象它帶來的恐懼);雖然不存在原質、“不可能主體”的主觀鏡頭,但我們必須想象它存在,否則就會失去實在界、原質。
正反打鏡頭是表現“看與被看”的常規方法。它之所以成對交替出現,是為了實現想象中的“視線匹配”,與齊澤克所說的“接近原質的推鏡頭必須被打斷”沒有什么關系。他所謂的允許與禁止使用的四種鏡頭,在電影敘事中也沒有足夠的區分度。概言之,為了強調電影符號體系中的客體小a,齊澤克無疑把希區柯克的推拉鏡頭哲學化(提取客體小a,由此反向建構現實的電影符號體系)、同時也神秘化了。在理論自信乃至獨斷的情況下,他試圖以一己之力,挑戰早已形成的具有確切分類標準的電影語言體系,這顯然難以奏效。事實上,我們只要注意希區柯克的電影語言就很容易發現,他在表現所謂的“一小片實在界”或客體小a時,從來都沒有畫地為牢,不會只在意齊澤克所說的推拉鏡頭或者快切。對電影來說,這里涉及的真正問題是如何凸顯對敘事、抒情具有重要意義的細節。顯而易見,電影語言結合了光(色彩)、形(景別)、運動等多種富有表現力的元素,不僅有推拉鏡頭、快切,也有快搖、跟隨鏡頭、特寫、靜止鏡頭(包括定格鏡頭),等等。這些表達重點的鏡頭語言,在希區柯克電影中廣泛存在。
結 語
“客體小a”是拉康理論中與實在界密切相關的抽象概念。齊澤克在文字表達與邏輯推理中,對它做出充分說明、闡釋,確實時有精彩之處。然而,他如同精神分析師一般,把這個悖論性概念落實到具體電影案例,用純粹的理論思辨將電影及其細節高度理論化,這在帶來思想深度的同時也制造了神秘和晦澀。客觀地說,這應該是哲學家闡釋電影文本時頗為常見的弊端,但齊澤克在反經驗、反常規等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正是基于理論闡釋能力的自信,他對文本“斜目而視”,用獨立于經驗層面的理論觀點顛覆日常經驗。
然而,作為現代工業背景下誕生的大眾藝術,電影與傳統藝術最大的區別在于具有較強的實踐性與理性思維。如果說文學依賴語詞意義的疊加創造出抽象而復雜的精神世界,那么,電影則是在理性邏輯中削減單個鏡頭(素材)的多義性與模糊性,建構出一個邏輯縝密、曲折有致的有機體。因此,組織鏡頭的蒙太奇技法,以及確定單鏡頭意義的上下文語境,在電影的敘事中至關重要。質言之,電影建構了一個以理性為根底的文本世界。因此,當齊澤克依據拉康理論和概念“斜目而視”文本時,就賦予了它某種原本并不存在的深刻內涵。他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把闡釋對象(具體場景或細節)抽離出理性的文本場域,取消上下文語境對它的規定和限制,即讓某些場景和細節擺脫電影的敘事原則。如此,就只能讓已經相信者相信其闡釋的內容。對于齊澤克在電影中“發揮”出來的客體小a,也當作如是觀。
① 法語objet petit a有多種不同的中譯法,如“客體小a”“對象a”“客體a”“小對形”等等。本文在引文中保持原譯本的譯法,但在正文行文中統一使用“客體小a”。
②??? 參見齊澤克:《延遲的否定:康德、黑格爾與意識形態批判》,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頁,第264頁注釋1,第222—223頁,第223頁。
③④????????????? 齊澤克:《斜目而視:透過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廣茂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頁,第1頁,第152頁,第286頁,第165頁,第233頁,第19頁,第19頁,第161頁,第161頁,第165—166頁,第166頁,第202頁,第204頁,第217頁。
⑤ 吳瓊:《對象a:拉康的欲望詩學》,《哲學動態》2011年第1期。
⑥⑨ 齊澤克:《延遲的否定:康德、黑格爾與意識形態批判》,第12頁注釋3,第24頁。
⑦ 齊澤克:《無身體的器官:論德勒茲及其推論》,吳靜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頁。
⑧ 張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后馬克思思潮哲學文本解讀》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頁。
⑩ 麥格芬是電影敘事的一種手段,指情節發生的借口。希區柯克被公認為設置麥格芬的大師,他在與特呂弗的對談中詳細解釋了麥格芬的由來與內涵。參見《希區柯克與特呂弗對話錄》,鄭克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6—108頁。齊澤克在1989年出版的成名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就把麥格芬作為“最后一個例子”,來論述實在界的特征。齊澤克所說的這個眾所周知的“最初的軼聞”,其實就是希區柯克回答特呂弗時所舉的例子。參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修訂版),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206頁。
? 參見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修訂版),第228—233頁。
? 參見齊澤克:《斜目而視:透過通俗文化看拉康》,第233頁注釋1。
?????? 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修訂版),第232頁,第232頁,第229頁,第227頁,第37頁,第67頁。
? 齊澤克對《揚帆》的論述參見《享受你的癥狀:好萊塢內外的拉康》(尉光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9頁;對《重播》《蘇菲的選擇》的論述參見該書第86—91頁;對《獵鹿人》的論述參見該書第88頁注釋1;對《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論述參見該書第96—97頁。
?? 參見齊澤克:《享受你的癥狀:好萊塢內外的拉康》,第96—97頁,第76頁。
??? 齊澤克:《享受你的癥狀:好萊塢內外的拉康》,第28頁,第135頁,第81頁。
? 愛森斯坦從動態角度理解藝術作品,強調“形象在觀眾感情與理智中形成的過程”不是復制情感的結果,而是使“情感發生、發展、轉變,即在觀眾面前生活”,因此,真正生動的藝術作品是“吸引觀眾參與正在發生的過程”。具體論述參見謝爾蓋·愛森斯坦:《蒙太奇論》,富瀾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287頁。
? 麥茨認為,電影帶給觀眾一種感知和感情的“參與”過程,它對感知進行“直接控制”,使之比他物更加生動可信。電影觀眾看到的不是“曾經在此”,而是“活生生的此在”。這就是“第一次”的呈現狀態。具體論述參見克里斯蒂安·麥茨:《電影表意泛論》,崔君衍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6—8頁。
? 不同于現象學所認為的“一切意識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德勒茲用柏格森的綿延理論來理解電影,認為:“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影像=運動的世界。……所有事物,亦即所有影像,都與它們的行動和反應混合在一起:這是普適變化。”這即是從影像、行動、運動體難以分割的同一性強調“第一次”的生成機制。也就是說,影像不是復制某種先在的人物、情感與事件,它就是人物、情感與事件,呈現出活生生的生命本質。具體論述參見吉爾·德勒茲:《電影1:運動-影像》,謝強、馬月譯,湖南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4頁。
? 羅杰·伊伯特:《偉大的電影》,殷宴、周博群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44頁。
? 齊澤克認為,推鏡頭的落幅就是實在界客體(斑點),它具有兩種形式:其一是他者的凝視,如骷髏的眼窩、《年少無知》中的眼睛;其二是典型的希區柯克式客體,如《美人計》中的鑰匙。然而,如前所述,他說的希區柯克式推鏡頭,不就是對準斑點、突出的實在界殘余、“一小片實在界”等特殊對象嗎?既然如此,鏡頭最后落在這種實在界客體之上也就毫不令人意外,沒有任何推理的必要了。
? 齊澤克:《真實眼淚之可怖: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穆青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