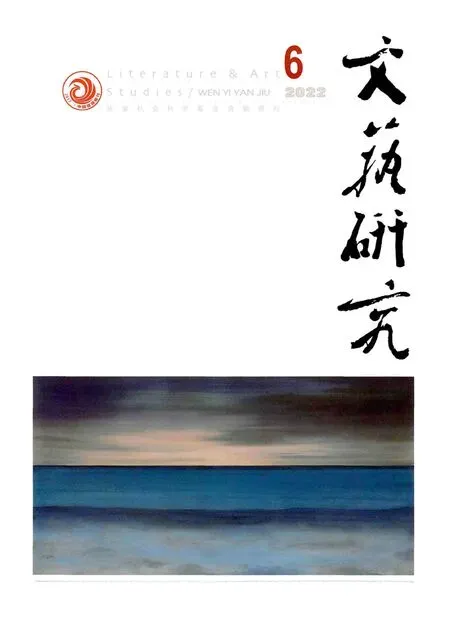何種“想象”,怎樣“共同體”?
——重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趙稀方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以下簡稱《想象的共同體》)一書,對國內學界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不但影響了民族主義研究,也影響了文學研究。就民族主義研究而言,它打破了關于民族主義的本質主義看法,如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的經典定義,將民族看成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這正應合了中國學界流行的后現代歷史建構觀。就文學而言,在安德森那里,印刷資本主義是構建民族主義的方式,這引發了學人將晚清以來媒體的發展與民族國家的生成聯系到一起,進行所謂“小說中國”的論述。
“想象的共同體”一時間成為一個很時髦的說法,不過,它在何種意義上是安德森的獨創?它處于西方民族主義的何種脈絡中?西方學界已經有不少學者對之做出批評,這些批評從何而來?本文試圖從民族主義研究的譜系出發,對這本書進行學術重估。
一、民族與種族
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的觀念受到了蓋爾納(Ernest Gellner)“民族主義發明了民族”這一說法的影響。從注釋來看,安德森閱讀的是蓋爾納1965年出版的《思想與變化》()一書。不能不說安德森很敏銳,蓋爾納在1965年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1983年他出版《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這句話才成為名言。
安德森很贊成蓋爾納的這個說法,不過他認為這還不夠。在他看來,這個表述的缺點是,“蓋爾納急于表明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虛假的偽裝,以致于他將‘發明’(invention)等同于‘編造’(fabrication)和‘虛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ing)和‘創造’(creation)。這樣的話,他就暗示還有‘真實’(true)的共同體存在,它較民族更為優越”(第6頁)。安德森不同意仍有真實共同體的看法,他認為:“事實上,所有較面對面的原始小村莊更大的共同體(甚至于它們自身),都是想象出來的。共同體之得以被識別,并非其虛假與真實,而是其被想象的方式。”(第6頁)安德森由此得出對民族的定義:“本著人類學的精神,我對民族定義如下:它是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這種想象是內在限制的和主權的。”(第5—6頁)在此,安德森明確道出了他與蓋爾納的差別:蓋爾納認為民族是被民族主義創造出來的,不過這里的“民族”是指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但構成民族的更小的族群(ethnicity)卻是歷史存在的,蓋爾納所考察的正是在何種歷史條件下族群轉換成了民族。安德森卻是一個完全的后現代主義者,他認為包括族群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象出來的。
蓋爾納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中提出,民族主義確乎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但它的形成需要條件。決定民族主義模式的有三種因素:權力、教育和共同文化。三種因素交錯,形成八種情況。其中五種與民族主義無關,因為沒有文化差異;剩下三種與民族主義有關的情況。其一是當權者受過教育,無權者沒受過教育,種族文化上有差異。在這種情況下,當權者經過努力,可以改造民間文化、發明民族傳統,這種模式以哈布斯堡王朝傳統的民族主義為代表。其二是當權者和無權者都受過教育,種族文化上有差異,這種情況造成了歐洲和自由的西方民族主義。其三是當權者沒受過教育,無權者受過教育,種族文化上有差異,這種情況造成了散居國外的人的民族主義,可以用以色列民族主義作為代表。
我們注意到,在蓋爾納提出的決定民族主義的三種因素中,種族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事實上,當社會生活的經濟基礎需要文化同一性或持續性(不是非階級性)、與文化相聯系的階級差異變得有害的時候,種族性(ethnicity)就會成為民族主義進入政治領域,而種族不明顯的漸進的階段差異卻仍舊可以容忍”。凡沒有種族差異的社會,都完全失去了產生民族主義的機會,這里的種族顯然并不是“想象”的。并且,只有同質性較強、有自己的政治傳統的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而多數民族在現代社會大潮中沒有進行任何努力,就慢慢融入了某個大的民族國家的文化之中。
這里還需要提一下霍布斯鮑姆(Eric J.Hobsbawm),民族主義“傳統發明”理論最系統的闡述者,其1983年《傳統的發明》一書對這一脈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霍布斯鮑姆打破了本質主義的歷史觀,認為并不存在所謂的悠久的民族主義傳統,這些傳統其實是應當代的需要而被發明出來的。霍布斯鮑姆將“被發明的傳統”定義為一種形式化和儀式化的過程,即通過重復來灌輸一定的價值和行為規范,從而制造一種與過去的歷史連續性。他在書中特別強調了民族主義與傳統發明的關系,認為“被發明的傳統”“緊密相關于‘民族’這一相當晚近的歷史創新及其相關現象: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民族象征、歷史等等”,民族主義就是一種典型的“被發明的傳統”。
不過,在我看來,霍布斯鮑姆雖然談論民族主義傳統的發明,但他其實并未忽略族群的作用。1990年,他出版了《1780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日程、神話和現實》一書,專門討論民族主義。在該書中,他對自己有關“傳統的發明”的論述做了糾正和補充。簡單來說,即民族主義傳統是發明的,不過它具有自己的基礎,他將其稱為“原型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他在該書的第二章專門討論“大眾原型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提到安德森,認為他的“想象的共同體”的確填充了歷史轉折后的人類“情感空白”。不過霍布斯鮑姆認為,到此為止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哪些東西能夠“動員各種集體歸屬的感情”,成為情感替代物呢?他的回答就是族群,包括血緣、部落、語言、宗教等因素。霍布斯鮑姆有些躊躇,他一方面很注意避免本質主義,另一方面又認為族群因素是民族主義的基礎,所以他小心翼翼地說,這些因素不一定能夠成為民族主義,不過它們肯定有利于現代民族主義的建立。
蓋爾納和霍布斯鮑姆有關民族主義傳統發明的觀點,已經對以種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論述做出了革命性的解構,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仍堅持種族性的基礎,只有安德森徹底放棄了種族的維度,認為“想象的共同體”并不需要種族的基礎。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么?很清楚,這是因為蓋爾納和霍布斯鮑姆所據的主要是歐洲的經驗,而安德森所據的是美洲的經驗。美洲的歐洲移民在種族上與歐洲人是一致的,他們發展出了最早的民族國家。不過,美洲的經驗在民族主義歷史上其實是一個特例,當安德森將其上升為一種有關民族主義的普遍定義,并運用于歐洲和亞洲的時候,其不當之處就顯示出來了。
安德森在討論歐洲民族主義的時候,主要是從語言這一角度進行的。我們知道,語言乃種族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安德森卻刻意回避這一問題。正如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所言,“對安德森來說,是語言而不是種族性形成了他的論述的出發點”。史密斯其實是認同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理論的,不過他認為這一派的缺陷也很明顯,即他們過于強調民族主義建構的現代性,而過于“貶低”(relegated)和“忽略”(omitted)了族群文化。在他看來,對民族主義而言,族群性是必不可少的。對此,他從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證:
種族現象無處不在,因此它必須居于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歷史社會的中心。這可以從幾個層次上進行分析。從定義上說,這種民族與種族群體之間的關系,是在其他集體文化身份形式中找不到的。理論上說,種族性——盡管存在各種問題——為解釋民族與民族主義不同形態和特性的關鍵因素,提供了一種富有成效的基礎。從歷史上說,我們可以看到種族共同體轉化成了“民族”的大量事例,更大量的事例表明不同的種族群體的象征因素,在民族形成的過程中融入了民族主義,或者為民族主義所利用。如果脫離了所有過去和現在的種族因素的參考,想要解釋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內容和吸引力是極其困難的。除了其歷史重要性之外,種族性還提供了有關參與者的“內在世界”、尤其是被民族召喚的強調獻身精神的重要解釋。
由此,史密斯認為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理論的這一缺陷需要彌補:現代民族主義既是被發明的,但也有其基礎,它們通過神話、象征、記憶、價值和傳統與前現代的族群相關聯,這就是他所發明的“族群-象征主義”。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這一說法,最有沖擊力之處在于打破傳統的以種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觀,而主張民族主義的建構觀。不過,民族主義建構觀的發明權其實并不在安德森,而在蓋爾納和霍布斯鮑姆。為了追求獨創性,安德森以美洲經驗為藍本,消除了其中最后的種族因素,將之稱為“想象的共同體”。然而這種說法并不能解釋主流的民族主義現象,它已經受到從原生主義到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理論的多方批評。
二、“朝圣”與革命
安德森民族主義建構觀的基本看法,認為民族主義是在傳統社會崩潰后出現的,是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對此,蓋爾納其實已經有過精彩論述。
蓋爾納的關鍵詞是“工業社會”,他認為這是民族主義得以產生的根本條件。農業社會是自給自足的,沒有現代教育,也沒有社會流通,這決定了它們沒有產生現代民族主義的土壤。在現代社會中,由于工業生產和勞動分工的需要,陌生人之間需要有持續、全面的溝通,標準語言和書面媒體得以產生,現代教育也因之形成,這些都需要有一個民族制度來實現。由此,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的根源不在于人的精神和本質,而在于不久前才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民族主義應特定的社會秩序需要而出現,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現代人不需要再忠于君主和宗教信仰,他們忠實于一種文化,文化的同質性是產生民族主義的前提。
與蓋爾納一樣,安德森也認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是民族主義意識出現的前提。由于經濟的沖擊、神學確定性的衰落、交往的加劇,宇宙與歷史的界線被打破,一種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開始出現。在推動新的民族共同體興起的過程中,有三個因素最為重要:“從積極的意義上,新的共同體想象的產生是半偶然的,然而又是爆炸性的,是生產體系與生產關系(資本主義)、傳播技術(印刷)和人類語言多樣性的宿命。”(第42—43頁)可以說,安德森繼承了蓋爾納的論述,不過他在“工業社會”中專門強調了“印刷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問道:“如果我們仔細看,安德森與蓋爾納有關20世紀民族主義的論述有什么實質性差別嗎?”他的回答是“沒有”。他認為,二人都指出認識社會方式上的巨大變化帶來了民族主義,只不過一者強調“工業社會”,另一者強調“印刷資本主義”而已。
“印刷資本主義”通常被認為是《想象的共同體》一書的關鍵詞,不過,強調印刷媒體對于民族主義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這實在算不上多么新穎的看法,多數從現代性角度討論民族主義問題的學者都會提到這一點。早在1931年,海斯在其《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一書中,就曾專門談及新式報紙如何成為法國民族主義形成的最有力的宣傳工具:“一種新式的報紙和雅各賓民族主義同時興盛起來——這種報紙的新聞和評論是以通俗與動人聽聞的格調撰作的,印得很迅速,賣得很便宜,銷行很廣。……一般的雅各賓主義者都熱烈地相信,如果‘人民’要民主化,要愛國,他們每日必須得到消息、意見與刺激。”“新式的報紙成為雅各賓民族主義最有力的宣傳工具。”
如果說在海斯這里,現代媒體的作用僅僅是民族主義宣傳,那么蓋爾納對媒體的強調則更進一步。蓋爾納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中提到,很多人認為媒體的作用是促進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比如將某些思想傳播到偏遠山村。他認為,媒體傳播什么內容并不重要,傳播本身所形成的統一文化才是現代社會的構成前提:“它所接受的傳播信息并不重要,是媒體自身,是抽象的、中心的、標準的、一對多交流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自動地產生了民族主義的核心思想。”
在我看來,真正屬于安德森的概念是“朝圣”(pilgrim)。安德森認為,世界上最早的民族主義起源于美洲殖民地官員的“朝圣”。在印刷媒體出現之前,人們之間的交流主要依靠旅行。美洲殖民地官員在回歐洲的“朝圣”之旅中,意識到彼此群體的存在,加之印刷媒體的出現,更催生了共同體意識。殖民地官員在歐洲母國基本上升遷無望,由此逐漸對美洲本地產生共同體的感覺,從而出現了最早的民族主義。安德森宣稱,無論是“經濟利益”“自由主義”或“啟蒙運動”,都無法創造“想象的共同體”的意識,只有“朝圣”及移民印刷業者,才能承擔這一“決定性的、歷史性的角色”(第65頁)。
安德森的這一論述未免有些聳人聽聞。沒有經濟發展以及由之而來的社會變化,沒有歐洲啟蒙主義,這些移民何來意識上的變化?安德森所說的“朝圣”,在這里是指一種讓人們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共同體的方式,這會帶來以下問題:第一,決定共同體意識的最重要因素是“朝圣”嗎?第二,具有了共同體意識,就可以產生民族主義嗎?對于這兩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朝圣”對于形成共同體意識可能確有作用,但從歷史上看,決定共同體意識的最根本因素顯然是殖民壓迫與民族革命,而不是“朝圣”。
這里姑且以我們熟悉的美國為例。在談到18世紀印刷媒體的發明創造了一個“美洲”想象時,安德森專門強調北美十三州領土的有利條件:“在北面,說英語的移民新教徒,更有條件認識‘美洲’這個觀念,事實上最后也成功地擁有了‘美國人’的日常頭銜。最初的13個殖民地所擁有的區域比委內瑞拉還小,也就是阿根廷的三分之一。由于在地域上較為集中,波士頓、紐約和費城的市場中心很容易互相聯系,它們的人口也被媒體和商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第64頁)不過,這些都是背景和條件,安德森沒有提到最重要的問題,即美國獨立戰爭。北美十三州原來是分離的,為了反抗母國英國的經濟壓迫和軍事鎮壓,他們被迫聯合起來反抗,最終走向美國的獨立。可以肯定地說,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在對大英帝國的反抗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安德森在書中一直避而不談美國獨立戰爭,這有些詭異,難道他寧愿相信民族是通過“朝圣”和媒體想象出來的,而不是通過革命創造的?
美國是美洲大陸最早實行民族獨立的地方,這是常識。人們在討論民族主義的時候,通常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不過也會提及更早的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安德森自詡發現了最早的民族主義,這種說法不免令人生疑。他曾抱怨自己有關“朝圣”創造了世界第一波美洲民族主義的說法在學界無人理睬,這似乎不是沒有原因的。
更加離奇的是,安德森不但忽略了美國獨立戰爭,也忽略了法國大革命。在結束了對美洲的討論后,他終于開始討論歐洲,不過直接跳過了被視為歐洲民族主義開端的法國大革命,而將第二波民族主義鎖定為1820年之后的歐洲群眾性語言民族主義。安德森的基本觀點是,隨著地理大發現和資本主義擴張,歐洲人第一次認識到歐洲文明只是世界文明的一種,同時也認識到拉丁語并非唯一神圣的語言,歐洲各地方言開始興起。通過印刷語言,不同地區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共同體,由此形成所謂群眾性語言民族主義。至于第三波民族主義則是由群眾向官方的延伸,即19世紀中葉歐洲君主開始用某種方言作為國家語言,由此形成官方民族主義。
事實上,歐洲民族主義早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就已經誕生,法蘭西共和國即是最早的歐洲民族革命的成果。并且,歐洲民族主義也自此得到理論表達,產生了法國的公民民族主義與德國的族裔民族主義兩種原型。其中,赫爾德已經建立了較為成熟的民族主義理論。對于語言民族主義,費希特也有過專門論述。1806年10月,拿破侖占領柏林,費希特發表著名的《對德意志國民的講演》,詳細論及語言與德國民族主義的關系,這是人類第一次關于語言與民族主義自覺的表述。可惜的是,這些都沒有被安德森注意,或者說被他刻意忽略了。
三、亞非還是美歐?
安德森認為,世界上最后一波民族主義是20世紀中期的東南亞民族主義,它是美洲“朝圣”模型與歐洲“語言”模型的結合。不出意料,他再次拈出了“朝圣”這一概念。他提出,與美洲殖民地官員“朝圣”一樣,東南亞殖民地官員無法在其母國得到升遷,他們所想象的升遷之路最高只能到達殖民地區的中心。東南亞殖民地官員在“朝圣”的路上,同樣發現了一大批掌握雙語的同伴,從而與他們產生一種共同體的感覺。與美洲“朝圣”略有不同的是,東南亞“朝圣”的人群已經不止于殖民地官員,還加入大量殖民地本地的雙語知識分子。這是因為俄羅斯化的西方帝國過于龐大,無法僅使用母國和歐洲的移民來管理殖民地,而必須在殖民地本地培養雙語知識分子來參與國家統治。
談論20世紀中期的“朝圣”,似乎連安德森本人也覺得很勉強。他也認識到這個時候交通已經很發達,過去那種漫長的旅途不復存在。因此他提出,在殖民“朝圣”之外,構建東南亞民族國家的另一個因素是殖民地教育體系的建立(這個說法也來自蓋爾納),不同地區的人們都來到城市或首府接受教育,這種內部“朝圣”也培養了他們之間的共同感。如此,在殖民地的邊界之內,就發生了從殖民國家(colonial state)向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轉變。
在《想象的共同體》1991年修訂再版的時候,安德森提到,他在第一版中將亞非民族主義僅僅看作對歐洲王朝民族主義的模仿,這是“短視”的。他對此做出糾正,認為亞非民族主義的產生應該歸結到當地殖民者的想象。他在修訂版中專門增加了《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一節,討論殖民地政府如何通過人口調查、地圖制訂和博物館來構建殖民地民族主義。其中談到殖民地官員認同上的變化,即早期殖民者直接把自己當作統治者,但隨著時間的消逝,他們越來越少“野蠻地談論征服的權力,越來越多地努力創造另外一種合法性。越來越多在東南亞出生的歐洲人,受到誘惑,把這里當作自己的家。里程碑式的考古學越來越與旅游相聯系,這使得國家看起來成為一種普遍的然而本土的傳統保護者”(第181頁)。
在我看來,無論是認為亞非民族主義出自殖民者對歐洲或美洲的直接模仿,還是認為其出自殖民者自身的想象,都具有相同的性質,即忽略了亞非的本地人,以及他們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斗爭。
查特吉對安德森將歐美民族主義模式移用于東南亞很不滿意,他的質疑是:誰的想象的共同體?他說:“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世界其他地區只能從適用于歐洲及美洲的特定‘模式’中選擇想象的共同體,那么還有什么剩下來可供他們想象的?”“我反對這種論點并非出于什么傷感的原因,我反對它是因為我無法將它與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調和起來。”在這里,查特吉有兩個質問:一是安德森將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模式移用于東南亞,從而忽略了東南亞的獨特性,也剝奪了東南亞的發言權;二是安德森完全忽視了東南亞民族主義最重要的內容,即反殖反帝斗爭。
《想象的共同體》中有一處提到了本地人的反抗,安德森說,本地雙語知識者接受了教育,了解到歐美民族主義,因此發生了民族意識的覺醒。1913年,印尼的荷蘭殖民者模仿海牙,舉行從法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獲得“民族解放”的慶典,結果早期爪哇-印尼民族主義者蘇瓦地·蘇簡寧瓜特(Suwardi Surjaningrat)用荷蘭文寫下了著名的反殖文章《假如我能做一次荷蘭人》,提到本地奴隸也渴望獲得從荷蘭人殖民統治下的獨立。這才是真正的本地民族主義。可惜安德森并沒有沿此思路進行論述,而是又回到了殖民民族主義的話題。
我們知道,殖民者在統治殖民地期間的確做了很多建設性的工作,包括保護本土傳統,不過這一切明顯都是為了殖民統治。查特吉對印度的研究可以提供參照。作為一位后殖民史學家,查特吉的貢獻在于,他在殖民政治批判之外,還分析了英國殖民主義對印度的文化操控。在《民族及其碎片:殖民與后殖民歷史》一書中,查特吉分析了英國將印度本土歷史的敘述納入西方現代殖民主義史學的過程,比如認為印度古代一直沒有真實的歷史,再如把穆斯林描繪為殘暴的民族等,其目的是合理化英國的殖民侵略和統治。這正是安德森所說的殖民政府對殖民地本土文化傳統的“保護”。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可以參考尼南賈納(Tajaswini Niranjana)對英國的印度文化學者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的分析。瓊斯翻譯和整理了大量印度古典文化,不過在他的筆下,印度人被建構成卑賤地祈求殖民統治的形象。殖民者看似是保護殖民地文化的行為,其實不過是西方的東方主義話語的構成部分。
當然,西方學者并不必然秉持一種帝國主義的立場。關于東南亞民族主義研究,需要特別提出一位西方學者作為對比,那就是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如果說安德森的研究是以殖民主義為主體的,格爾茨的研究則是以殖民地為主體的。格爾茨將東南亞民族主義分為四個階段,即民族主義形成階段、民族主義取得勝利階段、民族主義建立自己國家的階段和國家獨立之后的階段。格爾茨首先強調地方性,指出東南亞各地情況不一,“在印度尼西亞是地域,在馬來西亞是種族,在印度是語言,在黎巴嫩是宗教,在摩洛哥是風俗,在尼日利亞是類親屬關系”。在這里,我們看到東南亞不同國家強烈的本土特征,格爾茨認為,它們甚至很難用“民族主義”來進行概括。
在《燭幽之光:哲學問題的人類學省思》一書中,格爾茨再次重新論述民族主義。他延續地方性知識的視野,提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亞非新興國家的涌現并非對歐洲民族主義模式的模仿,而是對它們的一種挑戰,是在歐洲經典模式之外提出新的東西,從而質疑傳統歐洲民族國家模式和單一文化模式的唯一合法性,建立一種兼顧兩者的新型政治。這種政治不是將亞非民族主義視為歐洲民族主義的前期階段,而是將其視為不同的模式,從而發展出新的可能性。格爾茨說:“第三世界巨變對于20世紀自我理解的啟示是,它們不是對歐洲民族主義的模仿,而是逼迫我們看到民族主義所否定的文化的復合性景觀。”可以說,安德森將美洲模式或歐洲模式運用于對東南亞民族主義的論述,正是格爾茨批判的對象。
對于安德森的中國讀者來說,最大的諷刺或許來自印度裔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研究。杜贊奇以中國歷史的經驗批判了安德森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的集體和民族認同既不必等到現代才出現,也不必是現代印刷媒體的產物,泛中國神話如馬祖或關帝,就可以將不同群體加入一種民族性之中,這種神話是口語和書面語相結合的。中國歷史雖然被稱為“天下主義”,但民族主義并不乏見,如宋代抗金時期、明清之際,部分士大夫完全放棄了天下帝國的觀念,代之以界線分明的漢族與國家觀念。而種族中心主義在中國其實并非新事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左傳》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一書,即旨在反省歐洲民族主義史學模式對中國的影響。
綜上,本文從三個方面對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提出了質疑:一是他把美洲經驗普遍化,認為民族主義是“想象”出來的,忽略了種族性的基礎;二是他認為“朝圣”是美洲共同體的根本原因,忽略了更重要的革命與啟蒙的因素,忽略了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三是他將歐美模式套用到亞非國家身上,以殖民主義代替本地民族主義,忽略了亞非國家的主體,把自己變成一種帝國主義話語。
《想象的共同體》一書在中國,最吸引人的也許只是“想象的共同體”這個詞匯。這并不奇怪,它讓我想起當年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后最早得到的評論。據安德森,1983年《想象的共同體》一書出版后在美國并無反響,只有一位歐洲政治學家在《美國政治評論》發表評論,認為該書“除標題引人注意外一無是處”。
2014年,安德森應清華大學的邀請來華做了兩場演講,再次掀起熱潮。2016年,吳叡人譯本《想象的共同體》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增訂后第三次出版。作為近年來學界最流行的術語之一,“想象的共同體”被廣泛運用于社科研究的各個領域。面對這種熱度,筆者覺得有必要冷靜下來,認真地思考一下。
① 該書英文版首版于1983年,本文所據為1991年出版的修訂版:Benedict Anders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引文凡出自該著者均只隨文標注頁碼。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
③ 吳叡人的中譯本在這里出現了差錯,把關于雷南(Ernest Renan)的注釋,放到了討論蓋爾納的部分,這導致蓋爾納相關注釋的缺失,而缺少的注釋恰恰可以說明安德森的思想來源。參見Benedict Anderson,, p. 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④ 在中文里“民族”一詞既指民族國家,又指少數族群(少數民族),這很容易造成混淆和誤解,讀者需要對蓋爾納“民族”概念的所指范圍進行辨析。
⑤? Ernest Gelln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3,p.94,p.127.
⑥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3.
⑦ E. J. Hobsb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46.
⑧ Anthony D.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9,pp.17-18.
⑨ Partha Chatterjee,, Tokyo: Zed Books Ltd.,1986.p.21.
⑩ 海斯:《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帕米爾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
? Partha Chatterje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5.
? Cf.Partha Chatterjee,,p.102.
? Cf. Tajaswini Niranja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 Clifford Geertz,,New York:Basic Books,1973,p.306.
? Clifford Geertz,,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51.
?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5.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殼碗外的人生》,徐德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