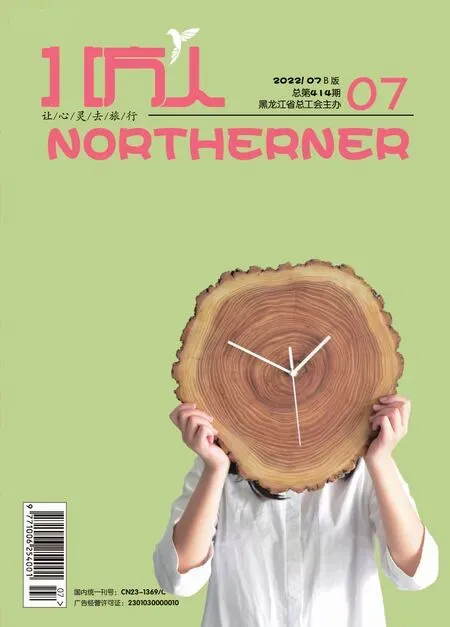最不重要的素質(zhì)就是“聰明”
文/施一公

我先說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質(zhì)就是你的聰明,無論學(xué)什么學(xué)科。至關(guān)重要的,首先是時間的付出。
不要以為你可以耍小聰明,世界上沒有免費的晚宴,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所以有時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說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機遇,我不信任何一個成功的科學(xué)家沒有極大的付出。
清華大學(xué)前生物系主任老蒲,在美國已是赫赫有名的終身講席教授。他在美國開組會時教導(dǎo)學(xué)生:“在我的學(xué)術(shù)生涯中,我最大的訣竅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時間超過60個小時。我知道你們不能像我一樣刻苦,但我要求你們每周工作50個小時以上,這意味著如果是8小時一天的話,你要工作6天以上。”而且,不要以為你早上8點去,晃晃悠悠做點兒實驗,晚上8點離開就可以了。他只計算你具體做實驗的時間,和你真正去查閱與實驗相關(guān)的文獻的時間。這樣一周工作50個小時,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實驗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離開。其實老蒲說的是大實話,是一個真正有良知的科學(xué)家說出的話。我想通過這個例子告訴大家,一個人若不付出時間,就一定不會成功。
其次,方法論的改變。
我的博士后導(dǎo)師是一個獨樹一幟的科學(xué)家,他只比我大一歲半。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10年中,他以通訊作者的身份在實驗室做出了30篇論文發(fā)表在《自然》《科學(xué)》上,是世界上一等一的高手。
我進入他的實驗室之后,滿懷希望要向他學(xué)習(xí),希望跟他學(xué)方法論、學(xué)習(xí)思維方式、學(xué)習(xí)批判性思維。但后面發(fā)生的事情讓我非常糾結(jié),我這才意識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維、真正的方法論應(yīng)如何養(yǎng)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訪,邀請我的導(dǎo)師進行一個小時一對一學(xué)術(shù)交流。我的導(dǎo)師讓秘書回復(fù),他那天恰好出差。可是講座那天,導(dǎo)師很早就來了,把自己關(guān)在辦公室里,解結(jié)構(gòu)、看結(jié)構(gòu)、分析結(jié)構(gòu),寫文章。我當時非常疑惑,于是問導(dǎo)師為什么,導(dǎo)師的回答非常簡單:“我沒有時間。”
任何東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時間不可以。科學(xué)知識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時候知道,還有在領(lǐng)域內(nèi)你所處的境地是什么樣的,你是否在科學(xué)前沿,你是否在做別人已經(jīng)做過的東西,都是如此。所以說,我希望大家不要簡單地接受一些習(xí)以為常的東西,你需要挑戰(zhàn)過去。
最后,要建立批判性思維。
除了方法論的改變,還要敢于挑戰(zhàn)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我的博士生導(dǎo)師在33歲時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開車時想象出ZincFinger(鋅指)的結(jié)構(gòu),這是我們?nèi)祟悮v史上的一個重大結(jié)構(gòu)。他在晚上做夢的時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滿思考。他經(jīng)常說:“懷疑是科學(xué)發(fā)現(xiàn)的推動力。”
有一天我們開組會,他看起來特別激動,說要給大家演示他的一個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問題。他開始畫了一個長方形,中間加一個隔斷,左面是氧氣,右面是氮氣。看到他畫出來的圖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證明熱力學(xué)第二定律——熵增的過程。他開始寫公式,滿滿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證明出熱力學(xué)第二定律是錯的。當時我們都震驚了。
可是,我在他寫出的公式里面發(fā)現(xiàn)了3處錯誤。開始我不敢提,但后來一想,那的確是錯的,這才哆哆嗦嗦地舉起手,所有同學(xué)都說我錯了。下午,導(dǎo)師找到我,問我本科是在哪個大學(xué)念的,我說清華大學(xué),是我們國家最好的大學(xué)之一。他又說,他不關(guān)心我來自哪個大學(xué),他關(guān)心的是我學(xué)得非常好,老師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們研究所的同事見到我便會主動跟我打招呼。這段公然鼓起勇氣的經(jīng)歷,在我的科研路上給予我無限自信,至今仍對我有很大影響。
我希望我們的學(xué)生能夠志存高遠,腳踏實地。你要時刻記住,你認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時還要記住,不可知足常樂。我認為的科研是一種生活方式,它讓我能夠無憂無慮地去思考和解決一些科學(xué)問題。但是,我們也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zé)任,我們做研究是為了回報社會,為人類做出貢獻。
(摘自2022年第6期《做人與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