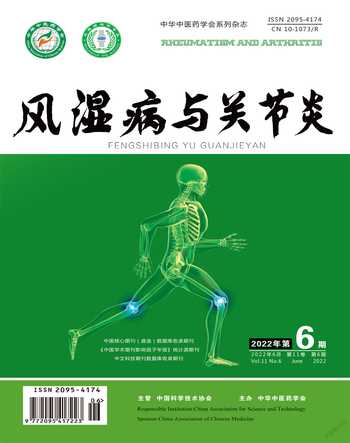慢性痛風性關節炎的中醫治療進展
李青璇 湯小虎 汪宗清 聶紅科
【摘 要】 對慢性痛風性關節炎的病因病機、中醫內治法、中醫外治法等方面進行分類總結。慢性痛風性關節炎病機多為正虛感邪,病性為本虛標實,以肝脾腎虧虛為本;濕熱、痰瘀、濁毒痹阻經脈為標。中醫治療慢性痛風性關節炎方法多種多樣,包括中藥湯劑內服、中成藥、中藥外洗及足浴、中藥外敷、針灸、放血等。治療時,緊緊抓住本病本虛標實的病機,中醫內治法與外治法相互配合,共同達到固護脾胃、補腎強筋溫陽、祛濕化濁、化痰行瘀、通絡止痛的功效。
【關鍵詞】 慢性痛風性關節炎;病因病機;辨證論治;研究進展;綜述
痛風性關節炎(gout arthritis,GA)是由于血液與組織液中尿酸濃度過高,形成單鈉尿酸鹽(monosodium urate,MSU)晶體,繼而沉積于關節而誘發的關節炎癥性疾病[1]。慢性痛風性關節炎(chronic gouty arthritis,CGA)指痛風反復發作,尿酸鹽晶體沉積于關節,久之侵蝕關節;病情嚴重者,可出現關節破壞、殘疾、腎功能不全、腎衰竭等。目前,西醫對于CGA的常規治療主要通過控制尿酸水平預防發作及痛風石的形成,促進痛風石溶解[2]。中醫藥治療疾病有著悠久的歷史,藥效良好和緩而不峻猛,藥物之間的配伍作用靈活且療效準確。本文通過對中醫治療CGA在病因病機、辨證分析、對癥治療的近況進行綜述,為CGA治療提供思路與方案。
1 病因病機
1.1 古代醫家的觀點 痛風在古代常被稱作“痹證”“歷節病”“白虎風”“痛風”等。痹證病名首見于《黃帝內經》[3],認為風寒濕邪氣侵入人體,阻滯人體經絡氣血運行,經絡不通、氣血不暢,進一步生成病理產物,病理產物堆積于四肢筋肉關節,加重經絡氣血壅滯而發為痹證。歷節病病名首見于《金匱要略》,張仲景認為歷節除了關節的劇烈疼痛外還存在身體消瘦、關節腫大等臨床表現[4],提出正虛感邪的病機及本虛標實的病性。唐·王燾著《外臺秘要·白虎方》提出白虎病病名,認為白虎病是指臟腑內虛而易受風邪侵襲,四肢筋肉骨節受邪氣所擾而疼痛劇烈的一種關節病[5]。元·朱丹溪首次提出痛風病名,認為痛風病因主要為痰、風熱、風濕和血虛[6]。明·李梴在《醫學入門》中提到歷節風,認為血虛、火、風、濕、痰為痛風歷節的病因[7]。《萬病回春》認為,若飲食不節、多食用膏粱厚味,則濕熱之邪容易停留于全身各處,以皮膚、骨節、臟腑等處為多,故飲食不節的人易患痛風、癰疽疔瘡等疾病[7]。痛風的發生,被認為與先天不足、臟腑虛弱、生活作息規律無常、飲食失節、外邪侵襲機體等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臟腑虛弱以脾腎虧虛為多,人體水液運化失司、輸布障礙;或過食肥甘厚味,濕濁之邪蓄積于體內,痹阻四肢骨骼筋肉關節,不通則痛,發為痛風[8]。總之,痛風的病機多為本虛標實,虛以肝、脾、腎虛為主,虛而易受邪氣所擾,標實多為風、寒、濕、熱、痰、瘀等[9]。古代中醫對痛風的病因病機有著較深入的認識,但未將病情進展各階段區分開,形成一個明確的醫學概念。
1.2 現代醫家的觀點 路志正[10-11]認為,CGA常與肺、脾、胃、肝、腎等臟腑有關,反復不愈的主要內因為脾胃失調,在脾胃失調基礎上,人體更容易感受外邪而發為痛風。朱良春[12]認為,CGA的兩大關鍵病因,其一是痰濁瘀阻,其二是脾腎失調,兩者膠結,臨床表現以虛實夾雜多見,治療以泄濁化瘀、調益脾腎為法,對于痛風標本兼顧,可獲良效。涂平生[13]認為,血瘀與脾腎虧虛是CGA發病的關鍵。丁林寶[14]認為,CGA病因以脾腎虧虛為本,治療上應重視補益脾腎。宋欣偉[15]認為,痰瘀痹阻、瘀重于痰,是CGA的主要病因,治療上應重視活血化瘀通絡,使痹阻之骨節經絡得以通暢。張華東等[16]認為,CGA久熱耗氣、久瘀傷血,病久而脾腎氣血虧虛,致脾運化失司、腎精不足充養臟腑而致病,故應重視補養臟腑氣血,標本兼治,方可獲得良效。總之,現代醫家根據自然病程把痛風進行分期,病機多為正虛感邪,病性為本虛標實,以肝脾腎虧虛為本,濕熱、痰瘀、濁毒痹阻經脈為標。
2 CGA的中醫內治法
2.1 中藥湯劑 路志正[10-11]在治療CGA的過程中不僅重視補養脾胃,還重視對于腎臟的調補,常用六味地黃丸、獨活寄生湯等補腎經方加減化裁,對于腎氣虧虛尿頻、水腫者,多用補腎滋陰藥如熟地黃、山藥、山茱萸等,加利水滲濕藥如豬苓、茯苓等,以達補腎泄濁消腫之功效;對于腎虛而下肢乏力者,多重用補肝腎、強筋骨藥,如牛膝、桑寄生等,補腎之余也奏活血通絡之功。朱良春[12]治療CGA多選用痛風顆粒加濃縮益腎蠲痹丸,對于濁瘀痹慢性期久病癥見下肢漫腫較甚者,用溫化寒痰藥如芥子、膽南星化痰消腫、溫經緩痛;對于痛風慢性期脾腎虧虛者,因濁邪傷及腰府、損及腎絡而癥見腰痛、血尿者,用利尿通淋藥如金錢草、海金沙配伍,加涼血止血藥如小薊、白茅根配伍通淋化石止血。夏璇等[17]在李濟仁治痹學術思想基礎上,結合自身經驗,認為CGA治療重點在于健脾補腎、祛濕化濁,故優化提煉出芪茯化濁湯,該方由土茯苓、粉萆薢、白術、山茱萸、巴戟天、威靈仙、黃芪、杜仲、淫羊藿組成,在減少痛風急性發作次數和緩解關節疼痛方面有良效。張磊[18]認為,CGA患者因病程日久,臟腑氣血皆受損,以脾腎受損為主,故在祛邪之時還應重視固護脾腎,以健脾化濕泄濁、補血活血通絡為治法,標本兼治,自創滌濁湯,組方:生黃芪、黨參、土茯苓、茵陳、生薏苡仁、白術、炒蒼術、山楂、砂仁、粉萆薢、澤瀉、桂枝、丹參、雞血藤、懷牛膝、甘草。該方治療CGA脾虛濕阻證療效佳,與西藥配合有很好的協同作用。王新昌[19]認為,CGA以虛寒內生、脾腎失運、濕濁不化為病機根源,治療上應遵循“治病必求于本”之古訓,以溫補、溫化立法,故脾陽不足為主者多加黃芪、高良姜、白術等,腎陽虛衰為主者多加懷牛膝、刺五加、淫羊藿等。張玉琴[20]認為,CGA以脾虛濕盛、痰濁瘀滯為主要病機,治療應以利濕除濁為主,兼健運脾胃,多選用四君子湯為基礎方,加入利水滲濕之薏苡仁、萆薢,化痰通絡之法半夏、炮山甲、浙貝母等,共奏利濕泄濁通絡之功效。孟鳳仙[21]認為,CGA的病因多為痰瘀之邪痹阻經絡,故治療應以祛濕活血通絡為主,清熱祛風化痰為輔,用藥多為桃仁、紅花、威靈仙、桑枝、海桐皮、全蝎、烏梢蛇、芥子、黃柏、土茯苓等。彭江云[22]認為,CGA病久不愈,臟腑虧虛,氣血運行不暢,無力將阻滯于機體的濕濁痰瘀等邪氣驅除體外,故治療應以治本為主,多選用黃芪防己湯加減溫經散寒、除濕通絡,該方由黃芪、防己、桂枝、細辛、當歸、獨活、羌活、白術、淫羊藿、薏苡仁等組成。
總之,現代醫家在運用中藥湯劑治療CGA時,緊緊抓住CGA本虛標實的病機,共同達到固護脾胃、補腎強筋溫陽、補血活血、祛濕化濁、化痰行瘀、清熱祛風、通絡止痛的功效。
2.2 中成藥 劉風云等[23]將60例CGA脾虛濕阻型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30例,治療組給予中成藥清濁顆粒(藥物組成:粉萆薢20 g、土茯苓20 g、土牛膝15 g、蒼術15 g、薏苡仁30 g),對照組口服別嘌呤醇片,共治療4周,結果2組關節疼痛積分改善情況相當(P > 0.05),且治療組的中醫證候積分較對照組明顯下降(P < 0.05)。吳洋等[24]選取寒濕痹阻型CGA患者60例,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30例,治療組給予中成藥痛風消顆粒(云南省中醫醫院院內制劑,云南名老中醫吳生元經驗方,藥物組成:附片、制草烏、黃芪、防己、桂枝、白術、川芎、茯苓、牛膝、獨活、秦艽、海桐皮、海風藤等),對照組給予別嘌呤醇片,治療時間為4周,觀察發現治療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 < 0.05)。肖敏等[25]將120例痰瘀痹阻型CGA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60例,治療組給予護腎痛風泰顆粒劑,對照組給予別嘌呤醇片,均治療2個月,觀察發現,治療組在改善UA值、ESR值、關節功能分級方面的療效優于對照組(P < 0.05),且治療組不良反應較少,用藥安全。
3 CGA的中醫外治法
3.1 中藥外洗及足浴 中藥外洗及足浴為臨床常用的治療手段。中藥煎煮完成后,待藥液溫度降至40 ℃時,將患足浸泡于藥液中外洗。藥液的熱力能夠打開汗孔,助藥物進入體內,促進全身經絡氣血的運行,以達溫經散寒、活血通絡止痛等功效。張榜等[26]將60例瘀熱阻滯型CGA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每組30例,治療組選用祛痹外洗方(藥物組成:芒硝、紅花、蘇木、威靈仙、艾葉、伸筋草、透骨草),對照組予雙氯芬酸二乙胺乳膠劑外用,共治療14 d,觀察發現治療組療效優于對照組(P < 0.05)。李琳琳等[27]將脾虛濕阻型CGA患者72例分為研究組與對照組,2組均予口服非布司他片治療,研究組加服中藥滌濁湯和中藥足浴(藥物組成:姜黃、蒼術、川芎、赤芍、木香、白芷、天南星、梔子、黃柏、獨活、羌活),治療3個月,觀察發現治療組對于關節疼痛評分和痛風復發情況的改善優于對照組(P < 0.05)。表明中藥足浴治療能夠活躍人體自身調節功能,促進自我康復,從多靶點、多環節、多途徑治療痛風,收效甚佳[28]。
3.2 中藥外敷 中藥外敷具有操作方便、臨床風險小的特點,得到了廣大患者的肯定,臨床上也常用該方法作為痛風的輔助治療。梁錦業等[29]將CGA患者115例分為觀察組60例和對照組55例,2組均予西藥依托考昔、秋水仙堿和非布司他治療,觀察組在關節腫痛部位增加外敷消瘀止痛軟膏(藥物組成:大黃、黃柏、救必應、雞矢藤、側柏葉、紅花),共治療7 d,觀察發現消瘀止痛軟膏外敷在改善關節腫痛和關節功能評分、恢復關節功能方面優于對照組(P < 0.05)。
3.3 三棱針刺絡放血 三棱針刺絡放血療法是臨床上治療各種實證、熱證、瘀血、疼痛等疾病的一種常見方法,有通經活絡、瀉熱開竅醒神、消腫止痛等功效。孫上明等[30]將76例CGA患者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38例。對照組選擇降尿酸、抗炎鎮痛等西藥治療;治療組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予給三棱針刺絡放血,治療穴位為曲池、合谷、太沖、太白、太溪、三陰交、足三里、陰陵泉、血海、阿是穴。2組均治療6個月。觀察發現,治療組皮質醇水平高于對照組(P < 0.05)。表明三棱針刺絡放血療法對于人體內源性糖皮質激素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作用,能夠控制關節炎癥,減輕CGA患者的炎癥反應。
3.4 耳穴治療 耳穴是位于耳郭上的腧穴,也稱為反應點、刺激點。人體各臟腑的生理病理變化常常可反應于不同的耳穴處,按壓耳郭對應部位的腧穴,對于人體臟腑經絡氣血的運行能夠產生一定影響,可輔助治療、調理臟腑。柯明珠等[31]將60例CGA患者隨機分為西醫治療組和中醫治療組,每組30例,西醫治療組予堿化尿液、降尿酸等西醫治療,中醫治療組給予中成藥健脾補腎二仙顆粒聯合王不留行籽貼敷耳穴(主穴:神門、腎上腺、皮質下),共治療28 d。觀察發現,中成藥聯合耳穴治療的患者關節疼痛緩解速度明顯優于西醫治療組,總有效率也明顯高于西醫治療組(P < 0.05)。證明耳穴療法在CGA患者治療過程中有一定的臨床療效。
3.5 針灸及經絡整脊療法 陳朝明[32]認為,CGA病機以肝腎虧虛、痰瘀互結為主,治療上宜補益肝腎、調節氣血、利濕泄濁。陳朝明發現,CGA患者多在肝俞、腎俞及脾俞3處有壓痛,而背俞穴常用于治療臟腑病證,故在CGA的治療上多選此3穴為主穴,配合膈俞、血海及足三里調節氣血,豐隆化痰祛濁,施以平補平瀉手法,配合艾灸治療,從病機根本上改善臟腑功能以緩解癥狀。
4 小 結
中醫藥治療疾病歷史悠久,一代代醫家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結合自身的臨床經驗對中醫藥進行傳承與創新,使中醫藥在治療疾病時療效突出、獨具特色。在治療CGA方面,中醫治療方式多種多樣,方法涉及中藥湯劑內服、中成藥、中藥外洗及足浴、中藥外敷、針灸、放血、耳穴、推拿等。中醫內治法與外治法相互配合,可改善CGA患者臨床癥狀,達到降尿酸、控制炎癥的效果,減少了痛風復發率,其療效也得到了試驗驗證。總之,中醫療法值得進一步研究、推廣及創新。
參考文獻
[1] 張志明,黃青青,齊張旸,等.痛風急性期起始降尿酸治療對臨床療效及用藥依從性的影響[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9,8(4):24-27.
[2] 張紅玲.痛風現代流行病學及其發病機制研究進展[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2017,17(71):79.
[3] 中華醫學會風濕病學分會.2016中國痛風診療指南[J].中華內科雜志,2016,55(11):892-899.
[4] 周仲瑛.中醫內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4:463.
[5] 劉雨佳,瞿溢謙,曹靈勇,等.從經方病傳理論探討歷節病機及病傳規律[J].中華中醫藥雜志,2020,35(12):6050-6052.
[6] 婁玉鈐,李滿意.特殊痹的源流及臨床意義[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3,2(11):49-57.
[7] 張帆,周勝利.淺論朱丹溪《格致余論》從血論治痛風特色[J].中醫藥學報,2018,46(6):106-108.
[8] 李滿意,婁玉鈐.痛風的源流及歷史文獻復習[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8,7(6):57-62.
[9] 李文靜,張曉朦,林志健.“整合論治”策略下張冰教授標本兼治痛風病臨床實踐[J].世界中醫藥,2021,16(1):8-12.
[10] 韓曼,姜泉,唐曉頗,等.路志正調理脾胃治療慢性痛風經驗[J].上海中醫藥雜志,2017,51(5):4-6.
[11] 石瑞舫.路志正治療痛風痹經驗[J].河北中醫,2011,33(7):965-966.
[12] 孟慶良,張子揚,苗喜云.朱良春泄濁化瘀法治療痛風性關節炎經驗[J].中醫雜志,2017,58(16):1368-1370.
[13] 陳理才,孔勇杰,涂平生.涂平生從瘀論治慢性痛風性關節炎經驗[J].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19,43(12):1365-1367.
[14] 王珺,晏飛,馬業,等.丁林寶治療痛風經驗探隅[J].江西中醫藥,2019,50(5):22-24.
[15] 楊鈞安,張瀾,宋欣偉.宋欣偉教授治療痛風的經驗[J].廣西中醫藥大學學報,2014,17(4):20-21.
[16] 張華東,王梓淞,王振興,等.析“高粱之變”,足生痛風[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2,18(10):1075-1076.
[17] 夏璇,李文杰,張磊,等.芪茯化濁湯對發作間歇期和慢性期痛風的療效觀察[J].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2020,26(23):120-124.
[18] 周淑娟,羅珊珊,盧海松.張磊教授診治痛風經驗[J].中醫學報,2016,31(11):1699-1702.
[19] 馮波,陸定其,胡文秀,等.王新昌運用溫法治療痛風經驗介紹[J].新中醫,2020,52(15):198-200.
[20] 陳霞,張玉琴.張玉琴教授治療痛風性關節炎臨床經驗[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9,17(16):21-23.
[21] 張承承,孟鳳仙,卜祥偉,等.孟鳳仙教授治療痛風病的經驗總結[J].中國醫藥導報,2019,16(22):123-125,130.
[22] 秦天楠,汪學良,劉念.彭江云教授寒熱分消治痛風經驗[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8,7(9):43-44,51.
[23] 劉風云,朱科達,陶麗紅,等.“清濁顆粒”治療脾虛濕阻型痛風慢性期30例臨床研究[J].江蘇中醫藥,2016,48(11):41-42.
[24] 吳洋,粟榮,顧玲麗,等.痛風消顆粒治療慢性期寒濕痹阻型痛風性關節炎臨床研究[J].光明中醫,2014,29(12):2571-2572.
[25] 肖敏,張劍勇,邱俠,等.護腎痛風泰顆粒劑治療痰瘀痹阻型慢性痛風臨床觀察[J].河南中醫,2017,37(6):1082-1084.
[26] 張榜,王瑩,崔炎,等.祛痹外洗方治療瘀熱阻滯型慢性痛風性關節炎臨床觀察[J].河北中醫,2020,42(6):858-861.
[27] 李琳琳,張珂珂,周淑娟.滌濁湯聯合中藥足浴治療脾虛濕阻型慢性痛風臨床觀察[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20,44(3):272-276.
[28] 張珂珂.中藥內服外用綜合治療痛風性關節炎臨床研究[J].深圳中西醫結合雜志,2018,28(9):35-37.
[29] 梁錦業,劉基鳳,唐榮德,等.消瘀止痛軟膏外敷配合常規治療對慢性痛風性關節炎發作期關節腫痛的效果[J].內蒙古中醫藥,2020,39(7):110-112.
[30] 孫上明,寧文瑾,葉青,等.三棱針刺血治療慢性痛風對內源性腎上腺糖皮質激素水平影響的研究[J].中國實用醫藥,2021,16(3):1-5.
[31] 柯明珠,馮小燕,黎勝駒,等.健脾補腎二仙顆粒聯合耳穴治療慢性痛風性關節炎的臨床療效觀察[J].中國醫學創新,2020,17(31):84-88.
[32] 陳子翔,陳朝明.陳朝明分期法論治痛風性關節炎經驗[J].吉林中醫藥,2020,40(12):1586-1589.
收稿日期:2022-02-15;修回日期:2022-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