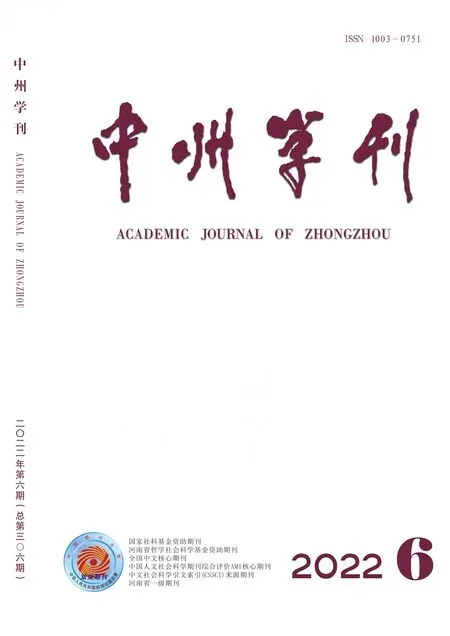我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相應的責任”之責任形態解讀
焦 艷 紅
我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有10個條文使用了“相應的責任”。作為一個特定的法律概念,“相應的責任”具有何種含義和性質?對此,理論上存在諸多解釋,特別是對數人侵權責任規范中“相應的責任”的含義,觀點尤為不一。有學者認為,“相應的責任”是一種新的數人侵權責任形態,具有與傳統責任形態不同的特點;也有學者認為,“相應的責任”并非一種新的責任形態,應將其解讀為某種傳統的數人侵權責任形態;還有學者認為,“相應的責任”表達的并不是某種特定的責任形態,應根據其所處法條的位置及不同的語境,確定其具體屬于何種責任形態。理論上存在爭議,必然影響到司法裁判難以統一,導致類似案件出現同案不同判、類案不類判的結果。因此,從理論上、立法上對“相應的責任”的含義和性質進行探討,進而對相關規定作出正確的解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相應的責任”及其解讀困境之由來考察
科學地界定一個法律概念的含義,有兩種基本方法:一是運用歷史法學的方法,探討該概念產生的歷史緣由,再基于其產生緣由和目的,確定其基本含義;二是運用法解釋學的方法,將該概念與相關概念及其適用情形進行比較分析,再基于各概念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界定該概念的確切含義。由此,探究“相應的責任”的真正含義,首先應考察該概念的由來及其發展沿革。
“相應的責任”作為對法律效果的一種表述,在我國民事立法中早已有之。我國原《民法通則》第61條首次使用了“相應的責任”,用以表達民事行為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后雙方均有過錯時應各自承擔的責任;此后,我國原《擔保法》、原《合同法》中相繼出現了多處“相應的責任”。原《擔保法》中“相應的責任”并未超出原《民法通則》中“相應的責任”所規范的對象和范圍,僅表明擔保合同因主合同無效而無效的情況下債務人、債權人和擔保人均有過錯時應各自承擔的責任。原《合同法》中“相應的責任”既表達合同無效或被撤銷后當事人雙方均有過錯時應各自承擔的責任,又表達雙方違約時應各自承擔的責任。可見,在原《侵權責任法》之前,我國立法中“相應的責任”表達的只是一種民事責任劃分、承擔方式。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并不存在爭議。


“相應的責任”在原《民法通則》中產生以來,含義、語境和適用范圍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原《擔保法》《合同法》雖然擴大了“相應的責任”的適用范圍,但未從根本上改變原《民法通則》中“相應的責任”的基本含義,仍然是對合同無效、被撤銷后或雙方違約時各自根據過錯大小或違約情況承擔份額責任的一種描述。此時,“相應的責任”并不具有責任形態的含義和性質。“相應的責任”被引入原《侵權責任法》后,所表達的法律效果發生了較大變化,相關條款的規范內容明顯突破了原《民法通則》《擔保法》《合同法》中“相應的責任”的含義、語境和范疇。《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與“相應的責任”有關的條款數量劇增,適用情形大致有三種:一是雙方存在混合過錯時各自根據其過錯大小承擔責任;二是數人分別實施侵權行為時各自根據其過錯或原因力大小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三是數人侵權情形下除直接責任人承擔責任外,其他責任主體也應承擔責任。第一種情形下“相應的責任”的法律效果比較清晰,屬于民事責任劃分和承擔的一種方式,并非一種責任形態;第二種情形下“相應的責任”的法律效果也比較明確,責任主體應承擔相應的按份責任;第三種情形下“相應的責任”的法律效果比較復雜,引發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極大爭議,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通過以上對“相應的責任”發展沿革歷史的考察,筆者發現:《民法典》侵權責任編雖然改變了“相應的責任”所處的語境,擴大了其適用范圍,但其作為一個特定的法律概念的基本含義并未發生根本變化。質言之,“相應的責任”仍然是一種根據行為人的過錯或原因力確定責任的一種責任劃分方式,并非一種獨立的責任形態。值得研究的主要是《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規定的第三種情形下“相應的責任”,其與前兩種情形下“相應的責任”的主要區別在于:后者的含義可以直接體現為根據過錯大小承擔責任,前者因處于特殊的數人侵權規范中而應根據數人侵權的不同情形確定責任人應如何根據過錯承擔責任;后者可以根據所處條文的規定予以直接適用,前者的規范含義須結合所處條款對應的另一個數人侵權責任條款才能最終確定。本文重點研究前述《民法典》侵權責任編7個特別條款中“相應的責任”的責任形態,對此必須借助于對相關的數人侵權責任條款的分析。
二、“相應的責任”之含義厘清
科學界定“相應的責任”的含義,既需要從性質和內容上辨析其與按份責任、連帶責任、補充責任、不真正連帶責任等相關概念的區別,也需要從詞語和文義上探析其確切法律內涵。
(一)“相應的責任”并非一種獨立的共同責任形態



最后,“相應的責任”可能是一種共同責任,也可能是一種單獨責任。比如,我國《民法典》第1193條規定的定作人的責任包括兩種情形:承攬人造成第三人損害的情形;承攬人造成自己損害的情形。在第二種情形下,定作人對承攬人的損害承擔責任,其承擔的實際上是單獨責任。既然“相應的責任”有可能是一種共同責任,也有可能是一種單獨責任,怎么能將其解釋為一種新的共同責任形態呢?
(二)對“相應的責任”之責任形態不宜作一體化解讀
“相應的責任”作為一個特定的法律概念,如果是一種共同責任,對其責任形態就應進行一體化解讀,否則違背概念的統一性規則。筆者認為,從規范體系考察,不宜將“相應的責任”統一解釋為同一種責任形態。
首先,“相應的責任”不可能被統一解釋為連帶責任或補充責任。因為這兩種責任形態通常被明確規定在有關條文中,立法者若有將“相應的責任”作為這兩種責任形態之一的意圖,完全可以直接在有關條文中予以規定,無須將原來的連帶責任、補充責任修改為“相應的責任”。

最后,將“相應的責任”統一理解為不真正連帶責任,也缺乏規范評價上的統一性。《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可稱為法定不真正連帶責任的條文,其內容均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都使用了“可以向……請求賠償,也可以向……請求賠償”的表述;二是都存在終局責任人,非終局責任人只承擔墊付責任,其本身并無過錯且有權向終局責任人追償。但是,承擔“相應的責任”的行為人本身均具有過錯,相關法條的內容中是否存在終局責任人、誰是終局責任人均具有不確定性。
(三)不宜將具體條款中“相應的責任”固化為單一責任形態

(四)“相應的責任”實質上是一個技術性、轉致性法律概念
根據上文分析,“相應的責任”本身不具有確切含義,既不是一種新的獨立的共同責任形態,也不是一種具體責任形態,甚至在同一條文中也難以固化解讀為同一種共同責任形態。那么,作為《民法典》中統一使用的一個法律概念,其含義究竟如何?對此,需要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考察。


三、《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相應的責任”之具體條款解讀
通過對“相應的責任”的立法緣由和規范含義進行考察,筆者認為,《民法典》中“相應的責任”除明確指向單獨責任的以外,在侵權法視域下實際上屬于轉致性規范。因此,對《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7個有爭議的“相應的責任”條款進行理論闡釋,應當按照前述解讀規則,采用體系化分析方法。
(一)對《民法典》第1193條的解讀

(二)對《民法典》第1209條、第1212條的解讀
《民法典》第1209條、第1212條是關于責任主體分離的情形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的規定。對于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筆者認為,兩者的主觀狀態不同,不宜對其責任形態作固化解釋,而應考察案件事實能被何種數人侵權責任規范所涵攝,據此確定責任形態。在機動車租賃、借用的情形下,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與使用人對安全適駕狀況負有相同的注意義務,若明知存在不適駕的情況,可推定其對致損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具有意思聯絡,從而構成共同過失,應依據《民法典》第1168條的規定共同承擔連帶責任;若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并非明知而是因過失而不知道使用人存在不適駕的情況或者機動車存在缺陷,則其與使用人乃分別實施侵權行為,應依據《民法典》第1172條承擔按份責任。此外,在《民法典》第1212條規范的未經允許駕駛車輛的情形下,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與使用人不可能就不適駕的情況相互明知或者就損害發生的可能性進行溝通,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的過錯主要表現為未對機動車妥善保管或管理,其過錯行為與機動車使用人的行為結合在一起導致損害的發生,因而也應依據《民法典》第1172條的規定承擔按份責任。
(三)對《民法典》第1256條的解讀

(四)對《民法典》第1169條第2款的解讀
對于未盡監護職責的監護人承擔的“相應的責任”,筆者認為,將其解讀為不真正連帶責任具有合理性。從體系上看,此種情形下監護人的責任不宜解釋為典型的連帶責任和補充責任。《民法典》第1169條第1款、第2款應是一般規定與特別規定的關系,前者規定教唆、幫助侵權人應承擔連帶責任;后者規范的是特別情形且對責任承擔方式的表述與前者不同,不宜將其解釋為連帶責任。在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適用補充責任應符合《民法典》第1198條第2款的構成要件,但監護人并不是安全保障義務人,沒有適用該條款的可能性,將其承擔的責任解釋為補充責任不具有合理性。從立法目的看,此種情形下監護人的責任不宜解釋為按份責任。按份責任意味著減輕教唆、幫助人的責任。《民法典》第1169條第2款規定監護人根據其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而不是連帶責任,立法本意應是減輕監護人的責任而非減輕教唆、幫助人的責任。將此種情形下監護人的責任解釋為按份責任,會削弱對受害人的保護,因而并不妥當。
從理論基礎的成熟度來看,將此種情形下監護人的責任解釋為不真正連帶責任比解釋為單向連帶責任更具有合理性。因為監護人與教唆人、幫助人之間并無共同或分別實施侵權行為的可能性,無法依據數人侵權的法律規定予以解讀。鑒于前述單向連帶責任的概念存在歧義,以及監護人有承擔全部責任的可能性,按照不真正連帶責任理論對此種情形下“相應的責任”進行解讀更具有合理性。其一,《民法典》第1169條第2款的文義符合不真正連帶責任的構成條件。立法規定教唆、幫助人與監護人都應承擔責任,但承擔責任的法律原因不同。前者是因被視為實施侵權行為的人,后者則是因未盡到監護職責,法律未對兩者之間的責任關系作出明確規定。其二,將此種情形下監護人的責任解釋為不真正連帶責任,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當事人利益。通常情況下,教唆、幫助人在主觀上具有故意,監護人未盡監護職責在主觀上是過失。監護人在極端不負責任的情況下,如被多次告知有不良或不法行為卻仍對被監護人不加管教,構成重大過失。此時,教唆、幫助人與監護人之間的主觀過錯程度差別極小,監護人承擔全部責任更能體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在兩者承擔不真正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就外部責任關系而言,實踐中可以根據不同情況,如教唆行為與幫助行為的差別、非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辨識能力的差別以及監護人主觀過錯程度的差別,認定不真正連帶責任的范圍。就責任主體的內部關系而言,依據《民法典》第1169條第2款的規定,教唆、幫助人與監護人之間互有追償權。至于追償權是否成立,可由法官酌情裁量。這符合不真正連帶責任內部法律效果不確定的法理。
(五)對《民法典》第1189條的解讀

監護人與受托人之間通常并無共同實施或分別實施侵權行為的可能性,因而不能依據數人侵權的一般規定對《民法典》第1189條進行解讀。在委托監護的情況下,監護人基于監護關系承擔替代責任,受托人因未盡約定監護職責而承擔過錯責任。產生這兩種責任的法律原因不同,這符合不真正連帶責任的產生條件。就外部關系而言,受害人可以請求監護人承擔責任,也可以請求受托人承擔責任。就內部關系而言,由于委托關系的存在,監護人承擔責任后可依照《民法典》第929條的規定,以委托人的身份向有過錯的受托人請求賠償損失。因為受托人是受托履行監護職責且承擔過錯責任,所以不存在受托人向監護人追償的可能性。
(六)對《民法典》第1191條第2款的解讀


四、結語
《民法典》侵權責任編7個條款中規定的“相應的責任”,并不是某種新的共同責任形態,不宜將其一體化解釋為某種既有的責任形態,或者將某一條款中“相應的責任”固化為單一責任形態。當“相應的責任”條款規范的情形屬于數人侵權責任的范疇時,“相應的責任”具有轉致性概念的性質,對其解讀應結合其他關于數人侵權責任的規定或不真正連帶責任理論,找到能夠發揮法律效果形成功能的規范。隨著《民法典》的施行,理論界和實務界應逐步深化對其中“相應的責任”條款的研討,形成更多理論共識,積累更多實務經驗,在理論與實務、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有更深溝通的基礎上,盡量消弭對此類條款在法律適用上的理解偏差,盡量消除同案不同判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