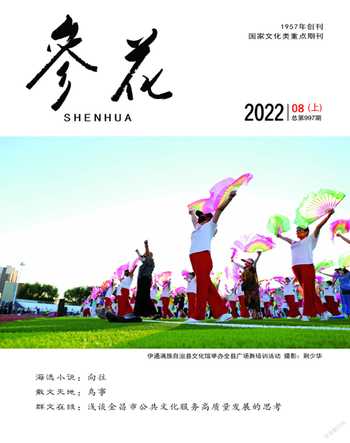影片《影》中的傳統意境美探究
一、引言
意境是中國傳統藝術的自覺追求,具有情景交融、虛實相生和意蘊豐富三方面審美特征。宗白華先生認為:中國藝術意境的創成,既須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曠空靈。纏綿悱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萬物的核心,所謂“得其環中”。超曠空靈,才能如鏡中花,水中月,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所謂“超以象外”。[1]筆者在追溯中國電影創作歷史時發現,深受傳統文化熏染的第一代、第二代導演所創作的詩情畫意般的《漁光曲》《姊妹花》《小城之春》等作品,以及傳達主流文化的第三代、第四代導演的許多影片,如《林家鋪子》《林則徐》《城南舊事》《早春二月》等,明顯借鑒了中國寫意山水畫的詩意,營造出獨具中華民族美學特征的中國電影。而影片《影》就繼承并發揚了中國電影這種美學特征,因此脫穎而出,帶給觀眾較好的視覺審美享受。《影》中俊逸秀美的山巒、滔滔不絕的江水、飄飄灑灑的細雨、蒙蒙雨中的刀光劍影等,無一不彰顯了影片的意境美。縱觀影片,飄逸輕揚的水墨畫面,再配以富有意蘊的表達,正是中國傳統元素意境的完美呈現。正如蘇東坡先生所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下面筆者就結合作品《影》來探討其中的意境美。
二、意韻悠遠的詩畫美
“詩畫一體”是對中國古典美學中意境說這一核心范疇的擴展。詩和畫兩種藝術形式都強調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以營造出玄妙的意境。其主要方法便是在客觀的、具體的、可視的物象之中,制造一種主觀的、抽象的、不可視的情緒或者情感,以實現令人回味無窮的表達方式。相比張藝謀的早期作品,如《英雄》的紅、白、黃、綠、藍五色映照人物,《十面埋伏》的黃、白、綠對照劇情,《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金黃主色調營造氛圍,《山楂樹之戀》的單色調表達青澀等,水墨風一氣呵成的《影》更像是筆墨勾勒出來的一幅會動的畫。其中,水墨丹青的服飾、太極和屏風、書法一般的高級質感,將彩色電影成功地拍出了黑白片的質感,把中國文化的美感放大到了極致。影片中呈現的子虞府,背鑲山中,三面環水,不僅給觀眾交代了府邸位置,而且營造出一種水墨山水畫的質感,沿著江水遠處的群山把子虞府掩飾起來,也和府邸的主人子虞一樣,把自己隱藏在暗中,壓抑著自己對王權的渴望。
再看下一個鏡頭,主人公境州坐在一葉扁舟上,從江面緩緩駛來,身后的群巒跟雨霧氤氳自成一景,山川與河流的空景給予觀眾最大的對比想象與景色描繪,畫面唯美。境州乘坐的小舟自偏一隅在畫面之中,對比意象于山川的王權和意象于河流的家主子虞一樣,宛如自己的身世一般,夾雜在龐大的山川,與能載他亦能覆他的水面之上,使觀眾能明顯感覺到他當時格外卑微的處境和渺小的力量。這一層由詩畫之景投影出人物之情的意境令人難忘。在境州最后一次上朝被貶為庶人,跟境州與楊蒼在城下決戰的時候,鏡頭也是給到了山水浩渺的景象,但是這一次區別于開頭畫面中的角落,此時的境州已經被構圖于畫面正中,與楊蒼的對決已經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影子代表著王權和子虞,更是通過與小艾的情感交融之后,找到了他內心之中真正的自己,洗刷著冤屈和殘酷的江山爭奪權大戰,從視聽的角度營造了詩畫合一、虛實結合、動靜結合的意蘊,含蓄內斂地表達了東方美學意境。
此外,在水墨畫般的影片視覺效果和意境布局中,導演在幾位主人公的服飾設計上也頗下功夫,其身著的漢服服飾設計也都遵循著中國水墨畫中所獨有的飄逸與詩意感。每個角色的服飾樣式與顏色也與其人物性格相對應,小艾的純白代表著她的善良與溫柔;子虞的純黑說明他欲望熏心,對王權的極度渴望;境州服飾的黑白交融,前期萬事遵從家主子虞時以黑色為主,隨著影片內容的漸漸推進,內心的覺醒也讓其服飾的顏色得到了亮化,彰顯了水墨畫般靈動飄逸的意境和黑白交融的藝術特色,充滿詩情畫意。同時,這種服裝設計的飄逸效果在影片人物打斗場景中盡顯靈動和灑脫。在密室中,小艾悟出了破楊刀之法,提出了“以女人的身形入沛傘”,小艾親身教境州體悟陰柔之法時,二者身體貼合,當簫聲響起,導演使用大量的升格鏡頭,飄逸的服飾配上陰柔身形的婀娜輾轉,每一招每一動作,每一鏡頭每一幕畫面都充分展現了中國古典之中詩意的情致。這種詩意的打斗鏡頭表達著其中人物的感情狀態,隱忍、不甘、掙扎,不僅讓觀眾在觀看時感受到精彩的打斗場面,同時也被其中所賦予的詩畫意境所感染。
三、虛實相生的朦朧美
“虛實相生”的概念被廣泛地運用于中國古典繪畫、詩文和戲劇的藝術創作理論中。王冀德曾就戲劇的創作目的與方法指出:“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明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用實也……以實而用實者易,以虛而用實者難。”即戲劇和電影應該反映真實的內容,但為了藝術效果,應該對原型在各方面的局限,在藝術形象的設計上進行虛構,這即是“出實用虛”。[2]在《影》當中,導演嘗試提出了一種新的美學概念——“陰陽虛實美學”。在影片當中最明顯的設計,就是大量的對立與統一,不論是重要的意象“八卦圖”,還是圍棋的黑白對弈,或者是朝堂之上文武大臣的分隔爭執。單一人物的抉擇與舉動和群像人物的激進與隱忍,意象畫面的真實與虛假,無不都在展現這個令人著迷的新式美學思維。
電影改編自朱蘇進的小說《三國·荊州》,但是導演卻放棄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吳蜀兩國爭奪荊州的故事背景,而是將故事置于一個架空的背景時代。架空后故事更自由,很多東西還需要自己體會,這就是“虛”。從整個影片的場景布置來說,導演都是力求從實際出發,不光是真實搭建的境州城、決戰時的石頭山,等等,還有演員一人分飾兩角,兩個角色外形差別很大,導演并沒有用替身演員來代替,而是讓演員飾演完境州這個角色之后,急速減重再飾演病態的子虞,正是這種力求實的方法將境州和子虞兩個形象完美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同樣,在有武打動作戲的時候,導演也是多采用固定鏡頭和慢鏡頭,更精細地雕琢每一個畫面的真實感。電影中所刻畫的境州這一人物,從八歲被帶到子虞府中,過著常人難以忍受的生活,到頭來,自己只是一個別人的工具、一個替身、一個影子,仗著子虞家的救命之恩與在沛國的權勢每天扮演著一個不屬于自己的身份。他的苦悶跟心情是可以表達給觀眾的,這些都是是電影想表達的“實”,是人物在欲望驅使下的內心沖突,以及在亂世生存的無奈和悲哀。
此外,電影在藝術處理上也是虛實呼應,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電影的主色調——以黑白兩個色調為主。水墨黑白,對應陰陽虛實哲學,表象的太極八卦,對應內里的人物關系制衡:文與武,影子與都督,虛偽與單純。易卦以黑為坤色,凡坤屬,多以為陰。[3]因此,黑色的使用多用以表現環境之兇險或人物內心的孤寂哀婉。以“白”為乾,多為陽,電影在人物服裝、場景布置上也都遵循這一規律。在人物服裝上,電影的一開始,境州與楊蒼宣戰之后回到沛良大殿接受沛王的詢問,在這場戲中,境州作為替身代表子虞出現在沛王面前,身上服飾顏色為黑,此時此刻他屬陰性,而小艾則作為真實的子虞的妻子身份,故身上的服飾顏色為白,代表陽性。而在子虞府的密室中,此時人物虛實關系發生了轉換,躲藏在密室中的真子虞成了陰性,而在朝廷上為替身的境州此刻卻成了陽性,服飾上以子虞為黑,境州為白。最后與楊蒼的決戰之中,楊蒼的大刀作為電影中至陽至剛的符號,卻身著黑色的盔甲,境州此時已被貶為庶人(此可理解為白身),身著服飾比較草莽。我們可以總結出,小艾身為女性為陰,卻服飾屬陽;境州在子虞面前名為替身屬陰,卻服飾屬陽;楊蒼作為陽剛符號,服飾卻屬陰。這樣的巧妙設計讓觀眾能明白其中所表達的陰陽虛實的深意,但是導演又沒有準確明了的表達,能讓觀眾有一種言之意而意無窮的朦朧感。
在場景布置上,觀眾可以看到子虞府和沛良大殿中掛滿的水墨畫和屏風,給觀眾以曖昧陰森之感。這種建筑內部的裝飾不存在三國之中,也不是中國古代任何一個朝代的內飾風格,讓觀眾真切感受到典雅美感的同時也造成了一個虛假的荒謬感,時刻提醒著觀眾這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不讓觀眾的思維局限于《三國演義》中婦孺皆知的歷史事件之中。影片的整體基調給觀眾以詩畫優美的感受,但內容內核的表達卻是人物心理與權謀的交融,正是這兩者一黑一白,一陰一陽,一虛一實的相互融合,才給觀眾以極具質感的朦朧美。
四、人物形象的深邃美
在意與境的結合中,“境”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可以寫景,可以敘事,可以狀物,也可繪人。[4]在影片《影》的故事里,人物的形象與故事發展至關重要,影片并未選擇一個王侯將相、位高權重的大人物入手,而是選擇了一個不知出處的小人物境州作為整個影片的立足點。他從八歲就被囚禁于子虞府中,終年不見天日。對于這樣困境,他沒有放棄自己的內心,表面上對于子虞家所謂的養育之恩表示忠心耿耿、至死不渝,但是他的內心不甘心一直作為別人的影子而存在,他也有著一腔真情,對于母親的期盼和對于小艾不敢言表的感情。他為子虞收復境州的最初目的也是為了回到家中見到自己的母親,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此外,他被作為棋子在爭權奪勢中斡旋,希望獲得人身自由的主線也表達了影片的一個內核:尋求本我,實現本真,追逐人性的自由。
在整部影片中,境州夾在國君與自己主子的權力爭奪中,在隱瞞和欺騙、真真假假中尋找著自我存在的意義。因此,母親被殺之后,“惡之花”在他心中發芽。在電影最后,子虞與沛王在宮殿進行最后的權謀博弈爭斗中,同樣境州也在權力的誘惑和人性的善良之間博弈,最終還是選擇了保留對小艾的真感情和對權力的欲望,借都督子虞之手殺掉了沛王,成為沛國新的主公,表現了真情與假義的融合,凸顯了人性的復雜。
如同《影》中朦朧的屏風,在沛王和都督的關系中拉開了一個等級分明的層次;在都督和替身之間劃出了一道全然透明的界限;在都督和田戰與王的君臣主仆關系之上,暗藏了看破不說破的倫理隱喻。子虞本是沛國的大都督,為沛國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一開始想要收復境州的說法是為沛國而收復,也算是以正義之名,但是在意識到沛王想在朝堂之上除掉自己的時候,其內心想法發生了轉變,后面的密謀中也是希望成為沛國的“天”,不想再被別人決定自己的命運。不得不說子虞作為大都督,開始是想為國收復失地,但隨著心態的轉變,最終做出了“弒君”這一決定,故子虞也是正義與邪惡交織的一個人物形象。在田戰心里,沛王只是一個誤國誤民的庸主,在朝堂之上也公然違背了君臣之禮,但是田戰并不是一個不忠之人,他忠于國家、忠于正義。沛良正是覺察到了這一點,同時也意識到了都督已功高蓋主,自古以來凡是臣強主弱、臣盛主衰的情況出現,君都沒有好的下場,所以他也想通過影子除掉真身子虞,轉而讓影子成為聽他差遣的都督。沛良不可謂不精明,他早就察覺到都督的影子跟魯嚴的叛變,將計就計收復了境州,派人妄圖殺掉真身,精心設計之后的“朝堂之戰”。
作為一個君主,沛王也不可謂沒有獨特的治國本領,他能夠任命前朝的大都督在本朝擔任重臣,大臣在朝堂上公然對他不敬也只是被剝奪了官職,體現了他作為君主的大度。在面對楊平言語羞辱自己妹妹的時候,其認識到還沒有能力與楊蒼父子抗衡,故而忍耐,體現了作為一個君王的隱忍。他的目的只是想成為一個真正有權力的君王而不是一個傀儡,所以爾虞我詐的權謀之術也無可厚非。
小艾也一直處于掙扎之中,作為子虞的妻子,她必須恪守婦道,在與影子朝夕相處的過程中自己的內心波瀾漸起,最終在道德的禁錮掙扎中與境州假戲真做。導演對每個人物的設立,都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的設置,而是通過影片故事的深入,不同的人物心理狀態的轉變,讓觀眾沉浸其中,體驗到可意而不可言的深邃之美。
五、結語
綜上所述,從電影內容來看,導演在影片《影》的畫面、情景營造、故事講述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是擁有中國傳統美學元素的電影,不斷凸顯著傳統的意境美。飄逸輕揚的水墨畫面,富有意蘊的美學表達,使得意境之美在筆墨之間被揮灑得淋漓盡致,不僅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為今后電影對傳統美學表達的影像化制作提供了寶貴經驗。
參考文獻:
[1]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孔艷霞.《影》對古典美學的視覺闡釋[J].電影文學,2018(23):95-96.
[3]彭德.中華五色[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8.
[4]胡經之.文藝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金堅,男,碩士研究生在讀,新疆藝術學院,研究方向:影視藝術)
(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