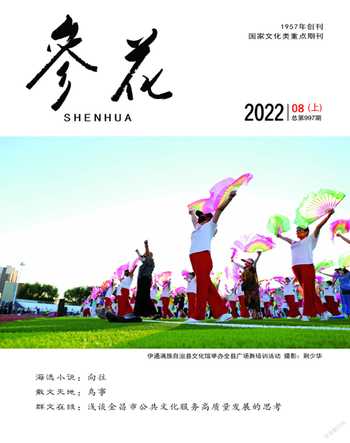從《你好,李煥英》看小品改編電影的創作
電影作為一種依托視聽語言表達敘事和傳遞情感的藝術,從多種藝術形式中汲取養分,用以豐富自身內涵;而小品作為一種與電影具有共通性的藝術,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傳播下,廣泛活躍于熒屏之上,成為人們日常娛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小品所呈現的極具觀賞性的鏡頭效果,能夠為電影創作提供藍本與素材,使小品與電影跨界聯動具有可操作性。《你好,李煥英》這部電影脫胎于同名小品,上映不久就斬獲了54億票房。該影片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對小品文本的視覺轉碼,對現代視聽語言意旨和感知的交互,對現實生活情感元素的挖掘,以及高水平的鏡像技術。特別是刺激和調動觀眾的審美期待,豐富當代精神文明內核,才使《你好,李煥英》這部電影成為近年來鮮有的既叫好又叫座的影視作品。上映一年之后的今天,雖然影片本身熱度減弱,但我們看到小品改編電影的創作熱度依然存在,對這一創作手段而言,發展空間仍然廣闊。
一、具有增值意義的跨媒介敘事
隨著電影事業的進步與發展,反映現實生活的影視作品越來越多,而這些影視作品都能迎合社會主流價值觀,彰顯大眾文化訴求。跨媒介敘事作為一種改編電影的藝術手法,并不是簡單地照搬照抄原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將原作品中的藝術元素直接挪用到影視媒介上,而是強調對原IP的解讀與重構,實現原文本的再生產與意義增值。正如國際知名傳播和媒介研究學者亨利·詹金斯所說:“一個整體要素在多個媒體渠道中系統地分散,能夠創造統一和協調的娛樂體驗過程。”《你好,李煥英》這部電影在跨媒介敘事的過程中,有機融合運用穿越、親情、娛樂等元素,對同名小品進行多方位、多層面、多角度的文本符號轉碼,充實和填補了原作品的細節空白,使敘事內容更加豐滿、順暢。
小品受舞臺空間、場景調度、表演時間等要素的影響,其故事情節簡單明了,矛盾沖突直截了當。這就使小品呈現出“事件小、人物少”的特點。在《你好,李煥英》中,是由簡單的人物背景和關系構建了小玲穿越時空探尋和追憶親情的故事。而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賦予人物角色更加復雜的情感關系,并對一些人物角色進行了取舍。比如舍棄小品中賣豆腐的小販,增加“古惑仔”形象的冷特。不僅如此,“李煥英”這一人物形象的地位和作用也發生變化。在小品中,李煥英只是故事中的關鍵性角色,用來凸顯主題和推動情節發展。在電影中,李煥英則是故事的主人公。相比較之下,電影中的李煥英比小品中的李煥英更具思想內涵和人格魅力。電影中的李煥英保留了質樸善良、活潑愛笑、平易近人的性格,依托與“小玲”之間的互動交流呈現出了當前中國家庭觀念和母女關系。特別是重逢與別離的情感交織,虛幻與現實的交相呼應,用一段段的溫情詮釋母愛的偉大,喚醒了當代無私奉獻的母親的集體記憶。同時也從兒女的視角,解讀了“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冰冷現實。加之演員依然是小品中的原班人馬,沒有任何違和感,進一步深化了人物形象,從而為整部電影加分。
電影文本與小品文本的交織共融,在時空上形成相互對話的符號網,是跨媒介敘事的成功之處。從《你好,李煥英》小品改編電影的敘事特征來看,電影有小品的敘事骨骼框架,對小品進行了更多層面的敘事和情感表達,且二者相互照應,融合呈現。在電影中,在得知馬上回到現實的基礎上,增加了小玲發現褲子上的精美補丁后恍然大悟的情節,使小玲明白母親與自己是一同穿越到過去的,這為后面回憶李煥英的行為做了鋪墊,渲染了情緒。這種反轉讓人措手不及,也正是在這種反轉的驅動下,使之前李煥英的語言、動作及行為有了更多的痛點和興奮點,從而將觀眾的情緒帶向對母愛的深刻思考,不禁讓人潸然淚下。總之,無論是小品還是電影,故事的主要情節沒有變動,都是小玲穿越到過去,幫助年輕的母親尋找真愛,想利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動讓母親“高興”一次,這與電影開始時的“從小到大沒讓媽媽高興過一次”,以及與冷特的感慨交相呼應,進一步突出了小玲心底深處對母親的愧疚與懷念。正是母親對女兒的包容、理解與關愛成了本部影片的動人之處,使小品改編電影的敘事情節產生了鮮明的互文關系,給觀影者帶來極大的情感體驗和內心沖擊。
二、交互感知意旨的視聽融合
小品是一種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更加貼近現實生活。特別是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場面的調度和鏡頭的運用成了提高小品藝術效果不可或缺的要素。視聽語言作為一種直觀的感官符號,就是對影像傳播“符號化”的表達過程。影片《你好,李煥英》就是依托鏡頭、剪輯、臺詞等元素訴諸情感,發揮影像的功能與價值,才使影片更具情感內涵,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產生情感共鳴,收獲更多的情感啟發。
在視聽藝術中,鏡頭作為一種情感傳遞符號,能夠在刻畫形象、渲染氛圍及引導情緒上發揮重要作用。雖然小品依賴鏡頭技術,但也保留著明顯的舞臺藝術特征。這就使小品在表達敘事的時候,不會過多使用鏡頭技巧。在小品《你好,李煥英》中,依托簡單的幕啟幕落實現時空間的切換,而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利用一些特殊影像符號,包括黑白電視機、化工廠、工人的服裝與面貌等,實現了現在與過去的銜接,從而更加富有穿越的奇幻色彩,并突出了時代的質感和厚度。通過拼接多個鏡頭,在深化小品文本內涵的同時,對小品文本進行審美性的改編,實現了舞臺化向影視化的跨度,給觀眾帶來豐富的視覺感受。特別是利用多組鏡頭刻畫排球比賽背景氛圍,如利用電線桿分割李煥英和王琴位置的鏡頭來昭示二人的敵對關系,暗示排球比賽的焦灼,從而激發觀眾對接下來的情境的想象。
剪輯是對多個鏡頭畫面的組織銜接,結合音樂和特效,讓敘事表達更加生動形象,從而將故事情節一步步推向高潮。在小品《你好,李煥英》中,觀眾情緒的調動主要依托場景的調度和演員的語言與行動,賈玲從第三視角來審視母親及其曾經的生活,利用幕后的深情對白,加之與之相稱的背景音樂,表達了賈玲對母親的感激與懷念。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鏡頭剪輯采用的是交錯式結構,打破了小品中時空的束縛,讓符合相關情感表達意境的場景交互,拉伸了敘事時間和擴充了情感容量。特別是在影片的最后,小玲意識到母親與自己一同穿越到過去,短短幾分鐘的鏡頭將情緒推向最高點,讓小玲注視自己與母親過去的溫情時刻。這無疑拓展了情感表達空間,豐富了情感表達內涵,以及延長了觀眾的心理節奏。
臺詞是劇中人物情感表達的直接載體,對劇情的發展具有導向作用。在小品《你好,李煥英》中,很多臺詞飽含笑點和淚點,能夠調動觀眾的內心情緒,緩沖觀眾的視覺疲勞。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很多臺詞都是經過小品藝術化拓展而來的,包括具有諧音特色的人物姓名、溫情質樸的對話等,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撥動觀眾的心弦,與觀眾產生情感共鳴。比如小玲說的“媽,我好想你”,李煥英說的“媽知道”等,與特定的場景和音樂相配合,迸發出更大的情緒張力,這不僅凸顯了小玲痛失母愛的遺憾,也表達了小玲對母親的深切懷念,更讓小玲表達的話語成為觀者的心聲。
三、浪漫與現實相生的情感抒發
酣暢、飽滿的情感表達往往能以情動人,給觀者更加直接的情緒體驗。《你好,李煥英》這部影視作品正是賈玲自身經歷的縮影。依托真誠的故事情節,巧妙的場景設計,不僅拉近了孩子與父母的心理距離,也引發了中老年群體的青春追憶。《你好,李煥英》是一部典型的現實主義風格電影,雖然融入了“穿越時空”的潮流元素,但它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將它作為用于修飾“身體”的外衣,用來更好地表達敘事和傳遞情感。確切地說,就是為了方便講述劇情而使用的浪漫主義手法。在小品《你好,李煥英》中,簡單的臺詞、肢體語言、場景布局等,集中表達了過去與現在的沖突,但受舞臺表現形式的限制,能夠給觀眾帶來的心理沖擊極為有限。比如先后出場的是瘸腿的張江、賣豆腐的小哥,以及李煥英。這里觀眾會想象張江的腿為什么會瘸,賣豆腐的小哥對劇情有怎樣的推進作用。雖然觀眾期待解謎,但基于小品時間過短,使得這些內容只能通過寥寥數語展現出來,而這一點觀眾是心知肚明的,顯然不能以此充分調動觀眾的情緒。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不僅有特寫鏡頭,如破褲子、升學宴、宴后母女談心等,也有更多的懸念設置,如尖銳的剎車聲、沉悶的撞擊聲等,都能給觀眾帶來極大的心理沖擊,使觀眾情不自禁地想象接下來發生的劇情。后面的劇情中,破褲子的鏡頭多次出現,儼然成了女兒懷念母親的情感寄托之物。正是依托有形的“物”來表達無形的“情”,使得賈玲在劇情中的情感迸發更有張力和穿透力。在小品《你好,李煥英》中,小玲的穿越是幕啟幕落的一個過程,形式簡單,手段單一,瞬間完成了時空的穿越。而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她的穿越是由仰拍和俯拍多個鏡頭拼接而成,給人以一種天外飛仙般的感覺。特別是落地的一瞬間將李煥英砸暈,造就了母女的相遇。這就是電影制造的巧合,使主人公與相關人物快速發生關聯。其中,小玲的落地位置頗有深意,不能簡單地理解成一場特別的“意外”。在小玲“從天而降”之后,母女以表姐妹的身份相知相識,體現出了輕喜劇的風格。而后小玲為了讓母親真正地“高興”一回,所以才積極幫助李煥英買全廠第一臺電視機,慫恿李煥英組織排球比賽,以及撮合李煥英和沈光亮,既充滿了現實主義色彩,又充滿了浪漫主義情調。
四、同感共情的價值觀念建構
藝術源于生活,也能回歸生活。也就是說,所有的藝術種類的改編創作都是基于對現實生活的思考,絕非簡單的視聽符號轉碼。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思想觀念的轉變,觀眾對銀幕影像的感知已超脫了表面的影像內容表達,更會有感知、想象、思考等一系列的內心活動,并在此基礎上對腦海中的“影像”進行深加工。《你好,李煥英》將小品的文學特征與影像的藝術手法相融合,構建了更加系統化的自我身份認證鏡像,不僅打破了原有藝術形式相分離的格局,更在無形之中拓展了電影的話語體系,與觀眾形成了新的情感橋梁。
影片《你好,李煥英》是由同名喜劇小品改編而來的,在表達母女關系主題時采用了現實與虛幻相結合的手法。面對意外離世的母親,小玲內心充滿愧疚和不舍,所以她用幻想的方式勾勒理想世界,敲開幸福的大門。以知曉未來的身份幫助母親追求幸福,以慰藉悲傷不堪的心靈,讓內心深處獲得滿足。青年人大多努力拼搏著,幾乎沒有時間陪伴父母,常常是“子欲養而親不待”。這種冰冷殘酷的現實正是大多數青年人的焦慮,反映出了社會群體價值。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小玲沒有自怨自艾,而是努力幫助母親尋找幸福,表達了作為女兒對母親的愛。同時面對物欲的誘惑,即使是在小玲的指引下,李煥英沒有迷失本心,依然真誠地選擇貧窮的賈文田,這不僅展現出了新時代女性的力量,也展現出了積極的社會意識和價值觀念。總之,電影《你好,李煥英》的許多情節都體現了真實生活經歷,雖然具有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但仍具有較高的精神價值。不僅脫離了消費主義層面,也上升到心靈關照層面,這也是該影片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五、結語
綜上所述,雖然影片《你好,李煥英》是由同名喜劇小品改編而來的,但它與小品《你好,李煥英》相契合、相呼應,展現出了更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呈現出了更多的美學肌理。隨著大眾文化審美趣味的不斷提高,由小品改編成電影的藝術作品必將會給觀眾帶來更多的情感體驗。電影《你好,李煥英》的成功充分證明了小品改編電影的可行性,為電影創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1]呂雪寧,曹丙燕.《你好,李煥英》的建構性品質與文化意義[J].漢字文化,2021(23):137-139.
[2]鐘之.電影《你好,李煥英》的創新及思考[J].戲劇之家,2021(29):140-141.
[3]張旭.《你好,李煥英》:小品改編電影的創作策略研究[J].電影文學,2021(12):100-103.
[4]陳茜.《你好,李煥英》的偶然和必然[J].商學院,2021(Z1):107-109.
(作者簡介:葉子,女,碩士研究生,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數字藝術與傳媒學院,研究方向:影視文學劇作、紀錄片創作)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