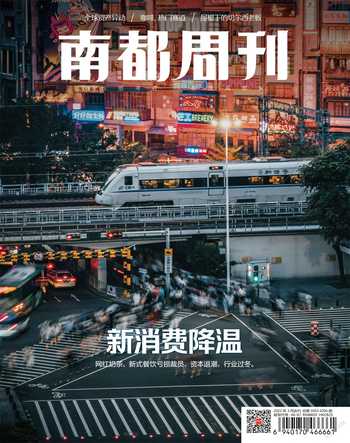咖啡是個好賽道
詹丹晴

有力咖啡,受訪者供圖 。
Blue Bottle藍瓶咖啡在國內第一家門店已經開業兩個多星期了,小迷沒想到,這家店在工作日的下午依然排起了長隊,她只好拐進了另一家咖啡館。
開業當天,有消費者足足等了6個小時才喝上一杯藍瓶咖啡。
這種排隊盛況與初代排隊網紅喜茶的當年有得一比。2017年春節,喜茶在上海第一家門店時,排成長龍的隊伍等候時間也要7小時上下。半年后,這條隊伍在喜茶北京首店前被“復制”“粘貼”。
現在,主角已經換人。
當年風頭十足的喜茶近來被傳出在裁員,另一個頭部品牌奈雪的茶遲遲未能扭虧為盈,茶顏悅色一口氣關店87家……一時間,茶飲頭部品牌好像都陷入了困境。而咖啡賽道則完全是另一副光景,他們高舉著大力開店的旗幟,2022年,想讓你變身咖啡人。
藍瓶咖啡被稱為“咖啡界的蘋果”,它由音樂家弗里曼于2002年在美國加州創立,主打精品咖啡,2017年9月,藍瓶咖啡的68%股份被雀巢斥資4.25億美元收購。目前,藍瓶咖啡在全球擁有門店約102家,主要分布在美國。
藍瓶咖啡引發的排隊熱潮讓不少人“種草”,外地的朋友可能要失望了,它的第二家門店已經敲定,依然在上海。
上海是國內咖啡館數量最多的城市,根據新一線城市研究所的報告,截至2021年1月,上海擁有6913家咖啡館,平均每萬人擁有2.85家咖啡館。
Manner、Seesaw coffee、M stand、Nowwa等咖啡品牌在上海創立,許多國外知名品牌的內地首店同樣設在上海,如加拿大咖啡品牌Tim Hortons、美國加州咖啡品牌Peet’s coffee。
不只上海人,大家在其他地方喝咖啡的選擇也將越來越多。
3月初, Manner宣布,3月8日-10日,Manner約200家店在上海、杭州、重慶、深圳、北京等10個城市同時開業。
Manner無疑是繼瑞幸之后最受關注的本土咖啡品牌。它主打價位在15-20元,2018年10月以來,包括今日資本、H Capital、Coatue Management、龍珠資本、字節跳動的投資砸向Manner。
Manner的店集中在上海,根據其公眾號,此前,它在全國共有377家門店,其中287家門店在上海。
要大力開店的咖啡品牌不只Manner,Tim Hortons預計2026年年底中國門店數量將拓展到2750家以上,目前其門店數量只有340家;Peet’s coffee在發布2021年財報時表示,去年他們已經在中國開出70多家門店,而他們的野心是開150家;Seesaw也表示,剛剛獲得的數億元A++輪融,將用于全國門店拓展和數字化建設。
除了連鎖咖啡品牌,不少跨界選手也想來分一杯羹。就在2月,狗不理被發現成立了咖啡公司,同一時間,全國第一家郵局咖啡館在廈門開業。
總之,咖啡賽道上,站滿了雄心壯志的各路選手。
這么多品牌想要大力開店,就意味著咖啡是門好生意?
比起茶飲市場,愿意開放加盟的咖啡品牌相對較少,像瑞幸直到2021年1月才放開加盟,星巴克、Manner、Tim Hortons等品牌則均為直營店。因此,比起經常在網上控訴加盟后虧空存款的奶茶加盟商,咖啡館店主的存在感不是很強。除了連鎖咖啡品牌外,各個城市還有一些獨立的咖啡館。
攝影師Ken原本兼職售賣咖啡相關產品,2021年年底,他和兩個拍檔合伙在廣州員村智慧園開了一家瀧枋咖啡館,主打意式現磨咖啡。
開業三個多月來,瀧枋咖啡館慢慢摸索出顧客們的喜愛,產品出品較為穩定,每天出杯量約為30-40杯。Ken告訴南都周刊記者,“我們沒有開通外賣,出杯量沒有其他店多,作為初創企業,我們不想跑得太急。”
在初期投入時,因Ken本來就有咖啡機、冰柜等裝備,撇除這方面的折舊,Ken預計開店6個月能夠實現每月盈虧平衡,但如果把這些固定資產算進去,“盈利則有些緊張。”
家住廣州的Jeff會開咖啡館,是因為他喜歡咖啡,而且想有一個可以把自己資源、興趣、想法實踐落地的地方。他的“有力咖啡”館開在廣州寶源路,店鋪面積只有28平方米,主打“貿易行”的概念,
Jeff告訴記者,“我們這是理想店,有故事、有氛圍,不是靠出杯量盈利,能夠打平經營就好。我們開店第一個月就有盈利,我希望3年能回本。”
除了連鎖咖啡品牌,不少跨界選手也想來分一杯羹。就在2月,狗不理被發現成立了咖啡公司,同一時間,全國第一家郵局咖啡館在廈門開業。總之,咖啡賽道上,站滿了雄心壯志的各路選手。
國內的咖啡館越來越多,在Jeff看來,“我感覺懂得喝咖啡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不會單純覺得喝咖啡比喝茶飲高端、環境更好。咖啡和茶一樣,貴的豆子、貴的機器,容錯率很高,也不會難喝。”
在Ken看來,開一家咖啡館易入難精。“現在有很多咖啡入門的相關培訓,但要真的做好、獲得好的口碑并不容易。這兩年,咖啡市場的氛圍確實比前兩年要活躍很多,但是咖啡的毛利率并不高,單純想要通過咖啡盈利很難,還需要組合推出一些周邊產品。”
據Ken透露,他身邊就有不少朋友經營咖啡館虧損甚至倒閉的。
對比咖啡賽道的熱鬧,茶飲業的日子就顯得有些暗淡。
今年2月,喜茶多款產品降價,還被傳大幅裁員;奈雪的茶2021年預計虧損1.35億-1.65億元;茶顏悅色去年集中關店七八十家,疫情期間每月曾虧損2000萬元。
同樣是飲品,為何茶飲、咖啡冰火兩重天?
餐寶典創始人、餐飲分析師汪洪棟告訴南都周刊記者,實際上茶飲和咖啡的生意邏輯并沒有本質區別。“這主要是因為發展階段不一樣,茶飲整體跑得太快,已經步入另一個階段,咖啡則要慢一些。”
易觀分析品牌零售行業分析師李心怡持同樣看法,她告訴記者,“咖啡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尚未達到茶飲市場那樣,茶飲賽道上門店數千家甚至上萬家的品牌不少,咖啡市場的連鎖化程度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再加上,咖啡也是餐飲賽道里容易實現標準化的品類,易于擴張,因此為資本所看好。”
從門店數量上看,咖啡和茶飲門店區別明顯。
咖啡門店數最多的瑞幸,截至今年1月,其門店數已經超過6000家;截至2021年,星巴克在中國的門店數為5557家;排名第三、第四的麥當勞麥咖啡和Nowwa門店數量斷崖式下降,分別約為2200家和1500家,而其他品牌則尚未突破1000家。
在茶飲市場,根據餐飲數據平臺“窄門餐眼”,蜜雪冰城的門店數突破1.5萬家,書亦燒仙草、古茗、茶百道、coco、益禾堂、滬上阿姨的門店數量也在4000家以上,門店數超過1000家的品牌有18個。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咖啡消費潛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間。根據德勤發布的《中國現磨咖啡行業白皮書》,2020年,我國大陸地區人均年咖啡消費量為9杯,日本、美國、韓國分別為280、329、367杯,對比明顯。不過,單論我國一二線城市的咖啡消費水平,則為300杯/年,接近成熟咖啡市場水平。
2021年我國咖啡市場規模約為3817億元,艾媒咨詢預計,行業將保持27.2%的增長率上升。
對于還在跑馬圈地的咖啡品牌而言,能否實現盈利,并不是眼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盡管市場潛力巨大,但是僅從本土唯一上市的咖啡品牌瑞幸財報上看,它也并沒有實現盈利。2021年第三季度,瑞幸營收為23.50億元,同比增長105.6%;凈虧損2350萬元,同比減少了98.6%。
當然,對于曾經陷入財務造假風波的瑞幸而言,能交出這份成績單已不容易。
“現階段的咖啡市場處于擴容的關鍵時期,對于咖啡品牌而言,擴大規模搶占市場仍然非常重要。”李心怡指出。
但是,當咖啡館的數量達到茶飲市場的程度時,他們會不會重演茶飲的故事?
汪洪棟認為,“按照目前的節奏,未來咖啡肯定也會跟奈雪、海底撈一樣,出現分流情況,單店營業額下降,接著會放緩開店。而好的鋪位是稀缺的,大家都在搶,對企業資金實力要求更高。咖啡想要快跑,必須有資金支持。”
喜茶在來福士廣場開下上海首店時,小迷也曾經跟風去排了兩個小時的隊,“第一杯喜茶的味道很驚艷”。現在,茶飲店開得遍地都是,對她而言,茶飲的吸引力已經退減,而且,“喝茶飲容易胖。”
現在,小迷基本每天會喝一杯咖啡,當咖啡館越開越多,她發現,不同咖啡館的咖啡口感區別不大,因此在選擇出品相似的咖啡品牌時,她會優先考慮價格和距離。
小迷的消費體驗讓她產生了疑惑:當咖啡館越來越多,如何脫穎而出?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有一款咖啡產品被多個采訪對象提起——瑞幸的生椰拿鐵。去年,這款產品為瑞幸在社交媒體上刷足了存在感。
根據“每日人物”報道,2021年,生椰系列產品單月銷量超1000萬杯,創下新品銷量最高紀錄。
Jeff坦言,對于咖啡館而言,“產品是根本,如果你選的東西,出品不好,就沒有回頭客,當然環境和店主、店員(的經營)也很重要。”
李心怡認為,“伴隨著規模的擴大,咖啡單店盈利模型、供應鏈管理能力、產品創新能力、精細化運營能力的重要性會愈發凸現出來。”咖啡品牌想要脫穎而出,除了市占率外,一要看能牢牢把握住消費者對口味的多變需求。中國市場的咖啡呈現出飲品化的趨勢,這就意味著用戶對于咖啡基本款之外有著更多樣化的口味需求;二是能否把供應鏈管理做到極致——供應鏈的成本和效率直接關系到門店的盈利能力;三是能否把數字化手段充分運用到咖啡賽道,實現降本增效,同時提升用戶體驗。

瀧枋咖啡館,受訪者供圖。

有力咖啡賣得最好的咖啡類特調——洛梨塔,受訪者供圖。


瀧枋咖啡館的咖啡+點心,可提高銷售額,受訪者供圖。

冰美式,受訪者供圖。
汪洪棟則認為,市占率仍然很重要,因為營收等財務指標,消費者很難直觀判斷,但線下密集開店,會形成品牌效應。咖啡的主流消費群體,對于咖啡品牌很注重,因此品牌的認可度很關鍵。“最重要的是,產品研發能力——產品要時刻保持熱度。好的產品不僅能提升復購率和業績,還可能吸引新的資金,因為投資者也會看到公司的研發實力”
事實上,盡管眼下咖啡館看起來仍然風頭十足,潛力無限,但是過去在這個賽道上,碰壁的人并不少。
2020年,倫敦咖啡品牌Costa(咖世家)接連關閉青島、北京及江浙地區的門店,不過優化店型后2021年它又在發力開店。同樣是2020年,韓系咖啡漫咖啡在北京約有2/3門店關閉。互聯網品牌連咖啡則從2019年起開始收縮戰線,接連關店,2020年9月,連咖啡放下咖啡館業務,轉型為零售市場的咖啡品牌。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一點,“咖啡陪你”、Zoo Coffee等一系列韓系咖啡的折戟也證明了,中國的咖啡市場沒有想象中那么好啃。
(應受訪者要求,小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