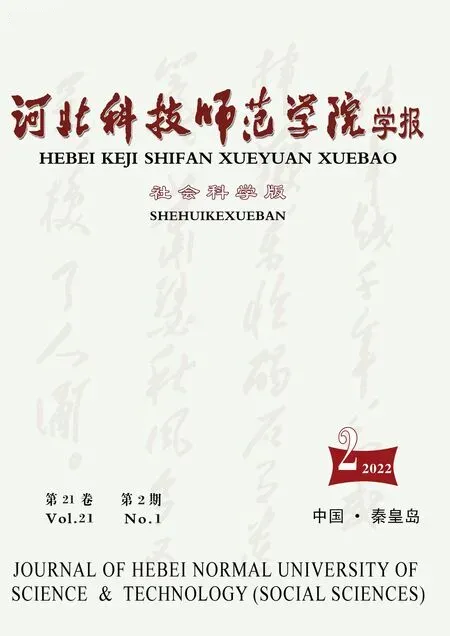《百越先賢志校注》疑誤商榷
李麗紅
(暨南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百越先賢志》一書,共四卷,由明代廣東順德學者歐大任所撰。歐大任根據《國語》《越絕書》《吳越春秋》《會稽典錄》《交廣記》《史記》《漢書》《后漢書》等82種史籍,進行百越地區人物史事編纂,其中共錄正傳105人,附傳30人,計135人。黃佐修《廣東新志》中漢以前之人物小傳,皆采是書。清道光、光緒間廣東南海人伍元薇(后名崇曜)立志輯理鄉邦文獻,廣收明清年間粵境著名學者力作,于道光同治年間以“南海伍氏粵雅堂文字歡娛室”之名刊行,稱為《嶺南遺書》。《百越先賢志》收入第一集中[1]。《百越先賢志校注》[2](為求行文簡潔,下稱《校注》)便據文字歡娛室《嶺南遺書》本為底本而進行校注。《百越先賢志校注》由劉漢東校注、孫順霞、孔繁士合校,1993年8月由廣西人民出版社行世,給人們的閱讀和研究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在通讀過程中亦發現書中的校勘、標點尚可進一步斟酌。今將可商榷部分分為若干類, 加以辨析,不當之處, 祈使指正。
一、字
根據底本對《校注》進行閱讀時發現在文字方面有誤字、漏字、增字三種情況。
(一)誤字
(1)歐冶子,越人,與吳人干將國師,俱能為劍。(《歐冶子》)
按:《校注》中“國”應為“同”。“同師”,《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即指歐冶子與干將師出同門,都是當時善于鑄劍的名師。
(2)邦家富有備器,八。(《大夫種》)
按:《校注》中“有”應為“而”。《越絕書》卷十二內經九術第十四:“八曰邦家富而備器”。“而”應為連詞,在此處表遞進。《校注》誤把“而”作“有”,形近而誤。
(3)巨聞王自耕。(《計倪》)
按:《校注》中“巨”應為“臣”。結合上文可知這句話出現在計倪回答趙王的對話中:計倪曰:“省賦歛,勸農桑,因熟積以備四方。毋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臣聞王自耕,夫人自織,此竭于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于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因此,“臣”是計倪在回話時的自稱。
(4)客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舉乎?(《薛燭》)
按:《校注》中“舉”應為“與”。與,意為給予,如《周禮·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鄭玄注引鄭司農云:“與謂予人物也。”
(5)祿仕秦,以史臨郡。《史祿》
按:《校注》中“臨”應為“監”。“監郡”指監察郡縣之官。《漢書·百官公卿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臨”“監”兩字應是形近而誤。
(6)粵桂林監居翁諭下甌路四十余萬為湘城侯。(《畢取》)
按:《校注》中“路”應為“駱”,“甌駱”,是西漢前期對嶺南越人即壯族先人的稱謂。據楊凌考證,先秦兩漢之所以用漢字“駱”命名交趾、九真之民,緣于駱人項髻的風俗。《說文》:“駱,白馬黑鬣尾也。”《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項髻徒跣。”李賢以項髻釋曰:“為髻于項上也。”《漢書·賈揖之傳》:“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由于駱越為髻于項后,裸身浴水,在漢人眼里乍看起來,白凈的身體和脖頸后邊烏黑的發髻猶如黑鬣的白馬。因此,漢人就以表示白馬黑鬣之意的漢字“駱”隱喻交趾之人[3]。
(7)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寫壘城,鎮撫諸國。(《鄭吉》)
按:《校注》中“寫”應為“烏”。烏壘城,地名,漢西域都護府治地,遺址大致應該位于今輪臺縣野云溝鄉稍偏西南的綠洲地帶[4]。
(8)梅福,字九真,九江壽春人也。(《梅福》)
按:《校注》中“九”應為“子”。《漢書·楊胡朱梅云傳》:“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
(9)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者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嚴光》)
按:《校注》中“者”應為“著”。著,意為建立,《禮記·樂記》:“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鄭玄注:“著,猶立也。”“著德”與“洗耳”相對成文。
(10)春夏則予恵,布施剛仁。(《養奮》)
按:《校注》中“剛”應為“寬”。寬仁,意為寬厚仁慈,如《漢書·韓王信傳》:“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后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同樣的內容也見于明林富、黃佐修《廣西通志》卷四十四:“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
(11)時彭城相左尚以贓獲罪,三府掾屬拷驗,踰年不竟,更選盛復拷。(《鄧盛》)
按:《校注》中“復”應為“覆”。覆,意為重復,《后漢書·班固傳下》:“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后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李賢注:“覆,猶重也。”同樣的內容也見于明林富、黃佐《廣西通志》卷一:“時彭城相左尚以贓獲罪,三府掾屬拷驗,踰年不竟,更選盛覆拷。”
(12)楊扶,字圣儀,會稽寫傷人,其先河東人也。(《楊扶》)
按:《校注》誤把“烏”作“寫”字。烏傷,古縣名。秦置。漢屬會稽郡。《宋書》卷三十五州郡志一:“長山令,漢獻帝初平二年分烏傷立。”
(13)猛善于其識,動無違禮。(《招猛》)
按:《校注》誤把“職”作“識”。職,意為職責。形近而誤。
(14)人覲者至容臺肄儀行事。(《招猛》)
按:《校注》中“人”應為“入”。“入覲”指諸侯或地方官員入朝進見帝王。形近而誤。
(15)命其妻侍獄中,后產一子。(《陳臨》)
(16)栩去官,蝗即日至,刺史媿謝,命還邑,蝗即去。(《徐栩》)
按:《校注》中此兩條中“命”應為“令”。兩字形近而誤。
(17)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詣共廬,疇咨理道。(《董正》)
按:《校注》中“共”應為“其”字,“其”代指董正。
(18)喜平末,張角袁術起難。(《董正》)
按:《校注》中“喜”應為“熹”,“熹平”是東漢靈帝年號。形近而誤。
(19)天挺俊父,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徐穉》)
按:《校注》中“父”應為“乂”,意為“才德出眾”。《書·皋陶謨》:“俊乂在官。”孔穎達疏:“乂訓為治,故云治能。”形近而誤。
(20)彌陵隔岨,巒阜錯連,隅輒壅遏,末由騁焉。(《郭蒼》)
按:《校注》中“輒”應為“陬”,隅陬,角落。《廣雅·釋詁》:“隅陬,角也。”形近而誤。
(21)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孫辰,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盛憲》)
按:《校注》中“辰”應為“氏”,“孫氏”即指孫策,前文提到“憲遷吳郡太守,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故孔融因擔心盛憲的處境而給曹操推薦盛憲,由此寫道“其人困于孫氏”,即指盛憲受困于孫策。
(22)而身不免于幽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當論損益之長。(《盛憲》)
按:《校注》中“長”應為“友”。這句話也源于孔融給曹操寫的信中,其中“吾祖”指孔子,孔融為孔子的二十世孫。“損益之友”出自孔子所說的“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這是說盛憲如此危險,無一友援手。
(23)汝并黃中通爽,終成竒器,向遽踰制,自取滅性耶?(《沉瑜》)
按:《校注》中“向”應為“何”,“何”與后面的耶構成疑問句式。
(24)吳刺史陸胤苦南海水咸,導泉為甘溪,寢后湮。(《姚成甫》)
(25)成甫復浚之。(《姚成甫》)

(26)曾祖放為廣州刺史,留一子居擎雷水上。(《阮謙之》)
按:《校注》中“廣”應為“交”。交州,原稱交阯,又作交趾,《禮記·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范圍大致相當于今天中國的廣西、廣東和越南的中北部一帶。東漢獻帝“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阯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交州之名始定[5]。
(27)賜其鄉日錦衣。(《莫宣卿》)
按:《校注》中“日”應為“曰”,結合上文是指朝廷賜其鄉名曰“錦衣”。形近而誤。
(二)漏字
(1)且舉咸陽而棄,何但越!(《嚴助》)
按:《校注》中“且”后漏了句子主語“秦”字。應為“且秦舉咸陽而棄,何但越”。此處結合《漢書》《史記》可知,在閩越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于漢的時候,田蚡認為越人相攻是常事,且在秦代已放棄閩越地,而嚴助則反駁道:“秦連咸陽都能放棄,何況越地。”由此指出不能學習秦代的行為。故雖然古人對話中主語經常可以省略,但此處“秦”作為一個被強調的主語,不應被省略。
(2)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刺史行部見昌奇之,辟從事。拜宛令。(《黃昌》)
按:《校注》漏“后”字,應為“后拜宛令”。所據底本即清道光同治間南海伍氏粵雅堂文字歡娛室刻本中作:“後拜宛令”。
(3)征上念明政,據刑申恥,今不使治郡,便無爪牙吏。(《徐征》)
按:《校注》于“爪牙”之后缺“之”字,應為“爪牙之吏”。“爪牙”常常用來譬喻輔弼之臣, 如《詩·小雅·祈父》 : “祈父, 予王之爪牙”, 鄭玄箋 : “此勇力之士也。”《左傳·成公十二年》: “略其武夫, 以為己腹心股膿爪牙。”《荀子·富國》:“彼愛其爪牙, 畏其仇亂。”因此“爪牙之吏”可以理解為得力的輔弼臣吏。所據底本即清道光同治間南海伍氏粵雅堂文字歡娛室刻本中作:“徴上念明政,據刑申恥,今不使治郡,便無爪牙之吏。”
(4)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風采,訪求世族。(《董正》)
按:《校注》中“訪求世族”前面漏“乃”字,應為“乃訪求世族”。所據底本即清道光同治間南海伍氏粵雅堂文字歡娛室刻本中作:“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風采,乃訪求世族”。
(5)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弘矣。(《盛憲》)
按:《校注》中“弘”前漏“可”字,應為“友道可弘矣”,與前文“孝章可致”相對應。所據底本即清道光同治間南海伍氏粵雅堂文字歡娛室刻本中作:“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三)增字
(許荊)嘗行來春,來陽蔣均兄弟爭財。(《許荊》)
按:《校注》在“行”后誤增“來”字。據《后漢書·鄭弘傳》載:“太守第五倫行春。見(鄭弘)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李賢注“行春”曰:“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故“行春”謂官吏春日出巡。
二、標點
(一)因詞義不明而標點錯誤
(1)越王又有客秦伊,善灼龜,戰必得龜,食乃陣。(《陳音》)
按:應為“戰必得龜食,乃陣”。《尚書·洛誥》:“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安國傳:“卜必先墨畫龜,然后灼之,兆順食墨。”即占卜先用墨水畫龜紋,之后燒灼龜甲,當龜甲所形成的裂痕與所畫的龜紋相吻合,則為吉利。因此把這一占卜方式稱為“龜兆食墨”,即“龜食”。校注因不明此義,把“食”理解為“食用”,將“龜”與“食”分開而誤。
(2)時魯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高固》)
按:“史記”本指記載歷史的書,如《尚書序》:“約史記而修《春秋》。”張守節《史記正義》:“諸國皆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后用以專稱《太史公書》,遂成為書名。因此,《史記》特指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
而原文“孔子史記”不應當加書名號,據姚曼波考證,“孔子史記”是有著“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史實、“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另一部《春秋》,是左丘明據以“具論其語”而成《左傳》的藍本[6]。故原文“史記”意為記載歷史的書,《校注》誤為“孔子《史記》”。
(3)(衛太子)及即位,為《石渠論》而《谷梁》氏興,至今與《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陳元》)
按:應是“為石渠論而《谷梁氏》興”。根據《漢書·藝文志》:“議奏四十二篇”,班固自注云:“宣帝時石渠論。”韋昭曰:“閣名也,于此論書。”《漢書·楚元王傳》:“會初立《谷梁春秋》,征更生受《谷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由此可知“石渠”是一個藏秘書的地方,儒生也在此處講經,在未央殿北。因此,原文意思是讓儒者在石渠這個地方討論而使《谷梁氏》興起。
(4)囂與紀伯為隣,伯竊囂藩地自益,囂不校益,徙地與之。(《陳囂》)
按:應為“囂不校,益徙地與之”;此處的“校”應作“計較”解,“益”為“更加、進一步”。在宋代鄭玉道的《琴堂諭俗編》中記載為:“囂見之,伺伯去后,密援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以及宋代王十鵬《會稽三賦·風俗賦》中提到“陳子公退侵墜之藩”,明南逢吉注云:“會稽陳囂,字子公……囂見之不言,移一丈以潤紀伯。”從這些不同的記載看,《校注》都應該句讀為“益徙地與之”,即陳囂遷移更多土地給紀伯。
(5)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正,舉事,干逆天氣。(《養奮》)
按:應是“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正舉事,干逆天氣”。“正”“政”常互相假借,如后漢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設想視者為不了,為如余道人不信薩蕓若。何以故?反謂有身,正使余道人信佛。”而在圣本《道行般若經》中“正”作“政”。“新詞因詞義引申而派生后,便孳乳出相應的新字,即孳乳字。孳乳字已經承擔了發源字分化出的新義,與發源字有了明確的分工,但由于長期的習慣,在孳乳字尚未被完全習用的過渡階段,仍有與源字通用的情況。如‘風’與‘諷’通用,‘正’與‘政’通用等。”[7]因此,原文中“為正舉事”應該是“為政舉事”,意為“處理政事,處理事情”。
(6)友尉馬日磾,嘉其行,履服竟即辟之。(《鄧盛》)
按:應是“友尉馬日磾嘉其行履,服竟即辟之”,“行履”是行為的意思,如梁沈約《宋書·周朗沈懷文列傳》:“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跡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一:“僧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以上書例都可證“行履”即行為。而“服”則指“服喪期”。所以整個句子應理解為:朋友馬日磾欣賞贊揚鄧盛的作為,在鄧盛服喪期結束之后征辟其為官。
(7)儁羸服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免死輸作。(《朱儁》)
按:輸作,指因犯罪罰作勞役,東漢謂罰作為“輸作”,《后漢書·和帝紀》:“永元元年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亦稱“輸”。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刑制總考二》:“輸作,蓋罰作之別,其但曰輸者,省文也。”因此,應斷為“免死,輸作”,意思為“免除了死刑,而被罰作勞役”。
(8)商賈湊集,貿遷易以致富。(《董正》)
按:湊集,指“聚集、會集”,如明袁宏道 《與伯修書》:“東西南北名士湊集者,不下十余人,朝夕命吳兒度曲佐酒。”貿遷,指“販運買賣”,如漢荀悅《申鑒·時事》:“貿遷有無,周而通之。”因此該句應理解為商賈聚集起來販運買賣,通過貨物交易來致富,標點應該斷為:商賈湊集貿遷,易以致富。
(9)舉孝亷,拜尚書郎,遷汝南、固始相。(《郭蒼》)
按:“汝南固始”為一個地方。《淮南子》:“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丑。”許慎注:“寢丘,今汝南固始也,前有垢谷,,后有(莊)丘,名丑。”因此,原文意思應為到該地方當太守。應當斷為:舉孝亷,拜尚書郎,遷汝南固始相。
(10)事聞天子,奇其才,因赦不問。(《尹牙》)
按:應為“事聞,天子奇其才,因赦不問”。此處“聞”意思應為“傳布、傳揚”,天子對尹牙的才能感到驚奇而赦免他的過錯。
(11)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姚文式》)
按:句子應斷為“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據吳壯達研究,“水坑陵”可理解為古人從一種小地區水陸分布關系特點提出的地貌名詞,指的應是多面臨水, 或被水所環繞的一片高阜地區[8]。既然是“陵”, 就不會是很高峻的地勢; 既然用“水坑”, 則不會是遼闊的水面 (后者是從粵人對“坑”的慣用詞義) 。“水沉陵”可以作為一般被水所環抱的高地來理解。因此,“水坑”和“陵”不當斷開。
(12)汜對曰:“明公上安宗廟,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虞翻》)
按:伊,商朝大臣,幫助湯攻滅夏桀。商湯三聘之后,輔助商湯打敗夏桀,為商朝的建立做出不朽功勛。湯去世后,伊歷佐卜丙、仲壬二王;霍,即霍叔,周代霍國的始祖,西周周文王之子,武王同母弟。時周武王因武庚還未心悅誠服,恐怕其有異心,便讓霍叔處和管叔鮮、蔡叔度協助監督武庚,一起治理商朝遺民。伊尹和霍叔處都為治國的能臣,虞汜以伊、霍二人勸勉孫綝。因此,原文當斷為:明公上安宗廟,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
(二)因不明語法而標點出錯
(1)風胡子奏之楚王,見而大悅。(《歐冶子》)
按:應為“風胡子奏之,楚王見而大悅”。“之”在這里是指代事情的代詞,而非介詞。若為介詞,則后面“見而大悅”句子成分不完整,缺少主語。
(2)知此二者,形于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計倪》)
按:應為“知此二者,形于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前文提到“時斷則循,智斷則備”,因此二者就是“時斷”與“智斷”,句子意思為:只有懂得了“時斷”與“智斷”就可根據世間萬物的形狀來體察它們的情性。因此,不應該把“體”與“萬物之情”斷開,“體”為動詞而非名詞。
(3)至于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回背無定所,謂日域在南者也。(《張重》)
按:應為“回背無定,所謂日域在南者也”。所謂,即“所說的”,在句子開頭常用于復說、引證等。如《禮記·大學》:“欲脩其身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在這個句子中同樣用于復說前面所提到的與“日域在南者”相關的內容。
(4)百姓困乏而不恤眾,怨欝積,故陰陽不和。(《養奮》)
按:應是“百姓困乏而不恤,眾怨欝積,故陰陽不和”。此處“眾”即是前面所指的百姓,作后面分句的主語。
(三)因不明文意而出錯
(1)祿乃自陽山,道水源以湘水,北流入于楚瀜江;為牂牁下流,南入于海,轉餉為勞。(《史祿》)
按:應為“祿乃自陽山道水源,以湘水北流入于楚,瀜江為牂牁下流,南入于海,轉餉為勞”。《漢書·溝洫志》:“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 顏師古注:“從積石山而治引之令通流也。道,讀曰導。”此處的“道”同樣理解為“疏導”,句子即為“史祿從陽山疏導水源,讓湘水往北流入于楚地”。
此外,根據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廣西水經》:“凡廣西諸水,無不自蠻夷中來。靜江水曰漓水,其源雖自湘水來,然湘本北行,秦史祿決為支渠,南注之融江,而融江實自傜峒來。……融州之水,牂牁江是也,其源自西南夷中來。”“融江”即“瀜江”,由此可知“瀜江”為廣西境內的水源,其源自傜峒,而在《百越先賢志》中歐大任提到“瀜江“是“牂牁下流”,這是誤把源自牂牁江的融州之水與瀜江相混淆。
(2)創造用武,守業尚文,故周勝殷則有載戢干戈之頌。(《楊孚》)
按:句子應為:創造用武,守業尚文,故周勝殷,則有“載戢干戈”之頌。“載戢干戈”語出《詩·周頌·時邁》:“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意思為國家安定繁榮,可以把兵器都收藏起來而不再用兵。在《百越先賢志》中是用來贊揚周能發展文武,所以勝過殷,因此有“載戢干戈”的贊頌。
(3)初平四年為太尉錄尚書事,以日食策免。(《朱儁》)
按:應為“初平四年為太尉,錄尚書事,以日食策免”。《后漢書·朱儁列傳》載此事云:“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此處“錄”為“統領、管領”的意思,因此原文意思應為:朱儁代周忠成為太尉,統領尚書事務,“為”是“成為”的意思。而《校注》則理解為朱儁替太尉處理尚書的事情,這就把“為”理解成介詞“替,給”。
(4)遷江夏太守,徐州牧。齊中書令邵,其后也。(《賀純》)
按:歷史上賀純并無做過徐州牧。晉虞預《會稽典錄·存疑》提到:案《姓篆》云:“后漢慶儀,為汝陰令慶普之后也。曾孫純,避漢安帝父諱,始改賀氏。孫齊,吳大將軍。齊孫中書令邵。”由此可知,“齊”即賀純的孫子賀齊,為徐州牧,“邵”則是賀齊的孫子,為中書令賀邵。
且校注本漏“皆”字,句子意思應是指“徐州牧齊”和“中書令邵”這兩個人是賀純的后代。句子應當斷為:遷江夏太守。徐州牧齊、中書令邵,皆其后也。
(5)及還,余姚雁亦隨歸國。卒,雁棲墓側不去。(《虞國》)
按:前文提到虞國為余姚人,因此句意應為“虞國回到余姚,雁亦隨之”。所以該句當斷為:“及還余姚,雁亦隨歸”。后面應是“國卒,雁棲墓側不去”,指虞國去世后,雁在虞國墓旁不離開,因此“國”“卒”不當斷開,否則就誤解了原文句意。
(6)(黃豪)弱冠,詣交趾部。刺史舉茂才,因寓廣信,教授生徒。及征至京師,除外黃令。(《黃豪》)
按:應為“(黃豪)弱冠詣交趾部刺史,舉茂才,因寓廣信,教授生徒,及征至京師,除外黃令”。詣,應為造訪之意。“茂才”即“秀才”,時因避漢光武帝名諱,改秀為茂。同時根據明郭棐、王學曾纂《廣東通志》:“元封五年初,置交趾部刺史,領七郡,治廣信。……別于諸州,令持節治蒼梧。”清戴肇辰修、史澄纂《廣州府志》:“弱冠詣交趾部刺史,舉茂才,因授徒廣信,征至京師,除外黃令。”句子應理解為黃豪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到了交趾部刺史,征舉茂才,因黃豪在廣信,教授生徒,后來征至京師,成為外黃令。
(7)(莫宣卿)一日與群兒戲題詩有云。(《莫宣卿》)
按:明郭棐、王學曾纂《廣東通志》記載相應的內容為“(莫宣卿)與群兒戲沙中,題詩云”。由此可知記載的內容意思為“小時候的莫宣卿與小伙伴們在沙中玩耍的時候,寫了一首詩”。因此,應斷為:一日與群兒戲,題詩有云。
三、注解
(一)應注解而未注解
(1)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師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黃昌》)
按:《百越先賢志》中的“師”應為“帥”,兩字形近而誤。盜帥,盜匪首領。其他文獻記載黃昌捕盜帥一事,如宋鄭克《折獄龜鑒·察盜》:“若后漢黃昌為蜀郡太守,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陳諸縣強暴姓名居處。”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四十七宦游記一:“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明胡中憲《浙江通志》卷三十六人物志六之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疆暴之人姓名居處。”清張玉書、陳廷敬《佩文韻府》卷九十九上:“捕盜帥一人,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其中均寫作“盜帥”而非“盜師”,作“盜匪首領”義。
另,《校注》把“帥”字誤作“沖”字,即把“盜帥”寫作“盜沖”,更加偏離原意。
(2)澹臺敬伯,會稽人,受《韋氏詩》于淮陽薛漢。(《澹臺敬伯》)
按:《漢書·儒林傳》:“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由是《魯詩》有韋氏學。”因此《百越先賢志》中的《韋氏詩》當指《魯詩》。而在文獻中可發現薛漢及弟子澹臺敬伯所習應為《韓詩》,如漢韓嬰《韓詩外傳》:“余聞后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后漢書·儒林列傳》:“(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明王圻《續文獻通考》:“薛漢召馴澹臺敬伯為《韓詩》。”而僅在《百越先賢志》中提到薛漢及澹臺敬伯受《韋氏詩》,則歐大任所言應為誤記。
(3)元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于家。(《陳元》)
按:《百越先賢志》的成書是依據《后漢書》等史籍進行百越地區人物史事編纂,而引文在《后漢書》里原句為“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百越先賢志》“當世”后缺“便”字。“便事”意思為“利國之事”,如《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敬勞從者,愿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后漢書·崔寔傳》:“(崔寔)明于政體,吏才有余,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因此,“當世便事”即當今利國之事。“當世事”理解為當時的世事,與原意不符。
(二)注解有誤
(1)鄭宏 (《鄭宏》)/冬寒徒病,過宏農。(《鐘離意》)
按:《校注》中稱“‘宏’‘弘’互為通假字”。
歷史上“鄭宏”本應為“鄭弘”,《百越先賢志》中寫作“鄭宏”。地名“宏農”本應為“弘農”。人名、地名等一般不使用假借字替代。“通假字主要發生于一般的語詞,而音訛主要發生于姓氏、人名、地名、國名、族名、官職、稱謂等非語詞性的名詞。”[9]因此,“宏”與“弘”在人名、地名的使用上相互通假的這一說法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2)脩排闥入拜于庭。(《彭脩》)
按:校注中于“排闥”處注云:“應為排閣”。
其實“排闥”與“排閣”義同,意思都為“推門”,因此無需注為“排閣”。《說文·門部》:“闥,門也。”《漢書·樊噲傳》:“十馀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顏師古注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土曷反。”宋李昉《太平廣記·騾鞭客》:“時講筵初合,有一人排闥叫呼。”《宋史》卷四百五十八隱逸傳中:“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五十一日用器物類三:“滄州李巡官子,夜讀書,有皁衣肥短人,被酒排闥而入曰:‘李白尚與我友。’”以上書例中“排闥”均為“推門”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