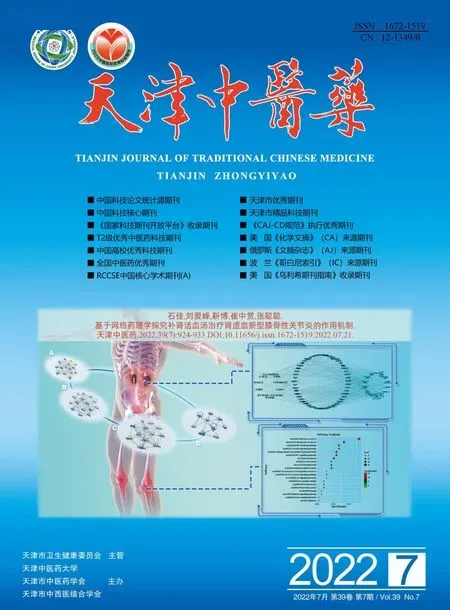痛風膠囊對非急性期痛風患者臨床觀察*
韓德軍,劉湘玲,姚方,楊玉超,王睿
(1.天津中醫(y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老年病科,天津 300381;2.國家中醫(yī)針灸臨床醫(yī)學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痛風是一種臨床常見的關節(jié)炎,是由血清尿酸超過其在血液或組織液的飽和度,形成尿酸鈉晶體沉積在關節(jié)和軟組織中引發(fā)炎癥反應,其臨床表現(xiàn)是一個或多個關節(jié)反復出現(xiàn)疼痛癥狀。目前全球發(fā)病率逐年升高[1]。2013年中國痛風患病率男性約為0.83%~1.98%,女性約為 0.07%~0.72%,較以前明顯上升[2]。2015年Meta分析顯示中國痛風的患病率為1.1%[3],成為另一種常見的代謝性疾病。高尿酸血癥是痛風發(fā)生的重要生化基礎[4],因此降尿酸治療(ULT)可以降低血清尿酸濃度,并將其維持在非飽和水平,以逆轉(zhuǎn)晶體沉淀,是治療痛風的關鍵[5-7]。然而,啟動長期ULT之初,由于血尿酸水平波動引起關節(jié)腔內(nèi)外痛風石或尿酸結晶溶解,導致痛風患者痛風性關節(jié)炎急性或反復發(fā)作[4,8]。有人認為,在ULT啟動過程中急性痛風的發(fā)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ULT的低依從性,從而導致較差的結果[9-10]。建議使用非甾體抗炎藥、秋水仙堿或糖皮質(zhì)激素,以預防痛風發(fā)作[4]。一項研究表明,多達90%的痛風患者可能至少有一種非甾體抗炎藥的禁忌癥,40%的患者對秋水仙堿有強烈的禁忌癥[11]。預防痛風發(fā)作抗炎藥物一定程度的毒副作用及耐藥性,往往給治療帶來很大困難。因此,對有效的、耐受性良好的預防痛風療法的需求尚未得到滿足。痛風膠囊是2000年由天津市名中醫(yī)曹克光教授帶領痛風研究課題組自主研發(fā)的,結合多年的臨床經(jīng)驗,從“濁毒瘀滯”為痛風病病機立說,以“清熱利濕解毒,活血化瘀止痛”為法,創(chuàng)立痛風合劑,后為方便患者保存及長期服用,劑型調(diào)整為膠囊。研究表明“痛風合劑”有明確的降低痛風患者血尿酸(BUA)作用,可緩解急性痛風性關節(jié)炎的臨床癥狀,防止其反復發(fā)作[12]。本研究觀察痛風膠囊干預非急性期痛風(濕熱瘀毒型)患者的臨床療效與安全性。本研究得到天津中醫(y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的同意,倫理批件號為TYLL2018[K]字001。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來源 本課題于2018年1月—2020年9月在天津中醫(y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老年病科門診納入符合本研究標準的臨床受試者60例。使用SPSS 26.0軟件生成隨機數(shù)字表,然后將受試者隨機分為中西藥組和西藥組各30例。
1.2 納入標準 1)符合2015年ACR/EULAR痛風分類標準。2)符合典型的急性痛風性關節(jié)炎≥發(fā)作2次/年或有痛風石≥1處的非急性期患者。3)BUA≥480 mmol/L。4)符合中醫(yī)辨證濕熱瘀毒型:主癥為關節(jié)活動受限,關節(jié)局部皮膚暗紫、結節(jié),關節(jié)腫脹;次癥為發(fā)熱口渴,心煩不安,唇色暗,小便黃;舌脈為舌質(zhì)紅、苔黃膩或苔黃厚,或舌質(zhì)紫暗或有瘀斑、苔膩,脈滑數(shù)或脈沉細澀或沉滑。以上主癥必須具備1項,次癥具備2項及以上參考舌脈即可診斷。5)年齡范圍在18~65歲者。6)患者自愿參加且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排除標準 1)由類風濕性關節(jié)炎、假性痛風等疾病引起的關節(jié)病變。2)由腎功能不全、腫瘤放化療、藥物等所致的繼發(fā)痛風。3)妊娠期、哺乳期婦女。4)嚴重的心、肺、血液系統(tǒng)、肝、腎病變,或影響其生存的嚴重疾病。5)懷疑有酒精、藥物濫用史,或某些原因經(jīng)常變動易造成失訪者。
1.4 研究方法 1)中西藥組和西藥組受試對象均接受相同的常規(guī)干預:①飲食:禁煙酒、軟飲料,低嘌呤飲食嘌呤含量<75 mg/100 g;②基礎治療:碳酸氫鈉,每次 100 mg,每日 3次,pH<6.0時使用,保持 pH 在6.5~6.8,尿量每日>2 000 mL,患者痛風急性發(fā)作不能控制時,應給予依托考昔片,60mg,每日1次;③保持生活規(guī)律。2)試驗用藥:試驗藥物:痛風膠囊[院內(nèi)制劑,批準文號:津藥制字(2003)Z第0814號,天津中醫(y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藥廠生產(chǎn)];②對照藥物:別嘌醇片(國藥準字H50020455,重慶昌野制藥有限公司)。3)試驗藥物治療:中西藥組:痛風膠囊,每次3粒,每日2次;別嘌醇片,每日每次0.1 g。西藥組:別嘌醇片,每日每次0.1 g。8周為1個療程。
1.5 有效性及安全性評價 1)有效性指標的測定:療效指標包括中醫(yī)證候、BUA變化、痛風性關節(jié)炎急性發(fā)作次數(shù)、膽固醇(CHO)、三酰甘油(TG)、血糖(GLU)。2)安全性實驗室指標:一般體檢項目[體溫(T)、脈搏(P)、呼吸(R)、血壓(BP)];肝功能[谷草轉(zhuǎn)氨酶(AST)、谷丙轉(zhuǎn)氨酶(ALT)];腎功能[尿素氮(BUN)、肌酐(Cr)]。
1.6 統(tǒng)計學方法 應用SPSS26.0軟件包進行統(tǒng)計分析,符合正態(tài)分布及方差齊性的計量資料以均數(shù)±標準差(±s)表示;治療前后采用配對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tài)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shù)、最小值和最大值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shù)檢驗。計數(shù)資料采用構成比或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研究結果
2.1 病例脫落情況 依據(jù)納排標準,每組納入30例。在試驗過程中,中西藥組自動退出2例、失訪2例,西藥組自動退出1例、失訪3例,最終兩組均有26例完成本臨床研究。
2.2 試驗前兩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 從表1可以看出,治療前中西藥組和西藥組在年齡、病程、身高、體質(zhì)量、體重指數(shù)(BMI)、血脂、血糖、肝腎功能的比較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說明中西藥組與西藥兩組的非急性期痛風患者(濕熱瘀毒型)在治療前沒有明顯的差異,具有可比性。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的比較(±s)Tab.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的比較(±s)Tab.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組別 例數(shù) 病史(年)年齡(歲)身高(cm)體質(zhì)量(kg)BMI(kg/m2)TC(mmol/L)TG(mmol/L)GLU(mmol/L)ALT(U/L)AST(U/L)BUN(mmol/L)Cr(umol/L)西藥組中西藥組26 26 5.96±2.73 43.77±14.83 172.42±4.12 5.65±2.78 44.23±12.82 175.04±5.93 83.46±14.17 85.62±11.82 27.95±3.55 27.92±3.52 5.00±0.89 5.04±0.85 2.51±1.46 2.74±1.68 5.63±0.45 5.75±1.04 30.93±14.84 33.33±16.30 22.93±6.28 5.11±1.85 85.95±16.96 22.99±8.65 5.15±1.22 83.92±11.87
2.3 兩組治療后中醫(yī)證候積分及變化的比較 從表2可以看出,治療前兩組中醫(yī)證候積分比較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治療后兩組的中醫(yī)證候積分均較治療前下降,且均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組間比較中西藥組證候積分優(yōu)于西藥組(P<0.05),兩組積分差值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說明兩組均對患者中醫(yī)證候有改善,中西藥組改善中醫(yī)證候的療效明顯優(yōu)于西藥組。
表2 2組治療前后中醫(yī)證候總積分比較(±s)Tab.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分

表2 2組治療前后中醫(yī)證候總積分比較(±s)Tab.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計較,*P<0.05,與西藥組治療后比較,#P<0.05。
組別 中醫(yī)證候積分 前后證候積分差西藥組 7.54±2.14 2.54±1.72例數(shù)26時間節(jié)點治療前治療后中西藥組 26 治療前 7.27±2.05 3.54±1.63#治療后 3.73±2.13*#5.00±2.10*
2.4 兩組治療后BUA及變化的比較 從表3可以看出,治療前中西藥組與西藥兩組的BUA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治療后兩組的BUA較治療前均下降,且均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組間比較中西藥組BUA降低并未優(yōu)于西藥組,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但兩組 BUA 差值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說明中西藥組在降尿酸方面的療效優(yōu)于西藥組。
表3 兩組治療前后尿酸比較(±s)Tab.3 Comparison of uric aci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μmol/L

表3 兩組治療前后尿酸比較(±s)Tab.3 Comparison of uric aci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μmol/L
注:與本組治療前計較,*P<0.05,與西藥組治療后比較,#P<0.05。
組別 BUA(μmol/L) 前后BUA差西藥組 549.80± 64.84 101.33±103.78例數(shù)26時間節(jié)點治療前治療后中西藥組 26 治療前 562.09± 57.85 166.38±100.68#治療后 395.72±103.12*448.47±107.79*
2.5 兩組急性痛風發(fā)作次數(shù)的比較 從表4可以看出,治療過程中在急性痛風性關節(jié)炎發(fā)作次數(shù)方面,中西藥組較西藥組次數(shù)減少,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表4 兩組急性痛風發(fā)作次數(shù)比較(±s)Tab.4 Comparison of acute gout attack frequ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次

表4 兩組急性痛風發(fā)作次數(shù)比較(±s)Tab.4 Comparison of acute gout attack frequ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次
注:與西藥組比較,*P<0.05。
例數(shù)西藥組 0 0.54±0.65組別 最小值 急性痛風發(fā)作次數(shù)最大值26中西藥組 26 2 0 0.19±0.42*3
2.6 兩組其他代謝指標的比較 從表5可以看出,兩組病例治療后總膽固醇(TC)、TG、GLU及且組間比較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表5 兩組治療后其他代謝指標比較(±s)Tab.5 Comparison of other metabolic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s)mmol/L

表5 兩組治療后其他代謝指標比較(±s)Tab.5 Comparison of other metabolic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s)mmol/L
指標 例數(shù)TC TG GLU西藥組 26中西藥組 26 4.81±0.83 2.28±1.26 5.58±0.79 4.96±0.82 2.8±1.46 5.45±0.49
2.7 兩組安全性指標比較 從表6可以看出,在臨床試驗過程中,尚未觀察到兩組病例有嚴重不良反應或不良事件。ALT、AST、BUN、Cr檢測值在兩組治療前后及組間比較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表6 兩組治療后肝腎功能比較(±s)Tab.6 Comparison of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s)

表6 兩組治療后肝腎功能比較(±s)Tab.6 Comparison of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s)
指標ALT(U/L)AST(U/L)BUN(mmol/L)Cr(μmol/L)中西藥組 27.31±12.66 20.88±5.98 5.08±1.35 82.24±12.68西藥組 31.41±15.66 22.14±5.90 5.13±1.65 86.35±16.59
3 討論
重視非急性期痛風患者的治療是中醫(yī)“緩則治本”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是控制本病進展并使之逆轉(zhuǎn)的關鍵。中醫(yī)認為痛風的發(fā)病多與“內(nèi)濕”邪有關。朱良春[13]、路志正[14]和胡玉靈[15]多位專家認為痛風的發(fā)生與脾腎關系密切,濕濁瘀滯內(nèi)阻為主要原因。由于脾胃失和,濕濁內(nèi)蘊,濁毒內(nèi)生;腎失開合,水濕內(nèi)停,釀生濁毒。濁毒沉積于體內(nèi),由外因觸發(fā),瘀痹于經(jīng)絡關節(jié)而成。因此,黏膩濕邪深蘊于內(nèi)是痛風反復發(fā)生、纏綿難愈的重要機制之一。由于本病為內(nèi)生濁毒之邪,外因誘發(fā)所致,與外感風寒濕熱之邪之痹病有所不同[16]。本病病機關鍵在濁毒,多挾痰、熱、瘀。本研究在以往工作成果的基礎上,探討痛風膠囊對非急性期痛風病(濕熱瘀毒型)患者的防治,從結果可以看出,痛風膠囊可以明顯改善濕熱瘀毒型患者的中醫(yī)證候,達到濕熱得清、瘀毒自除的目的。
痛風膠囊由土茯苓、萆薢、忍冬藤等藥物組成。土茯苓,解毒除濕,通利關節(jié)。《本草綱目》記載:“健脾胃,強筋骨,去風濕,利關節(jié),止泄瀉,治拘攣骨痛。”現(xiàn)代研究表明,土茯苓含有黃酮、鞣質(zhì)、生物堿等有效成分,抑制黃嘌呤氧化酶的活性,促進血尿酸排出體外,降低血尿酸水平,同時可通過抑制白介素(IL)-1β的分泌和下調(diào)NF-κBp65的表達等作用,減少炎癥因子及趨化因子的生成和炎性細胞浸潤,緩解急性痛風性關節(jié)炎炎癥反應[17-20]。萆薢,利濕祛濁;《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主腰背痛,強骨節(jié),風寒濕周痹。”單與土茯苓相配伍,加強祛風除濕,通絡止痛之功,為治療痛風的核心藥物之一。忍冬藤清熱解毒通絡,《本草綱目》:“治一切風濕氣及諸腫痛。”謝興文等[21]研究發(fā)現(xiàn)忍冬藤痛風顆粒能明顯降低模型大鼠BUA、關節(jié)軟組織基質(zhì)金屬蛋白酶3(MMP-3)和脂蛋白磷脂酶A2(LP-PLA2)的表達。周仲瑛[22]指出,凡藤蔓之屬,善于攀越纏繞,質(zhì)地堅韌,不但具有祛風除濕、行氣活血功效,更是通絡引經(jīng)之使藥佳品,用于痹證尤宜。因此,痛風膠囊具有清熱利濕解毒,活血化瘀止痛之功,同時降低BUA作用,抑制炎癥反應,緩解急性痛風性關節(jié)炎的臨床癥狀,預防反復發(fā)作。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西藥組及西藥組兩組均可降低BUA水平,但中西藥組在降尿酸方面的療效有一定的優(yōu)勢,說明痛風膠囊對降低BUA水平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在別嘌醇等降尿酸藥物的基礎上,有助于進一步降低BUA濃度。目前認為單核細胞對尿酸鈉晶體的吞噬和前炎性因子[IL-6、IL-8、IL-1β、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等]的釋放可能是痛風發(fā)作的始動因素[23]。單鈉尿酸鹽(MSU)誘發(fā)炎癥反應的免疫機制尚不清楚。中醫(yī)藥對非急性痛風患者在降尿酸過程中預防痛風復發(fā)的相關研究甚少。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急性痛風性關節(jié)炎發(fā)作次數(shù)方面,中西藥組較西藥組急性痛風發(fā)作次數(shù)減少,同時具有明顯差異。因此,痛風膠囊可以作為預防痛風發(fā)作抗炎藥物的替代用藥,預防患者急性痛風性關節(jié)炎的發(fā)作,從而避免出現(xiàn)抗炎藥物的毒副作用及耐藥性,提高患者依從性,為中醫(yī)藥對痛風病的防治提供臨床依據(jù)。
BUA升高與血脂紊亂、動脈粥樣硬化、腹型肥胖、高血壓、2型糖尿病等疾病密切相關[24-25]。本研究結果顯示痛風膠囊對痛風患者TC、TG、GLU無明顯影響。本研究的樣本量少,有待大樣本、長時間的進一步深入觀察。
4 結語
痛風病是一種可控的慢性疾病,需要長期甚至終身的藥物和生活方式等綜合干預。運用中醫(yī)藥治療能夠有效的防治痛風,使痛風患者不僅在降尿酸達標治療過程中減少西藥使用,降低西藥相關的不良反應,改善患者依從性;而且減少急性痛風性關節(jié)炎的發(fā)作,提高生活質(zhì)量,減輕患者的經(jīng)濟負擔。
問題及對展望:1)研究的樣本量較少。2)中藥干預的療程時間相對較短,最好應以3個月為1個療程、2~4個療程,能更好地觀察BUA水平變化和痛風復發(fā)的情況。未來需進一步完成多中心、隨機對照、雙盲臨床試驗,更好的探索中醫(yī)藥預防防治痛風發(fā)病及復發(fā)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