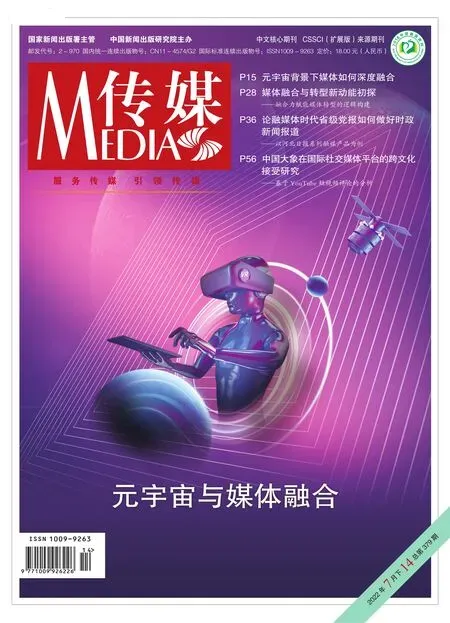《地久天長》中的空間設計與敘事構建
文/張瑩
巴贊(Bazan)在《電影是什么》一書中指出:“攝影機鏡頭讓我們擺脫對客體的偏見和習慣看法,清除了自我被蒙在客體上的精神銹斑,但唯有這般冷眼旁觀的鏡頭能夠吸引我的注意、還世界以純真的原貌,以此喚醒我的眷戀。”以王小帥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深受這種關于影像本體理論的影響,走出了第五代導演的“宏大敘事”模式。通常來講,他們喜歡將表現對象轉向底層小人物,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融入影片,讓觀眾在“時代真實”中進行審美體驗與反思社會。由王小帥執導上映的影片《地久天長》,以主人公劉耀軍一家的傷痕敘事為主題,借助城市空間記憶建構的方式再現了三十年間的社會變遷,完成了對社會變革中弱勢群體的回溯。電影中對城市形態的設計,讓觀眾在時代記憶里重新審視了影像中的生命價值和意義。這種影像創作理念與敘事方式對當下的社會問題反思及其影視劇創作都有著較好的借鑒意義。

一、空間意識與電影敘事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除了具有物理和精神空間的屬性外,還存在社會空間屬性。這一理念移植到電影創作時,空間結構可以理解成隱喻的象征,即導演希望通過電影中的空間塑造,將故事空間限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把人類的本能情感激發出來,最終促進故事發展以及矛盾的發生。《地久天長》的空間涉及南方漁港、北方筒子樓、工廠、醫院、舞廳等,在場景空間的選擇上有明確的地域性。關鍵性人物“星星”溺水之前主要以北方筒子樓的生活客廳為主,因計劃生育和下崗潮的出現,空間延伸至醫院和工廠。劇情中另外的戲劇沖突場景發生在漁村的房間內,室內設置了不同區間的門框,代表夫婦二人與養子“星星”之間的僵局與隔閡,一切都將在時代的蹉跎下不斷地隱忍、妥協。
王小帥電影的空間敘事特色主要體現在視聽語言中的鏡頭調度。在其電影中,長鏡頭的運用是其顯著特征,這一敘事方式能夠完整地展現一個事件或動作,并表現人物角色的內心情緒與狀態。《地久天長》秉承對空間的真實性把握,通過對長鏡頭的空間調度,細致地再現了獨生家庭的那種無奈與隱忍的生活狀態,從長鏡頭景深的控制,來強調特定的空間關系和推動故事發展。在電影的視聽語言中,聲音設計的加入和修飾為人物符碼的解構和影像“空間感”提供了表意真實。王小帥在電影中為避免由身體沖動產生的強烈視覺效果,特意選取聲音來營造出立體的影像畫面空間,這一視聽傳達技巧有效地營造了戲劇轉折,起到了延續畫面內在空間的戲劇效果。
二、人物塑造與生活空間設計
《地久天長》在表達敘事時十分重視家庭空間的運用。家庭空間在中國社會秩序中具有特殊意義;宏觀上,它是一種國家話語的重要組成要素,直接參與到國家媒介空間的建構;微觀上,它是家庭成員權力關系和性別的呈現。正如學者汪安民所指出的:“家庭并不是一個權力銷聲的場所,人們從學校或者公司回到家庭,只不過是從一個權力空間轉換到另一個權力空間。實際上,家庭室內的配置是政治性的。室內的空間權力配置是對社會空間權力配置的呼應,是對它的再生產。”
從故事主題來看,女性的性別建構是圍繞生育和家庭兩方面展開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女性主體在參與社會職能權力方面逐漸增多,依附于男性主體群體在逐漸消減,也由此獲得了更多的權力。這一現象在《地久天長》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首先是性別關系表現出比傳統中的性別更為平等的地位。王麗云在失去孩子后躺臥在床,沈英明透過門上窗戶窺看室內場景,透過玻璃的空白空間反映出她內心的痛苦與絕望。門框的隔閡也讓兩家原本親密的關系開始變得疏離和冷漠,一內一外的空間分布,也反映了性別屬性與公共空間的分配。這種性別關系還體現在家中就餐的座位分配(王麗云與劉耀軍一高一矮的空間表現方式)和筒子樓里的廚房空間(劉耀軍做飯、王麗云身后洗菜所呈現的家庭分工)。
其次,“父親”角色的內涵發生了改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男性在家庭中是權力者的象征,“父與子”的關系建構需要呈現出“父權”的特點,但是在《地久天長》中,劉耀軍形象的建構則以萎靡的形象出現,消解了以往作為男性和丈夫的權威形象。電影中用一組長時間的變焦鏡頭來表現劉耀軍與茉莉的出軌劇情,全景和近景交替切換的汽車空間景觀,映射出不同的人物心理反應。車里的茉莉,強烈地抒發自己情緒,通過虛實關系出現的劉耀軍,弓著腰、頹廢、焦慮的回答茉莉的質問,家庭權力象征的“男性”形象在衰敗和焦慮中逐漸喪失了身份認同。


貧富空間的構建是在真實和想象之外,融構了兩者之間的“差異空間”,其實質是表現空間的對抗性。《地久天長》里再現了這一差異空間的不平衡性,比如,南方王麗云夫婦的家與20年后沈英明夫婦的樓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沈英明家中廚房里的冰箱、微波爐、時髦的大電視機與王麗云家外破舊的漁船。從作為底層、遠離城市的流浪者王麗云一家來看,他們無法擁有兒子與正常生活,漂泊顛沛的生活也使得他們無法在精神層面再次融入城市,當他們再回到北方家中,鋪蓋在房間內白色單子,把他們與之前的生活隔離開來,把一切都變得熟悉又陌生。
媒介空間的使用作為城鎮空間電影的特殊背景,在參與敘事的同時與遷徙、想象產生關聯。影片里兩次舞廳與兩次家中舞會為營造媒介空間敘事提供了場景表征。收音機和錄音帶成為媒介空間傳播載體,參與了反抗的空間敘事,人物角色“建新”因為參加黑燈舞會而被抓進監獄后,收音機和錄音帶則成為恐懼和恐慌的代表。特別是在將錄音帶摧毀后,建新不再聽音樂和跳舞,由此表達他對當下環境的不滿和抗爭,“建新”也成為第一個被妥協的反抗者。然而,舞會本應該是城市青年活力的高潮表達,是媒介空間的跨地想象,是欲望和現代性的表達。正如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一書中所指出的“舞廳成了上海城市環境的另一個著名,或說不名譽的標記。”舞廳也被認為是城市和罪惡的代表,茉莉與劉耀軍的交際舞,正是表達對欲望的渴望,伴隨著舞會的結束也是對欲望的瓦解和自我認同的完成。故而,無論對劉耀軍來說,還是茉莉,舞廳都是個人欲望表達的空間。
三、空間重建與敘事的文化所指
電影的空間建構是一種通過鏡頭空間的調度來進行敘事從而實現影像的美學空間重建的過程。《地久天長》通過日常的生活片段及其空間重建來進行底層小人物命運敘事,反映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時代氣息,并詮釋了時代氣息下中國社會氛圍中的豐富文化意涵。
王小帥電影風格以紀實美學為主,大多聚焦在大時代中的小人物身上。《地久天長》細致地刻畫了底層群像,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問題,有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在計劃生育的時代背景中,劉耀軍夫婦得知懷孕的消息時而開心不已,但不幸的是被身為婦女主任的海燕拉去醫院做流產致使不能再生育,最終兒子“星星”落水身亡后夫婦二人痛苦地遠走他鄉。但在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驅使下,劉耀軍夫婦又收養了養子“星星”,兒子的叛逆與出走又使生活平添波折,好在最終兒子回歸了家庭。影片通過現實主義紀實手法、用長鏡頭的方式記錄了社會的矛盾,以個人的悲情命運呈現出了時代轉型發展中邊緣人的生命張力。
《地久天長》的故事背景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的中國和世界都在經歷轉型改革,有著特殊的時代情緒。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正值知青返城、計劃生育、全國嚴打等社會變革,這種集體記憶在《地久天長》中以孤獨、漂泊的敘事主題加以呈現,并有著強烈的時代情緒宣泄傾向。影片中劉耀軍夫婦是典型的孤獨者形象,一日三餐的矛盾、父子間的矛盾都是特殊時代下心理創傷的體現。慶幸的是,對于漂泊的人生中增加了對“回歸”的敘述視角,強調了無論我們走的多遠,再大的傷痛也無法抹去內心對回歸的向往。
后現代作為一種文化思潮,一般以反傳統、不確定性、碎片化、去中心化等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并通過語義的隨意指涉與敘事語境的狂歡化處理,塑造出陌生、無序、混雜的價值體系。而空間作為一個敘事層面,是后現代主義中一個表現形式,旨在打破以時間為主線的宏大敘事,通過秩序空間塑造人物角色并呈現非神圣化、商品化的價值觀念。《地久天長》中“支離破碎”的空間設計構造出了后現代社會所表現的疏離感和斷裂性。其中私人空間的呈現,揭露了社會限制中的個體精神覺醒。同時影片還通過碎片的敘事來完整敘事空間,使其創作風格呈現出“向整體展開”的特性。

四、對中國電影空間文化構建的反思
《地久天長》的藝術特點在于通過特定的空間設計與呈現來反映個人在社會中的命運轉向與救贖。盡管影片想為既有的傷痕敘事提供一種更加積極的救贖力量,使得中國第六代導演美學能被大眾文化所兼容,但仍有著諸多局限。甚至有些人認為,影片將倫理之美放置到了一個不恰當的地方,例如,王麗云被海燕帶去強制流產后,竟然還能與她成為朋友去俱樂部看跳舞。
電影意義的生成不僅依靠藝術表達的呈現,還包括時代中的評價主體,他們容易受到社會階層意識的影響,更傾向于故事能有人間煙火的質感。因此,我們想要講好中國故事,獲得更多觀眾的認同,往往要在影片內容表達中呈現出更多的共通性和普適性,特別是類似于愛、崇高、勇氣這些倫理價值。當這些“視覺記憶”被電影影像呈現出來時,能夠最大程度地喚起觀眾在生活中的“視覺記憶”,從而產生共鳴,這樣我們的電影才能夠有影響力,這也是電影能夠成為“大眾電影”的奧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