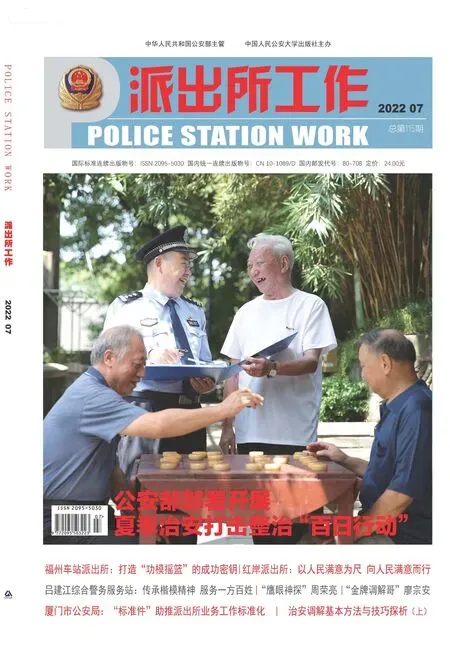接處警工作中應當具備的“證據(jù)思維”
文/張曉杰 楊小衛(wèi)
接處警工作是派出所及時發(fā)現(xiàn)、預防、打擊違法犯罪的首要環(huán)節(jié),也是派出所執(zhí)法公正、服務人民的重要抓手。近年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以及人民群眾法治意識的不斷增強,接處警工作面臨的情況越來越復雜,規(guī)范的要求越來越高,需要民警不斷提高工作技巧,不斷豐富工作思維。這里,筆者就接處警工作中應具備的“證據(jù)思維”加以簡單論述。
一、在接處警工作中要有“及時收集證據(jù)”的思維
負責接處警工作的民警是第一時間到達現(xiàn)場、直面矛盾的人員,在很短的時間內,其所了解到的、所認識到的事實不一定是客觀事實。一些表面上的家長里短、民生小案,如果民警簡單處置、草草收兵,便很可能導致小事變大、大事拖炸,而此時卻因為證據(jù)滅失、無法找到證人等原因導致補救工作難度加大。例如,在某案例中,民警到達現(xiàn)場后通過簡單了解,認為是一起糾紛引起的打架斗毆行為。民警在未對周邊證人信息進行登記,未對受害人是否身體不適進行當場問詢的情況下就組織調解予以結案。兩天后,受害人持病歷來到派出所要求處置行為人,民警分析該病歷所記載傷情應該能鑒定為輕傷以上,但因為已喪失證據(jù)固定的最佳時間,導致案件調查困難重重。
客觀地講,在接處警時,民警遇到的群眾在生活經(jīng)驗、法律知識、道德水準等方面還是存在不小差異的。這就要求民警時刻樹立“證據(jù)思維”,再小的案件也應該收集相應的證據(jù),防止變故發(fā)生。民警在到達現(xiàn)場后要第一時間收集固定證據(jù),一是此時當事人很少有欺騙民警的思想,或者說即使說謊了也容易漏洞百出,經(jīng)不起邏輯推敲。二是一些證據(jù)具有時效性,如果民警沒有及時固定,后期補充會非常困難。例如現(xiàn)場勘驗,又比如臨時路過的目擊者等。在某案例中,民警到達現(xiàn)場后發(fā)現(xiàn)受害人腿部受傷,民警立即對當事人進行了簡單的問詢,其肩部的執(zhí)法記錄儀記錄了全過程。受害人當時描述致傷原因為其堵住門口不讓行為人離開,行為人強行離開時,受害人拉扯行為人時被帶倒所致。民警后期調查時,受害人卻又一口咬定是行為人推倒所致,推倒的細節(jié)都描述得清清楚楚。而該案當時只有當事人雙方在場,只有行為人和受害人相互之間的指責,再無其他證據(jù)能夠還原案件現(xiàn)場,即俗稱的一比一證據(jù)情形。民警拿出錄像,受害人雖然對當時的說法不予認可,但由于該份證據(jù)及時客觀,為民警定性該案不屬于故意傷害提供了有力支持。實踐證明,如果開展接處警工作時就能保持及時收集證據(jù)的思維,發(fā)現(xiàn)、收集到的證據(jù)就越豐富、扎實、客觀。
二、在接處警工作中要有“客觀收集證據(jù)”的思維
在接處警工作時,要對現(xiàn)場的情況有著自己的判斷,要對行為進行初步定性,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構成要件有針對性地固定證據(jù),確保關鍵證據(jù)客觀固定到位。例如,兩個民警處理一起糾紛時,一方當事人主訴對方對其進行了毆打,而另一方當事人不承認存在毆打事實。民警觀察雙方當事人體表完好,無毆打痕跡,分析該案取證難度較大。民警立即將周邊潛在證人的信息予以登記。在后期的調查過程中,民警逐一走訪上述證人,甚至大量走訪附近樓宇住戶,證人和住戶均表示未發(fā)生過毆打的情況。證據(jù)確鑿,糾紛處理起來自然迎刃而解。
證據(jù)的客觀性、合法性、關聯(lián)性是案件辦理質量的基石。客觀地收集證據(jù)就是按照事情的真實情況來收集證據(jù),不能用主觀猜想來推測客觀事實,更不能唯口供論。有些辦案民警認為口供是“證據(jù)之王”,特別是偵查多人違法的案件時,此類情況尤為突出。例如,民警處警時,發(fā)現(xiàn)系兩方多人之間的毆斗行為,傳喚至所內后,往往因為警力、思維等方面的原因,只對主要犯罪事實進行了重點核查,對作用不突出的參與人員行為只注重本人的陳述,忽視了對其他證據(jù)的印證,便容易留下執(zhí)法隱患。
三、在接處警工作中要有“全面收集證據(jù)”的思維
在接處警工作收集證據(jù)時,要保持全面收集證據(jù)的思維。應收盡收,無論是有罪的、無罪的,罪重的、罪輕的,還是原始的、傳來的,能夠想到的一定要全面收集到位。例如,在某案例中,交警在路查時發(fā)現(xiàn)某嫌疑人出具的駕駛證系假證。通過詢問,該嫌疑人承認該駕駛證系買來的假證。交警將該嫌疑人以無證駕駛予以行政處罰,并將購買駕駛證的涉罪線索移送派出所予以查處。但是,交警在詢問時針對購買假駕駛證的行為僅問了兩句話,“你出具的駕駛證是否真實?”“是假證。”“這證怎么來的?”“是我買來的。”因為交警隊認為該案不屬于本單位管轄,且嫌疑人已承認其犯罪行為,假證實物已扣押,案件事實基本清楚,故再未針對該犯罪事實展開固定證據(jù)工作。派出所收到該線索后,也沒有意識到證據(jù)欠缺過多,導致兩單位未及時銜接。等到派出所訊問時,該嫌疑人早已有了應對之策,辯解說兩年前其在考科目二時,遇到一自稱姓何的外地男子。該男子告訴嫌疑人,只要給他兩萬元錢就能拿證。在被查獲之前,嫌疑人一直認為自己的駕照是真的。關于為什么交警查獲時嫌疑人陳述該駕駛證系假證的情況,嫌疑人辯解道,當時交警反復查驗該駕駛證,他才意識到該證是假證,自己也是受害人。嫌疑人還在被訊問時拿出報案材料,要求民警立案查處。同時,嫌疑人稱其不知道該男子的姓名,且當時雙方是約定時間地點見面,未留過聯(lián)系方式,交易方式也是從家中拿的現(xiàn)金。民警通過背景調查,發(fā)現(xiàn)嫌疑人家族中沒有人從事法律職業(yè)工作,嫌疑人的相關陳述也無法查證。這導致民警無法排除合理懷疑,一起簡單案件變成了疑案。
實踐證明,再簡單的案件都有其復雜的一面。民警在接處警時,需要迅速定性、準確取證。但隨著社會新生事物的不斷增多,接處警時遇到的新問題、新情況極為普遍,如買賣“笑氣”案件、同一事故多重報保險是否涉罪問題、電動三輪車在常規(guī)管理中屬于非機動車但在交通肇事罪中又被鑒定成機動車的問題、拾得手機后盜刷微信內資金的問題、騙取游戲裝備問題,等等。因此,在任何案件的起始,民警都不能確保自己的判斷準確無誤,必須樹立全面收集證據(jù)的思維,把涉及的證據(jù)盡量收集全面,從而為后期的偵查工作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