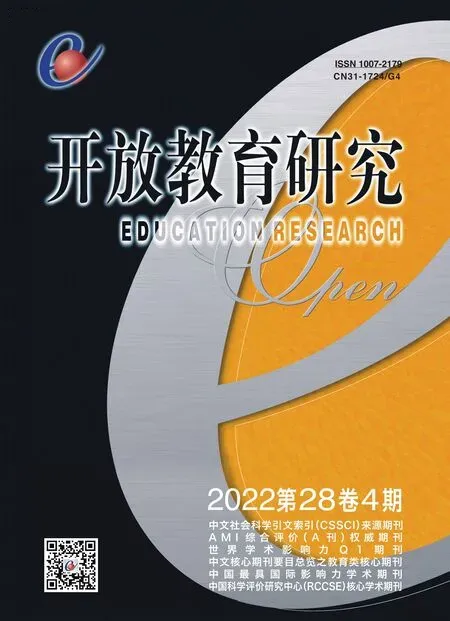人機協同學習:實踐模式與發展路向
郝祥軍 顧小清 張天琦 王欣璐
(華東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教育信息技術學系,上海 200062)
一、引言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邁入智能時代。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指出,人工智能加速發展,呈現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等新特征,大數據驅動知識學習、人機協同增強智能等更是成為人工智能發展的重點,要求探索人機智能共生的行為增強與腦機協同,發展“人在回路”的混合增強智能基礎理論研究。當前人工智能還處在對人類智慧的模擬和補充發展階段,雖然它在社會情感與價值觀等方面還不能和人一樣,但能勝任很多人類難以觸及的任務,使得偏向理性的機器智能與人類智慧形成互補優勢,“人機協同為未來人類智慧與機器智能的互構性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土壤”(羅生全,2021)。教育作為智能時代的重要發展領域,事關人才培養,《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強調,“利用智能技術加快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方法改革,構建包含智能學習、交互式學習的新型教育體系”。人機協同教學、人機協同學習成為智能教育實踐的重要方式,也是國際公認的教育人工智能發展方向(Pedro et al., 2019)。隨著智能技術深度介入教育以及教育設備的高可獲得性,人機協同學習已經走進現實,彰顯著自適應、智能化、個性化等特征,改變了學習者的角色。當技術成為世界的根本現象,且介入教育的過程越發自然,人機協同的教與學將成為未來教育無法回避的實踐形態。恰如毛剛等(2021)所言,人機協同是理解和建構未來教育世界的方式,而“人機協同下的智能教育世界是由學習者與智能技術在交互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生態”。目前大部分研究從教師視角探討人機協同教學,涉及教師角色(秦丹等,2020)、實踐形態(周琴等,2020)、協作路徑(余勝泉等,2019)等,鮮有研究從學習者視角探索人機協同學習的實踐模式、分析學習者的角色。隨著智能教育應用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乃至學校課堂,各類智能終端設備成為新時代人群(數字公民)的標配,泛在智能化的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學習型社會初具形態,人機協同視域下的智能學習越來越普遍(艾興等,2020)。因此,深入探討智能時代的人機協同學習的內涵、現狀以及可能的實踐模式,將有助于推動人機協同教育理論的發展。
二、概念內涵
隨著腦機接口、智能代理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學習分析等智能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通過改變學習環境,能夠讓學習者采用多種方式與客觀世界互動。智能技術通過強大的數據算力分擔人類的認知勞動,從以往的工具性和中介性角色向主體性發展。這使得學習的發生不僅是與外界環境的信息交互,也是人機分工協作,共同改變學習發生的過程與機制(郭炯等,2019)。智能技術支持的人機協同學習內涵如下:
一是在學習本質上,人機協同學習是人借助技術與世界交互、認識世界。學習科學關注的是學習如何發生以及怎樣發生,而知識是人對客觀世界的動態認識,是基于客觀世界的主觀構建。學習者只有從自身經驗出發與外界交互并積極建構意義,才能形成認知上的深層理解(任英杰等,2012)。因此,學習過程是學習主體通過一系列心理動作將外部世界的信息進行內在認知加工的過程。學習是學習者與環境互動的結果,其本質是在互動中認識世界和理解自我。智能技術與社會的深度融合,使其逐漸成為人與世界互動并認識世界的重要工具,扮演著中介者角色。其一,智能技術改變了人與外界信息互動的方式,因為技術改變了人類學習發生的情境,逐步延伸到虛實融合的空間。在技術構造的沉浸式學習空間中,復雜的知識能以結構化、情境化和交互式的方式呈現,人通過技術延展自己的感官去感知抽象的概念或者無法接觸的物質,甚至實現人機對話交流,通過人機交互建構知識。同時,新時代的數字公民浸潤在技術世界里,能夠通過各類智能終端獲取信息,與遠在千里之外的人或物交互。技術為此搭建了信息橋梁(人機交互、技術支持的人人交互),支持學習者的意義建構,并將交互生成的信息作為新的學習資源。其二,人的認知活動依賴基于技術的腳手架。維果斯基提出的支架式教學理論強調腳手架對學習引導的重要性,“基于軟件實現的腳手架”(software-realized scaffolding)能夠為學習者學習提供恰當的內容提示和認知支架(Quintana et al., 2004)。當前各類智能導師系統可以通過學習者模型、教學模型和知識跟蹤算法實現對學習者的學習輔導和知識訓練,自適應學習系統可實現個性化學習診斷、分析和資源智能推薦,為學習者規劃學習路徑,引導學習過程等。在智能技術的支持下,學習者可以準確識別自己的學習困境、挖掘行為特征,借助技術提供的支架,朝最近發展區深入學習。因此,人機協同學習使學習者能借助技術的中介效應與外部的人、物、信息等實現交互,推動學習者與技術建立協同的認知伙伴關系,更好地認識世界和自我。
人機協同學習闡釋的學習過程,揭示了人機協同學習的重要原則,即以人的價值為根本遵循,借助技術的智能實現人的自我發展。因此,人機協同學習可被定義為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作用于學習者身心,使其獲得智慧、健全人格和操作技能等品質的一種學習方式(艾興等,2020)。這體現了人機協同學習的人本價值取向,畢竟人的最優發展是所有計劃的標準(Fromm, 1968)。與一般的技術應用原則不同,人機協同學習遵循獨特的教育規律,重視學習者主體的學習發展需求,讓學習者有權掌控自己的數據信息、利用技術決定自己的學習,享受技術加持帶來的賦能感,實現高質量學習。
二是在學習形式上,人機協同學習是人與技術建立協作關系、協同發展的過程。智能系統逐漸逼近人類思維,在強大的數據算法支持下分擔人類的認知活動。人或將不再是唯一的主體,開始與“機器”協同認知。這就必須考慮人機關系的建立,兩者分工配合,共同完成學習任務。人機協同系統由計算機與人類共同組成,包含人、機器、人機協同三個要素,但對“協同”要素的理解需要根據技術的智能程度進行不同層次的界定(蔡連玉等,2021)。對于智能時代的人機協同學習,“人”就是學習者;“機”就是支持學習的智能技術系統或應用,包括支持學習的智能教育軟件以及具有一定推理思維、行動和互動能力的智能機器人。二者協同形成“1+1>2”的增強型智能。機器的優勢在于有強大的計算能力,能依據規則分析收集到的大量數據并做出決策,迅速完成重復性操作。人是生命體,具有情感、思維與精神性,其優勢在于生命屬性與社會屬性,能夠結合真實情境對事物作出價值判斷與理性推測。例如,在人機協同教學中,重復性、單調性和常規性工作通常由機器完成,創造性、情感性和啟發性的工作由教師負責(祝智庭等,2018)。人機協同學習包含“學習者+工具”“學習者+助教”“學習者+伙伴”三種形式(王良輝等,2021)。機器不僅可以充當工具為學習者推送個性化學習資源,監測學習過程,完成評價、反饋等工作,還可以扮演助教參與學習者的認知活動,引導與點撥學習者,促進學習目標的達成;機器甚至可以作為學習伙伴,促進學習者反思學習過程,培養批判性思維等高階能力。因此,人機協同學習也指學習者與智能系統建立協作關系,兩者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學習任務。
人機角色分工道出了人機協同學習的第二條重要原則,即明確人與機器的角色,以實現雙方價值最大化。人機協同帶來的學習形態變化源自數據智慧協同機制,即通過融合人的認知特征(“親而知”“覺而知”“構而知”“審而知”)以及機器的“學習”特征(“感而知”“描而知”“掘而知”“學而知”),構建協同發展的智慧環境(彭紅超等,2018)。人借助智能技術系統強化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認識,實現自我發展;智能系統通過使用人在活動中不斷生成的數據訓練內部算法和模型,實現優化升級。兩者基于彼此的“營養”供給建立互惠共贏的協同關系,通過人的智慧與機器的智能協作融合,達到人機協同的目標。
三、研究現狀
在人工智能技術與學習科學領域相關理論日益結合的趨勢下,人機協同學習逐漸常態化,智能導學系統、自動化測評系統、自適應學習系統等已經成為創設智能學習環境的典型工具。在人工智能與教育融合發展中,開發智能學習系統以支持學習活動,并利用這些系統探索和理解學習的本質是人工智能促進教育改革創新的目標之一(Roll et al.,2016)。因此,人機協同學習的實現主要有賴于創設智能學習環境以及揭示學習發生的原理與機制,為學習者提供有利的學習支持(Boulay, 2019)。
(一)理論研究
人工智能雖然逐漸被應用于教育實踐,但仍然缺乏對智能技術與學習科學理論、教育理論深度融合的深入研究(Chen et al.,2020)。目前,人機協同學習理論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兩方面:
其一,探索學習發生機制與學習方式的變革。智能技術不僅通過提供豐富的學習環境促使從知識學習向知識應用場景的學習轉變,更借助人機協同的智能結構延展學習者的認知邊界,改變學習的發生機制(郭炯等,2019)。學習發生機制的研究源自學習科學的發展,人們開始關注人如何主動進行意義加工和知識建構。學習科學領域的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嵌入認知(Embedded cognition)、生成認知(Enactive cognition)、延展認知(Extended cognition)以及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等都強調“人的認知發生”離不開與環境的交互(張婧婧等,2021)。技術改變了交互過程,使學習方式與形式、學習環境與支持發生明顯變化,技術促使學習走向“從設計中學”,讓人基于技術提供的腳手架理解知識(任英杰等,2012)。研究者也由此開始關注智能技術支持下的學習變化。例如,艾興等(2020)提出人機協同視域下的智能學習,強調關注學習目標的整合性、學習過程的動態性、學習主體的互通性、學習內容的生成性和學習評價的可視性。何文濤等(2021)闡述了人機協同的信息技術教育應用新理路,論述了人機協同技術觀、人機協同教育系統、教育中的人機角色,提出遵循教育本位、人機互信、人控規則和人機分評四條基本原則,認為人機協同學習應是智能技術支持的個性化學習,人機結合為學習共同體,協同完成學習任務。
其二,探討人機共生或人機協同視域下人機關系的建立。人機共生源自生物學的共生理論,可用于描繪智能時代人與機器形成的互利關系。為了實現人機共生,人機協同是重要方式,二者往往內涵相似。張學軍等(2020)認為人機共生是智能時代的應然選擇,智能時代的學習者需要學會人機共生的思維方式,掌握包括人機協作在內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有效學習方法,適應從人機協同到超越機器的學習文化。李海峰等(2020)闡述了人機共生的學習形態,即人機學習共生體通過共同化、表出化、聯結化和內在化等實現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轉化,促進知識的共同創造。其實,人機協同走向智能化旨在通過人與智能機器建立協作,促進人的成長發展。目前許多大規模應用的智能教學系統的智能程度不高,我們應該關注如何通過人機協同增強學習者的智能,而非執著于放大機器的智能(Baker, 2016)。安薩里等(Ansari et al., 2018)討論了高度數字化與智能化的工業4.0場景的新人機協同學習模式,指出應根據具體任務合理考慮人機的功能優勢,賦予學習者角色。王竹立(2019)認為網絡和智能時代的知識生產已逐漸由人類主體向人機共同主體轉變,人機合作式學習將成為主流,技術在人類學習中扮演的角色將由單純的工具,向環境、伙伴角色轉變,并最終與人類形成共同體。
總而言之,不少研究者已意識到智能技術改變了學習發生的過程,初步探討了智能學習環境中學習的本質與機制,也開始嘗試建立人機協同關系重塑學習形態與技術角色,然而少有研究對人機協同學習的實踐模式及學習者角色開展深入的理論探討。
(二)實踐研究
從斯金納的程序教學機器,到智能導師系統,再到人工智能教育應用,能展現人機協同學習實踐形態的案例不勝枚舉。本研究從智能系統支持的學習形式出發,總結人機協同學習的實踐現狀。
目前,常見的人機協同學習是以確定學習路徑為指導的適應性自主學習。認知導師(cognitive tutors,CT)或許是其中最典型的。它依據廣泛的實證調查確定需要學習的知識概念和知識點,呈現一系列問題供學生解答與練習,并根據學習者的進度進行調整(Koedinger et al., 2007)。例如,范萊恩等(VanLehn et al., 2005)利用智能導師系統分析學習者解決多步驟物理問題的具體行為和過程,提供即時反饋和學習提示。基于約束的建模(constraint based modeling,CBM)是另一種應用廣泛的智能學習支持(Mitrovic, 2012),它也可劃定學習者的學習路徑。兩者的區別在于基于約束的建模是將陳述性知識表示為學生行動結果的約束(如角A是底角)。當表示動作的謂語與學生回答相匹配時,技能即被視為已掌握。認知導師是將程序性知識轉變為規則(如已知角A求角B),規則與學生的表現動作相匹配,就表明學生掌握了這項技能(Desmarais et al., 2012)。目前,各類以習題測試為主的自適應學習系統是這類實踐的典型代表。因此,以認知學習為主的智能系統按照規劃的學習路徑呈現問題陳述,分析學習者的學習情況確定后續的學習內容,并在學習者遇到困難時提供過程性提示或解決方案。
受自然語言處理、語義分析、情緒識別、感知計算等技術的推動,智能系統支持的學習開始向協作互動學習發展,包括智能系統參與的人機互動學習與智能系統支持的人際互動學習。在智能系統參與的人機互動學習中,具備對話智能的系統通常就某個主題的知識向學習者提問,然后分析和回應學習者的回答,讓學習者在互動中學習相應主題的概念(Nye et al., 2014)。有些系統甚至設計多個觀點沖突的智能虛擬教師與學生互動,讓學生分辨對錯,提升學生的認知能力(Lehman et al., 2013)。有的智能系統能同時扮演指導者、計劃者、監控者、策略制訂者等角色,指導學生掌握自我調節學習(Trevors et al., 2014)。基于協商的自適應學習系統采用學習者與智能系統協商機制,幫助學生開展自我調節學習,明確哪些情況下尋求幫助的行為是受鼓勵的(Chou et al., 2018)。不僅如此,智能系統還可以作為被教學的對象,即學習者通過教授智能系統來學習。例如,學習者指導智能系統構建生態循環概念圖,判斷答案是否正確并給出反饋,以“教中學”的方式學習生態循環的概念與知識(Biswas et al., 2016)。其次,智能系統支持的人際互動學習由智能系統分析學習者的學習狀況,并據此推薦合適的真人學伴協作學習。例如,同伴個性化學習推薦系統(Recommendation in Personalised Peer Learning Environments, RiPPLE)可根據學習者的知識狀態為學 習者推薦學 習 同伴(Potts et al., 2018)。楊 等(Yang et al., 2014)基于自適應特征矩陣分解框架開發的快速助手(Quick Helper)智能學習系統,能為慕課學習者匹配合適的論壇話題和學伴;沃克等(Walker et al., 2009)設計的協作智能學習輔導系統,旨在構建同伴輔導環境,為學習者提供同伴輔導服務,強化同伴之間的互動對話。
從規劃好路徑指導自主學習到支持人機互動協作學習,學習者的自由度逐漸提高,逐步擺脫系統的控制而獲得學習主導權。為了向學習者提供科學、合適、個性化支持,探索和理解學習本質日益重要和迫切。為此,許多智能學習系統利用貝葉斯網絡、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智能技術與算法對學習者建模,為學習者提供智能和個性化的學習服務,促進學習者的能力釋放與生命成長,提升學習者在人機協同學習的獲得感(范建麗等,2022)。此時,智能系統的角色不再是為學習者提前規劃好學習路徑,而是實時分析學習者的行為和表現,推薦合適的資源與服務,由學習者靈活選擇,通過以人為本的教育人工智能實現學習的自適應與個性化(Yang et al., 2021)。因此,構建智能自適應學習環境、揭示學習發生原理與機制為導向的教育人工智能(郝祥軍等,2019),可助力人機協同學習。
四、實踐模式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人機協同的方式日益便捷化、智能化。愛潑斯坦(Epstein, 2015)由此提出“協作智能”(collabortive intelligence),即在人與智能機器之間建立協作以實現人類目標。建立人機協作關系能實現人和機器雙方智能的互惠強化,將各自擅長的能力優勢互補,創造新的價值。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人機協同的學習發生以及技術支持學習的具體方式,缺乏對人機協同學習實踐模式的歸納和凝練。本研究認為有必要解構人機協同的實踐模式,并以此辨析學習者角色。
(一)人機協同學習實踐模式解構
人工智能期望模擬人類思維實現與人的對話和協作。人工智能與人類協作經歷了人機共生、人機交互到人機協作三個階段(李憶等,2020)。智能機器最初是將知識打包植入專家系統,即表征人類專家知識、模擬人的推理思維解決專門領域問題。計算智能的發展推進了人機關系,它通過將人與計算機之間的協作可視化,增強人類智能(Kordon,2010)。智能代理是計算智能的一種應用,是具有多種智能特征的人工實體,能自主響應環境變化,以及通過與其他代理交互來保持其靈活性和社交性。它可模仿人類的交互特征,與人談判、協商和合作。隨著人機交互的增強,人類似乎失去對智能技術應用過程的控制,人機正進行著一場“主導地位”的較量,人類稍有不慎就會陷入被機器“牽著鼻子走”的窘境。
智能教學系統作為智能代理的教育應用,通過模仿人類教師搭建學習者與計算機之間的協作交互關系,推動學習者與媒體的交互漸漸轉向學習者與智能體的交互。人機交互關系中,“自主度”是關鍵概念,指團隊成員擁有的自由度、獨立性和決定權(Kim et al., 2006)。學習者既希望智能教學系統支持有效學習,也希望它能靈活調節自己的學習,即人機協同學習應彰顯學習者的自主度。例如,“在學習者與智能教學系統交互過程中,擔任教練角色的系統比擔任同伴角色的系統享有更大的自主度,學習者相應地在教練系統中的自主度就更小”(樂惠驍等,2021),此時學習者的行為就會受制于扮演教練角色的智能教學系統。但機器過多干預人的行為會降低人對協作過程的滿意度與持續協作的動機和意愿。因此,人機有效協作在于如何控制人與機之間自主度的平衡。根據自主度的高低,人與智能系統的協作模式包括人工智能主導、分工合作和人類主導三種(李憶等,2020)。人工智能主導模式說明計算機的自主度高于人;人類主導的模式是人占據的自主度高,能實現協作活動的控制;兩者分工協作是自主度相對均衡,建立了平等協作關系,達成目標或意見的一致。據此,本研究從學習者視角將人機協同學習解構為三種實踐模式(見圖1),即人工智能引導的訓練學習模式、人工智能支持的協作學習模式和人工智能賦能的探究學習模式,并以此分析學習者角色。

圖1 人機協同學習實踐模式
1.人工智能引導的訓練學習模式。從斯金納提出程序教學開始,機器引導學習就已出現在日常教學實踐中,教學機器通過程序性學習內容指導學習者學習過程,給予即時的學習反饋(Skinner,1958)。很多智能系統繼承了這一思想,尤其是以作業和習題訓練為主的導學系統,把學科知識按邏輯呈現,獲取學習者的行為與反應,并立即提供正確的知識引導,如正誤判斷、相關解答和問題提示。這種模式的智能系統的自主度較高,它通過預先指定的知識序列和事件邏輯為學習者提供學習支持;學習者的靈活度相對較低,只能按照智能系統給定的學習內容和規劃路徑學習。一些智能系統雖然宣稱它能采集學習者的信息與特征進行個性化學習診斷,但終究是遵從規定的學習內容、程序和目標開展的(Boulay, 2000)。因此,人工智能引導的訓練學習模式中,機器實現對學習過程的控制,學習者與機器協同時只能執行系統設定的學習活動,自主度較弱。不可否認的是,人工智能引導的學習訓練模式能幫助學習者解決學習困境,促進學習者的知識學習和認知加工,使其在合理的學習路徑中快速掌握學習內容。
2.人工智能支持的協作學習模式。智能系統目前已從學習的知識整合和路徑規劃,逐漸轉向關注學習者的互動協作,構建系統與學習者共同控制學習過程的模式(Corbalan et al., 2009),即“機”的自主度等于人的自主度。與人工智能引導的訓練學習模式相比,學習者與智能系統的互動協作與共同控制,強調學習者自我調節的重要作用。例如,周等(Chou et al., 2018)設計的基于協商的自適應學習系統意在實現系統控制與用戶控制的結合,使學習者與系統在對話協商中達成學習意見的統一。基于對話協商的智能系統或智能技術構建的學習環境,實現了系統和學習者之間的交互: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統通過收集和分析學習者的多模態數據,準確理解學習者的學習狀態,精確地表示系統中的知識和技能;另一方面,學習者可以與系統溝通,了解系統的決策過程,做出更好的選擇(Ouyang et al.,2021)。研究表明,智能系統在協作學習模式中可以扮演助學者、導學者、督學者和伴學者等角色,與學習者靈活配合(王一巖等,2021)。因此,隨著人的體力或腦力勞動被人工智能所分擔,人機分工的協作形態也將更具象化。
3.人工智能賦能的探究學習模式。當學習者占據主導位置時,智能系統主要通過提高透明度、準確性和有效性幫助學習者增強智能,指向的是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I)(Yang et al., 2021)。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強調人類對智能系統的控制。人類控制和人工智能自動化之間協作,能以高水平的可靠性、安全性和信任性增強人類生產力(Shneiderman,2020)。對教育而言,學習者需要學會利用人工智能增強自身的認知和能力,實現智能系統與人類智能之間的協同交互,實現自適應、個性化學習。尤其在創造性解決問題上,人類主導的人機協作伙伴關系更具優勢(Mccaffrey et al., 2018)。這類增強學習者智能的學習模式是人工智能賦能的探究學習模式,即通過智能系統為學習者提供學習支持,搭建認知支架,助力學習者對世界與自我的認知探索,降低學習者的認知負荷,促進學習者的探究性學習。探究性學習強調自主性和控制性,要求將學習控制權交給學習者,即學習者能夠借助外部指導和支持獨立開展知識探究和建構(楊剛等,2019)。例如,智能學習分析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識別有風險的學習者,幫助學習者以個性化和自定進度的方式學習技能和知識,包括為學習者提供精準的信息,明確如何推進學習以及為了實現學習目標學習者必須做什么(Yang et al., 2021)。總之,人工智能賦能的探究學習模式通過智能診斷、預測、干預和預防等分析和討論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學習環境和學習策略,幫助學習者靈活選擇人工智能系統提供的分析結果,自主建構和設計學習過程,探索符合自己特征和需求的有效學習方式。
(二)人機協同學習的學習者角色
對人機協同學習實踐模式的解構可以看出,學習者會根據“機”的自主性強弱,調整自己的行為和角色,以適應“機”在協作關系中的作用。
1.學習者作為接受者。在人工智能引導的訓練學習模式中,智能系統的作用是為學習者提供預先設定的學習目標與路徑,引導學習者按既定路線進行知識學習和認知加工。這種模式適用于缺乏專業知識背景和方法引導的“新手”學習者,因為他們不知道什么對學習最好,智能學習系統能為他們提供指導。學習者在“機”的引導下逐步習得知識點,在既定路徑中接受知識傳遞,提高學習效率(Corbalan et al., 2009)。學習者在該模式下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當前的智能導學系統已成為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應用,在支架式寫作指導、學習指導與監控、差異化學習和個性化學習提示等學習實踐中成效顯著(郭炯等,2020)。智能導學系統是人工智能引導的訓練學習模式的典型應用,主要包括兩個循環:內循環旨在為學習者提供智能導學,外循環旨在為學習者推薦個性化學習資源和規劃學習路徑(Murray et al., 2003)。智能導學系統對整個學習過程提供指導和適應性反饋,學習者接受系統的服務進行認知加工、解決問題,實現學習目標。需注意的是,學習者作為知識接受者,需要對智能系統提供的內容做出真實反應,只有充分而準確地展示學習行為信息才能獲得系統的適應性反饋。從某種程度上說,學習者向系統“輸入”個人學習特征信息時也在制衡著“機”的自主度,使他們不至于一直被系統牽制而產生倦怠。
2.學習者作為協作者。人機協同學習倡導人的價值實現,學習者應善于發揮自己與機器的各自優勢,借助技術實現自我發展。為了避免智能系統對學習過程的過度控制,人機交互協商的機制意在提升學習者的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對自我學習的決策與控制。人工智能支持的互動協商適合于有社會情感需求以及喜歡同伴合作學習的學習者。人工智能支持的協作學習模式可以從兩方面支持學習者扮演好協作者角色:一是智能系統作為學習者的協作伙伴。它通過自然語言處理、語義分析等技術實現人機對話協作。比如,周等(Chou et al.,2015)提出基于協商的自適應學習序列調節學習,即學習者的自我評估與系統評估出現沖突時兩者會互動協商,達成一致的學習選擇。學堂在線智能學習助手“小木”是典型的教學答疑助手(清華控股,2019),它能主動與學習者進行窗口交互,還可以為學習者制定學習計劃,給予階段性的學習提示與反饋,對進度落后的學習者給予善意提醒。二是智能系統作為協作中介促進學習者之間的聯結。針對目前自適應學習系統聚焦于學習內容推薦與路徑規劃、對社會性兼顧不足問題,郝祥軍等(2021)構建了基于人機協商的自適應學伴推薦系統,以學習者向系統請求匹配協作學習伙伴的方式,促進人機共同調節學習,支持學習者通過系統組建學習共同體,實現學習者之間的協作互助。由此可見,在人工智能支持的互動協商中,學習者不僅是另一端的同伴協作者,也是智能系統的協作者。
3.學習者作為建構者。以學習者為主導的人機協同學習模式凸顯發展人本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它通過增強人類智能實現學習者對自我學習范式的創新探索。這是因為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的問題和需求是什么,系統過多控制學習決策會降低學習動機。人工智能賦能的探究學習模式適合學習能力強、尋求學習控制感的學習者(如成人學習者),這些學習者可擁有充分的自主度,靈活運用智能化學習服務,根據系統提供的反饋自主規劃學習過程、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同時結合系統數據分析結果做好自組織學習設計。例如,姜強等(2019)設計的自適應混合慕課模式,依據對學習者學習數據的分析和可視化呈現,幫助學習者準確認識學習結果,明確當前應學習的內容并反思下一步學習計劃。在人工智能賦能下,學習者將一改只能作為知識接受者的被動狀態,轉向自我建構的主動狀態,以自我導向、自組織設計、自主調控的方式開展探究性學習,獲得學習活動的決定權,并通過智能學習分析發現自身學習問題或學習特征,調整學習節奏與進度。總體而言,智能時代的人機協同學習已具備自我設計、自我監控、自我調節、自我評價的特征(陳凱泉等,2022)。在人工智能賦能的協同創新中,人機協同學習將走向學習者自我建構的學習形態,推動人類學習走向新的階段。
五、發展路向
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發展為教育變革帶來了機遇,使得人機協同學習初具實踐形態,但教育實踐的復雜性與育人價值的獨特性要求我們以審慎的態度看待技術的教育應用,避免誤入歧途。
(一)關系路向:協調學習者與技術的自主度實現互惠共贏
人機協同學習提倡以人的價值為根本導向并借助技術智能實現人的自我發展。顯然,將學習的選擇權完全讓渡給技術是不可取的(Baker, 2016),因為一旦將學習診斷與學習決策交給機器負責,學習者就只能認同并跟隨機器被動學習,被困于算法控制下的牢籠。誠然,人機協同學習需要關注并賦予學習者自主度,但并非學習者的自主度越高,效果就越好。如果學習者的自我調節學習能力弱,他們反而會因過多選擇而無所適從。因此,人機協同學習需要協調學習者與技術的自主度。學習者尤其要適應智能技術帶來的便利,提升數字素養與自我調節學習能力,根據自身的學習情況進行權衡,選擇合適的實踐模式開展主動學習、有效學習,達到深度學習的目的。
此外,機器智能越來越趨近人類智能,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人類智能。人工智能擁有的計算和認知智能可以實現機器學習和知識圖譜的構建,為學習者推薦個性化學習資源和規劃適配性學習路徑;人工智能擁有的感知和社會智能可以識別學習者的生物和心理特征,刻畫學習者立體畫像,與學習者進行過程性的情感互動,促進對學習者進行多維度動態評價。但是,機器智能的更新升級同樣需要“學習”,需要源源不斷的數據“營養”供給,訓練算法模型。人機共學就是學習者和機器之間的互動交流、相互學習。機器通過“學習”獲得更加強大的社會智能,與學習者進行更深層和更接近高階思維的交流(范建麗等,2022)。因此,機器和人類在協同關系中分別承擔著不同的角色,未來的人機協同學習實踐還需要探討和回答“人應該做什么?技術機器應該做什么?以及人機如何協同?”三個關鍵問題(陳凱泉等,2022)。只有明確了兩者的角色分工,人機才能實現最佳的搭檔效果,達到自主度的平衡,最終促進人的發展。
(二)價值路向:人機協同學習需要朝向人的生命成長邁進
智能技術為未來教育帶來了無限可能,但其中也充斥著技術異化教育的現象。人工智能進入教育領域是因為人工智能在記憶、識別、推理等方面表現出強大的學習能力而使人類形成技術依賴心理。面對智能時代,人類在技術面前喪失自信心的態勢,學習者必須從“人本價值”出發,恢復在技術和機器面前的自我價值感,利用技術按需學習。人類亟需警惕用技術的邏輯替代人的生命成長邏輯,因為技術的邏輯在于追求事物的成功與高效,即“成事”與“成物”,但教育的邏輯在于人的生命成長與全面發展,即“成人”(李政濤,2020)。
未來的人機協同學習應該也必然需要善于借助技術的優勢探尋人本教育價值的回歸,即運用人機協同的數據智慧機制,聯結人(“親而知”“覺而知”“構而知”“審而知”)與機器(“感而知”“描而知”“掘而知”“學而知”)的雙向理解力,實現數據向智慧躍升(彭紅超等,2018):一是在人機協同學習活動中利用智能系統促進學習者對知識的體驗、察覺、建構和理解,促使學習者在人機協同過程中轉識成智。例如,智能系統可以借助虛擬現實或增強現實技術構建虛實融合的學習情境,帶動學習者開展場景式學習,加深對事物的感知和理解,以及培養學習者的社會情感能力;二是利用智能系統開展學習情境的感知計算,即通過全面采集學習者的行為數據,刻畫學習者的數字成長軌跡,從而挖掘學習者的個性化認知規律和行為變化特征,探索圍繞學習過程的增值評價、綜合評價等教育評價方式。
(三)倫理路向:提升人機協同學習實踐中的技術安全系數
人機協同學習的數據安全與技術本身的局限性值得關注。數據安全主要涉及教育數據的使用與管理,數據管理是人機協同教育發展的核心能力,能否安全高效地收集、篩選和管理數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機協同教育的最終效果(王曉瑩,2021)。技術的局限性可能導致數據隱私和算法偏見等問題,使學習者被迫遭遇信息泄露、偏見歧視。因此,我們應該重視數據安全,明確數據收集、使用和傳播規范,出臺教育價值引領下的數據規范標準;盡量避免潛在的設計偏見、數據偏見和算法偏見,不斷優化迭代算法,增強算法的可解釋性,打破“算法黑箱”的藩籬。同時,我們還要防止學習者與技術之間的關系“異化”,致力于實現真正的“協同”。學習者對智能技術的正確倫理認知是影響學習效果的決定因素。盡管智能技術在學校、家庭和社區教育中的應用日益普及,但學校、家庭等對學生的教育人工智能倫理問題關注度并不高。最新頒布的《義務教育信息科技課程標準》明確要求從低學段就應開始培養學生的信息安全意識和增加數字設備體驗,高學段應注重感知與理解數據編碼和算法,以及互聯網、人工智能的正確應用與創新,加強新時代青少年的數字素養與科學素質。作為教育實踐引導者的教師應該率先樹立教育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理念與原則,知曉倫理與安全規范,并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正確看待自身與技術之間的協同關系,鼓勵學生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樹立人機協同學習過程中的風險意識,提高技術辨別與判斷能力,合法合理使用智能技術。
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影響越來越大,智能機器和人類之間的區別逐漸在縮小,人機協同的默契度在不斷提升。我們一方面為智能時代的技術福祉感到欣喜,可以利用技術追求更加卓越的未來,但另一方面也充滿擔憂,擔心教育逐漸陷入技術加速邏輯,盡顯倫理、安全風險。面對人機協同的發展趨勢,人類如何構建人機關系法則,實現人機互惠共生?如何保持自我意識和主體性?這或許是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人們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