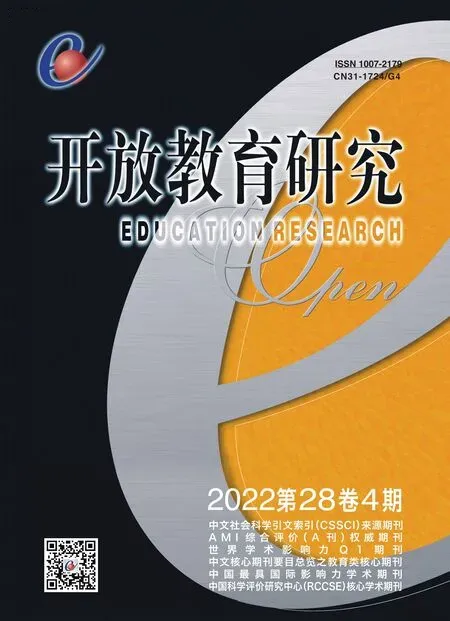教育信息化2.0時代教育均衡發展研究
——基于面板門檻回歸模型
陳 卓 尚海洋 樊姣姣
(1.西北政法大學 科研處,西安 710122;2.西北政法大學 管理學院,西安 710122)
一、引言
教育信息化是我國促進教育均衡發展的重大舉措。我國將信息化融于教育的探索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為應對基礎教育城鄉與區域發展的嚴重不均衡,逐步開展了一系列教育信息化專項建設。自此,我國教育信息化進入1.0時代。根據不同時期教育信息化建設側重點的不同,以2008年為界限可將1.0時代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信息化基礎資源的建設,包括教學計算機、網絡多媒體教室、校園網、電子圖書等。這一階段的教育信息化城鄉及區域差異主要體現在基礎資源上,也被稱為“物理資源鴻溝”。到第二階段,資源鴻溝仍然存在,但除了“三州三區”等偏遠貧困地區外,各地區基礎資源建設水平普遍較高。這一階段我國重點關注教育信息化資源的應用能力,包括關注信息化人才的培養,即加大人力資源的投入;關注學生的信息素養,即學生應用信息化資源與所學信息化知識獲取、應用信息的能力。該階段的教育信息化城鄉和區域差異主要體現在信息化資源的應用能力上,可稱為“應用素養鴻溝”。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的頒布意味著我國教育信息化進入2.0時代,主要關注智慧教育、網絡扶智、信息素養等,出現了新的數字鴻溝即“智能鴻溝”。由此來看,在教育信息化2.0時代初,回顧1.0時代的建設成效十分必要且具有價值,可為2.0時代應對教育智能鴻溝提供啟示。
教育信息化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主要涉及三大類:一是建立教育信息化測度指標體系,描述分析教育信息化的均衡性。李葆萍(2012)、陳純槿等(2018)、白文倩等(2019)分別以統計指標對比某一時期我國義務教育信息化建設的均衡性;李毅等(2020)建立信息素養的評價指標體系評估教育信息化2.0時代師范生的信息素養水平;二是使用問卷調査研究教育信息化發展水平及其影響因素。吳砥等(2016)使用問卷調查中部五省市的基礎教育信息化指數,據此描述分析其差異性及影響因素;萬淼(2017)采用問卷調研河南省部分地區中小學,分析城鄉基礎教育信息化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盧春等(2016)采用問卷調研東部G市中小學,建立指標體系量化該地教育信息化水平,分析導致教育信息化水平差異的關鍵因素;三是政策解讀分析。馮仰存等(2018)在解讀《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中提出了數字、新數字、智能鴻溝的三層數字鴻溝概念,分別對應于教育信息化建設的不同階段;雷勵華等(2019)站在教育信息化2.0時代反思1.0時代城鄉教育均衡性問題,提出教育資源與質量不完全呈線性關系。陳琳等(2021)探索了教育信息化的新發展策略。還有少量實證分析類研究,如李志河等(2019)采用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等研究工具構建指標測算基礎教育信息化發展水平,并對政府支持度、社會信息化水平對基礎教育信息化發展水平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
總體而言,當前教育信息化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一是對教育信息化水平的研究以構建測度指標為主,且大多是為了輔證描述性分析,基于數據的分析較少;二是缺少對教育信息化水平區域差異影響因素的定量分析,少量研究通過調查數據量化比較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區域差異,且對影響因素的分析仍以描述為主。受統計數據的可獲得性、連續性、完備性、現實性等因素限制,很難建立系統、全面的指標體系來衡量教育信息化水平。本研究基于2004-2017年我國大陸31個省(市、區)的教育信息化、教育投入等面板數據,建立門檻回歸模型,分析教育信息化投入與教育信息化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以期為縮小2.0時代教育信息化的區域差異、促進信息時代教育改革與發展提供參考。
二、教育信息化發展水平評估
(一)評估指標
參考已有文獻并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對教育信息化水平的評估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軟件資源建設水平、信息化資源應用能力、學生信息素養(見表一)。1) 信息化基礎設施是實現教育信息化的物質載體和前提,主要包括教學用計算機數量、開通校園網數、網絡多媒體教室數量、微機室面積等硬件資源。2) 軟件資源是硬件基礎設施發揮效用的主要媒介,主要包括電子圖書、網絡課程、虛擬實驗室、各類交互式和生成式學習工具等(趙國棟等,2009)。由于統計年鑒中電子圖書藏量的連續數據并不完整,本研究通過整體圖書藏量(電子圖書藏量是其重要部分)衡量地區軟件資源建設水平。3) 信息化資源應用能力反映的是信息化硬軟件資源的應用質量,是教育信息化產生效益的關鍵要素,主要包括信息技術課專任教師數、教師教育技術技能、教育信息化平臺建設等。4)學生信息素養反映的是教育信息化建設最終實現的效益,代表的是信息化資源投入的產出,是評估教育信息化水平最主要的指標,主要包括信息意識、知識、能力素養等。當前國內外研究對該指標的評估多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但實際調查中,信息素養測度涉及多方面要素且無統一標準,因此調查問卷方法實際操作較難。對此,部分學者(劉駿等,2012,羅廷錦等,2018,李健等,2018)用替代指標反映信息素養。本研究借鑒以上文獻,選取15 歲及以上人口中非文盲、半文盲比例等四個二級指標綜合測度有較強信息意識與能力的人口比例,間接反映學生的信息素養。

表一 教育信息化水平評估指標體系
(二)評估方法
由于測度教育信息化水平的變量較多,為避免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導致測度結果失真,本研究采用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因子分析法對各地區教育信息化水平進行測度。在測算前,研究者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次,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代表性因子,得到KMO值為0.736,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顯著性為0.000,證明各因素間關聯程度較高;最后通對標準化數據的相關關系矩陣求解,提取出兩個主成分,見公式(1)、公式(2):

將2004-2017年我國大陸31省(市、區)的標準化數據代入公式(3),計算得出各地區2004-2017年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得分值。
(三)區域差異
2004-2017年我國31個省(市、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綜合評估結果見表二。由表二可知,2004-2017年我國教育信息化水平區域差異總體呈逐漸縮小趨勢,但差異仍然存在,尤其是北京、上海等東部發達地區與西藏、青海等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始終存在較大差異。例如,2004年,北京教育信息化水平達到8.32,幾乎是西藏的七倍;2017年,北京教育信息化水平仍高于西藏六倍。可見,1.0時代教育信息化的區域差異雖有縮小但幅度很小。

表二 2004-2017 年各省(市)教育信息化水平綜合分值
需說明的是,本研究所建指標體系主要是為了評估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區域差異,未能體現如云教育平臺等新資源的建設與應用水平,因此對各地區自身教育信息化水平的縱向分析存在滯后性。例如,北京、上海以及河北等地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存在不同幅度的下降,這與經濟較發達地區較早地重視教育信息化新資源的建設與應用密切相關。早在教育信息化1.0時代的第二階段即數字化建設時期(2008-2017年),我國教育信息化已進入應用素養的數字鴻溝時期,但統計數據未能與時俱進,未能收錄體現新數字資源和應用素養等指標。
為客觀真實地評估教育信息化水平,我國教育統計數據指標體系亟需更新。尤其是在我國教育信息化進入2.0時代后,區域間出現了新的數字鴻溝,即智能鴻溝。這要求教育現代化進程需關注新資源、信息素養等因素。就區域差異看,與已有研究結論一致,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區域差異雖呈現縮小趨勢、但區域差異仍較大。對此,我們需要對教育信息化水平區域差異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能夠找到促進教育信息化區域均衡的突破口。
三、實證分析
(一)研究假設
1)地區教育信息化投入。郭莉等(2008)認為教育信息化投入差異是導致教育信息化水平差異的第一原因。教育信息化投入水平直接決定了教育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軟件資源建設和信息化人才培養等水平的高低,這些要素是評價教育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指標。也就是說,教育信息化的投入與其效益即教育信息化水平正相關。
2)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熊才平等(2004)認為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直接與教育信息化水平正相關,還通過正向調節教育信息化投入影響教育信息化水平。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會影響地方教育信息化投入的絕對量并最終體現在教育信息化水平上。
3)地區社會信息化水平。教育信息化屬于社會信息化的一部分。一個地區的社會信息化水平高低反映了該地區信息化資源應用效率的高低。當某一地區的社會信息化程度較高時,該地區的信息化資源建設水平也較高。此外,該地區居民的信息化意識普遍較高,其對信息化知識、技能的學習意愿也較強烈;當地居民對信息化知識、技能的掌握程度普遍較高,他們對信息化資源的應用能力也較強,進而激發他們更強烈的學習意愿,提升信息化技能,如此循環往復,使得該地區與社會信息化水平較低地區的差異逐漸明顯。
4)地區內城鄉教育信息化的均衡程度。我國教育信息化的區域和城鄉差異一直存在,地區內的城鄉差異是區域差異的一部分促成原因。教育信息化水平存在城鄉差異的根本原因是城鄉發展的不均衡。當城鄉居民在消費意識、結構、水平等差異較大時,就會出現教育信息化資源的擁有與應用上的差異并最后作用在教育信息化水平上。
5)地方政府對教育信息化的重視程度。地方政府對教育信息化的重視程度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地方政府看重教育信息化建設,即使經濟發展水平低也會在教育信息化投入上努力與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持平,最終實現教育信息化水平相當。
除上述因素,各地區教育信息化水平還會受地方的經濟開放度、辦學規模、對升學率的重視程度等的影響。本研究主要分析教育信息化投入與教育信息化水平之間的相關關系。根據已有研究可知,教育信息化投入與教育信息化水平之間并非完全呈線性相關關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并通過構建面板門檻模型對其驗證。
H1:教育信息化投入與教育信息化水平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
H2:教育信息化投入與教育信息化水平的相關關系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二)模型設定
本研究參照已有文獻以及門檻模型的設計思路(Zhouet al.,2022),構建了我國教育信息化投入對教育信息化水平促進作用的門檻回歸模型:

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EILit為被解釋變量(教育信息化水平),lnEIIit為核心變量(教育信息化投入);Xit為其他影響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社會信息化水平(IL)、收入差異(GINI)、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水平(EF)等;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對數值(lnPGDP)為門檻變量,γ為未知的門檻值,I(lnPGDPit≤ γ)和I(lnPGDPit> γ)是指示函數,εit~iid(0,σ2)為隨機擾動項。門檻回歸模型分為三個步驟:一是估計門檻值 γ和參數 β ,二是檢驗門檻效應,三是檢驗門檻值。
(三)變量描述
1.變量選擇與說明
1)教育信息化投入(EII)。本研究選用學校產權資產統計的固定資產值與當年人口數的比值(萬元/人),即人均固定資產值,反映教育信息化投入水平的高低。這是因為直接衡量教育信息化投入水平的數據難以獲得且完整性較弱,教育信息化投入主要包括教學和科研儀器設備資產、信息化設備資產,這兩者都是衡量教育信息化投入的重要要素。另外,本研究對人均固定資產值取自然對數,以分析其變動率對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影響。
2)門檻變量(PGDP)。本研究選取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人)指標,反映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同樣,在回歸中對該指標取自然對數,以分析其百分比變動對調節教育信息化投入影響教育信息化水平的作用。
3)控制變量
① 信息化水平(IL)。衡量信息化水平的指標很多。熊才平等(2004)采用地區的互聯網發展水平評價該地區的信息化水平;王艾敏等(2015)選用代表農村信息化水平的物質載體(農戶家庭電腦、電話等的擁有量)衡量農村信息化水平;俞立平(2011)認為信息化是為了提升信息傳遞水平,故而利用地區的郵電業務額衡量信息化水平。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與完整性,本研究選用各地郵電業務量占GDP比重(%)評價各地區社會信息化水平。
② 收入差距(GINI)。對該指標的衡量可以選用基尼系數、城鄉收入差距等。本研究借鑒王甘等(2012)的研究,利用城鄉間收入差距(%)測算該指標,計算公式為:

城鄉間收入差距越大,表明該地區的城鄉發展均衡程度越低,反之越高。
③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水平(EF)。本研究選用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水平”(梁功平,2013),該值越大表明該地區政府對教育投入的重視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2.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我國教育信息化1.0時代始于20世紀末至2018年,綜合考慮統計數據的可得性與完整性,本研究以2004-2017年我國大陸31個省(市、區)為樣本構建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本研究在實證檢驗中對樣本部分變量取自然對數(消除異方差)。為避免偽回歸,參考陳燕翎等(2019)的方法對所有變量進行單位根LLC檢驗,所有變量都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即面板數據具有平穩性。變量統計結果見表三。

表三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門檻回歸模型檢驗
1.門檻效應檢驗
本研究利用STATA15.1軟件檢驗模型的門檻效應,以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為門檻變量,對存在三門檻、雙門檻、單門檻的三種情況進行估計,通過反復抽樣與bootstrap方法得到F統計量和p值,并據此確定模型的門檻個數及形式(見表四)。

表四 門檻效應自抽樣檢驗
由表四可知,在抽樣300次下,單門檻效應在1% 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雙門檻和三門檻均未通過水平為10%的顯著性檢驗。因此,本研究建立單門檻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2.門檻值估計和真實性檢驗
模型通過門檻效應檢驗后,還需對模型的門檻值進行檢驗。由模擬結果可知,單門檻模型的門檻估計值為11.40,對應的95%置信區間為[11.36,11.44]。本研究進一步檢驗門檻估計值的真實性(見圖1)。圖中水平線為LR值在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虛線以下部分為門檻值對應的95%置信區間。從圖1可以看出,在95%的漸進有效置信區間[11.36,11.44]內,LR統計量趨近于零,即接受“門檻估計值與真實值一致的原假設”,這說明門檻估計值通過了真實性檢驗。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根據STATA15.1軟件對該單門檻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五),教育信息化投入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均正向促進教育信息化發展,這種促進效應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減弱。當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 (lnPGDP≤11.40),其回歸系數β1為0.0675(t=3.07),此時增加教育信息化投入對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當經濟發展處于較高水平(lnPGDP>11.40),其回歸系數β2為0.0181(t= 0.84),此時增加教育信息化投入對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的促進作用減弱,且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增加教育信息化投入不能顯著影響教育信息化水平。

表五 門檻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
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證明,研究假設H1與H2,即教育信息化投入與教育信息化水平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相關關系,而是存在以經濟發展水平為門檻變量的門檻效應。本研究依據門檻值將經濟發展水平分為較高與較低兩個層次,依此標準,只有北京和上海在2012年、江蘇在2015年、浙江在2017年跨過門檻進入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
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過門檻值,增加教育信息化投入對提高教育信息化發展水平作用較弱,這一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更關注教育信息化資源的應用;二是如前所述,本研究對教育信息化水平的評估指標未能反映云教育平臺等新資源的建設與應用;三是影響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因素復雜多樣,本研究未能將各方面因素都納入考慮,如地區的經濟開放度等。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于門檻值時,增加教育信息化投入能顯著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一般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仍需完善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加教育信息化投入會取得較為顯著的效果。
表五也報告了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社會信息化水平(IL)與教育信息化水平呈正相關,但未通過水平為10%的顯著性檢驗。這是因為社會信息化水平反映的是信息化資源的應用能力,本研究對教育信息化水平的資源應用能力的測量指標較少。總體來看,該變量的回歸結果與前文分析基本相符;收入差距(GINI)對教育信息化水平顯著負相關,回歸系數為0.0675,這一模擬結果與前文分析相符;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水平(EF)與教育信息化水平顯著負相關,這一結果與前文分析似乎不符。原因在于,政府重視教育信息化建設會促進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提升,選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衡量該因素就隱含一個假設,即地方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代表了對教育信息化的重視程度。事實上,各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分配結構存在差異,并非重視教育的地區一定重視教育信息化。綜上所述,模型的回歸結果與前文分析基本一致。同時,為確保分析準確且有意義,本研究參照陳燕翎等(2019)研究檢驗了模型的穩健性。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2004-2017年間,教育信息化投入對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具有顯著的單一門檻效應。當經濟發展水平處于門檻值以下時,增加教育信息化投入能顯著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處于門檻值以上時,增加教育信息化投入對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不顯著。與已有研究結論不同的是,本研究發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對促進教育發展非常重要,但是教育信息化的教育經費投入仍有待完善。鑒于此,本研究建議,地方政府應繼續適當加大教育信息化投入,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縮小區域差異。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是研究數據獲取方面,所選取的教育信息化投入與教育信息化水平的評估指標存在滯后性,未反映如云教育平臺等新資源的建設與應用,以及電子圖書藏量、學生信息素養以及地方政府對教育信息化的重視程度等,而是選取了替代指標,存在一定片面性;二是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影響因素復雜多樣,本研究所建面板門檻回歸模型未能將地方經濟的開放度、地方對升學率的重視程度等因素納入,有待后續改進與完善。
[注釋]
① 本研究的“生均”數選用的是每十萬人口各階段平均在校生數(人),包括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和高等學校。其中,初中包括普通初中和職業初中;高中合計數據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普通中專、職業高中、技工學校和成人中專;高等學校包括普通高等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