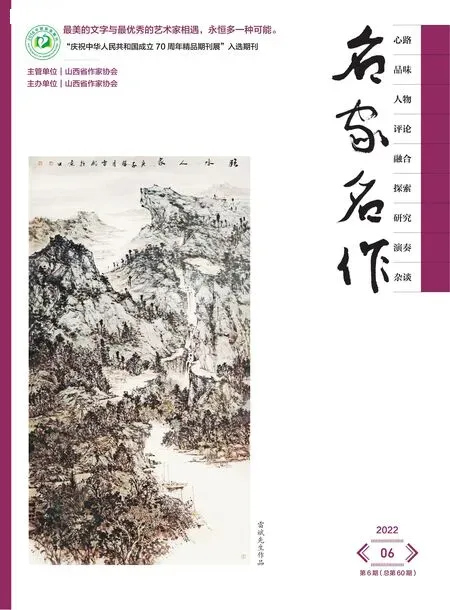時代群像與家國情懷
——從《茶館》到話劇《花橋榮記》
席冠南
一、引言
胡筱坪執導的話劇《花橋榮記》由張仁勝編劇,改編自作家白先勇的小說集《臺北人》中的《花橋榮記》,于2016年10月26日在桂林大劇院首演。話劇《花橋榮記》主要講述了因為世道紛亂從桂林流落到臺北長春路的春夢婆在離亂的艱辛中苦苦支撐著自己的桂林米粉店花橋榮記的故事。她看著身邊的桂林老鄉顛沛流離的命運,真切懷念著她的桂林老家。話劇在她不停的回望中表現了當時紛亂的時代落在每個小人物身上的悲劇。
《茶館》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老舍戲劇的巔峰之作,以裕泰茶館為縮影講述了戊戌變法、軍閥混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三個時代近半個世紀的社會風云變化。這兩部作品都是以動亂年代一家小店的浮沉為視角,塑造涵蓋各個階層的時代群像,折射小人物的家國情懷。話劇《花橋榮記》的改編以米粉店花橋榮記為基點,用人物群像素描展現了山河破碎下的濃烈鄉愁,其深層與“東方舞臺上的奇跡”《茶館》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花橋榮記》是對《茶館》內容和形式上的回望與繼承,從戲劇美學上看,是一脈相承的。
二、時代群像的展現
《花橋榮記》中的人物都是1949年以后生活在臺灣長春路上的人,這些經歷迥異的人相聚在一條街上,看似熱鬧的交往中潛藏著各自過往的傷痕。有開花橋榮記的老板娘春夢婆,也有家境優渥的小少爺,有容縣的縣太爺,也有手握著柳州半座城的李半城。除了流落臺灣的廣西人,《花橋榮記》還塑造了好色的擦鞋匠、潑辣的洗衣婆阿春和阿春媽、尖酸的包租婆顧太太等性格鮮明的人物,包含各行各業,通過群像速寫展現著人性的不同方面。
老板娘春夢婆展現的是中年女性的情感悲劇。春夢婆一直在為自己的米粉店張羅奔忙,是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形象,但展現精明的同時并沒有遮蔽她個人柔軟的情感世界。在劇中,春夢婆常是在關注身邊廣西同鄉們離散的情感遭遇時,回想起自己的感情故事,在理智的現實和感性的回憶中游走。春夢婆回憶自己還是桂林水東門外花橋橋頭榮記米粉店的米粉丫頭時,和桂林行營的營長戀愛結婚,跟著他去了不少大地方。春夢婆的丈夫是軍人,在“蘇北那一仗”中下落不明,毫無音訊。與丈夫失散的春夢婆,只能獨自狼狽地逃往臺北,不知何時可以再與丈夫團圓。她在許多夜晚里夢見丈夫一身血淋淋的,夢境暗示著她身為營長的丈夫可能已經在戰爭中喪命的悲慘結局。春夢婆之所以被叫春夢婆,也是因為她心中始終都懷著與丈夫團聚的執念,“可憐無定河邊骨,尤是春歸夢里人”。戰亂給人帶來的生活的傾覆、家庭悲劇給女性所帶來的悲苦可見一斑。
盧先生展現的是希望的破滅和精神的迷惘。在桂林家庭優越、無憂無慮的小少爺,到了臺北變成了長春國校教國文的盧先生。一邊教書一邊養雞,把自己搞得臭烘烘的,就為了存一點錢,可以托香港表哥把自己的愛人羅小姐從大陸帶到臺灣來。但他辛苦積攢十幾年的十根金條被表哥生生騙了過去,和未婚妻羅小姐相見,也沒有了希望。他頓時精神崩潰,一改過往斯斯文文的知識分子形象,和放蕩潑辣的洗衣婆阿春搞在了一起。因為精神支柱的倒塌,沉迷性愛、人性墮落的盧先生最終郁郁而終。驗尸官在死亡單上填了“心臟麻痹”,這其實是盧先生真正死因“精神麻痹”的另一個說法。盧先生當年與羅小姐矢志不渝的忠貞終究因社會的沖擊和戰亂的折磨、自我的墮落而告終,釀成了悲劇。
秦癲子展現的是過往輝煌被戰亂打破之后的沉淪頹廢。廣西容縣縣太爺在臺灣成了臺北市政小公務員,游蕩在街頭巷尾,大家總覺得他瘋瘋癲癲的,喊他“秦癲子”。從前心愛的幾房小老婆在戰爭中走散,再加上身份地位的落差,秦癲子精神開始扭曲變形。他不但在工作上漫不經心,在情愛上也變態,“在市政府做得好好兒的跑去調戲人家女職員,被開除了”。秦癲子丟了工作,毛手毛腳的毛病更是愈演愈烈。劇中秦癲子有兩次挨打,都是因為調戲女性。一次是在菜市場侵犯賣菜婆,被追著打幾條街。后來更加過分,變成了在板縫里偷看阿春洗澡。他侵犯女性的地點從辦公廳、米粉店到了菜市場,再到了浴室板子縫后面。空間流于低俗,手段從公開調戲變成了猥瑣下手。在瘋瘋癲癲中,秦癲子在暴雨后的一條臭水溝里淹死,好幾日才被打撈上來。
李半城身上呈現的是財產價值的灰飛煙滅和父子倫常的崩潰。李半城出場在花橋榮記熱鬧開張時,大家傳說他“做木材生意,賺了大錢,買房收租,整個柳州城的房子都是他的”。但在他與秦癲子發生口舌后,卻連一碗粉錢都掏不出來。從廣西跑到臺灣,只要出門他都提著箱子,守著箱子里的179張房契,可戰亂頻頻,房契早就失效了,只有他還當寶貝一樣守著。他盼著兒子寄錢過來,兒子卻一直沒有消息,仿佛把他這個父親忘掉了。沒幾年光景,他沒等來兒子的支票,手也扯起了雞爪瘋,生日那天也只能求老板娘賒賬再吃一餐,最終在窮困潦倒中絕望吊死。
1949年,從桂林流落到臺北的這一群人,曾經各自有各自的堅持和輝煌,后來卻流落于一條小小的長春路,不得善終,滿是現實的苦澀心酸和無可奈何。他們時常會想起自己的故鄉,會想起過去的生活,感嘆命運的不公與當下的窘迫。這些小人物只是千千萬萬裹挾在戰爭時代洪流里鮮活生命的縮影。
《花橋榮記》借鑒的是《茶館》對群像人物的速寫手法。老舍在寫《茶館》時并沒有按照戲劇創作中人物少而集中的傳統,而是延續自己寫小說的習慣,將小說人物塑造方法引入了劇本的創作。《茶館》一共寫了70多個人物,進行了跨時代的群像速寫,且70多個人物個個特色鮮明。有清宮的太監,吃皇糧的旗人,吃洋教的教士,主張實業救國的資本家,借“改良”而謀生存的商人,貧苦到賣兒賣女的農民,軍閥的軍官、大兵、警察,還有一大批依附于清朝、軍閥、國民黨的社會渣滓——特務、流氓、打手、相面的、拉纖的、女招待等。人物眾多但不雜亂,各有其代表的社會階層。作者以茶館為舞臺,把人物的不同經歷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形成時代的剪影,通過復雜的人物關系反映時代背景。
茶館掌柜王利發苦心經營裕泰茶館,在三個時代更迭中不斷地苦心“改良”,支撐茶館,謀求生存,但戰亂不斷的社會環境帶來了經營的大蕭條。特務官吏對茶館的搶占剝削終于把王利發逼得上吊自殺。
搞實業救國的民族資本家秦仲義躬行實踐,但到頭來他的工廠被國民黨當作“逆產”沒收了,他只從工廠的廢墟中撿回幾個機器零件和一支寫過宏偉藍圖的破舊鋼筆,體現了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重壓下民族資本家的悲劇。
常四爺在第一幕中是個有“鐵桿莊稼”特權的滿族旗人,因為說了一句“大清國要亡了”,便被吳祥子、宋恩子二人抓走坐牢了。出獄后,他便參加了義和團,進行抗日,具有剛正不阿的愛國精神。在義和團失敗后,他便歸隱于北平城內,成了一個自食其力的小商販,賣蔬菜、賣花生米。隨著封建社會的瓦解,從原來的階級中分化出來,成為貧苦的自食其力者,但還是逃不脫毀滅的命運。《茶館》中的人物群像與《花橋榮記》一樣,人物悲苦的命運之下折射著時代悲劇。
《茶館》中還出現了一些人物,他們父子相承,有很強的象征意義。像小二德子、小劉麻子、小唐鐵嘴各自繼承了父親流氓打手、買賣人口、江湖騙子的職業。此類負面人物也“子承父業”“代代相傳”,在《花橋榮記》中這種手法也有展現,愛勾引男人的阿春曾在街坊四鄰面前對阿春媽說:“反正你要嫁去花蓮,莫要在長春路給我立什么烈女牌坊!”洗衣婆阿春媽和阿春都生性潑辣開放,人物父子、母女之間的繼承性具有極強的諷刺性,藝術構思巧妙。
三、店面興衰中的家國情懷
在《花橋榮記》中,春夢婆在臺北長春路重開花橋榮記,開業街坊四鄰都在捧場,恭賀開業,好不熱鬧。但好景不長,米粉店好死不活地運轉八年之后,生意靠幾個廣西老鄉幫襯支撐不下去了,只得迫于生計放棄了只賣米粉的原則,也在牌匾邊上寫上了“炒菜米飯”,違背了祖傳米粉店的傳統,是對生計的妥協。連吃不膩桂林米粉的盧先生也向老板娘提出要換成米飯炒菜。到十五幕,從前幫襯店面的廣西老鄉死的死、瘋的瘋,從前和祖宗牌位一起供奉起來的米粉秘方也被白蟻蛀了。
春夢婆回憶年輕時奶奶給她講秘方,說桂林米粉的精髓在配伍,做一碗小小的粉,就如同布下千軍萬馬一般。做粉就是擺陣帶兵,將主題指向了處在戰時的時代背景。而被白蟻蛀了的秘方,更加深了老板娘對無法回故鄉的絕望。劇中春夢婆有一句臺詞:“我面對一個‘花橋榮記’找準帥不難,菩薩面對這片海。會以什么為帥?”這里從秘方暗喻著本劇深刻的主題:鄉愁背后對和平和祖國統一的渴望。
《花橋榮記》的作者白先勇先生,祖籍是廣西桂林。他的童年便是在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苦難深重的時代大背景下度過的。1944年長沙大火之后湘桂大撤退,白先勇便跟隨家人離開桂林,輾轉到了重慶。在此之后,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生活了幾年,1949年以后遷居臺灣,一去便是半個世紀。白先勇的生活背景從戰爭年代跨越到了和平年代,生活空間也經歷了從大陸到臺灣以及海外等諸多轉換。這些生活經歷使他對戰爭與和平、家與國的感悟愈加深刻,也給了作品深刻的歷史底蘊。
白先勇表示,在創作“臺北人”系列小說時是以劉禹錫的《烏衣巷》作為基調:“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在戲劇改編中,《花橋榮記》的作品意義也在不斷生長。
《花橋榮記》處處在說鄉愁,在鄉愁背后是動蕩的社會環境和戰亂不斷的世道對百姓生活直接的影響。可以說,是戰亂造成了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身份的百姓在正當壯年或是已經可以頤養天年的年紀里仍然背井離鄉、流離失所,懷著對過往美好生活的追憶,在異鄉臺北生活,甚至是在一地雞毛中茍且生活。在《花橋榮記》中,處處在懷鄉,其實也是處處在呼喚著生活的和平安定,反對令百姓流離失所的戰爭。“鄉愁”是編劇拖到觀眾眼前的主題,而呼喚和平和反對戰爭的家國情懷才是深層的內蘊。
可以說戰亂對當時百姓的生活是毀滅性的,它作為一個根本的原發導火索,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引爆。具體說來,戰亂之下親情、愛情的離散以及事業的重創和精神的迷茫,是《花橋榮記》中幾乎每個人物都要面臨的人生的痛楚。
結合《花橋榮記》作品的故事背景,我們會體會到一些具體的時代困局。但事實上,一部作品的指稱可以從更為宏大的人類學視角來看。《花橋榮記》呼吁的是人類文明的和平,期待的是雙方止戈獲得統一后國泰民安的美好生活,不單單只指向一個孤立的戰爭或者是只指向一個區域的人。
《茶館》也是在用小店的經營悲劇來折射整個時代的悲劇。《茶館》的故事集中發生在老北京的裕泰茶館中。茶館是三教九流的會面之處,容納了各色人物。全戲只有三幕,卻用茶館這樣一個方寸之地承載了清朝末年至民國時期5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全劇并未正面描寫社會上的重大歷史事件,而是將小人物揉進大歷史,用小茶館表現大社會,將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后、民國初年北洋軍閥割據時期、國民黨政權覆滅前夕三個時代的橫斷面與歷史縱線交錯結合。
對社會背景的反映直接體現在了茶館的布景變化中,從第一幕到第三幕中茶館陳設的變化便可以看出社會環境的活躍程度在日漸下降。第一幕中,茶館的“屋子非常高大”,“擺著長桌與方桌,長凳與小凳,都是茶座兒”,后院還有高搭著的涼棚,“棚下也有茶座兒”,“屋里和涼棚下都有掛鳥籠的地方”,這表明,茶館的經營狀況非常好,不但上座率高,還承擔著百姓茶余飯后遛鳥的休閑功能。
然而時隔十余年,袁世凱死后,中國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局面,內戰時時爆發,茶館作為市民的活動領域已然遭到破壞。茶館看似經過改良后獲得了新的發展,實則已經逐漸走向沒落的邊緣,悲劇氛圍已經顯現。
而到了第三幕,抗戰勝利后,日本人被驅除出了中國的土地,但隨之而來的不是幸福的生活,而是國民黨特務和美國兵在北京橫行的境況。茶館此時早已不復從前的熱鬧沸騰,而是蕭索冷清,“藤椅已不見,代以小凳與條凳。自房屋至家具都顯著暗淡無光”。
茶館包羅著人世百態,對茶館經營由盛轉衰的描述使人深感民族前途命運堪憂。《茶館》是從歷史文化的深層對國民自身的劣根性進行現代性的審視與面對中華民族所處困境的反思。有多少類似唐鐵嘴這類的中國人民麻木愚昧、毫無目標地活著。在時代沖擊下,他們找不到活著的意義,只是隨波逐流。當悲劇的時代推動百姓往前走時,面對的必然也是悲劇。老舍面對如此社會群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從麻木的百姓身上看到了麻木的舊社會,老舍對民眾麻木心智的喚醒是家國情懷的升騰。
四、結語
一間小店,來往路人皆匯聚于此。在時光的流逝中,從客人身上看到了歲月的變遷、時代的更迭和所處的社會環境。從王謝廳堂到了尋常百姓,一家小店就是歷史見證者。來往的人命運滄桑巨變,這背后便是時局混亂帶給每個人的悲劇,悲劇之下展現的是作者深重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