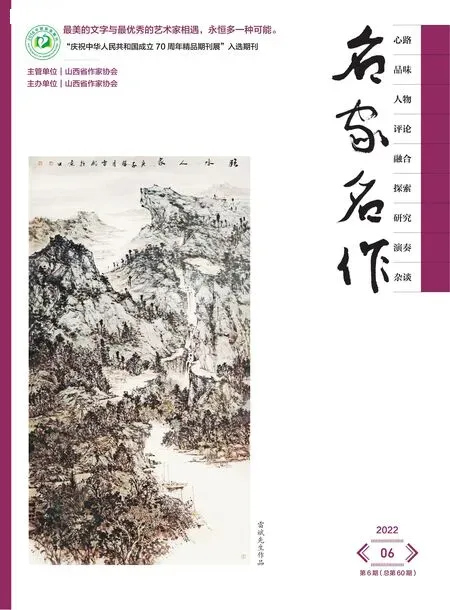從《幽蘭操》談中國古詩詞作品的創作與演唱
聶俊楠
一、《幽蘭操》音樂文本分析
(一)背景介紹
《幽蘭操》又名《猗蘭操》,原為一首古琴音樂作品,相傳最早為孔子所作,是用以贊美蘭花的一首抒情音樂作品。在《琴操·猗蘭操》條目下,也有“《猗蘭操》為孔子所作”的記載。截至目前,《幽蘭操》的創作者仍有異議,但其中表達對蘭花精神的贊賞則沒有爭議。后世有傳言《猗蘭操》作者另有韓愈之版本,目前沒有統一的說法。關于琴曲幽蘭的記錄,最早可見為文字譜的《碣石調·幽蘭》,據傳是梁代琴家丘明所傳的一首古琴曲。
(二)曲式分析
《幽蘭操》曲式結構為再現單三部曲式。結構包括引子、A、間奏、B、間奏、A、尾聲共七個部分。
樂曲第1~8小節為引子部分,以鋼琴作為導入性的陳述,建立在E羽清樂的調式基礎上,以縱向和聲為基礎引入樂句的主題。si和dol兩個臨時音作為E羽清樂的偏音出現,改變了縱向和聲的結構,形成一種既明亮又帶有獨特音響效果的和聲感。第8小節和聲停留在E羽清樂的屬音位置,按照中國調式而言,屬于商音位置,并由此引入樂曲的聲樂部分。
作品的A樂段由同一樂句的兩次陳述構成。旋律一開始采用五度、四度跳進與歌詞的“蘭之猗猗”相稱,緊接著是二度、三度之間的進行,與歌詞“揚揚其香”“眾香拱之”“幽幽其芳”相應。
作品的B樂段為第22~59小節,對比主題中部,屬于展開性陳述。第37~44小節作為間奏在調性上與主題起著一個重要的作用,偏音dol(變徵)的反復出現,在音樂色彩以及和聲效果上是與平穩進行有所變化的。在西洋大小調中,調性轉換的基礎常用屬音和主音作為轉換,但在中國調式中并非如此,可以看出E既是羽音又是商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羽音和商音就是一種五度的關系,雖然沒有固定的說法,但同樣的音程關系進行也是具有一定調性轉換作用的。因此E羽清樂—E商清樂—E羽清樂的調性切換使整個中部一直在轉變與回歸穩定中徘徊進行,主—下屬—屬—主的和聲進行功能,解決了音樂對比帶來的緊張感。在這樣突出的對比情況下,為了避免其帶來的片段性效果,開始了中部反復段落第45~59小節。第44小節最后屬七和弦的出現,是調性主題回歸的重要體現,使前后音樂色彩形成明暗對比。在音樂內容上引入更加豐富和強化“幽蘭”的音樂形象。最后結束在延長音上,與間奏整合并連接在一起。
作品的A樂段為第61~69小節,是再現段落具有動力性再現的總結部分。在主題回歸的基礎上,作品往往不會采用原樣再現,比如將第一部分A的旋律加以變化,由5+5對稱樂句緊縮后變成4+5的樂句小節數量,將原有的“揚揚其香”與“眾香拱之”由平均八分音符構成的一小節四拍,變換為3個四分音符加入雙八音符構成一小節四拍后又并延長最后一個字作為單獨四拍的陳述演唱。在樂句分配上回到了最初的詩性韻律的語句分配(詩詞是中國特色,它講究押韻,強調韻律,詩的文體是很嚴格的,包括段數、句數、韻律、字數、句式、平仄等)。
歌曲第70小節尾聲運用E羽的主和弦配合聲樂演唱單音的弱化與鋼琴的延長詮釋了整首作品與主題的結合。
二、《幽蘭操》詞曲結合分析
作為此首作品的“肢體語言訴說”,鋼琴伴奏開始部分左右手均以柱式和弦為源,第3小節右手九連音的小字5組高音mi的重復營造了幽蘭幽靜清淡的意境。第一部分鋼琴伴奏左手以單音(和弦拆分)、右手以柱式和弦為主,呈示陳述著整首歌曲的穩定形象。第14小節以及第17小節鋼琴左手都與聲樂旋律進行著反向的跳進,使音樂的流動性不斷加強,走向高潮部分。
此作品聲樂旋律的進行是中國古詩詞寫作中“詞與旋律”的特色創作的重要表現。整首曲子旋律是完全與漢語的語速、語感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如,第14小節“不采而佩”與“蘭之猗猗”旋律跨度由高到低。第17小節“我行”與第18小節“四方”通過字的歸韻與聲樂旋律進行連線的歸韻。第一樂段通過樸素的聲樂旋律直接地表達“蘭”的本真之思和漢語音韻。
中部“文王夢熊,渭水泱泱”“采而佩之,奕奕清芳”連續大跳的出現打破第一樂段對蘭花淡雅舒張的旋律,從特別縹緲的意境開始以實際且明顯的高音旋律進行著,與每個漢字相對應。鋼琴伴奏由最初的左手三連音的連續進行、右手柱式和弦的穩定彈奏發展成左手全十六音符的連續進行、右手增音的和弦變奏。半音的向上和向下進行依然以其獨特的旋律效果引申在整個中部。將鋼琴伴奏的主調音樂肢體作為基本音樂材料,靠和弦的變化豐富鋼琴音樂色彩,形成“幽蘭”色彩的和聲性伴奏織體。十六分和弦的出現使間奏的動力性更強,再一次推動了“文王夢熊”的旋律上漲。
第32~36小節旋律及調性的回歸帶來了蘭花平靜的訴說。“雪霜茂茂,蕾蕾于冬”兩句聲樂旋律在后兩拍的休止與鋼琴伴奏在后兩拍的留白相接,避免了歌曲的片段停頓。疊詞的出現與旋律平穩演唱再次呼應,休止符的間斷與“子孫”的大跳連線旋律強調著抒情中“蘭桂齊芳”的經久不衰與子孫昌盛的熱切希望;第37~44小節間奏是鋼琴伴奏的最為特性且巧妙的部分,右手和弦看似簡單,但卻有著極其強調的重音要求,而左手則是抒情線條的完美體現,此樂句承上啟下地聯系著整首歌曲,將德澤永駐的美好延伸,從另一個靈感出發,是伴奏肢體按著展衍逐漸加入新的變化。
第三部分和尾聲依然在抒情中散發著鋼琴伴奏的魅力,“猗”“香”“之”“芳”以四拍全音符作為演唱旋律,平衡了整首旋律的進行要求,使其更加完整地結束。力度從p—mp—mf—mp進行小范圍對比發展,使音樂風格保持豐富化。
歌曲從頭至尾的鋼琴伴奏中,裝飾音的運用是鋼琴伴奏營造意境的展現。通過裝飾音的個性化設計和音色,帶動演唱者演唱過程中對于音樂作品流動性要求的把握。
三、《幽蘭操》演唱分析
(一)演繹版本
目前通過各類視頻、音頻網站檢索,可搜到9個版本演繹情況,具體版本如表1。

表1 《幽蘭操》演繹版本
通過表1可知,作為聲樂作品的《幽蘭操》,既有美聲演唱版本,也有民族美聲演唱版本。其中王菲演唱的通俗版本《幽蘭操》則為特例。關于聲樂作品唱法分類最初是在中央電視臺青年歌手大獎賽上為了比賽評比進行的劃分。現今在各院校中,也以這種劃分方式開設不同的學科。以《幽蘭操》現有的演唱版本為例,結合視頻、音頻的數據分析,看各種演唱方法對這首音樂作品的處理。
在演唱過程中,我們通過自身聽覺感官能夠體會到,在“混合聲音”方面,美聲唱法的真聲占比小于假聲占比,民族唱法的真聲占比遠遠大于假聲,通俗唱法則是真假聲各占一半的效果。由于共鳴腔體的占比不一樣,聲音傳唱廣度也有所影響。美聲最強調通道,最重要的就是共鳴腔體的打開狀態。在演唱中有母音豐滿的歸韻,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句歌詞的最后一個字“香”“芳”“傷”“方”“泱”“昌”都是ang的歸韻特點,這就要求每一個字起音和落音都要“準”“輕”“巧”,只有做到這些,通道才能完全打開,達到最大限度的傳聲。
民族唱法就不僅要求聲音要在通道里、共鳴里,在美聲要求的基礎上,還要將聲音的垂直線和水平線保留。也就是說歌唱的聲音支點一定要呈持續性支撐,同時音色還要保持甜美、明亮、靈活。在歌唱過程中,民族唱法最重要的是語言和咬字,與前段美聲的歸韻不同,民族唱法的咬字要精確在每一個字,此首作品中基本每一樂句都會出現民族唱法特定韻腳和裝飾音,在不影響旋律發展以及內容上進行小范圍的演唱。比如“香”“孫”字,用美聲只需將音韻歸位,所以我們在聽《幽蘭操》會明顯感覺到兩種唱法的不同。還比如說,民族唱法主要表現在:(1)“字頭”要夸張。“蘭”“不”“渭”等每一小節的第一個音都是靠夸張的字頭音代入,通過字頭音代入后在此音上進行再演唱、再抒情。(2)“字符”要延長。從時間上講,比如“不采而配”中“而”字符,美聲的時長大概是2.30秒,民族唱法時長在4秒,從聽覺來講,民族唱法字符的延長是音樂語言歌唱性的表現,對于情感的表達也具有延續性的影響。(3)“字尾”要講究。美聲唱法字尾大多以自然音響效果歸韻為主,歸韻后自然放松,不會一直咬音韻到結束。民族唱法則是一直咬住最后的韻母直接進行結束。通過咬字直接過渡到下一句的起始音韻,比如“于蘭和傷”“以日以年”,“傷”和“以”是直接從ang到yi,中間沒有太多其他因素的過渡。同時民族風格也是民族唱法的重要表現之一,這首藝術歌曲的民族風格不帶有地域性,但具有的文化性要求是非常特殊的表現。
通俗唱法與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有所區別,它主要講究張揚演唱者自身的個性,混合真假音是它最突出的要求,需要在真假聲音中,隨時在歌曲的情感轉換時進行調整,隨之音色也要有變化,并且需要經常變化,這也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化表達。最簡單的例子,一首歌可以翻唱出各種版本,每個人唱法都不一樣,每個人對這首歌的理解都不一樣,所以表達的也就更不一樣。這也是流行音樂相比下來更為受眾接受的原因。通俗版本是王菲所演唱,她獨特的音色和語氣情緒是整首歌曲最大的亮點。相同的是她演唱也很注重尾音的歸韻,如“茂茂”——ao、“奕奕”——yi、“東”——ong等字的尾音都進行完全回歸,在演唱風格上打破古琴古曲的一板一眼的演唱形式,除了旋律的演唱外,加入部分歌詞非同旋律的單聲部重復(第一段副歌后)“不采而配”“采而佩之”。還引入A、HA、WU等哼唱吟詠,延續蘭花的未盡之意,表達孔夫子對未來世界充滿仁愛大同的期待,以及寄托著對后代延續化的教導,與其作為電影《孔子》的主題曲密切貼合。
(二)演唱實踐
作為一名美聲專業學生,筆者在多個場合下演唱了這一首作品,也通過對作品的曲式分析、作品背景的了解,領悟到了這首作品所表達的意境,也體會到作為中國詩詞音樂的特色,音樂旋律與詩詞的韻律是緊密相關的。
《幽蘭操》常出現“一字長拍”“大連線”“旋律線條緊湊相接”,對于氣息有著極高的要求,把每個字都賦予針對性的氣息源動力;位置上不能因為旋律在高音與低音間的來回大跳影響聲音位置的固定,第32~36小節中出現連續3小節中低音區旋律,這就意味著聲音是落下來的,一張嘴就要馬上起“雪”的音,但位置要豎立在胸腔里振動,使這個管子口一直向下通著氣息,只有把這個點落正確,才能保證后面大跳音程旋律位置的統一;共鳴則要在保證聲音大的基礎上做到音色的悅耳,只有這樣才能得到觀眾的認可,尤其是在演唱“文王夢熊”中部段落時,要一直保持吸著唱的感覺,一直保持胸腔位置的支持,保持音色的統一。不能由于高音部分就過度使用氣息等其他外力造成音色的不平衡,咬字方面則要求準確性、形象性的歸韻。比如“渭水泱泱”的“泱”是長久以來的夢想“摯賢”的追尋,“奕奕清芳”的“奕”在深廣且復雜的環境因素下依然能夠看到獨立且散發著幽香的幽蘭,能夠使內心的霧氣散去。這些都是要靠咬字去強調的音色。最后的表現力則是用旋律訴說著詩詞主角“蘭”,將“蘭”與“自我”的境遇結合,面向所有人訴說著人生的變動和永恒。看似非常簡單的演唱要求,卻有著不簡單的實踐理論支撐。
四、結論
在聲樂演唱藝術中,唱一首作品很簡單,但唱好一首作品表達的情感是非常難的。音樂的聲音是具有人為創造性的,音樂人的創作思維也充滿著各種變化,聲樂演唱作為一門學科,它是有一定規律性的。掌握好聲樂演唱的規律,同時把握作品的創作思維,體會中國調式中偏音特色,使整首作品的演唱更加順暢,小二度的上行是心中抱負未實現的延伸,加上鋼琴伴奏明朗暗澀的變換,更能帶動演唱者情感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