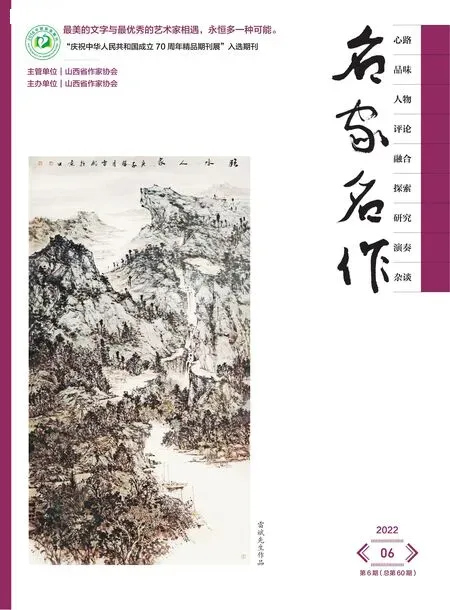從《申報》看早期電影的視覺體驗及其現代性與民族性(1874—1921)
李曉東
隨著電影技術的更新,對于電影的本體和實踐探究在新的時代和文化語境下呈現出更深入的認識成果,但回到“原點”與現實歷史語境去探析電影的起源和發展對認識電影本性十分重要。中國早期電影粗糙的形式外觀,以及報紙上零落甚或不成片段的電影廣告和觀感文章,看似淺顯無法落實,卻是非常直觀豐富的電影史料。“其中體現出與電影起源密切相關的心理學的關系”,電影的現實理念,電影的“真實”概念與“真實感”,電影的視覺特性和電影藝術的萌芽,都值得去深入研究并具體闡述,如此才可真正把握電影史料的價值并回答“電影是什么”的經典論題。
一、視覺經驗與“心理真實”
電影誕生并傳入中國之初,在《申報》與其他時興報刊中,常被稱為“外國影戲”“西洋影戲”“影戲”,與同時期的幻燈相比,名稱上同以“影戲”命之。同時,幻燈作為一種光學器具,與電影具有同樣的機械設備操作,電影放映之初報刊廣告中也時常沿用幻燈的放映用語。新式幻燈與電影同為“西洋舶來品”,從《申報》上關于它們的觀感文章可看出二者具有相似的視覺感觀體驗,如對二者都采用“栩栩如生”“靈妙無比”等詞反復描述觀感。電影本體不同于幻燈本體,因此,辯證地思考幻燈為電影放映奠定的視覺接受基礎尤為重要。
(一)部分觀影經驗的沿用
1897年后,電影與幻燈放映同時出現,“幻燈技術于18世紀90年代日益得到完善”。到了19世紀末期已然迎來了幻燈放映的高峰時刻。一定程度上,當時電影在放映規模及技術手段上并未超越幻燈放映的程度。就本土而言,新式幻燈為電影提供了放映技術等經驗,促進了電影技術的發展。粗糙的早期電影沿用了幻燈的部分觀影體驗,新式幻燈影戲也為電影奠定了較為深厚的文化基礎,二者同作為觸動人們感受的視覺媒介,從最初的“極視聽之娛”到“通過視覺來體驗事件、性格、感情、情緒,甚至思想”,強調以視覺形式表現經驗。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的風潮下,時人也漸漸浸潤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如幻燈和電影的影響里,體驗著它們帶來的視覺快感。
從18世紀七八十年代到電影最初傳入中國這一時期,幻燈主要作為娛樂活動形式而存在,從《申報》上可看到幻燈影戲“開演”于各園各地的廣告和文章,而是否有被用于當時的文化和宣傳活動還需繼續考證。電影被認為具有幻燈的商業性和娛樂屬性,“在放映電影最早的那些年頭,電影本身就是一種雜耍”,從報刊的廣告中可看到商業屬性使得電影在當時風氣開放的上海被廣泛放映。
(二)幻燈與“心理真實”
電影的本體不同于幻燈,有著“復原物質現實”的本性。首先,新式幻燈作為機械電氣、近代科技,紀錄表達著現實世界,但幻燈卻并非表征現實,只能被稱為“心理真實”。于果·明斯特伯格從心理學角度論述電影,他認為觀眾的心智相比導演的創作更具有啟示性。新式幻燈把外界事物視像化,使觀眾對部分呈現與整體經驗主動關聯處理,從而獲得超越性的心理真實感。
其次,電影與幻燈所依賴的放映技術與器具并非完全一致,電影和幻燈的實際放映空間也不大相同,極其關鍵的一點還在于幻燈放映時人的介入特性。電影在獲得一定的發展之后便不再靠人力講解,而幻燈放映卻一直需要考慮人這一因素:人的講演、放奏音樂等。人的參與在幻燈放映中變得極其重要,人的介入使得幻覺心理真實感被操縱,觀眾的思想變化也依賴于他人。電影與幻燈相比,更加去人化、機械化,顯示出機器對人力的超越及對人性一定程度上的切割。人的介入性被減弱后,電影的真實感被增強,正如瓦爾特·本雅明所說的電影“通過其最強烈的機械手段,實現了現實中非機械的方面,而現代人就有權要求藝術品展現現實中的這種非機械的方面”。
二、新的觀看體驗與現代化想象
無論如何,電影還是為人們帶來了不同于以往幻燈等視覺媒介的新的觀看體驗。電影最初模仿幻燈的名稱、傳播策略、放映內容,構建與其類似的消費空間,直至超越幻燈的結構等,最后獲得了重制與成功。1897年7月,《申報》上便發表了數十篇“請看美國新到機器電光影戲”廣告,并在8月份繼續發布相關廣告文章。1897年至1915年間,《申報》中的電影報道多為放映廣告,介紹放映內容,再略加感嘆和評論,次為租售收購影片以及影戲機器,并出現定制影片及征求影戲情節廣告。盡管廣告有推廣、夸張的嫌疑,但從大量廣告發文可看出,電影在當時確實獲得了普及和極高的放映量。外國放映商也看到了電影放映獲利頗豐,通過改建更加適宜的觀影場所等方式逐漸擴大觀影群體,一定意義上促進了上海娛樂業的發展,建構了現代性的觀影文化。
(一)新的觀看體驗與觀影空間建構
1912年至1921年,這一時期總體呈現出“專職放映”和“借地演映”并存的局面。電影最初是處于一種混雜的、多元的放映空間,是“舶來品”電影“在地化”、符合國人娛樂與觀影習慣的一種放映。而當時現代工業文明、西方思想不斷沖撞著上海本土文化,作為近代科技的電影顯示出西方先進文明的一面。隨著電影的普及,再加上外國放映商出于獲利等現實緣由,逐漸建設了眾多影院,建構起了獨特的影院觀影空間——公共性的黑暗空間、現代空間。
獨特的觀影空間使得觀眾產生了從未有過的“體驗真實”,這種獨特的觀看體驗得益于電影內在真實的運動幻覺感知和外在影像層面的現實指涉。讓·米特里認為,“在知覺和影像層面上,真實的指涉無可避免”。觀眾在觀影中確實是被這種“再現”的“真實”時空所刺激到,感受到了真實的現實縱深,就如外國人第一次觀看《火車進站》時的驚慌失措,或是第一次面對被“切割”的特寫鏡頭的惶恐。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盡管是真實的運動幻覺,但觀眾仍將呈現于銀幕上的世界認作真實的世界,并著迷于其中的異國情調和本國的社事人情。觀眾在“被觀看”與“觀看”的體驗中完成自我認同和身份建構,進行著現代化的獨特體驗。
(二)影院建設與現代化想象
早期電影的雜耍性質使得電影最初放映并非獨立的“演出”形式,和其他娛樂形式如魔術等都是共同進行的。為了吸引觀眾,早期電影的放映形式依附于傳統藝術及娛樂形式。隨著電影普及,電影放映才逐漸從混雜、多樣的放映場所脫離出來,但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并未達到影院專營的程度,而只是建造了電影院。此時電影作為一個新型現代娛樂產業與傳統娛樂產業并存。
清末民初是中國思想文化轉型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同時伴隨著西方現代工業、思想文明的傳播。此時電影及影院建設等體現出時人對西方現代化文明的體驗和想象。“紛繁的類型,群星及影迷的狂熱崇拜,諸如影院建筑、現代音樂伴奏以及‘電影演出’之類的招徠手段將我們領入電影文化這一領域,這一文化同時又是新興的現代文化的一部分,包括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時尚、娛樂及休閑。”從電影放映中,我們可以看出1921年以前人們對現代化不同程度的接納或排斥,而電影卻并非完全是先進的象征。
電影的技術主義外表下亦有著西方文明的缺陷。電影象征著現代都市生活體驗,但影片中都市空間的精彩紛呈又顯得現代世界并不那么光彩亮麗。早期上海電影的內容、布景、影院建設、節目介紹和海報設計等一方面體現出西方現代思想,營造出富有現代感的視覺世界,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傳統和現代價值觀的沖突。因而,20世紀初期作為半殖民地的上海,其電影的現代化外表一定程度上只是現代化的視覺表象,觀眾的觀影體驗只是完成了現代化的“想象的能指”。
三、視覺政治與民族性
電影的廣泛普及使得電影藤蔓般地生長于高雅文化與流行文化的分水嶺中。隨著外國商人到上海與國內其他地區發展,國內一些商人和其他團體也開始轉向開拓電影的新型娛樂潛能,早期電影顯示出大眾性和流動性的一面。盡管一個行業的興起發展主要依賴于經濟效益,但在19世紀初期,思想文化等急劇轉型的年代,電影也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體現出當時特定的民族心理,顯示出“中國性”的一面。
(一)電影的大眾性與視覺政治
“早期上海電影放映經歷了一個從傳統戲園、花園、茶館、新式劇場等到專業影院的發展過程”,娛樂屬性使得電影廣泛獲得受眾。不同經營場所的票價定位,亦使得電影迅速普及。純商業性放映、公益性放映和宗教性質放映雖目的不同、受眾不同,但最終普及到了廣大受眾,并且電影放映內容也根據不同受眾隨時調整,盡可能地符合觀眾的觀影心理,迎合時代風潮。
觀眾從電影中獲得了機械攝影的“生命化”的體驗,從進入電影里的想象秩序開始,從想象和現實中感受體驗。此時國外放映商以及國內相關人員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電影的視覺特性及其與政治的關系,試圖用電影傳達政治意圖,電影進而成為治理國家、控制社會的媒介。電影具有促進社會民主化的作用,但礙于政治局勢和社會心理,此時其大眾性、民主性卻顯得局限和被動,這也是電影作為舶來品必須經歷的文化融合過程。故而此時有許多如戰爭類的時事影片攝制,出于不同政治派別目的對影片放映內容和場所等有所干涉,卻并未產生“紀錄新聞片”的概念。
(二)電影與新劇的關系及其民族性
1905年之前,新聞記錄影像和其他性質的影像是作為“戲法”“玩藝”存在的,無論影像題材有多么重大。但在1905年6月13日,日俄戰爭記錄影像作為“以耀國威”的一種方式,達到了一種去戲法化。特殊的政治語境下,隨著人們對科學的不斷關注與進化論退潮的國民性改造焦慮,再加上電影與此時新劇、教育的關系,電影被添上了一種民族性的色彩。此時民族性邏輯加之于電影也體現出了本土觀念和西方思想的沖突,以及電影本體觀念之外時代利益的局限,電影無法脫離其時代背景,并被文化政治轉型所裹挾。
五四新劇是中國話劇在思想文化轉型之際改進發展中的重要環節,它順應著時代前進的趨勢和文化發展的潮流,探索民族化的舞臺語匯和表現形式,是兼具現代性、民族性、現實定位和價值的文化樣式。當時有志之士在中國面臨危急存亡之際提出電影與教育的關系,并倡導電影應學習新劇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發掘電影的現實功用,達到電影之教化的目的。然而,電影涉及教化以及“開通智識”,卻可能是徒勞的,落實情況亦依托于原始資源。將電影納入“開通智識”的視野,體現出了傳統思想的包容性,但電影的民族性與先進性在此時還難以像新劇一樣被發掘和呈現。
觀影的被動性亦使得早期電影無法承擔“開通智識”的教育功能。首先,放映早期影片選擇的局限性使得觀眾主動選擇和接受的程度較低,選擇空間不足造成選擇意識有限。賑災電影等公益性質的及帶有宗教性質的放映是暫時的,意味著電影院線之外的組織放映方式亦受局限。其次,國外電影公司形成了一種略帶壟斷性質的放映體系,束縛了國產制片公司的發展,如不將影片租售給國人影院,國人影院無片,經濟效益不好,因而難以發展國人影院或攝制影片。最后,當時華人參演影片也呈現出被動的一面。
但從西商創辦的影院名稱和建設等可以看出,外國放映商意識到了國人覺醒的民族意識,但國人影院建設和影片攝制力量卻有所不足,此時電影創作界和評論界亦缺乏深度和廣度,其民族意識缺乏自覺。但1921年影片《閻瑞生》《張欣生》出現并引發熱議,一方面體現了“電影的社會影響力”,另一方面標志著在這一時期電影“完全脫離了外來雜耍的角色,成為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至此,國人也逐漸開啟了國產制片的摸索期,中國民族影業開啟新的篇章。
四、結語
電影從舶來品到發展為本土影業,經歷了漫長的探索時期。對于早期電影的研究不應用“先見之明”過分強調電影的自律性,從而認識不到電影的真實背景。本文通過對《申報》上電影的“史前史”研究,電影話語、電影背后歷史脈絡和社會背景的整合,融合現代性、視覺性、民族性等理論視野,重新閱讀中國早期電影史,探析上海早期電影的發展史及其背后的文化、歷史邏輯,進而豐富早期中國電影史理論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