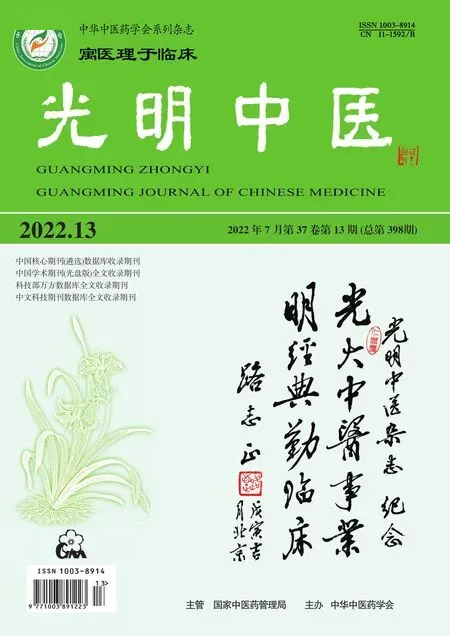過偉峰教授從痰熱論治失眠經驗擷菁
王小玲 過偉峰
失眠是指患者對睡眠時間和(或)睡眠質量不滿意并且影響日間功能的一種主觀體驗[1]。失眠嚴重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生活質量、工作效率及公共安全,導致巨大的社會負擔及經濟成本[2,3]。隨著社會高速發展、生活水平和習慣的改變及社會壓力增大,失眠發病率逐年增高,中國睡眠研究會近階段發布的睡眠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有超3億人存在睡眠問題。
過偉峰教授師從國醫大師周仲瑛,從事中醫腦病學教學、臨床工作多年,學驗頗豐,從痰熱論治失眠每獲良效,筆者有幸跟師學習,聆聽教誨,受益匪淺,現將其從痰熱論治失眠的臨證經驗介紹如下。
1 痰熱是引起不寐的重要因素
《仁齋直指方·病機賦》[4]:有因火而生痰, 有因痰而生火”。痰多為熱邪煎熬津液所致,并阻礙氣機,氣機不暢又郁而化熱,使熱邪加重,痰與熱互為因果,循環加重,痰熱擾神導致失眠。
1.1 因痰生熱《類證治裁》[5]云:“痰飲皆津液所化……而痰則隨氣升降,遍身皆到”。津液的產生和輸布五臟六腑密切相關,依賴于氣的推動,臟腑功能失調、氣機運動失常則津液停滯,聚而生痰。隨著現代飲食結構的變化,人們嗜食肥甘厚味,過逸少動,脾胃功能受損,氣機升降失常,運化不健,水液停聚生痰。此外,生活工作壓力過大,情志不遂者為多,內傷七情,氣機逆亂,津液停滯而生痰,痰濕郁久化熱。素體稟賦不足,心膽氣虛,或突受驚恐令膽氣虛怯,或年老體虛,心膽之氣漸弱,則少陽樞機不利,氣機疏泄失常,痰濁內生,郁久化熱。
1.2 因熱生痰熱分虛實,皆可煉液成痰。臟腑氣化失司,氣化失常,郁則化熱化火,火熱內灼,津停痰生。陰虛內熱,或陰虛火旺,虛火內灼,痰則內生。①火熱生痰。胃熱熾盛,熱邪熏蒸,水谷結而成痰,痰熱相結。情志郁結,久郁化火,熱灼津液,釀生痰熱。情志過極,心火亢盛,熱灼津液,痰熱內生。②虛火生痰。年邁體虛,腎陰虧耗,不能上濟于心,心火熾盛,心陰耗傷,陰虛火旺,虛火灼津,結而為痰,導致痰熱。
1.3 痰熱擾動心神導致失眠失眠的基本病機為陽盛陰衰,陰陽失交[6]。《黃帝內經》中言:“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中醫學認為,白晝屬陽,夜晚屬陰,隨著晝夜的變化,人體陰陽發生消長和轉化,從而產生人的睡眠和覺醒更替。人寤寐依賴于營衛陰陽調控,與臟腑功能有關[7]。心主血脈、主藏神,為五臟六腑之大主。人體的一切精神活動由心統帥,心神正常,則各臟腑功能互相協調,營衛陰陽得以正常運行。故神安則寐,神不安則不寐。《景岳全書》[8]中記載:“痰火擾亂,心神不寧,思慮過傷、火熾痰郁而致不眠者,多矣”。心主陽氣而惡熱,痰熱為陽邪,易擾動心神,心神不安,陽氣偏亢,浮越于外,陽不入陰,陰陽失交而致失眠。
2 審證求機 知常達變
臨床上疾病的發生發展因人而異,證候表現復雜,臨證不但要審證求機,還應做到既能知其常,又能知其變[9]。
2.1 典型痰熱失眠的表現《中醫內科學》記載不寐痰熱擾心證的主要癥狀為:心煩不寐,胸悶脘痞,惡心噯氣,頭昏目眩。心主陽氣而惡熱,熱為陽邪,痰結于熱,痰熱客于心而不祛,蒙閉神機,心神被擾,故表現為睡眠不安、寐淺多夢、心煩懊憹。痰熱阻滯,氣機郁滯不展,停蓄與胸中、胃脘,肺氣宣發不利,脾胃升降失常,可見胸悶憋氣、胃脘作脹。火熱之象顯著時,胸脘可自覺灼熱之感。痰濁閉阻,困遏脾氣,痰因火動,上壅頭目,阻滯氣血,清陽失展,則出現頭昏沉不清、困倦欲寐、目視動亂。
2.2 非典型痰熱失眠的辨析臨證發現,患者除入睡困難、寐淺易醒多夢、醒后難寐等失眠主癥外,沒有其他不適癥狀可供辨證分析。痰熱屬痰和熱2種病理因素膠結而成,互相依附,共同致病。痰熱擾動心神而見不寐,痰熱亦可侵襲全身各部,產生特有的臨床表現。臨床通過療效反證,不寐屬痰熱擾神者,多具有以下特征:①面泛紅光,頭面油垢脫發:痰邪黏膩,熱性炎上,痰熱隨上升之氣至于頭面,透于肌表,則可見面泛紅光、頭面油多;痰熱上蒸巔頂, 侵蝕發根, 致頭發油膩脫落。②胸悶脘痞:痰熱阻滯,氣機郁滯不展,停蓄與胸中、胃脘,肺氣宣發不利,脾胃升降失常,可見胸悶憋氣、胃脘作脹。火熱之象顯著時,胸脘可自覺灼熱之感。③頭沉困倦、身重乏力:痰熱停滯肌肉筋絡,氣血運行不暢,故肢體重著乏力;痰熱閉阻,困遏脾氣,清陽失展,則出現頭昏沉不清、困倦欲寐。④大便干結或黏膩不爽:痰熱留滯腸腑,熱灼腸液,腸腑傳導失司,則大便難解,黏膩不爽;火熱熾盛,津枯腸燥,可見大便干結,幾日一行。⑤形體肥胖:“肥人多痰”,痰熱阻滯臟腑氣機,水谷精微得不到正常輸布,過度蓄積于皮下,漸而形體臃腫肥胖。⑥苔黃膩:舌苔為脾胃功能之外候,熱痰互結,客于脾胃,濁氣上逆,舌苔色黃厚膩。
3 清熱化痰安神法的應用
3.1 寧心安神貫穿始終痰熱失眠的病理基礎是痰熱邪氣擾亂心神,令心神失寧而不寐。故在清化痰熱基礎上,結合寧心安神法以治其標是提高療效的關鍵。而且,經現代藥理學研究,安神類藥物一般均具有鎮靜、改善睡眠的作用,延長睡眠的總時間。根據上述對失眠痰熱證病因病機的認識,故以寧心安神貫穿治療始終,注重安神類藥物的運用。
3.2 痰熱輕重用藥痰熱有輕重之別,可分為痰重于熱、痰熱并重、熱重于痰3種病理情況,通過對四診信息的綜合分析,判定痰熱輕重(見表1),以明確清熱與化痰治療的主次。

表1 痰熱輕重辨析表
痰重熱輕者以痰濁蒙閉神機、阻滯氣機、困遏肢體經絡為主要表現,火熱之象并不顯著。臨床表現為頭昏沉不清,胸腹滿悶,納差,肢體困重酸脹,排便不暢,心煩、口干苦不顯,舌色淡紅,苔以滑膩為主。治療以化痰為主,以溫膽湯加減。溫膽湯出自《集驗方》,治療病后體虛膽寒所致失眠,后《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對溫膽湯加以變革,拓寬其臨床應用,用于治療氣郁痰阻諸證,后世醫家沿用至今。
痰熱并重者,除痰濁致病表現外,多了火熱因素的影響。臨床表現為心煩急躁、面泛紅光、油膩脫發、胸腹滿悶而灼熱、肢體困重身熱不揚、口渴不欲飲、大便黏滯、舌紅、苔黃膩。治以清熱化痰兼顧,以黃連溫膽湯加減。溫膽湯以和胃化痰為主,清熱之力較弱,益以黃連加強清熱之效。
火熱熾盛、痰火交結者,臨床主要表現為煩躁易怒,目赤腫痛,口咽干燥喜冷飲,胸腹痞滿,肢體困重,且全身灼熱感明顯,大便干結難解,舌色鮮紅,苔黃厚膩甚至黃濁膩。痰性黏滯難消,非峻烈之劑難攻,治以礞石滾痰丸加減。礞石滾痰丸為治療濕熱頑痰之要方,方中青礞石墜痰下氣,大黃瀉熱通腸,使痰熱隨腸中積滯而去。該方藥性峻烈,素體虧虛者慎用。
在臨床使用過程中,需仔細斟酌清熱藥物用量。清熱藥性屬寒涼,多服久服易損陽氣,熱邪輕者,清熱之品用量宜輕,如黃連可不用或小劑量使用,一般3~4 g為宜。熱重者則需足量應用清熱藥物,若火熱熾盛,可加用龍膽草、梔子等加強清熱力度。
4 臨證加減
痰雖為臟腑功能失調、氣機運動失常的病理產物,但亦可作為致病因素隨氣而流竄于全身各處,使臟腑功能進一步紊亂和氣的郁滯。痰熱存于體內,無處不到,可累及多個臟腑。病性以邪實為主,實中夾虛,病機復雜[10]。由于痰熱致病具有多變性,遂易與他證兼夾,互為因果,循環往復,導致失眠難愈,治療要把握病機,謹慎分析,靈活變通。
痰熱亦可阻于中焦,易使脾胃受損,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受損則生化無力,日久氣血兩虛,不能上榮于心,心神失養。除痰熱表現外,兼脾虛者,癥見面色無華、納差便溏、疲勞乏力,可加白術、茯苓等益氣健脾。
痰熱易阻滯氣機,肝氣郁結,肝郁日久必化火,邪火內擾心神。兼肝郁者,癥見情志低落、悲傷欲哭,女子經前乳脹、月經不調,可加醋柴胡、香附、梅花等行氣疏肝,易合歡皮為合歡花解郁安神,若肝郁化火,可酌情加清肝瀉火之品,如龍膽草、夏枯草等。
痰性流動,停聚于膽,阻遏膽氣,也可致心虛膽怯,心失所養,神魂不安。兼心膽氣虛者,癥見膽怯易驚、心情緊張、害怕恐懼,可加黨參、龍齒等益氣鎮驚。
痰熱亢盛,日久化火,暗耗陰血,使心腎兩虧,陰虛血少,虛火內擾心神,久則氣陰兩虧,心神失養。兼陰虛者,癥見潮熱盜汗、五心煩熱、口干咽干、腰膝酸軟,可加知母、石斛滋陰清熱,天冬、麥冬養陰生津。
5 典型醫案
焦某,男,48歲。2020年9月15日初診。主訴:失眠8年。8年來入睡困難(1~2 h),夜睡5 h,多夢易醒,伴有煩躁不寧,頭面油多,油膩脫發,腸鳴便秘,舌紅苔黃膩,脈滑。中醫診斷:不寐病(痰熱擾神證),治宜清熱化痰、寧心安神。處方:黃連5 g,枳實10 g,竹茹10 g,膽南星6 g,酸棗仁20 g,茯神15 g,首烏藤30 g,蜜遠志6 g,合歡皮15 g,生龍骨(先煎)30 g,石菖蒲6 g,法半夏10 g,陳皮6 g,炙甘草6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2020年9月29日二診。睡眠明顯改善,半小時入睡,夜睡7 h,伴隨癥狀改善。患者排便通暢,初診方枳實減量為6 g續求,14劑,水煎服,每日1劑。10月17日三診。睡眠穩定達7~8 h,伴隨癥狀好轉。原方繼進,鞏固治療,14劑,水煎服,每日1劑。藥后隨訪,患者睡眠基本正常。
按:患者平素飲食不節,嗜食肥甘,積濕生痰,因痰生熱,痰熱上擾,故失眠心煩,苔黃膩,脈滑均為痰熱表現。患者失眠日久,痰熱膠結,隨氣升降,痰熱壅滯肌膚,故見頭面油多,油膩脫發;痰熱停于胃腸,則腸鳴便秘。導師在黃連溫膽湯的基礎上進行加減,加用安神類藥物,去辛溫的生姜,加用膽南星加強清熱化痰作用,改茯苓為茯神。方中酸棗仁、茯神、合歡皮寧心安神;夜交藤養血安神;蜜遠志祛痰安神;生龍骨重鎮安神;黃連瀉火燥濕、清心除煩;枳實、石菖蒲行氣化痰;竹茹、膽南星清熱化痰;法半夏、陳皮燥濕化痰、理氣和胃;甘草調和諸藥。共奏清熱化痰、寧心安神之效,痰去熱清,心寧而神安,不寐則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