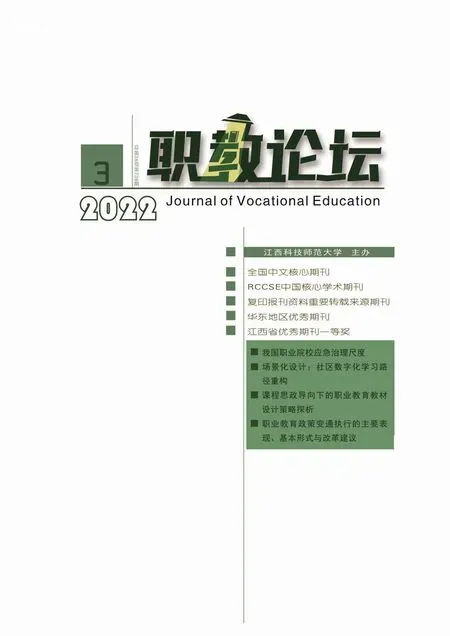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的主要表現(xiàn)、基本形式與改革建議
□孫靜 崔志鈺 倪娟 廖忠智
職業(yè)教育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離不開精準的政策供給和高效的政策執(zhí)行。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受政策制定、政策環(huán)境、執(zhí)行主體、體制機制等多重復雜因素的影響,政策執(zhí)行過程往往難以完全遵循政策設計的路徑或規(guī)則,政策執(zhí)行效果往往難以完全吻合政策制定的本源目標,使政策執(zhí)行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變通。這種政策變通執(zhí)行可能是合理的、積極的,也可能是歪曲的、消極的,不論是合理的“漸進調(diào)適”還是不合理的“政策梗阻”“政策變形”,政策變通執(zhí)行都是職業(yè)教育改革發(fā)展中必須高度重視且理性面對的現(xiàn)實課題。
一、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的主要表現(xiàn)
學者們對政策變通執(zhí)行存在多元理解,有學者認為政策變通是執(zhí)行者在未得到制度決定者的正式準許就自行做出改變原制度中某些部分的決策,推行一套經(jīng)過改變的制度安排的行為[1];有學者認為,政策變通是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政策執(zhí)行者根據(jù)政策環(huán)境的變化情況,在堅持政策精神實質(zhì)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執(zhí)行政策以實現(xiàn)預期政策目標的政策行為[2];有學者認為,政策變通是在政策實施中,政策執(zhí)行者對政策內(nèi)容和政策約束作出調(diào)整后實施的一種政策行為[3],不論怎么理解,政策變通執(zhí)行應是政策執(zhí)行者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對某一(幾)個政策元素作了變動,致使政策沒能完全遵從政策制定者意圖的政策行為。根據(jù)政策執(zhí)行的構成元素,政策變通執(zhí)行可分為以下三種情況:一是政策目標變通,如自主提升或降低政策目標要求。二是政策內(nèi)容變通,如通過對政策內(nèi)容的增刪改以選擇性地執(zhí)行某些政策內(nèi)容。三是政策過程變通,如不遵循規(guī)定的政策執(zhí)行原則、進程、路徑等,自主地執(zhí)行政策。當然,政策目標、政策內(nèi)容、政策過程三者的任一變動都可能引發(fā)連鎖改變(見圖1)。

圖1 政策變通執(zhí)行的常見形式
政策變通是政策過程中時常遭遇的問題[4],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也是政策“執(zhí)行運動”①發(fā)生的根源,這一普遍現(xiàn)象同樣反映在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中。
在政策目標方面,政策變通表現(xiàn)在預期目標與最終目標達成的落差上。比如,《國家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十二五”規(guī)劃》提出“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yè)學校招生規(guī)模大體相當,2015年全國中等職業(yè)學校在校生2250 萬人”,根據(jù)《2015年度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2015年中等職業(yè)教育招生601.25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shù)的43.0%,全國中等職業(yè)學校在校生為1656.70 萬人,比預期目標相差593.3 萬人,可謂落差巨大;《國家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十三五”規(guī)劃》再次提出“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yè)教育招生規(guī)模大體相當,2020年中等職業(yè)教育在校生規(guī)模為1870 萬人”,根據(jù)《2020年度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2020年中等職業(yè)教育招生規(guī)模為644.66 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shù)的42.38%,在校生1663.37 萬人,比預期目標相差約207 萬人(見表1),可見政策目標的變通在中長期政策規(guī)劃的執(zhí)行中較為普遍。

表1 “十二五”“十三五”職業(yè)教育部分目標與實際完成情況對照
在政策內(nèi)容方面,政策變通表現(xiàn)在政策設計內(nèi)容與政策執(zhí)行內(nèi)容之間存在差異。比如,《國家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十三五”規(guī)劃》明確要求“規(guī)范職業(yè)學校辦學行為,嚴格落實專業(yè)教學標準,防止以升學為目標組織教學”,隨著職業(yè)教育立交橋的暢通、類型教育的確立和職業(yè)學校“以發(fā)展為宗旨、以就業(yè)為導向”向“以促進發(fā)展為宗旨、以服務就業(yè)為導向”的轉變,為高職院校提供生源已經(jīng)成為中等職業(yè)學校辦學的目標之一,職教高考制度已經(jīng)成為高考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面向升學與就業(yè)雙重人才培養(yǎng)目標已經(jīng)成為很多職業(yè)學校的教學常態(tài)。
在政策過程方面,政策變通表現(xiàn)在政策執(zhí)行的進度、方式、路徑等方面與政策設計存在差異。比如,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高職院校擴招100 萬人,在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兩年高職擴招200 萬人的政策目標。在政策執(zhí)行中,各地沿用“錦標賽式”層層加碼、加壓的方式執(zhí)行,2019年高職院校招生4836146 人,比2018年新增1147805 人,完成政策目標的114%。然而,2020年高職院校完成招生5243364 人,只完成兩年目標任務的20%(見表2)。如果要完成兩年高職擴招政策目標,2021年高職院校的招生人數(shù)需達到680 萬人,這就必然要在政策執(zhí)行方式、執(zhí)行策略上作出改變。

表2 2018—2021年高職院校實際招生數(shù)和目標招生數(shù)②
變通執(zhí)行成為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的常見形式,一是因為很多職業(yè)教育政策本身的宏觀、中觀特性,需要各政策執(zhí)行主體因地制宜地執(zhí)行政策;二是政策執(zhí)行主體對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差異,有的理解深刻,有的限于表層,這種不同的理解反映在政策執(zhí)行的行動中,使政策執(zhí)行呈現(xiàn)“時差”和“溫差”;三是政策執(zhí)行受到實踐慣性和惰性的制約,加上政策執(zhí)行的激勵機制不健全,影響了政策執(zhí)行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二、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的基本形式
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根據(jù)執(zhí)行主體的主觀意愿可以分為積極變通執(zhí)行和消極變通執(zhí)行兩種形式。
(一)積極變通執(zhí)行成為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的主要形式
積極變通執(zhí)行是指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以正面的、進取的方式對原定的政策目標、內(nèi)容或過程進行適當變更,以便政策精神的落實。統(tǒng)觀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積極變通成為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的主要形式,如果從教育政策內(nèi)容、教育政策組織、教育政策過程三個方面[5]對職業(yè)教育政策進行分析,政策的積極變通執(zhí)行主要表現(xiàn)為:一是積極的內(nèi)容變通。為了提高政策的可執(zhí)行性,根據(jù)實際情況主動對政策內(nèi)容作適當調(diào)整。二是積極的組織變通。為了保證政策執(zhí)行的效度,建立便捷的政策反饋回路,改變慣常的組織執(zhí)行架構。三是積極的過程變通。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可能會遭遇一些現(xiàn)實的困難、問題或受到若干因素的干擾,也可能政策執(zhí)行極為順利,需要對政策執(zhí)行周期、策略等作出調(diào)整。無論哪種類型的變通,積極的政策變通執(zhí)行都是為達成或趨近政策目標,以主動求變的方式執(zhí)行政策。
內(nèi)容變通是政策執(zhí)行的常見形式,積極的內(nèi)容變通大致包括以下三種情況:一是暫不具備執(zhí)行政策內(nèi)容的條件,以積極的行動為政策的執(zhí)行創(chuàng)造條件。比如,關于職業(yè)院校產(chǎn)業(yè)學院建設,并不是每個地區(qū)、每所職業(yè)院校都適合建設產(chǎn)業(yè)學院,產(chǎn)業(yè)學院的組建需要滿足一些基礎性條件③,尤其對合作企業(yè)有著明確的要求,“產(chǎn)業(yè)必須在區(qū)域產(chǎn)業(yè)鏈條中居主要地位,或在區(qū)域產(chǎn)業(yè)集群中居關鍵地位”[6]。在基礎性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很多職業(yè)院校并沒有消極等待,而是圍繞產(chǎn)業(yè)(集群)對專業(yè)(群)進行改革,通過組建專業(yè)群為建設產(chǎn)業(yè)學院做好鋪墊。二是政策內(nèi)容在區(qū)域執(zhí)行時難度大、風險高,采用暫緩執(zhí)行和替換執(zhí)行。比如,關于職業(yè)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決定》提出“探索發(fā)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職業(yè)院校,允許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辦學并享有相應權利”,這是一項關乎多方利益調(diào)整的復雜的辦學形式改革,無先例可循、無實施細則,存在較高的執(zhí)行難度和風險,很多職業(yè)院校選擇了暫緩執(zhí)行,改之以深化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積極探索多元合作辦學形式,涌現(xiàn)出職教集團化辦學、校企共建產(chǎn)業(yè)學院等辦學形態(tài)。三是政策內(nèi)容本身存在缺陷,在實踐過程中遭遇現(xiàn)實困境,適度修改政策內(nèi)容后執(zhí)行。比如,關于普職融通,《職業(yè)教育提質(zhì)培優(yōu)行動計劃(2020—2023年)》指出,“建立普通高中和中職學校合作機制,……支持有條件的普通高中舉辦綜合高中”,在具體實踐中,普通高中舉辦綜合高中的意愿普遍不強,很多地區(qū)在政策執(zhí)行時就改由以中職學校為主體試辦綜合高中。
組織變通在政策執(zhí)行時被越來越多地采用。我國實行的是多級垂直的政策執(zhí)行組織架構,不同的職業(yè)院校存在不同的管理權限,有的職業(yè)院校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管轄,有的職業(yè)院校由市級教育行政部門管轄,有的職業(yè)院校由縣級教育行政部門管轄,有的職業(yè)院校可能由人社部門或其他政府部門管轄。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一般采用逐級傳遞的方式,如中央制定的政策一般通過省、市、縣、校的流程執(zhí)行,政策執(zhí)行存在多個中間層級(見圖2)。為了減少政策執(zhí)行“流通”層級,提高政策執(zhí)行效率,政策設計時對組織變通給予積極地考慮。比如,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教育部按照“自愿申報、省級推薦、部級評議”的工作程序,組織遴選了三批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單位,實現(xiàn)了政策制定主體(教育部)與政策執(zhí)行主體(各試點單位)的對接,簡化了政策執(zhí)行的中間層級,取得了良好的試點效果。1+X 證書試點、國家產(chǎn)教融合建設試點等均在政策組織上作了相應的變通,這種組織變通也在省級和地級教育行政部門的政策執(zhí)行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圖2 我國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一般流程
過程變通在政策執(zhí)行時往往被忽視,無論政策制定者還是其他政策相關主體更為關注政策執(zhí)行結果,因此在政策制定時忽略了對政策執(zhí)行過程的明確要求。模糊的政策過程要求為積極的過程變通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種積極的過程變通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執(zhí)行周期變通。以現(xiàn)代學徒制政策執(zhí)行為例,國家先后遴選了三批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單位,前兩批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較為圓滿地達到了試點的預期成效,驗收通過率高達96.7%,在第三批試點還沒完成之時,國家提前在全國推行現(xiàn)代學徒制,縮短了政策實驗的周期,這是一種主動的周期變通,旨在將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中形成的成果及時向全國推廣。二是執(zhí)行方式變通。很多探索性政策在制定時就配套了相應的資源,如《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工作實施方案》中就明確要求“加大投入力度,通過財政資助、政府購買等措施,引導企業(yè)和職業(yè)院校積極開展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在具體執(zhí)行時,有的地方財政資金配套不到位,影響了現(xiàn)代學徒制的試點,很多職業(yè)院校沒有簡單地等靠要,而是主動應變,在試點規(guī)模和執(zhí)行方式上作出相應的調(diào)整。三是執(zhí)行程序變通。通常的政策執(zhí)行包括政策宣傳、政策分解、物質(zhì)準備、組織準備、政策實驗、全面實施等環(huán)節(jié)[7],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一般并不機械地遵循政策程序,而是根據(jù)政策本身及執(zhí)行難度等對部分程序進行精簡,如對于一些經(jīng)驗性政策,往往會省略政策實驗環(huán)節(jié),對于一些單項性政策,則會省略政策分解環(huán)節(jié)。
(二)消極變通執(zhí)行在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中并不鮮見
消極變通執(zhí)行是指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以被動的、阻礙的方式對原定的政策內(nèi)容、過程或目標進行變更。這種消極的變通執(zhí)行在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中并不鮮見,主要表現(xiàn)為“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替換性執(zhí)行、“曲解政策,為我所用”的選擇性執(zhí)行、“軟拖硬抗,拒不順從”的象征性執(zhí)行、搞“土政策”的附加性執(zhí)行、“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的殘損性執(zhí)行、“生搬硬套,缺乏創(chuàng)新”的機械性執(zhí)行等[8],這些消極的變通執(zhí)行背離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導致職業(yè)教育政策失真,產(chǎn)生了較為負面的政策影響。這些消極的政策變通執(zhí)行源于主體的行為消極,這種主體行為消極深層次地反映在政策執(zhí)行主體的“知”“情”“意”三方面。
“知”即“認知”,即政策執(zhí)行主體對政策本身的認識和理解。不同的政策執(zhí)行主體對“政策是什么”的理解不一定相同,尤其在多個政策相繼出臺時,很多政策執(zhí)行主體對政策之間的邏輯關系缺乏清晰的認識,使政策執(zhí)行遭遇梗阻。比如,2014—2018年教育部分三批開展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2019年現(xiàn)代學徒制在全國全面推行;2019年3月,教育部、財政部啟動了《關于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yè)建設計劃的意見》;2019年4月,教育部等印發(fā)《關于在院校實施“學歷證書+若干職業(yè)技能等級證書”制度試點方案》;2019年10月,國家發(fā)展改革委、教育部等6 部門印發(fā)《國家產(chǎn)教融合建設試點實施方案》;2020年7月,教育部辦公廳、工業(yè)和信息化部辦公廳發(fā)布《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學院建設指南(試行)》……,職業(yè)教育改革政策的密集出臺,使作為政策執(zhí)行主體的職業(yè)院校應接不暇,以至于有的政策還沒執(zhí)行完,另一個政策又待執(zhí)行。職業(yè)院校往往孤立地看待并執(zhí)行每一個政策,很少將相應的政策結合或連貫起來,比如專業(yè)群建設是產(chǎn)業(yè)學院建設的基礎,有的職業(yè)院校在專業(yè)群建設還沒到位的情況下,盲目地建設產(chǎn)業(yè)學院,自然導致專業(yè)群建設和產(chǎn)業(yè)學院建設都難達預期,進而連帶影響了其他相關政策的執(zhí)行。《國家產(chǎn)教融合建設試點實施方案》雖然面對的是區(qū)域、行業(yè)和企業(yè),但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1+X 證書制度試點、產(chǎn)業(yè)學院建設、專業(yè)群的組建等都是產(chǎn)教融合建設的應有之義,如果孤立地進行產(chǎn)教融合建設試點,必然因載體缺失而實踐消沉。
“情”即“情感”,也就是對政策執(zhí)行的價值判斷,如果看不到、看不清政策執(zhí)行的價值必然導致執(zhí)行過程失范。比如,職業(yè)院校1+X 證書試點,本來是促進職業(yè)院校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的一個重要載體,很多職業(yè)院校并沒有看到1+X 證書試點對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的意義和價值,只是局限于考證,片面追求考證的通過率,將1+X 證書試點異化為另一類“應試教育”。再比如,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出臺了《關于建立中等職業(yè)學校教師到企業(yè)實踐制度的意見》,由于該政策在職業(yè)院校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執(zhí)行,2016年教育部等七部門又印發(fā)了《職業(yè)學校教師企業(yè)實踐規(guī)定》,要求“職業(yè)學校專業(yè)課教師(含實習指導教師) 每5年必須累計不少于6 個月到企業(yè)或生產(chǎn)服務一線實踐”,這本是建設高水平職業(yè)教育專業(yè)教師隊伍的政策保障,然而很多職業(yè)院校以師資緊缺等各種原因拒不執(zhí)行,只是要求教師利用暑期自行下企業(yè)實踐,又因缺乏相應的過程監(jiān)督和目標考核機制,使專業(yè)教師企業(yè)實踐在很多職業(yè)院校遭遇執(zhí)行難。可以說,當下職業(yè)教育“政策文本繁榮與政策實踐消沉”[9]與執(zhí)行主體對政策的價值判斷偏頗有著直接關聯(lián)。
“意”即“意志”,也就是為達成政策目標而決定怎么執(zhí)行政策,如果意志薄弱或不堅定,政策執(zhí)行就會出現(xiàn)搖擺,一遇政策執(zhí)行困難就會退縮,稍微遇政策執(zhí)行風險就會避讓。應該說任何政策執(zhí)行都存在風險,尤其是一些探索類政策,其執(zhí)行的風險更大。面對復雜的政策執(zhí)行環(huán)境,面對政策執(zhí)行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和困難,一些政策執(zhí)行主體意志不堅定,一遇困難就退、一有風險就避、無顯性利益不趨,奉行“謀定后動”和“拿來主義”,滿足于經(jīng)驗性的政策執(zhí)行,使政策執(zhí)行遭遇“發(fā)夾彎”。比如,當前職業(yè)教育政策試點呈現(xiàn)空前繁榮樣態(tài),爭取政策試點機會的競爭異常激烈,呈現(xiàn)“一票難求”之勢,無論是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還是其他試點,都取得了良好的試點效果,但試點后的政策推廣卻“熱情不再”“盛況難現(xiàn)”,致使“政策試點與政策推廣間存在效果落差、少數(shù)試點與多數(shù)觀望間存在行動落差”[10]。根本原因在于參與政策試點能爭取到資源和資金,且政策試點有各級領導和行政的關心和支持,“只會成功很難失敗”,政策執(zhí)行的風險反而小。政策正式大面積推廣后,失去了資源和資金,沒有了各級領導和行政的關心和支持,其政策執(zhí)行的困難和風險反而增大,消極的變通執(zhí)行就會時常出現(xiàn)。
三、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的改革建議
(一)建立逐級完善的職業(yè)教育政策制定架構
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有利有弊,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都使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陷入不確定之中,增加了政策執(zhí)行的風險,我們既應保持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的韌性與彈性,也應保證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的穩(wěn)定性和可預期性,這需要就職業(yè)教育政策本身加以檢視。
任何政策都是有局限性的,沒有哪一項政策是絕對完美的。一般而言,教育政策的層次越高,政策就越宏觀,政策的指導性就越強而其操作性則越弱,政策的目標、措施及對象就越模糊;反之,教育政策的層次越低,政策就越微觀,政策的指導性就越弱而其操作性則越強,政策的目標、措施及對象也就越清晰[11]。如此,所謂“良策”應該既有指導性又有操作性,應該逐漸明晰政策的目標、措施和對象,這就要求職業(yè)教育政策不應孤立或單獨存在,不應局限于宏觀、中觀或微觀,而應是一組政策。這一組政策有兩層含義:一是每一職業(yè)教育政策的出臺都應涵蓋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在縱向上形成政策梯度。二是每一職業(yè)教育政策的出臺都應有相應的配套政策或措施,形成政策的“組合拳”。
職業(yè)教育政策設計由“一個政策”向“兩組政策”轉變,需要建立逐級完善的職業(yè)教育政策制定架構,這種政策制定架構縱向上由宏觀逐漸轉向微觀,橫向上政策工具箱逐漸“填充”,與政策相關的配套逐漸豐滿,正如林德布洛姆認為的,公共政策不可能做到一次性周全而應采取“漸進調(diào)適”[12],這種政策制定架構就是一個政策“漸進調(diào)適”的過程。國家(教育行政)應專注政策的宏觀層面,確定職業(yè)教育的大政方針和改革總體推進,明確每一政策的意義價值、目標、原則、方向;省級(教育行政)應專注政策的中觀層面,出臺每一個國家政策的實施意見和地方性教育政策,明確每一個教育政策的執(zhí)行周期、階段目標、實施方略、政策配套、考核評估等;市縣(教育行政)應專注政策的微觀層面,確定上級職業(yè)教育政策的實施細則,明確實施策略、各類保障、操作流程等;職業(yè)學校主要是根據(jù)上級政策的方針、意見和細則實施政策(見表3)。一個制度安排的效率極大地依賴于其他有關制度安排的存在[13],這種縱向與橫向交融的整體制度安排為政策的精準執(zhí)行提供了保障。

表3 職業(yè)教育政策制定架構
長期以來,對政策執(zhí)行主體在政策執(zhí)行層級上缺乏明確的界定,很多宏觀政策通過層層轉發(fā)的方式落到基層職業(yè)院校執(zhí)行,由于宏觀政策操作性弱的特點使基層職業(yè)院校很難精準執(zhí)行,影響了政策的最終落地。建立逐級完善的職業(yè)教育政策制定架構,有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優(yōu)化了政策組織。重塑了各級政府(教育行政)在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中的角色,各級政府(教育行政)既是上級政策的執(zhí)行者,也是本級政策的制定者,中間層級不再是可有可無、隨意“跳躍”,而是必不可少、關鍵環(huán)節(jié),這也有效避免了“會議落實會議、文件落實文件”的政策傳遞。二是保證了政策內(nèi)容的完整性。避免了基層政策執(zhí)行主體對政策的過度解讀,各級政府(教育行政)在執(zhí)行上級政策、制定本級政策時都需要對政策進行再審視,這有助于及時發(fā)現(xiàn)政策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使政策精神和政策內(nèi)容得到全面貫徹落實。三是保障了政策過程。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一個逐漸細化的過程,這就確定了省級(教育行政)以執(zhí)行宏觀政策為主、市縣級教育行政以執(zhí)行中觀政策為主、職業(yè)學校以執(zhí)行微觀政策為主的政策執(zhí)行架構,避免了政策的單層級執(zhí)行,實現(xiàn)了政策執(zhí)行層級的多元化,完善了政策執(zhí)行鏈,保證了政策執(zhí)行主體與政策本身的匹配性。
(二)政策設計應預留政策積極變通執(zhí)行空間
當前,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缺乏一個明確的邊界,也就是對哪些職業(yè)教育政策是不需要或不可以變通的、哪些職業(yè)教育政策是需要因地制宜變通執(zhí)行的并沒有明確界定。應該明確,凡是出臺實施細則的應按實施細則執(zhí)行,凡沒有實施細則只有實施意見的,應參照實施意見執(zhí)行。由于各地政策執(zhí)行環(huán)境千差萬別,一味地剛性執(zhí)行和肆意地變通執(zhí)行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政策執(zhí)行效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職業(yè)教育政策都能制定出實施意見或實施細則,尤其對于一些探索類的職業(yè)教育政策,其在政策制定時并沒有現(xiàn)成的解決方案,需要在實踐中探索,需要在探索中逐漸形成相應的模式或范式,這就需要為政策的積極變通執(zhí)行預留空間,讓政策執(zhí)行主體敢于探索、勤于探索和樂于探索。當前,一些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同樣陷入“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14]的怪圈,在“管”與“放”之間需要保持一個政策變通執(zhí)行的空間。
將職業(yè)教育政策按可以變通執(zhí)行的程度分為嚴格執(zhí)行、允許探索、鼓勵探索三類。嚴格執(zhí)行的政策一般都制定有明確實施細則。比如教育部出臺《職業(yè)院校教材管理辦法》后,陜西、浙江等省出臺了《職業(yè)院校教材管理實施細則》,各職業(yè)院校自然應嚴格按照實施細則來管理和使用教材。允許探索的政策一般都有明確的實施意見而沒有詳細的實施細則,可以參照實施意見進行探索執(zhí)行。比如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決定》(國發(fā)〔2014〕19 號)后,江蘇省接著出臺《關于加快推進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蘇政發(fā)〔2014〕109 號),在此基礎上,鹽城市人民政府出臺了《關于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實施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工作重點和保障體系,然而省市兩級《實施意見》 并沒有對每一重點內(nèi)容給出詳細的操作說明,也就是《實施意見》只說明了“應該怎么做”,各職業(yè)院校可以根據(jù)各自實際決定“具體怎么做”,這是一種“框架下的執(zhí)行浪漫”。鼓勵探索的政策就是國家大力倡導卻沒有成熟方案或實施意見的政策,需要通過大膽探索以形成可資推廣的教育政策。比如,《職業(yè)教育提質(zhì)培優(yōu)行動計劃(2020—2023年)》明確提出“實施職業(yè)教育創(chuàng)新發(fā)展高地建設行動”,但職業(yè)教育高地究竟怎么建、高地究竟高在哪里,并沒有明確的說明和現(xiàn)實的參照,需要各地結合實際創(chuàng)新實踐。
對于需要嚴格執(zhí)行的政策,一般都有明確的實施意見或細則,但嚴格執(zhí)行并不等于沒有變通,一是政策執(zhí)行的環(huán)境是動態(tài)的,二是政策本身的科學性有待實踐的檢驗,實踐始終是檢驗政策科學性和可行性的唯一標準。比如,在教育部《關于開展現(xiàn)代學徒制試點工作的意見》 中明確提出四項試點內(nèi)容,即積極推進招生與招工一體化、深化工學結合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加強專兼結合師資隊伍建設、形成與現(xiàn)代學徒制相適應的教學管理與運行機制。在政策執(zhí)行時,由于中職學生入學時的年齡大多不滿16 周歲,達不到企業(yè)招工的最低年齡要求,招生與招工一體化也由政策文件中明確要求的“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廠、校企聯(lián)合培養(yǎng)”變通為“先招生后招工、先入校再入廠、校企聯(lián)合培養(yǎng)”。積極的政策變通執(zhí)行強調(diào)執(zhí)行者在政策執(zhí)行時必須遵循政策的精神實質(zhì),而不是盲目地、機械地、不加思考地執(zhí)行政策,因此對于需要嚴格執(zhí)行的政策,在政策設計時應為實施細則的優(yōu)化留下變通執(zhí)行的空間。
對于允許探索、鼓勵探索的職業(yè)教育政策,在政策設計時應根據(jù)政策本身的性質(zhì)預留相應的變通執(zhí)行空間。這一政策變通執(zhí)行空間是動態(tài)的,需要不斷調(diào)整的,既要避免隨意變通、任意變通,也要避免變而不通、通而不變。例如,對于職業(yè)教育高地建設,強調(diào)“鼓勵地方試點試驗,在東中西部選擇若干省或地級市先行先試,總結出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jīng)驗”④,對于哪些地區(qū)建設怎樣的職業(yè)教育高地,政策并沒有明確,對于職業(yè)教育高地的建設標準,政策也沒有明確,這就給各地留下了廣闊的探索空間。2020年9月,江蘇省人民政府出臺了《關于整體推進蘇錫常都市圈職業(yè)教育改革創(chuàng)新打造高質(zhì)量發(fā)展樣板的實施意見》,公布了教育部和江蘇省支持政策清單和蘇錫常都市圈34 項任務清單,蘇錫常都市圈按照任務清單進行改革探索。這一任務清單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最終的,職業(yè)教育高地建設永遠在路上,任務清單不可能因探索任務的完成而逐漸清零,而是根據(jù)試點和推進情況加以變通調(diào)整。對于沒有獲得教育部職業(yè)教育高地政策試點的江蘇其他地區(qū)(如南京、南通等)如何推動職業(yè)教育高地建設,需要在國家職業(yè)教育高地建設基本精神的指引下,參照蘇錫常都市圈等職業(yè)教育高地改革樣例,結合區(qū)域實際,對建設方向、目標、任務等作出調(diào)適和變通,這種“變通”就是使政策越來越切合地域特點和實際,越來越具有可操作性。
(三)制度設計應堵塞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漏洞
政策的消極變通執(zhí)行不僅使政策實施效果與政策設計初衷大相徑庭,更為嚴重的是對政策嚴肅性、權威性和政府公信力等產(chǎn)生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是政策效果碎片化與政策失敗的關鍵原因。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主體通過政策附加、政策敷衍、政策歪曲、政策抑制等[15]多種方式消極變通執(zhí)行相關政策,嚴重阻礙了職業(yè)教育的改革與發(fā)展。堵塞職業(yè)教育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漏洞不僅是職業(yè)教育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應有之義,更是職業(yè)教育各類改革不斷深化的必然要求,這就需要從職業(yè)教育政策環(huán)境、政策周期和治理體系三個維度加以審視和應對。
政策環(huán)境是引發(fā)職業(yè)教育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的外部因素,具有區(qū)域性、復雜性和易變性的特點,任何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都有賴于相應的政策環(huán)境。避免因政策環(huán)境引發(fā)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應著重從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政策制定階段的深入調(diào)研、反復論證。政策制定者應充分考慮各地自然、社會和人文環(huán)境的差異,尤其要調(diào)研各地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水平、產(chǎn)業(yè)結構和教育結構等,了解社會對職業(yè)教育政策的現(xiàn)實需求,使職業(yè)教育政策制定建立在堅實的社情民意基礎之上。二是政策正式執(zhí)行前的廣泛試點、充分檢驗。首先,保證試點樣本的代表性。試點樣本不是遴選出來的,而是隨機產(chǎn)生的,應避免政策試點的選擇性執(zhí)行,只有足夠代表性的試點樣本才能讓教育政策在正式實施前經(jīng)受充分的政策環(huán)境檢驗。其次,保證足夠量的試點樣本。樣本只具有代表性是不夠的,應保證足夠的樣本量。比如,職業(yè)教育高地建設試點,雖然教育部遴選了7 個整省試點和5 個城市試點,試點樣本涵蓋了東中西部,但樣本數(shù)并不足以涵蓋全國所有情況,尤其在一些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沒有相應的試點樣本。再次,試點的常態(tài)化。保證政策試點時的政策環(huán)境是常態(tài)環(huán)境,不能另外附加一些優(yōu)惠政策、獎勵政策,形成試點“小氣候”。三是政策執(zhí)行階段的預案準備、路徑選擇。改變政策執(zhí)行只有一條路徑、一種樣式的現(xiàn)狀,制定多樣化的政策執(zhí)行預案和多元化的政策執(zhí)行路徑,國家層面為政策執(zhí)行可能遇到的“水土不服”準備好“廣譜藥方”,地方層面更要為可能遇到的政策梗阻準備好“特效藥方”。
政策周期存在階段性缺陷是職業(yè)教育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的內(nèi)部因素,政策周期包括政策制定、執(zhí)行、評估、監(jiān)控、調(diào)整等環(huán)節(jié),最后歸于終結的整個過程[16]。由此,政策制定不是政策的終結,政策執(zhí)行也不是政策的終結,政策應該是一個不斷“升級”的過程,所有的政策都有周期,都在周期內(nèi)發(fā)揮政策效應,一旦政策效應衰減至一定水平,就必然會被新的政策所取代。當前,政策周期存在的階段性缺陷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政策評估機制不健全。政策執(zhí)行的過程怎樣、執(zhí)行的效果怎樣,目前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評估機制,正因為評估機制的缺失,為消極變通執(zhí)行開了“后門”,健全政策評估機制是堵塞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漏洞的現(xiàn)實需要。二是政策監(jiān)控機制不健全。對政策執(zhí)行的全過程實施監(jiān)控是保證政策執(zhí)行不走偏的應然舉措,應設置常態(tài)化的政策執(zhí)行監(jiān)測機構,適時進行大數(shù)據(jù)政策執(zhí)行數(shù)據(jù)采集,全面把握政策執(zhí)行動態(tài)過程,讓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在大數(shù)據(jù)面前“現(xiàn)形”。三是政策調(diào)整機制不健全。通過全過程監(jiān)測和全方位評估,及時發(fā)現(xiàn)政策執(zhí)行中存在的問題,便于對政策作出適時的調(diào)整,而當下政策的調(diào)整機制并未有效建立。比如,《國家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十三五”規(guī)劃》中要求“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yè)教育招生規(guī)模大體相當”,然而當2015—2019年普職招生比持續(xù)擴大時,并沒有看到政策的適時調(diào)整。這種政策調(diào)整機制的不健全,進一步助長了職業(yè)教育政策的消極變通執(zhí)行。只有及時修補政策周期中存在的階段性缺陷,才能阻斷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的“鏈條”。
治理體系不完善是職業(yè)教育政策消極變通執(zhí)行的客觀因素。職業(yè)教育治理是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市場、公民個人等教育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職業(yè)教育事務的決策、管理與資源支持,共同或協(xié)同提供職業(yè)教育服務的過程[17],具有多元性和協(xié)同性的特點。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也應具有多元性和協(xié)同性,不依賴于單一的執(zhí)行主體,而是通過多元、多層級執(zhí)行主體的密切協(xié)同來推動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進而形成人人有責、各負其責、有錯問責的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責任體系。由于治理體系不完善,當下很多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仍存在單一主體的現(xiàn)象,而“底層官員的自主性和自由裁量行為往往服務自身利益而非公益”[18],這是導致政策消極執(zhí)行、任性執(zhí)行的組織根源。完善職業(yè)教育治理體系,就是將職業(yè)教育政策執(zhí)行置于一個共同體視域下,通過協(xié)商互助、多元協(xié)同來保證政策得以貫徹落實。
普遍存在的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折射出當前我國職業(yè)教育改革發(fā)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優(yōu)化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既要有政策執(zhí)行戰(zhàn)術層面的查漏補缺,更要有政策執(zhí)行戰(zhàn)略層面的體制機制改革,只有進一步深化職業(yè)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加快實現(xiàn)職業(yè)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才是破解職業(yè)教育政策變通執(zhí)行“頑疾”的長效之策。
注釋:
①20世紀70年代西方興起“執(zhí)行運動”(implementation movement)。其標志是1973年普雷斯曼和韋達夫斯基對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的政策項目——“奧克蘭計劃” 執(zhí)行進行了跟蹤研究并寫成了報告 《執(zhí)行——聯(lián)邦的計劃在奧克蘭的落空》一書。
②數(shù)據(jù)來源于2018-2020《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
③具體見教育部辦公廳、工業(yè)和信息化部辦公廳印發(fā)的《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學院建設指南(試行)》。
④2020年1月,國務院職業(yè)教育工作部際聯(lián)席會議第二次會議強調(diào)“鼓勵地方試點試驗,在東中西部選擇若干省或地級市先行先試,總結出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jīng)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