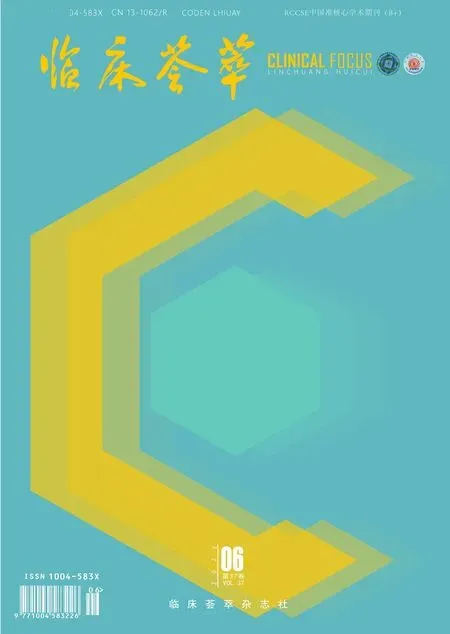單核細胞/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在心血管疾病中研究進展
張 怡,崔曉冉,楊曉紅
(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 心內六科,河北 石家莊 050000)
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目前仍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有顯著增長[1]。動脈粥樣硬化是一種進行性疾病,其特征是脂質和纖維成分在大動脈中積聚,進一步發展可能會導致血流受限,存在斑塊破裂的風險。單核細胞作為一種免疫細胞,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單核細胞可分化為巨噬細胞,上調吞噬活性,導致脂質堆積和泡沫細胞形成。這些細胞表達一系列炎癥因子和基質金屬蛋白酶,基質金屬蛋白酶負責基質降解,這可能與斑塊不穩定相關[2]。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可逆向轉運膽固醇,抑制單核細胞的遷移、活化及增殖,調節血管功能,有抗動脈粥樣硬化作用[3]。單核細胞/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monocyte to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atio,MHR)作為一種新型炎性標志物,整合了機體炎癥狀態及抗炎能力,其被證實與多種心血管疾病相關。本文就MHR在多種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為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分層及預后提供新思路。
1 MHR與冠狀動脈疾病

1.2MHR與支架內再狹窄 支架內再狹窄(in-stent restenosis,ISR)是支架對治療部位的動脈壁造成機械損傷的結果[10]。其發病機制常與血管內皮炎癥反應、血管外基質重構等相關[11]。Avci等[12]研究發現裸金屬支架治療后的STEMI患者ISR的發生與性別、支架長度、MHR相關,且是獨立有效的預測指標。另外,我國學者納入了214例的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患者,研究顯示,與無ISR的患者相比,ISR患者的術前MHR水平更高[13]。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分叉病變、血小板計數和MHR與ISR的發生顯著相關,多因素Cox回歸分析顯示,高水平的MHR是ISR的獨立危險因素,并且MHR在預測ISR方面具有良好的臨床價值。
1.3MHR與冠狀動脈慢血流現象 冠狀動脈慢血流現象(coronary slow flow phenomenon,CSFP)的發生可能與內皮功能障礙、炎癥、小血管病變、亞臨床動脈粥樣硬化、冠狀動脈解剖特性有關[14]。Canpolat等[15]對冠狀動脈造影正常的患者(CSFP組253例,對照組176例)進行回顧性了研究,結果顯示MHR與超敏C反應蛋白呈顯著正相關(r=0.352,P<0.01),說明MHR與全身炎癥反應密切相關。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MHR是CSFP的獨立危險因素(OR=1.24,95%CI:1.230-1.451,P<0.01),且預測CSFP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75.9%和68.2%(AUC=0.755,95%CI:0.707-0.802)。
1.4MHR與冠狀動脈無復流 無復流現象(no-refiew phenmomeon,NRP)是指在無主要心外膜冠狀動脈阻塞或血流受限的情況下,冠狀動脈血流量急劇減少[16]。目前已經提出了許多機制,如血栓碎片的遠端栓塞、內皮功能障礙、炎癥反應、微血管痙攣等[17]。NRP是STEMI患者行直接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的嚴重并發癥[18],增加了術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猝死等風險的發生。Balta等[19]的研究選取了600例STEMI患者,結果發現,MHR是STEMI患者行直接PCI術后無復流的獨立預測因子。在一項納入了426例非STEMI患者的回顧性研究中[20],分為慢血流/無復流組和正常血流組,結果顯示慢血流/無復流組MHR水平顯著高于正常血流組,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MHR、左心室射血分數、吸煙、血栓分級均是PCI術后慢血流/無復流的獨立預測因素。
2 MHR與高血壓
高血壓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炎癥和氧化應激導致的內皮損傷對其發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Aydin等[21]研究了原發性高血壓(primary hypertension,PHT)患者MHR與無癥狀器官損害(asymptomatic organ damage,AOD)的關系,研究選取了275例PHT患者和91例健康志愿者,結果顯示MHR與AOD指標(左室質量指數、尿蛋白量、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呈正相關,且MHR是PHT患者發生無癥狀器官損害的獨立預測因素。Kaplan等[22]研究發現MHR可用于預測高血壓患者的終末器官損害,其中包括左心室肥厚、視網膜病變、蛋白尿,也可用于區分非勺型和勺型高血壓。頑固性高血壓(resistant hypertension,RH)占到高血壓總人群的12%~15%[23]。Gembillo等[24]對214例慢性腎臟病合并高血壓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其中有72例診斷為RH,結果發現RH組的MHR水平顯著高于非RH組,通過多元回歸分析發現MHR是RH的獨立危險因素。在ROC曲線中,MHR預測RH的最佳截點為10.11,其敏感性為87.50%,特異性為88.03%(AUC=0.937,95%CI:77.6-94.1),但需要前瞻性研究來進一步來證實。高血壓患者常表現為左心房擴大,這是由于左心房壓力增加和炎癥所致[25]。一項橫斷面研究發現MHR、年齡、性別是高血壓的獨立預測因素,MHR升高與高血壓和左心房容積指數增加有關[26]。這項結果支持了炎癥的存在,也說明了MHR對高血壓患者左心房擴大具有預測作用。
3 MHR與心房顫動
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AF)是成人最常見的持續性心律失常,在弗雷明翰心臟研究的人群中,37%的患者在55歲以后發生了AF[27]。研究表明,炎癥參與心房基質的改變,與AF的發生發展有關[28]。急性心肌梗死后易并發AF,左心室舒張末期壓力升高、心房壓力增加、左心室功能急性惡化、心房缺血或梗死都可能導致AF的發生[29]。李虹敏等[30]的研究發現 MHR是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新發AF的獨立危險因素,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同樣,Ulus等[31]的研究也證實了MHR是老年急性冠脈綜合征(ACS)患者PCI術后新發AF的獨立預測因子,ROC曲線分析顯示,預測新發AF的截點為15.87,其敏感性為75.9%,其特異性為65.0%(AUC=0.750,95%CI:0.698-0.798)。
目前導管消融術已廣泛應用于藥物療效欠佳的AF患者,但術后晚期復發率仍較高[32]。一項回顧性研究選取了行射頻消融術的陣發性AF患者125例,平均隨訪時間(25.1±12.0)個月,晚期復發的有47例,研究發現,在預測射頻消融術后晚期復發方面,MHR的預測價值與左心房內徑相當,二者的ROC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712(95%CI: 0.618-0.806)和0.739(95%CI: 0.653-0.814)[33]。Canpolat等[34]研究發現MHR也是冷凍導管消融后AF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
外科手術也是治療AF的一種方式,標準的手術方法是迷宮手術[35]。然而,這通常需要與二尖瓣手術等其他心臟手術同時進行。基于射頻消融的迷宮Ⅳ手術被廣泛接受,為治療瓣膜病AF的有效方法。Adili等[36]回顧分析了131例持續性AF合并瓣膜病患者行射頻迷宮術后3個月的隨訪結果,有70例患者術后早期復發,結果顯示,MHR對AF早期復發具有顯著的預測價值,其敏感性為89%,特異性為54%。另外,有研究發現MHR對預測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AF的發生也有一定的價值[37]。
4 MHR與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是各種心臟病的終末階段,神經-體液-細胞因子過度激活是心力衰竭的重要病理生理機制,炎癥反應也參與其中。研究發現,約有25%的STEMI患者出現了心力衰竭[38]。在心肌損傷后數小時內,單核細胞迅速從骨髓和脾臟轉移到血液,滲透到梗死區并參與炎癥反應[39]。因此,單核細胞是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構的重要調節因子。HDL-C是一種公認的心血管保護因子,其特點是具有膽固醇逆向轉運活性以及強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特性。研究表明,HDL-C可減少氧化、內質網應激,阻止炎性細胞因子的分泌和釋放[40],這些都有利于預防心力衰竭。周瓊等[41]選取了102例射血分數保留心力衰竭患者,結果發現,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MHR顯著升高且與 NT-proBNP水平密切相關,提示MHR可能對慢性心力衰竭有一定預測價值。
5 MHR與其他心血管相關疾病
5.1MHR與代謝綜合征 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是一種促炎和促血栓形成狀態,其特征是炎性細胞因子活性增加。它與慢性炎癥和血管內皮功能障礙所致的動脈粥樣硬化加速有關,并顯著增加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42]。研究表明,MetS的最常見發病機制為胰島素抵抗,其他可能的機制包括慢性炎癥和氧化應激[43]。Uslu等[44]研究選取了147名MetS患者和134名年齡和性別匹配的健康人,結果顯示,MetS患者的MHR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且MHR是MetS的獨立危險因素。因而MHR可能是評估MetS患者的疾病嚴重程度的一種有用的炎癥標志物。
5.2MHR與急性主動脈夾層 急性主動脈夾層(acute aortic dissection,AAD)是一種危及生命的主動脈急癥,據統計,每100萬人中大約有5~30例發病[45]。炎癥參與了AAD的形成,多種炎性細胞的募集和激活導致血管平滑肌細胞凋亡,從而使血管壁脆弱,進而導致主動脈擴張、剝離,甚至破裂[46]。有研究發現,AAD患者的MHR水平較健康對照組顯著升高,且MHR值與癥狀出現的時間呈正相關[45]。除了高血壓和冠心病病史外,MHR水平是AAD發生的獨立預測因子,當MHR為最佳界值時,預測AAD的敏感性為86.70%,特異性為93.60%。另有研究選取了637例接受手術治療的急性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結果顯示,MHR與院內死亡率(OR=2.11,95%CI:1.16-3.85)和遠期死亡率(HR=1.78,95%CI: 1.31-2.41)獨立相關[47],提示MHR可能有助于識別院內和遠期死亡率高風險的患者,作為臨床實踐中的風險評估工具。
5.3MHR與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是一種與睡眠相關的呼吸障礙,其特征是夜間發生部分或全部上氣道塌陷,導致呼吸暫停/低通氣,伴有間歇性低氧和短暫覺醒。OSAS與心血管疾病風險增加有關,這與交感系統激活、氧化應激增加及內皮功能障礙有關[48]。同樣,炎癥在OSAS的發病機制中也起著關鍵作用。間歇性的缺氧啟動炎癥反應,炎癥激活OSAS中的促炎細胞因子和黏附分子,進而導致內皮功能障礙[49]。一項研究共納入246名高血壓患者(67名對照組、65名輕度、51名中度和63名重度OSAS),分析高血壓患者MHR和OSAS之間的相關性,結果顯示,OSAS組的MHR顯著高于對照組,此外,重度OSAS組的MHR在所有組中最高[50]。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MHR是OSAS(OR=1.152,P<0.01)和重度OSAS(OR=1.142,P<0.01)的獨立預測因子。在ROC曲線分析中,預測OSAS和重度OSAS的MHR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634和0.660。因而MHR有望成為評估高血壓患者OSAS風險和嚴重程度的一個可用指標。
5.4MHR與急性缺血性腦卒中 急性缺血性腦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的典型臨床表現是局限于單個大腦動脈血管區域的神經功能缺損的快速發作,顱內動脈粥樣硬化是其重要病因。一項基于中國農村人群的隊列研究分析了MHR與缺血性卒中患病率之間的關系,MHR水平最高的四分位數組發生缺血性卒中的風險(95%CI:1.045-2.524)是最低四分位數組的1.6倍,MHR與缺血性卒中的發病率之間存在相關性[51]。研究首次證明了MHR對中國農村成年人缺血性卒中有重要的預測價值,其預測價值高于傳統的臨床風險因素,從而為缺血性卒中患者的風險分層提供了臨床依據。此研究還發現MHR與發生AIS后3個月內的預后獨立相關(OR=2.58,95%CI=1.21-5.51),因此MHR可能是AIS患者不良功能預后的重要獨立預測因子。
6 小結
綜上,MHR是一種反映炎癥狀態的新型標志物,與多種心血管疾病相關并對其發展、預后有預測價值。MHR不僅具有穩定、高效等特點,還有經濟、臨床易獲得等優勢。一方面,MHR為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分層提供了依據,還為心血管疾病的預防提供了新思路。因此,臨床中應更加重視MHR的意義,我們期待有大規模、多中心的臨床試驗進一步探究其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