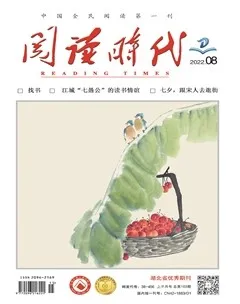什么是文學的真知
格非
我不太愿意解釋自己的作品,不太愿意給讀者太多的誘導。一部作品交到讀者手里時,應該有著百分之百的新鮮和神秘,需要讀者來介入,來尋找。寫作在某種意義上類似于我們小時候玩的躲貓貓,作者躲起來,設置重重機關,然后等待最終被讀者找到。而閱讀,反過來,就是讀者尋找作者的過程。讀者和作者在作品中彼此尋找,并由此建立起某種美學上的認同,這是小說最迷人的地方。
任何一個作家在寫作時都有意圖:要編織什么樣的故事,塑造什么樣的人物,傳達什么樣的思考,采取什么樣的修辭手段來讓作品得以完成,等等,我們把這稱為作家的意圖。而當作品到了讀者手里,它會出現另外一個意圖,敘事學把它稱為文本意圖。文本意圖是由文本本身帶出來的,和作家意圖完全不同。
由此引發出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作家設想的東西跟實際的作品呈現出來的東西會不一樣?
差異性的產生有兩個原因:
首先,任何作家都是有缺點的人,有局限性的人,這些缺點和局限會影響他的立場。當他開始寫作時,他就成為了我們所說的“有經驗的作者”。這里的經驗不是指寫作經驗,而是生活經驗。他會把自己日常的生活經驗、個人氣質、對社會的思考以及自己的價值觀都在寫作中代入到作品中來。
但與此同時,作家會在寫作過程中走到自己的反面,比如本來不喜歡一個人物,寫著寫著就喜歡上這個人物;或者本來對某種觀念深惡痛絕,寫著寫著發現這種觀念也有道理。我們把這種情況稱為“出現了一個模范作者”,這個作者是超越了“經驗作者”本身的——比如魯迅,他在實際生活中的思想跟他在《吶喊》《彷徨》等作品里呈現出的思想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說明什么?說明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會變得更好、更寬廣、接受度更高。他會在一個更大的空間里檢點自己的想法,甚至會放棄自己原先的想法。
其次,寫作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無意識的活動,作家能控制的部分是很有限的。以長篇小說的寫作為例:長篇小說的開頭很好寫,可以有一萬種開頭的方法,但結束卻很難。因為作家設置的所有人物、所有線索都已經決定了,這就意味著它們在后來的發展中必須遵循既定邏輯,從而強烈地牽制住作家,讓作家不能隨心所欲。
但是作家往往越寫到后來想法越多,甚至多到超出自己的某種預估。比如一些人物,會因為被賦予了性格而自說自話,生長出作家原先根本沒有想到過的內容,自動地展開故事。也就是說,人物具有了自主的生命。
第三,對于一部作品的閱讀和理解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所謂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當今天的讀者面對拉伯雷的《巨人傳》或者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時,對它們的解讀和幾百年前它們剛剛被完成時一樣嗎?當然不一樣。為什么經典常讀常新?一方面因為這些作品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的變化所導致,我們會站在一個歷史的新階段來重新審視作品里發生的故事,帶著當下對生活的理解。
文學到底是什么?
當我二十多歲從事寫作時,對于如何在小說里體現出某種知識和智力非常著迷。因為這種著迷,我對那種一眼可以看到底的故事沒有興趣,更希望在寫作中跟讀者進行一種智力上的游戲。所以我會寫一些所謂別具一格的故事,《迷舟》就是在這種心態下寫出來的。
但是最近這些年來,我的想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越來越多的寫作以娛樂讀者為目的,文學里最好的、最核心的東西被屏蔽了。這個東西,我稱為真知。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里告訴我們的東西很多,其中就包括什么是文學的真知。文學提供一個媒介,需要我們去了解生活,然后獲得我們對生活的某種感覺。
而這樣一種真知,在當下文學的創作和閱讀中都缺失了。
就創作層面而言,現代作家和施耐庵那個時代的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們能夠利用的資源不是歷史、神話和民間故事,而是我們的日常經驗,因為我們要描寫的是日常生活。這里涉及到的問題是:作家筆下的人物跟作家作為一個實際生活中的人到底是什么關系?也即所謂自傳性跟實際生活關系的問題。
日本評論家小林秀雄有一個觀點,認為從薩克雷、狄更斯以后,小說建立了無數的范式來描寫所謂客觀化、對象化的社會生活,而林林總總的社會生活又為寫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這使得小說家幾乎無所不能:沒有什么角色能把你難住,沒有什么領域是你無法觸及的。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現實主義小說家不是在寫小說,而是被小說寫。
這個論述讓我非常震撼,因為它揭示了一個問題:一個作者的特定修養、特定出身、獨屬于自己的情感結構和社會認知,甚至獨屬于自己的絕望和痛苦,在今天似乎已經沒有用了。也就是我在上文提到過的“有經驗的作者”,在寫作中越來越不重要。這導致小說在今天遭到的最大問題就是不具備任何神秘感,不帶有任何真正的情感,所有人物都可以互換而不具備特定性。一個寫作者盡可以把故事編造得非常復雜離奇,因為今天有大量社會新聞來為之提供模板,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藝。
在這種情況下,假設一個人具備很好的語言能力和講故事的能力,是不是一定能成為好作家?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再高的才華,再好的講故事能力,都無法幫助一個人真正寫出生活中哪怕一點點的、充滿光芒的真知。在小林秀雄的觀點里,文學中真正重要的是“獨一無二的人物”,而不是“宛如真實的人物”。我們之所以對文學作品中的有些人物不能忘記,正因為他是獨一無二的,他有強烈的特征。我們在孩提時代就記住的這些民間故事、這些歷史傳說,里面的人物飛檐走壁,有非常大的能量,具有某種傳奇性,不管他真不真實,他是獨一無二的。
這種刻畫人物的能力連帶著這樣的人物在今天的小說寫作中已經失去了。我們把筆下的人物當成是一個跟我們沒有關系的客體,只不過是我們把他定向化,把他變成社會的一個部分,我們來描述他,而不是像小林所強調的那樣:要寫好一個人物必須具備三樣東西,首先要尊重這個人物,第二要理解這個人物,第三要愛這個人物。實際上這并不是小林一個人的觀點。汪曾祺也說過,文學寫作最重要的前提是你要鉆到對方心里去;海明威當年教學生觀察人物時也提出過類似的要求,就是一定要跟人物心意相通。
你怎么了解一個人的心?只有通過愛,通過理解,通過真正的交往,所以這時候你要調動的是你真正的經驗,這個東西我把它稱為文學當中的真知。這種真知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被掩蓋了。然而如果這樣的真知跟你筆下的世界沒有關聯,我們怎么跟讀者之間建立真正的聯系?
真知的缺失同樣存在于閱讀層面。很多人在讀了小說之后就去模仿小說,用小說來指導自己的生活。《包法利夫人》里的愛瑪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這樣的讀者,她讀了大量的浪漫主義小說,覺得生活中充滿浪漫,一生就應該這樣過,她的生活觀在她沒有進入實際生活之前已經奠定了,所以整天做夢,夢見一個英俊的、風度翩翩的人,跟自己在燈下跳舞,但是她偏偏嫁給了一個獸醫,這個人很木訥,半天不說一句話,也掙不了幾個錢,這導致了她生活最終的崩潰。
閱讀不是為了模仿,對于讀者來說,文學作品里真正可貴的是那一點真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文學跟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它可以幫助我們改變生活,而且應當幫助我們改變生活,但它絕不是說我們直接模仿小說里的人物,而是需要我們綜合理解作品里的智慧,找到寫作者對存在的、理解的態度,然后獲得某種感知,把這種感知用于你的實際生活,如果得到印證,真的能夠幫到你,才會成為真正有用的東西。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重塑文學和生命、和生活的關系,才能在文學和生命、和生活之間,建立起某種深刻的聯絡。
(源自《文匯報》,有刪節)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