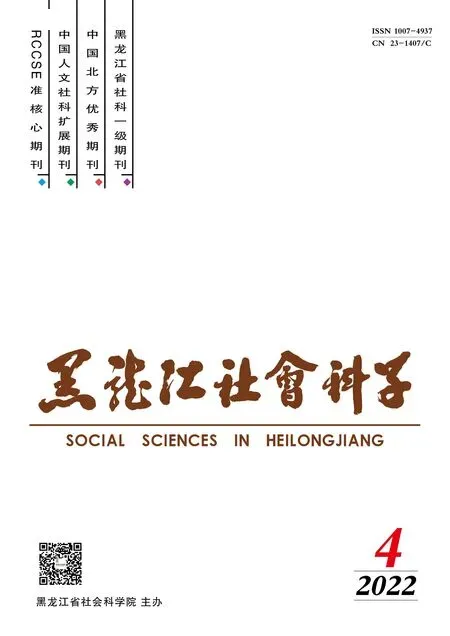《金史·食貨志》修纂考
陳 曉 偉
(復旦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433)
《金史·食貨志》(下文簡稱《食貨志》)記載有金一代經濟總況,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其史源亦受到學者的關注。元初王鶚《金史大綱》列“帝紀九”“志書七”及“列傳”,三大門類計二十四細目[1]卷8,181,陳學霖(Chan Hok-Lam)據此認為,元末編修《金史》基本沿襲了王鶚擬就的這份凡例,并且書中有部分內容直接脫胎于王鶚《金史稿》。證據是,《百官志》《食貨志》稱哀宗為“義宗”,此乃金亡后王鶚輩采用的私謚[2]。梁方仲《十三種〈食貨志〉介紹》亦持今本《食貨志》源于王鶚說[3]。邱靖嘉全面論述王鶚之貢獻,提出《金史》卷46《食貨志一》前有一篇長篇序文,深刻剖析了金代財賦制度、錢幣之法的利弊得失及其對金朝覆亡的影響,很有可能是元初修史時王鶚等金遺民的辨亡之辭[4]89-111;又《金史大綱》志書有“食貨(交鈔附)”,大概今本《食貨志》是在王鶚稿本基礎上修訂而成的[4]169-170。曾震宇提出,《食貨志》的內容系主要抄自金朝的《實錄》《國史》及地方路、府、州、縣田賦及稅收檔案而成[5]。
不過,我們通檢《金史》全書,逐條核查卷46~50《食貨志》五卷史文,得出的結果則與上述觀點齟齬不合,并且有幸從中探明至正初年史官編纂《金史》志書的一般模式,證明《食貨志》應該全部修成于至正時期,與王鶚無涉。
一、從《食貨志》序文中的“奴婢戶”概念談起
卷46《食貨志》總序歸納金代戶口類型曰:“其為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6]1028對于“奴婢戶”的性質,學界分歧甚大:王曾瑜認為金朝奴婢在總人口中占有一個相當大的比例,確實存在“奴婢戶”[7]。宋立恒支持此說[8]。劉浦江則指出,“奴婢戶”一詞在《金史》中僅此一見,在當時只是泛稱或習稱,既非金朝實際存在的戶類,亦非戶籍制度中的正式戶名[9]。張博泉等意識到,“奴婢戶”乃是《金史》作者概括出來的[10]。諸家似乎未能從根本上揭示問題之源頭所在。
細檢卷46《食貨志》全文,以上諸類戶口于正文中均有對應記載:
第一,課役戶、不課役戶。《戶口》云:“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無夫為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為丁。戶主推其長充,內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
第二,本戶、雜戶。《戶口》云:“明昌六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回避女直、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漢戶及契丹,余謂之雜戶。’”
第三,正戶、監戶、官戶。《戶口》云:“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
第四,二稅戶。《戶口》云:“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為民。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遼亡,僧多匿其實,抑為賤,有援左證以吿者,有司各執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
將史文逐一排比,知“奴婢戶”一詞顯然源自第三條。按徐元端《吏學指南》良賤孳產條亦謂:“官監戶,謂前代以來配隸相生,或今朝配役,屬諸司州縣無貫者,即今之斷按主戶是也。其斷沒者,良人曰監戶,奴婢曰官戶。”[11]意謂金朝斷沒者根據身份來區別,良人為監戶,奴婢則是官戶,這與《食貨志》文義相一致。總序作者蓋據“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提煉出“奴婢戶”,實則是對史料理解有誤。那么,從衍生的“奴婢戶”概念判斷,這篇序文恐非評論時弊的金人之作,而僅僅是總結史文。
這樣,由“奴婢戶”概念切入,對《食貨志》“戶有數等”記載進行考察,從而揭示出其全部內容出自本卷《戶口》諸條系事。據此線索,我們全面分析這篇1500余字的總序,可將其所涉具體史事細分為兩種情況:
第一種,與志書正文相關照。
首先,總序云:“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咨及其增減,則州縣征求于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凡此諸名目,詳見于:卷47《食貨志二·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卷48《食貨志三·錢幣》:泰和元年(1201)六月,宰臣謂“宜令諸名若‘鋪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興定元年(1217)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壞,制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征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挽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
其次,總序云:“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窯冶。”《食貨志三·錢幣》寫作:“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后,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制交鈔,與錢并用。正隆二年,歷四十余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兩者內容基本相同。
最后,總序云:“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卷50《食貨志五·入粟鬻度牒》則言:貞祐二年(1214),“從知大興府事胥鼎所請,定權宜鬻恩例格,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與前者相合。
以上三則總序內容與《食貨志》正文內容大體吻合。這樣來看兩者之本末關系,顯然總序是據《食貨志》正文總結而來,而不是元末修志書時將所謂王鶚舊有序文條目分類拆解、擴充其中的。更有說服力的是,上述《食貨志》三條正文還能查出更為原始的出處:《食貨志三·錢幣》泰和元年六月條,即卷11《章宗紀三》所載泰和元年六月乙巳“初許諸科征鋪馬、黃河夫、軍須等錢,折納銀一半,愿納錢鈔者聽”;同卷《錢幣》所載“正隆二年,歷四十余歲,始議鼓鑄”,即指卷5《海陵紀》所載正隆二年(1157)十月乙卯“初鑄銅錢”;《食貨志五·入粟鬻度牒》所載貞祐二年從胥鼎所請定權宜鬻恩例格,卷108《胥鼎傳》則有較詳細的記載[6]2373-2374。據此可以推測出一個合理的編纂順序:《章宗紀》《海陵紀》《胥鼎傳》據相同的原初文獻編纂,《食貨志》同樣加以采摭,而其序文蓋據志書相關條目歸納。
第二種,本紀、列傳能夠印證相關說法。
如總序謂:正隆年間,“凡產銅地脈,遣吏境內訪察無遺”,《海陵紀》則載:正隆三年二月甲午,“遣使檢視隨路金銀銅鐵冶”;總序謂:“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章宗紀三》則載:承安三年(1198)十月丁亥,“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設回易務,更立行用鈔法”;總序謂:“高琪為相,議至榷油”,卷15《宣宗紀中》則載:興定三年四月庚寅,“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請榷油,歲可入銀數萬兩,高琪主之,眾以為不便,遂止”;總序謂:“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卷14《宣宗紀上》則載:貞祐四年八月甲寅,“三原縣僧廣惠進僧道納粟多寡與都副威儀及監寺等格,從其言鬻之”。這四條均與本紀有關。此外,總序謂:“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卷92《曹望之傳》則載傳主上書論便宜事說:“論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易之,過期以銷錢法坐之。”[6]2039可見以上記載分別與本紀、列傳相合。
序文中還有一條并見于紀、傳的史文,即:“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而卷2《太祖紀》則謂收國二年(1116)五月,“東京州縣及南路系遼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卷71《斡魯傳》所載文字相同[6]1633。由此可見,《食貨志》序文與紀、傳皆有關,但并不是采自今本《金史》自身,而是意味著存在同源關系。
根據以上所述兩種情況可知,《食貨志》篇首序文并不是一篇獨立的撰述,其所涉諸事的文獻源頭,乃與本志正文內容及同書本紀、列傳密切相關。根據所列諸條文獻所呈現出的相互聯動關系判斷,《食貨志》全文當出自一批人之手;從總結史文過程中錯誤歸納出“奴婢戶”的概念判斷,編纂者不大可能是具備較高史學素養且熟諳金史的王鶚。
二、以本紀為主線探索《食貨志》的史料來源
要想徹底厘清《食貨志》的編纂問題,最有效的手段當數一條條地核查整個志書的史文。在此探源過程中,我們發現《食貨志》其實與本紀直接相關。《食貨志》五卷史文,今檢到與本紀相合者如下:
卷46《戶口》有14條:《章宗紀》泰和六年正月辛丑,《太祖紀》收國二年二月己巳、天輔五年二月、七年四月癸巳,《太宗紀》天會元年十一月己巳、十二月甲午、二年正月戊午、四月乙亥、三年七月壬申、七年三月壬寅,《熙宗紀》皇統四年十月甲辰,《世宗紀》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章宗紀》明昌元年正月戊辰,《宣宗紀》興定元年十二月庚午;《通檢推排》有6條:《世宗紀》大定四年十月己卯、五年十一月癸亥、二十六年八月丁亥,《章宗紀》承安二年十月壬午、泰和二年閏十二月辛酉、八年九月甲子。
卷47《田制》有10條:《太宗紀》天會九年五月丙午,《熙宗紀》天眷元年二月己巳,《世宗紀》大定十一年正月戊戌、二十一年正月壬子,《章宗紀》明昌五年二月丁酉、承安二年十二月癸未、泰和四年九月壬申,《宣宗紀》貞祐三年七月辛酉、十月丁亥、十一月庚午;《租賦》有25條:《章宗紀》泰和五年三月癸亥,《太宗紀》天會十年正月壬子,《世宗紀》大定三年三月庚戌、五年正月辛未、六年十月甲申、十六年正月甲寅、十七年三月辛亥、十八年正月庚申、十九年二月乙卯、二十年三月乙丑、二十六年四月壬戌、二十七年六月戊寅、十一月甲寅,《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七月辛酉、明昌三年六月乙丑、九月庚午、己卯、五年十二月丁卯、泰和四年四月甲寅、五年正月乙亥、八年六月癸未,《宣宗紀》貞祐四年正月庚辰、興定二年二月甲辰、四年七月癸丑、十二月乙酉;《牛頭稅》有3條:《太宗紀》天會三年十月壬戌、五年九月丁未,《世宗紀》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
卷48《錢幣》有24條:《海陵紀》正隆二年十月乙卯、三年二月壬辰,《世宗紀》大定十九年八月戊戌、二十七年二月癸未,《海陵紀》貞元二年五月丁卯,《章宗紀》明昌三年四月丙午、五年三月壬申、承安二年十二月己卯、三年十月丁亥、泰和元年六月乙巳、四年七月甲戌、六年十一月戊戌、七年七月壬午、八年正月癸酉、八月壬申,《宣宗紀》貞祐三年四月癸巳、七月甲申、四年正月癸亥、興定元年二月戊申、三年十月壬申、四年十二月乙酉、五年閏十二月己酉、元光二年五月丁巳,《哀宗紀》天興二年十月戊寅。
卷49《鹽》有4條:《海陵紀》貞元二年七月庚申,《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章宗紀》泰和四年十月甲午、七年九月甲申;《醋稅》有1條:《章宗紀》承安三年三月壬寅;《茶》有4條:《世宗紀》大定十六年十二月庚寅,《章宗紀》泰和六年十一月庚子、七年正月己亥,《宣宗紀》元光二年三月辛酉;《諸征商》有3條:《海陵紀》貞元元年五月乙卯、七月戊子,《世宗紀》大定二年八月辛卯。
卷50《榷場》有4條:《海陵紀》正隆五年八月辛亥,《世宗紀》大定二十一年正月壬子,《章宗紀》承安二年九月乙巳、三年十月癸未;《金銀之稅》有2條:《世宗紀》大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章宗紀》明昌五年九月戊辰;《和糴》有4條:《世宗紀》大定九年正月庚午、十六年九月己酉、十七年三月乙丑,《宣宗紀》貞祐四年四月丙申;《常平倉》有2條:《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乙酉、三年十月甲寅;《水田》有3條:《章宗紀》明昌六年十一月戊申,《宣宗紀》興定五年十一月庚寅、元光元年正月壬子;《區田之法》有1條:《章宗紀》承安元年四月戊午;《入粟鬻度牒》有4條:《世宗紀》大定二年正月庚寅,《章宗紀》明昌二年八月己亥,《宣宗紀》貞祐三年九月丁丑、四年八月甲寅。
以上總計114條,約占《食貨志》1/3篇幅。這些相對應的條目,多有文字雷同者,一般是志詳而紀略,由此可以確定它們有共同的源頭。
除與諸本紀相互契合外,《食貨志》與列傳相合的史文條目也很多。卷46《戶口》載,天輔五年(1121),“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鹵,將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昱等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摘諸猛安謀克中民戶萬余,使宗人婆盧火統之,屯種于泰州”。這條記載不僅與《太祖紀》天輔五年二月條吻合,大致相同的情節還見于卷71《婆盧火傳》中[6]1638。值得注意的是,《食貨志》中“婆盧火舊居阿注滸水”一句的“又作按出虎”這條小注,則與《婆盧火傳》“婆盧火舊居按出虎水”有所關照,表明原文中該河名有兩種寫法,這兩條史料具有同源關系。屬于同類情況的還有,《食貨志五·和糴》和《宣宗紀》均載貞祐四年四月丙申河北行省侯摯言“北商販粟渡河”事,卷108《侯摯傳》同[6]2386。又如,《食貨志一·通檢推排》所載“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與卷76《永元傳》所載[6]1745;《食貨志三·錢幣》所載大定二十六年(1186)上曰“中外皆言錢難”及太尉丞相克寧曰“民間錢固已艱得,若盡歸京師,民益艱得矣”與卷92《徒單克寧傳》所載[6]2049,所載泰和八年十月孫鐸言與卷99《孫鐸傳》所載[6]2194;《食貨志五·榷場》所載興定元年集賢咨議官呂鑒言與卷106《術虎高琪傳》所載[6]2344:《食貨志》與本傳文字都能夠一一對應。
而通過卷107《高汝礪傳》[6]2351-2363則能全面看出《食貨志》、紀、傳三者之關系(見文尾表1)。
表1所列,《食貨志》通檢推排、田制、錢幣、鹽、金銀之稅、和糴六門凡涉“高汝礪”15條,其中有5條在《高汝礪傳》中有文辭相近的記載,而《章宗紀》承安二年十月壬午,《宣宗紀》貞祐三年八月癸巳、十月丁亥、十一月庚午4條亦正相合;另,《食貨志》泰和七年七月壬午條,《章宗紀》有而《高汝礪傳》無。根據上述志、傳、紀史料互相雷同的情況,可以證明三者間非直接傳抄,也就是說,不是志書從本傳、帝紀中裁剪史料,而是三者應有同一源頭,此即實錄無疑。那么,今本《食貨志》《高汝礪傳》與章宗、宣宗紀相重合的4條,就當本諸《章宗實錄》承安二年十月壬午及《宣宗實錄》貞祐三年八月癸巳、十月丁亥、十一月庚午諸條。此外,《高汝礪傳》所載泰和六年六月“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云云,《食貨志三·錢幣》有相應條目印證,這種兩者相合而本紀無,乃至唯見于志書者,仍當是取自實錄,只是因為三者體例所需史料取舍標準不一致而已。

表1 《食貨志》與本紀、列傳史文對比
而將《食貨志》與《胥鼎傳》[6]2373-2384進行對比,更能說明問題(見文尾表2)。
表2所列,《食貨志》錢幣、入粟鬻度牒兩門共4條涉及“胥鼎”,相關內容亦見于《胥鼎傳》,且后3條文字大致相同,均當取自實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第1條,《錢幣》載貞祐三年四月胥鼎上言“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民力征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云云,即《胥鼎傳》所言“建言利害十三事”之“鈔法”,但后者未載具體內容,今檢《宣宗紀》貞祐三年四月癸巳條,所言“河東宣撫使胥鼎言利害十三事”與之吻合。據此可以證明,《金史》志、傳、紀互見相同史文,當系同源,這一條當是共同采據《宣宗實錄》貞祐三年四月癸巳條。

表2 《食貨志》與列傳史文關系
要之,《食貨志》乃是元末史官直接采摭諸帝實錄編纂而成,這在今本《金史》中還有許多證據。如,《世宗紀》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條簡記“括定猛安謀克戶口田土牛具”,而相關最原始的具體統計數據不僅見于《食貨志一·戶口》,亦載于《食貨志二·牛具稅》。又如,卷16《宣宗紀下》興定四年十二月乙酉條云“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幣、稅賦二事”,而《食貨志三·錢幣》和《食貨志二·租賦》則各自保存了與本門類主題有關的思敬上書言事的原始內容。可見,根據不同專題門類和實際情況,前者是兩次重復利用《世宗實錄》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條,后者則是分別歸類抄錄《宣宗實錄》興定四年十二月乙酉條。《食貨志》征引實錄,相比于敘述較為簡略的本紀,一般較多地保留了原始文獻。
以上為《食貨志》與本紀、列傳比較的結果,而其他志書同樣遵從這種編纂模式,是為重要旁證。上引《世宗紀》及《食貨志》錢幣、租賦兩門所載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括定猛安謀克戶口田土牛具”云云,在卷44《兵志·兵制》中也有雷同表述,并且還多出“是時宗室戶百七十”等內容[6]996。另外,《食貨志二·田制》載興定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魯言”云云,《兵志·養兵之法》亦記之,并且注明“語在《田制》”。而更典型的一例是,《宣宗紀上》記有貞祐四年正月癸亥“監察御史田迥秀條陳五事”,但省書“五事”具體內容,不過在諸志中則有所保留。《食貨志三·錢幣》載貞祐四年正月:
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余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偽造寶券官賞。
又卷58《百官志四·百官俸給》載:
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行才數月,已后停滯,所患在支太多、收太少,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收,庶可久也。”因條五事,“一曰朝官及令譯史、諸司吏員、諸局承應人,太冗濫宜省并之。隨處屯軍皆設寄治官,徒費俸給,不若令有司兼總之。且沿河亭障各駐鄉兵,彼皆白徒,皆不可用,不若以此軍代之,以省其出”[6]1353-1354。
兩志所載田迥秀條陳“五事”緣起,文字基本一致。不過,《食貨志》抄錄了此五事條目,而《百官志》則只收錄了與門類主題有關的“省冗官吏”“節兵俸”“罷寄治官”這三條及其具體措施。關于第二條“損酒使司”,《食貨志四·酒》載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后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員,虛費月廩,宜依大定之制。”綜合本紀和兩志可知,監察御史田迥秀條陳五事的記載當源于《宣宗實錄》貞祐四年正月癸亥條。
而論者根據今本《金史》哀宗被稱為“義宗”的兩條材料,證明《食貨志》源自王鶚《金史稿》,這樣的看法存在很大的破綻(邱靖嘉承陳學霖之說,對王鶚采用“義宗”謚號及今本《食貨志》《百官志》本諸《金史稿》有詳細論述)[4]108-110。《金史》卷18《哀宗紀下》載:“帝自縊于幽蘭軒。末帝退保子城,聞帝崩,率群臣入哭,謚曰哀宗。”[6]403王惲《玉堂嘉話》敘王鶚履歷云:“后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為變色。仍私謚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1]卷1,41-42《大金國志》解釋王鶚等亡金士人改謚之緣由說:“后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謚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或謂哀不足以盡謚,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謚。”[12]可知“義宗”“哀宗”并見于史。
采用哪一種謚號,大概不過是金末元初士人的習慣而已,如元好問的文章均稱“哀宗”,許衡《編年歌括》[13]、王惲《金故忠顯校尉尚書戶部主事先考府君墓志銘》[14]及《玉堂嘉話》(“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云云)[1]卷7,165-166等亦采該謚號。而盡管王鶚《汝南遺事》稱作“義宗皇帝”[15],然而其所擬《金史大綱》“帝紀九”則謂“哀宗”[1]卷8,181,看來用法尚不一致。因此,根據謚號來推測文獻來源并不可靠,很難說《金史》有“義宗”的字樣就可證其源于王鶚舊稿。
上文表明,元人是以實錄為依據編纂《食貨志》《兵志》及《百官志》相關內容的。據此,可以重新檢討《金史》有關“義宗”的兩條記載。第一條,《食貨志三·錢幣》載“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未見相應記載。第二條,卷55《百官志一》載“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略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必列于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6]1216,則有線索可循。卷56《百官志二·益政院》載:“正大三年置于內庭,以學問該博、議論宏遠者數人兼之。日以二人上直,備顧問,講《尚書》、《通鑒》、《貞觀政要》。名則經筵,實內相也。”[6]1280此與卷17《哀宗紀上》正大三年(1226)八月辛卯條所載“詔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楊云翼等為益政院說書官,日二人直,備顧問”同源,當是共同采摭哀宗朝留存的日歷檔案而成。從史料傳承源流看,《百官志》篇首之“義宗”云云系作為序文,以與正文內容相關照,當是元末史官的手筆。
綜上所述,我們揭示了至正修史不僅以實錄為藍本編纂諸志,而且從中檢點個人事跡編入本傳的過程,由此從《金史》編纂的整體文獻環境坐實了《食貨志》作者及史源問題。總之,《食貨志》非出自王鶚之手,乃是元末新修。
三、元修《金史》志書的編纂模式及其問題
上文我們以本紀為主線結合列傳等對《食貨志》進行了全面探源,證明其直接抄撮自實錄。該志“金銀之稅”門中的一項疏漏則對史官編排文獻的細節有所呈現。按卷49《食貨志四》設有“金銀之稅”一門,但正文較為單薄,僅有大定三年、泰和四年、七年三月3條[6]1111,然而卷50《食貨志五》“榷場”“和糴”兩門間復見“金銀之稅”條目,此下共系有大定五年、九年、十二年、二十七年、明昌二年(1191)5條[6]1116。《金史》點校者指出:“當是本書上卷《食貨四》金銀之稅條之文,誤置于此。”[6]1127細繹各條史文,我們發現《食貨志五》這5條系年正好介于《食貨志四》大定三年、泰和四年兩條之間,它們當構成一個完整內容。若論原始出處,大定十二年“詔金銀坑冶,恣民采,毋收稅”條與《世宗紀》大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詔金、銀坑冶聽民開采,毋得收稅”條若合符契、明昌五年“以御史臺奏,請令民采煉隨處金銀銅冶,上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議謂”云云與《章宗紀》明昌五年九月戊辰“初令民買撲隨處金、銀、銅冶”之記載相合,由此可以確認這兩條史文來自世宗、章宗實錄。對于上述《食貨志》門類重出的問題,最合理的解釋是:史官從實錄中檢出有關條目擬歸類為“金銀之稅”,但在整合分篇環節粗疏不慎,遂將其拆分到兩卷而又未暇統稿。我們以諸種細節為線索,綜合上文《食貨志》與本紀同源自實錄的考證結果,可復原今本《食貨志》編纂的一般流程:至正修史時,史官首先全盤梳理諸帝實錄,從中摘錄出各種“食貨”類史料,然后分門別類,最后厘定為“戶口”至“入粟鬻度牒”十八個門類。《金史》其他志書的修纂當仿此。
《食貨志》的史料雖來自實錄,但經過元人的摘抄、拆分、整合,不免有失,筆者將其歸納為四種類型:
第一,斷章取義,節抄史料失當。《食貨志一·戶口》謂興定四年:
時河壖為疆,烽鞞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僅從此處文義看,“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一語似承“亳州戶舊六萬”。而卷104《溫迪罕達傳》敘其興定時仕履云:
改集慶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薦饑,達上疏曰:“亳州戶舊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為州?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為減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憂兵食,達謾聞二縣無主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萬斛,即具奏[6]2294。
經比較可知,志、傳同源。根據今本《溫迪罕達傳》較完整的史文可知,乞量減免賦役才是其上言的內容和目的,而“碭山、下邑野無居民”則為緣起,《食貨志》僅抓住“戶口”這個字眼,節略粗率,以致興定四年條史文語焉不詳。
第二,編排不慎,造成史文重復。《食貨志四·鹽》云:
(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
時既詔罷乾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寧推官宋扆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余貫為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為額。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后一條文末“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一句明顯與前一條重復(參見《金史》該卷校勘記[5])[6]1111。今檢卷9《章宗紀一》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條有“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仍罷巡鹽使”之記載(點校者將“巡鹽使”校改作“西京、解鹽巡捕使”)[6]213、226,知《食貨志》上述記載來自《章宗實錄》是條。其中第一條僅節略大意,第二條則抄錄原文。由于兩者文字相差較大,志書編纂者未加辨析一并收錄其中,由此導致復文。
第三,望文生義,無關條目闌入。《食貨志五·榷場》謂正隆五年八月“命榷場起赴南京”,此條與卷5《海陵紀》是年八月辛亥條“命榷貨務并印造鈔引庫起赴南京”同源于《海陵實錄》。關于“榷貨務”的職能,卷56《百官志二》記載稱,“在京諸稅系中運司,見錢皆權于本務收”,以及“掌發賣給隨路香茶鹽鈔引”[6]1283。《海陵紀》的記載與此旨意相合。點校者指出,“此處蓋修史者誤以榷貨務為榷場”[6]1126。
第四,系年有誤,以致時序淆亂。《食貨志二·租賦》謂:
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稅,恐廩粟積久腐敗。省臣奏曰:“臣等議,大定十八年戶部尚書曹望之奏,河東及鄜延兩路稅頗重,遂減五十二萬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以歲入度支所余無幾,萬一有水旱之災,既蠲免其所入,復出粟以賑之,非有備不可。若復欲減,將何以待之。如慮腐敗,令諸路以時曝涼,毋令致壞,違者論如律。”制可。
點校者注意到省臣奏曰“去年赦十之一”指上文“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事,故“四月”前當補“明昌元年”(《金史》該卷校勘記[13])[6]1066。不過該條下又載:
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南荒閑官地,許人計丁請佃,愿仍為官者免租八年,愿為己業者免稅三年”。詔從之。
這與《食貨志二·田制》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條相同[6]1049。則上述兩條引文顯然時序顛倒,當是編者未能理順史文編年。
從以上四個例子及“金銀之稅”一門重出,可見《食貨志》編纂之硬傷。此乃緣于至正纂修《金史》并無成熟的稿本可供參用,遂從實錄中逐條摘取相關史文,匆忙之下疏漏難免。所幸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實錄原貌,甚至可以據此質證本紀。例如,《宣宗紀》載:
(興定五年十一月)庚寅,募民興南陽水田。
此事并見于《食貨志五·水田》:
(興定五年)十一月,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于南陽灌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為新陂,通運二百余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之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獲多于陸地數倍。”敕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依陸田,不復添征,仍以官賞激之。
若按編纂習慣,本紀一般記述議事的結果,故《宣宗紀》此條當取《食貨志》此條末尾“敕令”內容。但其卻不當節取“省奏”所引“南陽灌溉”的歷史典故,而“募民”則是概括“有可開者誘民赴功”,結果將“省奏”“敕令”混為一談,所謂“興南陽水田”也明顯乖離原意。
梁方仲通觀歷代正史《食貨志》之編纂,認為《金史·食貨志》質量很高,“在十三種《食貨志》中是寫得比較成功的一部”[3]。據本文考證,根源在于其所據史料直接出自諸帝實錄。通過對《金史·食貨志》史料構成及編纂過程的分析,希望做到:首先,進一步解決《金史》纂修問題;其次,厘清金代經濟史研究中的文獻基礎;最后,為歷代《食貨志》研究提供一個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