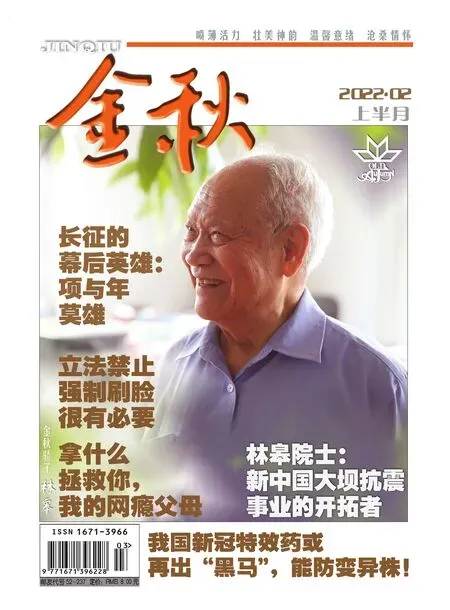憶邵光同廠長的坦蕩和正氣
※文/曹鋼

我1970年11月去陜北子洲縣農機廠當學徒工,1972年4月離開那里去陜西師范大學學習。在這18個月的經歷中,我見證了副廠長邵光同的率直真實、坦蕩正氣和勇于擔當。
1970年10月,“插隊”已滿兩年的我,符合招工條件,便報名申請去農機廠當學徒。但縣政工組給我反饋的信息是:農機廠的革委會副主任邵光同不愿接收我(盡管我與他并不相識,甚至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理由是他與我在“文革”中不是一個“派”的,他是造反派,我是保守派,而且我還被造反派關押整治了近7個月,兩派間確實積蓄了不小的恩怨。如果我去廠里,他“不好管理”。但是我堅持要去,我想我是去當學徒、學技術,又不是去鬧派性。
我一進廠就和近20名老工人和幾個新招來的學徒工跟著老邵為安裝機床當小工。每一個機床基礎的處理,從放線、挖坑、布管道,到定機座、校正螺絲桿、做混凝土,一切都聽他指揮,直至把3個車間的機床全部安好。起先我以為他是搞技術出身,是個“內行”,一打聽才知道,他從娃娃開始就在部隊當通信員,還去過朝鮮戰場。轉業后在西安培訓了一段就分配工作,去年才到我們廠。但他很愛鉆研,每干一件事總要想法子搞明白。這次安裝機床,事先他把所有的說明書都鉆研了一番。聽了這個情況,我不由對他產生了敬重之心。
春節后,我們學徒工正式分配崗位了,我被分配到車工車間,但卻把僅保留下來的那臺老皮帶車床分給了我。那時我的感覺是:老邵在跟我較勁!我的任務是加工架子車軸皮,最大難度是加工機件難固定。十幾厘米長的毛坯,只有不足一厘米的邊可夾,運轉稍微快點便搖擺起來,不是掉了下來,就是發生打刀。一個班苦苦站上8個小時,最好時也只能加工七八個成品。干了一段時間后,我找到了一點感覺,讓師傅幫我做了個能夾緊加工件的模具,于是一個班可做出二十四五個成品。聽到這個消息,老邵專門到我的機床邊看了一會,離開時第一次面帶微笑地向我點了點頭,猶如監考老師看到考生的滿意答卷一樣。
邵廠長的家屬還在山東,他的辦公室也是宿舍。每天晚間不工作了,他便找人聊天。我宿舍的兩位師傅最同他談得來,所以幾乎每天晚上,他都會來我們宿舍。豪爽的山東漢子放開嗓門說話,語速又快,打開話匣子,一口氣可講個把小時。這時的他變得十分隨和,上班時的那股嚴肅勁一點也沒有了,甚至同工人們稱兄道弟。我雖然獨自坐在旁邊看書,但也能體會到他的直率而真實。
1971年夏秋之際,子洲縣也照地區的樣子開了個大會,提出對我(我曾是子洲中學我們這派學生組織的負責人)等幾個原群眾組織的頭頭進行批判。縣上的一個專案小組進駐了農機廠,直接負責查證揭批我的問題,不但把我降到鍛工班去掄大錘,而且還召開對我的全廠批判大會。奇怪的是老邵在大會小會甚至是閑談中,從未介入過我的事,老工人中對立派的那些人也沒有誰乘機發泄私憤。我心里很清楚,老邵雖是個副職,但在廠里是一言九鼎,他的不介入就是表態,就是無形中給了我一定的保護。最后這段運動到年底便草草收場,專案組也無聲無息的不見了。
這年春節剛過,國家突然宣布已停辦多年的大學重新招生,但并不考試,而采取“推薦方式”在工農兵中選拔。縣上給農機廠分了兩個推薦名額,我知道在這上百個青工中,論學歷條件數我好,但自己畢竟還遺留著“大尾巴”,僅這一條誰要卡你都可制造出麻煩。正在我忐忑不安的時候,廠里的消息傳了出來:我和另一位雙中女同學已被推薦到縣上了。很快縣上正式通知我,已被陜師大錄取,專業是政治教育。事后我才知道,在討論我上學的會上,邵廠長不但沒說一個“不”字,反而還說我“喜愛學習,肯吃苦,是塊料,值得培養”。
時光荏苒,我離開農機廠已半個世紀了,邵廠長也已在2002年去世,但我一直無法忘懷我人生中的關鍵一步是邵廠長幫著我邁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