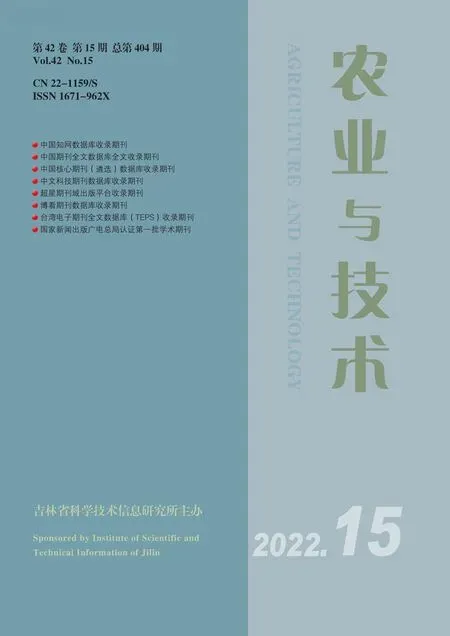不同品種牧草對大渡河干旱河谷地區土壤動物群落的影響
張艷 李佳 宋思夢
(四川民族學院橫斷山區生態修復與特色產業培育研究中心/川藏滇青林草撫育和利用研究中心,四川 康定 626001)
甘孜州位于我國西南部、青藏高原東南部,占據了中國牧區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我國在四川省內發展高原畜牧業的重要基地,是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根本[1]。然而近年來,受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共同影響,甘孜州草原生態功能下降,草原生態系統退化嚴重。為改善生態環境并且基于甘孜州的生態條件,選擇的草種應該極耐干旱、耐高溫、耐貧瘠,具有根系發達、有一定土壤改良效果的特點,且以可供畜牧業青飼料、青貯飼料、顆粒加工飼料等用途的牧草最佳[2],如巨菌草(Pennisetum giganteum)、綠洲一號(Oasis No.1)、高冰草(Agropyron elongatum)等,巨菌草種植過程較簡便并且生態、經濟效益顯著。綠洲一號是一種能改善鹽堿地,使鹽堿土壤自身的土壤肥力得到有效恢復的菌草[3],有較高的生態和經濟價值。高冰草適應能力強,產量高,經濟效益顯著[4]。
土壤生物群落包括土壤微生物與土壤微型動物,土壤動物是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與土壤環境因素密切相關,土壤動物還能促進凋落物和有機質分解,提高了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的速度,改變土壤結構等,在平衡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和生態服務功能等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5]。目前,國內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生境之間[6]、不同耕作模式之間[7]、不同植被類型間[8]土壤動物的差異性,對于甘孜州干旱河谷地區以及牧草的研究較少,為了解甘孜州干旱河谷地區不同牧草間土壤動物差異,以四川民族學院黑日村試驗地巨菌草、高冰草、綠洲一號為材料,研究3種牧草之間土壤動物數量、生態指數等的差異。
土壤動物是土壤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參考土壤環境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其變化也和生態系統中的各種變化分不開[9]。甘孜州是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重要基地。近年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導致甘孜州生態功能下降。本試實驗對3種不同牧草根際土壤中土壤動物進行實驗,旨在了解不同牧草根際土壤中土壤動物組成,并根據土壤動物的生態指數,為甘孜州的生態恢復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甘孜州地處四川省西部川西高原(E97°22′~102°29′,N27°58′~34°20′),位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過渡的地帶,是我國第2大藏區。根據緯度來劃分,甘孜州屬于亞熱帶地區,但由于甘孜州特殊的地形,形成了典型的高原大陸型氣候,干、雨兩季分明[10]。川西高原冬季寒冷,夏季涼爽,在冬季時氣溫相比于同緯度的低海拔區低8~10℃;夏季比較溫涼,氣溫一般在8~18℃,年降水量為600~800mm[11],甘孜州境內有多條河流,如金沙江、大渡河等。
1.2 樣地設置
本試驗在四川民族學院黑日村試驗地進行。選取高冰草、綠洲一號、巨菌草3種牧草根際土作為研究對象。每種牧草選擇3個樣方,大小為1m×1.5m。在每塊樣地的對角線上進行3點取樣法。每處理3個重復。
1.3 土壤樣品采集和土壤生物分離及鑒定
每個樣地選取3個取樣點,在每個取樣點內分別取0~10cm的根際土作為復合樣,裝進土壤動物收集袋內,帶回實驗室進一步分類鑒定。本試驗主要采用干漏斗分類法,將土樣倒入口徑為10cm的篩網中,下接裝有濃度為75%酒精的培養皿,收集的所有土壤動物在實驗室解刨鏡下進行鑒定計數,分類鑒定主要參照《中國土壤動物檢索圖鑒》。
1.4 土壤理化性質分析
土壤含水率的測定采用烘干法:將土壤樣品在分析天平上稱重記數后放入烘箱內,烘干至恒重,取出于干燥箱再次稱重;土壤pH的測定采用電位測定法:將土壤樣品研磨后,過60目篩網后,稱取20g土樣加入蒸餾水20mL,攪拌后靜止,使其澄清,然后將pH復合玻璃電極插入上部清液中,輕輕搖動,取最后穩定的pH值(pH玻璃電極棒測定前應先用緩沖液進行校正)。
1.5 數據分析
在科的水平上,計算土壤動物類群數。
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計算公式:
Simpson優勢度指數計算公式:
式中,pi=ni/N,ni為第i個分類單元的個體數;N為樣品中所有動物的個體總數;S為類群數;pi為第i個分類單元的個體數占總數的比例[12]。
Pielou均勻度指數計算公式:
E=H/lns
式中,H為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S為類群數[9]。
Margalef豐富度指數計算公式:
DMG=S-1/lnN
式中,S為類群數;N為樣品中所有動物的個體總數[5]。
數據統計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和SPSS 23軟件,為研究不同牧草對土壤動物群落的影響,對不同品種牧草土壤動物數量、類群、多樣性指數、優勢度指數、均勻度指數、豐富度指數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進行分析。作圖采用Origin 2018軟件。
2 結果
2.1 土壤動物數量和群落組成
本試驗中調查到的土壤動物共有137只,隸屬于3門7綱15目21科。在目水平上,窄咽目和裂盾目為優勢類群,分別占總數量的39%和21%;半翅目、膜翅目等7目為常見類群,共占總數目的33%;古蚖目、離爪目等6目為稀有類群,共占總數的6%;在不同的牧草品種中的優勢類群均為窄咽目,見表1。

表1 土壤動物群落組成
由圖1a可得,3種牧草中巨菌草中的土壤動物數量表現為巨菌草>高冰草>綠洲一號,并且巨菌草樣地中的土壤動物數量顯著多于高冰草樣地和綠洲一號樣地;土壤動物類群數在3種不同牧草之間的差異不明顯,但土壤動物類群數在巨菌草樣地中最高,在綠洲一號樣地中最低,見圖1b。

圖1 不同品種牧草的土壤動物數量和土壤動物類群數(平均值±標準誤)
2.2 土壤動物多樣性
物種的豐富度和均勻度可以用多樣性指數相關聯,多樣性指數的大小也反映土壤的生物多樣性。目前,應用的最多的是辛普森指數(Simpson)和香農-維納(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9]。結果分析表明,3種牧草之間的多樣性指數無顯著差異(P>0.05),表現為巨菌草>高冰草>綠洲一號,優勢度指數則相反,表現為巨菌草<高冰草<綠洲一號。多樣性指數最高的是巨菌草樣地,最低是綠洲一號樣地,見圖2a;而優勢度指數在巨菌草樣地最低,綠洲一號樣地最高,見圖2b。
土壤動物豐富度指數反映了土壤動物在該樣地的土壤動物多樣性,研究表明,雖然3種牧草之間的土壤動物豐富度指數和均勻度指數均無顯著差異(P>0.05),但高冰草樣地中的豐富度指數最高,巨菌草樣地和綠洲一號樣地的豐富度指數沒有明顯差異,見圖2c,均勻度指數表現為巨菌草>高冰草>綠洲一號,見圖2d。

圖2 不同牧草品種土壤動物多樣性、優勢度指數、土壤動物豐富度以及均勻度指數(平均值±標準誤)
2.3 土壤環境因子
由圖3可知,不同牧草根際土壤pH有顯著差異(P>0.05),其中高冰草土壤pH顯著高于綠州一號和巨菌草,見圖3a。土壤含水率在3個樣地間差異顯著(P<0.05),綠州一號樣地的土壤含水率最高,其次是高冰草,巨菌草最低,見圖3b。

圖3 不同牧草品種中的土壤pH值、含水率(平均值±標準誤)
2.4 相關性分析
由表2可知,在巨菌草樣地,多樣性指數隨著類群數、均勻度指數的增加而增加,而優勢度指數則隨著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的減少而增加,豐富度隨著類群數增加而增大。由表3可知,高冰草樣地中,個體數隨著類群數、多樣性指數、均勻度指數的增加而增加,但隨著優勢度指數的增多而減少。多樣性指數隨著豐富度指數的增加而增加,相反隨著優勢度指數的增加而減少。由表4可知,在綠洲一號樣地中,多樣性指數隨著類群數、豐富度指數和均勻度指數的增加而增加,而優勢度指數隨著多樣性指數、均勻度指數、豐富度指數的增加而減少。

表2 巨菌草、高冰草和綠洲一號樣地相關性分析
3 討論
土壤動物類群數、個體數和多樣性指數是衡量土壤動物群落結構、功能和水平分布差異性的重要指標[5]。多樣性越高的群落,群落結構就越復雜,抗壓能力也越強。研究結果表明,多樣性指數與類群數均為巨菌草>高冰草>綠洲一號,土壤動物數量、類群數和多樣指數在巨菌草樣地中最高,綠洲一號最低,見圖1、圖2,可見與高冰草和綠州一號相比,種植巨菌草可提高土壤動物群落的類群、數量及多樣性。土壤動物是土壤中的有機活體,可用于衡量土壤肥力狀況,從而被認為是土壤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13,14],土壤動物還對土壤的理化性狀有一定的改善作用[15]。巨菌草屬于C4植物,其太陽能轉化率比闊葉植物高3~4倍,其根系復雜,具有減少表層土壤養分流失的作用,同時龐大的根系通過穿透作用以及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使得種植巨菌草地區土壤養分含量產生明顯增幅效果[16]。較高的土壤養分含量使得巨菌草樣地土壤動物群落、數量及多樣性指數最高。
在3種牧草樣地中,多樣性指數與優勢度指數均呈現負相關,均勻度指數與優勢度指數則呈負相關,這與劉姣[5]等得出相同的結論。并且在3種牧草樣地中,豐富度指數與優勢度指數呈現的是負相關。也有研究表明,優勢度指數與豐富度指數呈現的是負相關關系,這是由于豐富度越大類群數也越多,個體就會分散到更多不同的類群中,優勢度指數也會降低[17]。總體來看,在3個不同牧草品種中,優勢度指數以綠洲1號樣地最高,表示在綠洲1號樣地中,有著較高的群落穩定性,土壤動物更為集中的分布在種群中,而巨菌草樣地的優勢度指數最低,表示巨菌草樣地的土壤動物在種群中是較為分散的;豐富度指數在高冰草樣地中明顯高于其他樣地,表示在高冰草樣地中土壤動物類群多,多樣性較高。
4 結論與展望
綜上所述,在不同的牧草根際土壤動物的多樣性、類群數、數量以及理化性質等也發生相應的變化。相對于綠洲一號,巨菌草、高冰草在甘孜州的種植對土壤中的土壤動物群落結構有更好的效果。土壤動物群落結構與植物之間的影響是錯綜復雜的,后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其他因素對土壤動物多樣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