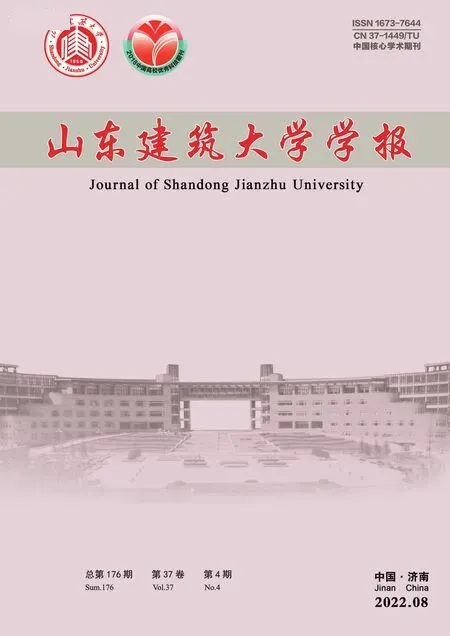黃河下游城市林地生態網絡構建與分析
——以濟南市為例
王琦王晨張立國郭晗
(1.山東建筑大學 測繪地理信息學院,山東 濟南250101;2.山東省國土測繪院,山東 濟南250013)
0 引言
近年來,國家戰略強調了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方面的重要地位,其可構成我國主要的生態屏障。 濟南作為黃河流域的特大城市,其高質量、快速發展勢必與城市生態環境相互制約。 因此,科學準確地分析、評估濟南市生態網絡現狀,并以此作為未來城市發展規劃的依據,對建設生態文明濟南以及黃河流域城市群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林地是城市維持生態文明發展的重要可再生資源之一,也是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維護生態平衡、促進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1-3]。 保護林地資源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本質途徑之一,同時與城市可持續經濟發展具有密切的聯系。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利用自然資源和發展經濟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保護生態環境與發展經濟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點,是新時代中國與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要課題。
城市生態網絡是城市生態安全格局研究的重要方法,目前國內外已有很多相關研究。 何建華等[1]以武漢市濕地為研究對象,從生態網絡視角客觀分析了武漢市生態格局。 陳南南等[2]通過構建秦嶺(陜西段)山地生態網絡,比較了其內部斑塊,識別了重要生態廊道。 張曉琳等[3]對長江中下游平原的金壇區進行生態網絡識別與優化,并提出差異化生態網絡修復策略。 此外,也有研究者從景觀視角出發,構建由斑塊、廊道和基質所組成的林地生態網絡[4-5];利用景觀指數反映景觀在結構組成與空間配置方面的特征[6-7];通過生態網絡反應景觀功能連通性特征,增強格局分析的準確性、科學性[8]。其中,形態學空間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MSPA)模型是提取研究區域生態源地的有效方法[9-10];最小累計阻力(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CR)模型可以計算生態源地到其他各點的最小累計阻力值,通過設立阻力參數構建最小阻力面;重力模型則可以優化生態廊道的提取[11-15]。 目前,MSPA 方法與MCR 模型相結合進行生態網絡構建的方法已經較為成熟,但從區域生態研究的角度,目前還缺乏對如濟南等黃河流域下游重要城市的林地資源生態網絡構建分析、生態保護紅線合理性評價、生態保護區分級評價等相關研究。
文章以濟南市林地資源為研究對象,基于10 m分辨率土地利用數據,利用MSPA 模型識別提取林地生態源地,然后對地形坡度、高程以及地物景觀類型賦值建立綜合阻力面,借助MCR 模型建立濟南市林地資源生態網絡,并通過重力模型提取重要生態廊道。 在此基礎上,從景觀結構組成、生態源地分布、生態阻力分布、生態網絡配置等方面分析、評價濟南市林地生態格局,并提出濟南市林地資源保護和空間優化配置策略。
1 研究區域與研究資料
1.1 研究區域
濟南市位于山東省中西部,有“泉城”美稱,是山東省省會、環渤海地區南翼的中心城市,其地理位置圖如圖1 所示。 所用地圖審圖號為魯SG(2021)013 號。 同時,濟南市是山東省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和金融中心及重要的交通樞紐。 濟南市地形可分為北部臨黃帶,中部山前平原帶,南部丘陵山區帶。 濟南市氣候為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氣候類型為溫帶季風氣候,特征為春季舒爽、降雨量低;夏季氣候炎熱、降雨豐富;秋季氣溫、濕度適宜;冬季平均氣溫≥0 ℃[16]。 此外,濟南市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林地資源作為濟南市維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對于其生態環境保護與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

圖1 研究區位置圖
1.2 數據來源
采用的數據包含濟南市土地利用數據和數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數據。 其中,濟南市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清華大學數據中心(http:/ /data.ess.tsinghua.edu.cn/),分辨率為10 m。按照清華大學數據中心標準將土地劃分為耕地、林地、草地、灌木林地、濕地、水體、不透水地表、裸地,土地利用分布如圖2 所示。 所用地圖審圖號為魯SG(2021)013 號。 DEM 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http:/ /www.gscloud.cn/),分辨率為30 m。基于DEM 數據,利用地理信息系統軟件ArcGIS 坡度分析進一步計算坡度數據以構建生態阻力面。

圖2 濟南市土地利用分布圖
2 研究方法
2.1 基于MSPA 模型的林地景觀形態類型識別
MSPA 起初設計為用于林地資源的景觀格局研究,利用形態學分析加強景觀之間的結構連通,是精確識別林地資源的關鍵途徑[17]。 利用ArcGIS 對濟南市分辨率為10 m 的土地利用數據進行二值化重分類,將林地設置為MSPA 的前景數據,并將其余各類用地設置為MSPA 的背景數據。 利用圖像對象與形狀描述軟件工具Guidos Toolbox 進一步識別MSPA 景觀形態類型(見表1)。

表1 MSPA 的林地景觀形態類型及生態學含義表
2.2 基于景觀連通性的林地重要生態源地識別
景觀連通性是評判研究區域內生態與景觀斑塊聯系強弱的重要指標,是客觀反映不同生態源地生物遷徙難度的關鍵途徑,對于識別重要生態源地具有積極意義[14]。 采用可能連通性指數(Probability of Connectivity,PC)和可能連通性指數變化量(the delta values for the Probability of Connectivity,dPC)[18-19]識別重要生態源地。
可能連通性指數PC 由式(1)表示為

式中n為斑塊總數,個;ai、aj分別為斑塊i、j的面積,km2;pij為生物在斑塊i、j間擴散的最大概率;AL為研究對象的景觀總面積,km2。 利用景觀指數數據輸入軟件Conefor_Inputs_10 設置斑塊間的距離閾值為2 000,其連通概率為50%。
可能連通性指數變化量dPC 由式(2)表示為

式中PC 和PC′分別為連通性計算結果和去除某要素之后的連通性計算結果,dPC 為去除要素的重要性程度。
2.3 耦合多因子的林地景觀阻力面構建
景觀阻力表示生物在不同景觀單元間遷徙的難度,其可以反映斑塊的環境抵抗力,判斷景觀斑塊重要程度[20]。 由此建立的綜合阻力面可以由空間角度表示研究區域內景觀格局的相互作用,并作為確定景觀斑塊間的最短、最優路徑的基礎[21]。 文章從林地資源的分布特征出發,選定地形坡度、高程以及景觀類型作為基準進行阻力賦值(見表2 ~4),并分別構建阻力面(如圖3 所示)。

圖3 阻力面構建圖

表2 地物景觀類型阻力賦值表
林地作為研究對象,其生態適宜性最高,因此地物景觀類型阻力值最低。 濕地、草地、灌木林地景觀類型對于林地影響阻力較低。 耕地由于非自然形成景觀類型對于林地的阻力稍高,同時水體作為天然屏障對于林地的阻力略高。 裸地與不透水地表被人類行為干擾,生態適宜性極低,景觀類型阻力極高。由于林地多分布于丘陵與山地地區,綜合地形坡度和高程,分析地形地勢變化,設定平原地區阻力值最高;高程>400 m,坡度>35°阻力最小。 因此,設定地形坡度,高程以及景觀類型對應權重分別為0.3、0.3、0.4,進行加權求和建立綜合景觀阻力面。

表3 高程阻力賦值表

表4 地形坡度阻力賦值表
2.4 基于MCR 模型的林地生態網絡構建
生態網絡是由一系列自然保護區及其連接體組成的系統,能夠將破碎的景觀重新連接為一個綜合整體,維護生態環境穩定性[22-23]。 借助MCR 模型,聯合綜合阻力面,可以計算出不同斑塊之間的最小累積阻力,從而借助ArcGIS 建立斑塊間的最低成本路徑,憑借最低成本路徑可建立研究區域內的生態網絡。
最小阻力模型由式(3)表示為

式中MCR 為生態源地到其他各點的最小累計阻力值;fmin為Dij與Ri的函數關系;Dij為生態源地i與j的空間距離,km;Ri為通過景觀時的綜合阻力系數。
2.5 基于重力模型的林地重要生態廊道識別
重力模型原用于處理地理空間中城市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 有學者[15,24]將其引入到生態網絡中用于識別提取重要生態廊道。 利用重力模型對MCR 構建的生態網絡進行重要性判別,客觀反映不同林地景觀之間的生態作用力,科學體現各個林地斑塊之間的聯系強度。 重力模型由式(4)表示為

式中Gij為林地核心斑塊i與j之間的相互作用力;Mi、Mj分別為斑塊i、j的權重;D2ij為斑塊i與j間的潛在廊道聯系阻力值;Si、Sj分別為斑塊i、j的面積,km2;Lij為斑塊i與j進行聯系的景觀阻力值;Lmax為研究區域內廊道阻力的極大值。
3 結果與分析
3.1 林地生態景觀格局分析
利用MSPA 模型對濟南市林地景觀形態進行分析,識別出核心區、孤島、孔隙、邊緣、環道、橋接、支線與背景(如圖4 所示),并對各類型進行了統計(見表5)。 濟南市林地景觀中核心區分布最廣泛,面積占比達46.35%;邊緣和孤島規模較大,占比分別為18.14%和12.52%;支線與橋街區的面積占比較少;環道與孔隙分布極少。 由此可知,濟南市林地邊界高度繁雜,分布集中但形態破碎,內部存在大量缺口,對外部影響抵抗力較弱,且各個林地景觀斑塊之間的連通性較低,對于生物遷徙、能量流通易產生消極影響。

圖4 濟南市基于MSAP 林地景觀類型圖

表5 基于MSPA 的林地景觀類型面積表
濟南市林地資源總體上較為豐富,集中分布于中南部山地地區,在西南與東南地區景觀分布規模較大,在北部平原地區零星分布。 濟南市林地分布高度集中,分布極不均衡。
3.2 林地生態源地分析
借助可能連通性指數變化量(dPC)提取重要核心區及其矢量數據;依據核心區面積對其進行排列,并根據均勻分布的原則,選取其中dPC 最大的8 個核心區斑塊即可覆蓋濟南市的中南、中西南與東南部3 大核心區。 核心區景觀連通性重要程度排序見表6(編碼采用Conefor2.6 提取的節點Node)。
根據表6 可知,選取的林地重要核心區斑塊(生態源地)的總面積為190.99 km2,其分布較為集中(如圖5 所示),但單個生態源地的面積較小,與濟南市林地資源分布相吻合,體現了濟南市林地資源分布高度集中但斑塊極其破碎的特點。

表6 核心區景觀連通性重要程度排序表

圖5 林地生態源地分布圖
3.3 林地生態阻力分析
由圖3 中的地物景觀類型、高程以及地形坡度各自的阻力面,可以得出由地物景觀所造成的阻力主要集中在濟南市中西部與東南部的不透水地表;北部地區以耕地為主,阻力值中等;中南與東南、中西南地區以林地為主,因此阻力值極低。 由高程和地形坡度引起的阻力主要集中在北方與西部的平原地區,而在中南部與東部的山地丘陵地區阻力極低。疊加上述3 個阻力面得到綜合阻力面(如圖6 所示)。 由圖6 分析可知,濟南市北部與西部地區的阻力值極高,東南區域阻力分布復雜;在東南部分(萊蕪區)中東部阻力值較高,東南角阻力較低;中南與東部地區的阻力值極低。 說明濟南市的地物景觀類型與地形地勢等自然要素高度統一,總體規劃與自然條件吻合度較高。

圖6 濟南市林地生態綜合阻力面圖
3.4 林地生態網絡分析
利用MCR 模型與濟南市綜合阻力面建立了濟南市林地生態結構網絡,是由提取出49 條生態廊道組成的(如圖7 所示)。 圖7 表明了濟南市生態格局與生態過程流在濟南市綜合阻力面上所受到的阻力值強弱。 由于林地生態源地分布高度集中,生態廊道分布也極不均勻,高度集中于中南與中西南地區,但廊道結構相對合理,利于進行生物交流和提高林地的環境抵抗力。 東部生態廊道單一,生態抵抗力較弱,生態系統易破碎。 如維持濟南市生態可持續發展需加強東部廊道的建設,減少人類經濟生產活動的干擾,減輕廊道的生態壓力,必要時可在東部阻力值較低區域建立新的林地景觀生態源地,緩解單一廊道的負擔,提高東部廊道的生態連通性。

圖7 濟南市林地生態網絡圖
3.5 重要生態廊道分析
借助重力模型判斷不同林地斑塊之間的聯系性強弱,并以此作為評判廊道連通研究區域內林地斑塊的重要指標,然后提取出濟南市的重要林地生態廊道。 斑塊間作用程度的閾值設置為>1.5(見表7),共選取出10 條重要廊道(如圖8 所示)。 結果顯示,提取的重點廊道與濟南市戰略規劃以及林地斑塊分布相吻合。

表7 生態廊道間相互作用程度表

圖8 濟南市林地生態網絡分級圖
濟南市重要林地斑塊分布在中西南部分,斑塊間聯系密切,能量流動與生物交流也較強。 地處歷城區的0 號斑塊與歷城區、章丘區的2 號斑塊相互連通性最優,相互之間作用程度達15.639 5。 地處歷城區與長清區的8、9 號斑塊次之,相互間作用程度為12.274 2。 第一組斑塊分布于中南部山區,作為濟南市重要生態保護區,森林資源豐富,物類充足,具有良好的生態調節功能[25]。 第二組斑塊在濟南中西南部丘陵地區,借助跨域歷城區、章丘區、萊蕪區的6 號斑塊與第一組斑塊建立聯系,建立起中南與中西南的生物遷移、能量流通鏈條。
長清區與歷城區間斑塊相互作用能力強,使得濟南市中西南部分林地生態斑塊具有良好的連通功能。 萊蕪區斑塊分布于濟南市東南角山地,由于周圍地形平緩,建有城市,易受人類活動影響,與其他廊道的相互作用力較弱。 因此,維持濟南市東部林地生態源地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生物交流與能量流動需要對萊蕪區的生態廊道加強維護,以便山地生物進行遷徙;減少對于東部山地資源的開發,并加強其周圍林地景觀核心區的管理維護,提高其dPC,降低人類經濟開發活動對萊蕪區斑塊的集中影響。
4 結論
通過上述研究可知:
(1) 濟南市森林資源豐富,總面積1 938.57 km2,其中核心區面積占比為46.35%。 森林資源集中分布于中南山地地區,在西南與東南地區分布規模相對較大,在北部平原地區分布稀少,空間格局極不均衡。林地景觀邊緣破碎,內部空洞多,且單個生態源地的面積較小,連通性平均水平較低,不利于生物棲息、遷徙和能量流動。
(2) 濟南市的地物景觀類型與地形地勢等自然要素高度統一,城市總體規劃與自然條件吻合度較高,濟南市林地生態網絡與其市戰略規劃以及林地斑塊分布相吻合,總體質量較高。 但是生態廊道呈聚集分布,主要集中于中南與中西南地區,東部廊道單一,連通程度高度不平衡,整體結構相對簡單,不利于生物交流和提高林地的生態環境抵抗力,生態系統易破碎。
(3) 濟南應加強對萊蕪區林地資源生態源地的保護,注重維護周圍林地景觀核心區,適當減少人類活動的影響并建立東部生態網絡。 對于中南與中西南地區,應降低林地景觀的破碎化,填補內部空洞,在北部和西部適當建立一定規模的林地資源生態源地,加強生物交流,促進濟南市林地資源均衡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