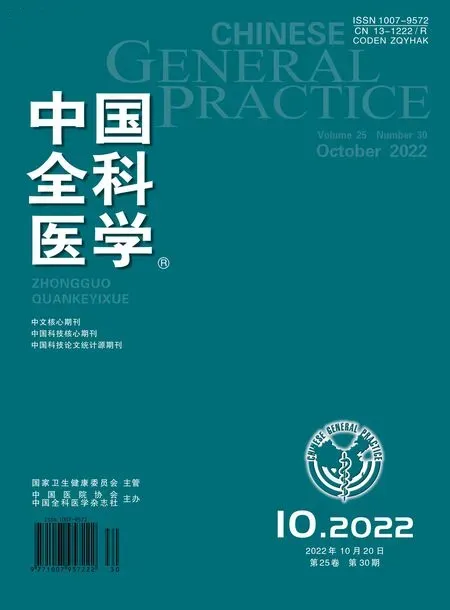HIV相關知識及預期污名化對男男性行為者抑郁的影響
——基于潛在類別分析
戴振威,司明玉,吳奕錦,陳旭,付佳琪,黃依漫,王浩,肖偉軍,于飛,米國棟*,蘇小游*
男男性行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者作為HIV感染的高危人群,其感染HIV的概率是一般人群的26倍[1]。在中國,MSM者的HIV感染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研究顯示,中國HIV感染歸因于MSM的比例從2006年的2.5%上升到2016年的28%[2-3]。此外,MSM在中國仍然不被公眾廣泛接受,他們可能在生活和工作中遭受歧視和污名化[4]。上述原因均可導致MSM者產生負性情緒,如焦慮、抑郁等。研究顯示,MSM者的抑郁發生率普遍高于一般人群,202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西部MSM者抑郁的發生率為38.0%,一項系統綜述的結果也顯示中國MSM者抑郁發生率為40%[3,5]。長期的抑郁癥狀不僅會對身體造成損害,還會增加自殘、自殺等行為的發生風險,因此MSM者的抑郁問題亟待解決[6]。既往研究指出,MSM者的HIV相關知識可對抑郁產生影響[7]。該人群的HIV預期污名化也可能是抑郁的影響因素[8]。MSM者的抑郁狀況可通過量表評估獲得,但是通過量表評估僅能從整體水平反映其抑郁狀況,無法準確識別該群體的抑郁特征,即使兩個個體得分一致,他們在各條目上的答案也可能有所差異。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是利用潛在類別模型將人群按照不同特征分為多個類別的統計方法,其分類的準確度高于傳統分類方法,在心理學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本研究旨在使用LCA探索MSM者抑郁的分類特征,并探究HIV相關知識和HIV預期污名化對不同水平抑郁的影響,為針對不同特征群體實施特定干預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樣的方法,于2020-12-16至2021-03-02選取1 394例未感染HIV或感染狀態未知的MSM者進行線上問卷調查,納入標準:(1)生理性別為男性;(2)最近1年與男性發生口交/肛交;(3)未做過HIV檢測或檢測結果為陰性;(4)能獨立完成問卷;(5)自愿參加本研究。排除標準:(1)年齡<18歲;(2)不能配合調查者。本研究已于2020-05-20經過淡藍公益倫理委員會審批(DLIRB202005-01),研究對象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知情同意。
1.2 研究設計 本研究采用同性社交軟件Blued7.5平臺對注冊用戶進行線上調查,線上調查的方式不僅可確保問卷的完整性和匿名性,且受試對象能夠在更自然的狀態下填寫問卷,提高問卷結果的真實性。問卷通過“近6個月內,你與多少名男性發生過肛交性行為”這一題項進行質量控制,調查由專業研究人員于2020-12-16至2021-03-02將招募信息及電子問卷發布至平臺,感興趣的用戶打開鏈接后點擊“同意并開始作答”按鈕方可填寫問卷。無效問卷標準:(1)“近6個月內,你與多少名男性發生過肛交性行為”題項的填寫結果≥300;(2)選項明顯規律,如所有條目選項相同。
1.3 調查內容 (1)一般資料:自行設計一般資料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年齡、婚姻狀況、工作狀況、民族、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是否做過HIV檢測、近6個月是否與男性發生性行為、近6個月是否與女性發生性行為、近6個月是否使用助性劑、抑郁情況。(2)HIV知 識 問 卷(HIV Knowledge Questionnaire,HIVKQ-18):該問卷由CAREY等[9]于2002年編制,用于衡量個體對HIV及其預防相關知識的了解程度,共18個條目,每個條目分為“對”“錯”和“不知道”3個選項,答對的條目得1分,答錯或不答得0分,總分越高說明對HIV及其預防的相關知識掌握越好。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90。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59。(3)HIV預期污名量表(Anticipated HIV Stigma Scale,AHSS):該問卷由GOLUB等[10]于2013年編制,用于衡量MSM者的HIV預期污名化程度,共7個條目,各條目采用Likert 4級計分法,“完全不同意”計1分,“不同意”計2分,“同意”計3分,“完全同意”計4分,得分越高說明預期污名化程度越嚴重。 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20。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37。(4)簡版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0):該量表由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RADLOFF[11]于1977年編制,共包含20個條目。YU等[12]于2013年引進國內并精簡為包含10個條目的CES-D10,各條目采用Likert 4級計分法,“沒有或很少有”計0分,“有時或小部分時間”計1分,“時常或一半的時間”計2分,“絕大多數或全部時間”計3分,得分越高說明抑郁程度越嚴重,總分≥10分提示存在抑郁癥狀。本研究在進行LCA時根據KOHOUT等[13]的建議將該量表的各條目轉換為2分類,其中原條目的“0”和“1”轉換為“0”,原條目的“2”和“3”轉換為“1”。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50。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25。
1.4 統計學方法 將原始數據導入Excel軟件,采用SAS 9.4和Mplus 8.3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計量資料以(±s)表示;MSM者抑郁的潛在類別應用LCA,本研究采用穩健極大似然法(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MLR) 對 1~5個 潛 在類別的模型進行擬合,并通過擬合指標及實際理論決定最佳模型,擬合指標包括:赤池信息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貝葉斯信息準則(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校正貝葉斯信息準則(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aBIC)、熵值(Entropy)、似然比檢驗指標(lo-mendell-rubin,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檢驗(the 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結果等。其中AIC、BIC、aBIC越小提示模型擬合越好;Entropy>0.8說明類別分類合理;似然比檢驗若P值達到顯著性水平(P<0.05),則表明k個類別的模型顯著優于k-1個類別的模型,此外,還需結合分類的實際意義來確定最終的類別數目。模型選擇完畢后利用Kappa值評估通過潛在類別模型所得的分類與量表截斷值所得的分類的一致性,利用χ2檢驗對抑郁分類和研究對象一般資料進行單因素分析,單因素分析達統計學顯著的變量與HIV預期污名化、HIV相關知識共同作為自變量,抑郁分類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最終收回問卷1 396份,有效問卷1 394份,有效率為99.9%。1 394例研究對象中,年齡>30歲530例(38.0%),未婚1 210例(86.8%),無固定工作483例(34.6%),其他民族152例(10.9%),受教育程度為本科及以上716例(51.4%),月收入<7 000元1 013例(72.7%),做過HIV檢測1 029例(73.8%),近6個月與男性發生過性行為967例(69.4%),近6個月與女性發生過性行為159例(11.4%);近6個月使用過助性劑461例(33.1%),見表1。HIVKQ-18得分為(13.7±3.2) 分,AHSS得 分 為(23.3±4.4)分。

表1 研究對象一般資料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2.2 潛在類別模型擬合指標 以CES-D10的10個條目為外顯指標,依次選取1~5個潛在類別模型對MSM者抑郁狀況進行探索性LCA,不同類別數的潛在類別模型的擬合指標見表2。結果顯示AIC、BIC、aBIC隨著類別數的增加而降低;類別數為2、4、5時Entropy值>0.8;盡管隨著類別數的增加,似然比檢驗均達統計顯著性(P<0.05),但是當類別數為5時,其中一個類別概率僅為0.090,提示該類別樣本數量太少,實際意義低,因此綜合上述考量,本研究選擇含有4個類別的潛在類別模型進行分析,各條目在每個潛在類別上的條件概率見圖1和表3。根據CES-D10,各條目得分越高,表明MSM者的抑郁程度越嚴重,從圖1可知,C4類別在10個條目的得分概率均較低,根據其得分特征,將這一類別命名為“無明顯抑郁”;C1類別在各條目上的得分概率均明顯高于C4,低于C3,因此將C1命名為“可能存在輕微抑郁”,并將C3命名為“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C2類別的各條目得分概率與C4相似,但是條目4和條目7的得分概率較高,兩條目的意思分別代表“平時不感到高興”和“覺得生活沒那么有意思”,反映該組MSM者可能有發生抑郁的風險,故將該組命名為“可能存在抑郁風險”。各組的類別概率見表3,其中“無明顯抑郁”占40.1% ,“可能存在抑郁風險”占21.6%,“可能存在輕微抑郁”占28.0%,“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占10.3%。為檢驗該分類的準確性,將根據CES-D10的截斷值所判斷的抑郁結果(0=無抑郁;1=存在抑郁)與LCA所得結果進行一致性檢驗(0=無明顯抑郁+可能存在抑郁風險;1=可能存在輕微抑郁+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結果顯示Kappa=0.735(P<0.001)。

表2 探索性LCA模型擬合指標Table 2 Model fit indices in exploratory latent class analysis

表3 各條目在每個潛在類別上的條件概率及類別概率Table 3 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 and class probabilities of each item of the CES-D-10 on latent classes

圖1 4個抑郁潛在類別條件概率分布圖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 on four latent classes of depression
2.3 MSM者抑郁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不同抑郁分組MSM者民族、月收入、HIV檢測情況、近6個月與男性性行為情況、近6個月與女性性行為情況、近6個月使用助性劑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抑郁分組MSM者年齡、婚姻狀況、工作狀況、受教育程度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MSM者抑郁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n(%)〕Table 4 Univariat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Chines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2.4 MSM者抑郁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以年齡(賦值:1=>30歲,2=≤30歲)、婚姻狀況(賦值:1=未婚,2=已婚)、工作狀況(賦值:1=全職工作,2=無固定工作)、受教育程度(賦值:1=本科以下,2=本科及以上)、HIV預期污名化(賦值:實測值)、HIV相關知識(賦值:實測值)作為自變量,抑郁分組(賦值:1=可能存在輕微抑郁,2=可能存在抑郁風險,3=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4=無明顯抑郁)作為因變量,將“無明顯抑郁”作為參考類別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高水平HIV相關知識(OR=0.926,P=0.001)、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OR=0.642,P=0.003)是可能存在抑郁風險的影響因素;HIV預期污名化(OR=1.594,P<0.001)、已婚(OR=0.593,P=0.026)是可能存在輕微抑郁的影響因素;高水平HIV相關知識(OR=0.935,P=0.026)、HIV預期污名化(OR=2.239,P<0.001)、無固定工作(OR=1.518,P=0.045)是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的影響因素,見表5。

表5 MSM抑郁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5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Chinese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3 討論
3.1 LCA方法的科學性及優勢 除LCA外,還有許多其他方法可對研究對象進行分組,如聚類分析、Taxometric分析法等。但是與聚類分析相比,LCA是基于模型的方法,分類的標準和結果的檢驗更為合理;與Taxometric分析法相比,Taxometric分析法只能將研究對象分為2個類別[14]。因此,本研究采用LCA法將研究對象進行分組。
3.2 MSM者抑郁的潛在類別特征 本研究采用LCA探討了MSM者抑郁癥狀的異質性,結果顯示無明顯抑郁的MSM者占40.1%,可能存在抑郁風險的MSM者占21.6%,可能存在輕微至重度抑郁的MSM者占38.3%,與王毅等[15]、薛建等[16]的研究結果類似。該結果提示MSM者的抑郁發生率仍高于一般人群,應重視這一人群抑郁狀況的臨床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從個人、社會等多角度進行干預[17]。
3.3 MSM者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狀況對MSM者抑郁的影響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高學歷(本科及以上)是MSM者可能存在抑郁風險的保護因素;已婚是MSM者可能存在輕微抑郁的保護因素;無固定工作是MSM者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的危險因素。與潘蓉等[18]、荊少華[19]、楊昊等[20]的研究結果類似。分析原因可能為:(1)學歷方面,教育可以使個體擁有更多應對壓力源的資源,從而減少抑郁發生的可能[21]。(2)婚姻狀況方面,由于MSM者特殊的性取向可能有悖于了中國結婚生子的文化傳統,其行為通常會遭受社會的偏見,因此,在中國,許多MSM者選擇結婚并向他們的妻子和周圍的人隱瞞他們的同性行為[22]。結婚可以掩蓋同性戀行為、滿足大眾期望、避免被家庭或社會“淘汰”和緩沖來自父母和家庭的壓力源,從而降低抑郁的發生率[23]。(3)工作狀況方面,有固定工作的MSM者一般會有穩定的收入,該特征增加了其在經濟上的穩定性,使其更不容易產生抑郁癥狀[24]。但是由于學歷、婚姻及工作狀況等均屬于較難進行干預的變量,且可能產生一系列倫理問題,因此,相關部門應優先考慮對易于實施干預的因素進行干預,如HIV及其預防相關知識、HIV預期污名化等,以期為改善MSM群體心理健康的長期目標打下基礎。
3.4 HIV及其預防相關知識對MSM者抑郁的影響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高水平HIV相關知識是MSM者可能存在抑郁風險及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的保護因素,與高迪思等[7]的研究結果類似。分析原因可能為,對HIV相關知識掌握越好的MSM者越能夠對HIV有更客觀地了解,也有較強的自我保護動機,并能夠以正確有效的方式預防感染HIV,從而減少發生抑郁的風險;而對HIV及其預防相關知識掌握較少的MSM者不僅會增加抑郁傾向,還易發生無保護性性行為,增加感染HIV的概率[25]。研究顯示,社交媒體是加快知識傳播、擴大知識影響力的有效途徑[26]。因此,相關部門可考慮在MSM者中開展HIV及其預防相關知識的健康教育,如借助網絡社交媒體發布HIV相關知識,從而更方便、有效地提高MSM者對HIV及其預防知識的掌握程度,進而影響其抑郁的發生和發展[27]。
3.5 HIV預期污名化對MSM者抑郁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HIV預期污名化是MSM者可能存在輕微抑郁和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的危險因素。與劉越男等[28]的研究結果類似。分析原因可能為,HIV預期污名化程度較高的MSM者對自身的認同感比較低,面對困難時通常采取回避型應對方式并減少獲得來自外界支持的機會,從而增加包括抑郁在內的心理問題發生的可能性[29]。由于MSM者的HIV預期污名化的根本來源是社會對HIV人群的污名化,因此,相關部門一方面可考慮針對大眾開展HIV相關知識的宣教,引導公眾正確認識HIV,減少社會對HIV的恐懼和歧視,從而改善MSM者的HIV預期污名化,進而防止其抑郁的發生[30]。此外,相關部門可考慮通過MSM線上社交平臺促進MSM間的同伴支持,降低其自我歧視;也可考慮針對該人群進行如基于正念的心理干預,引導MSM者在掌握安全性行為及HIV預防相關知識的基礎上關注當下,不必過度擔憂未來是否會感染HIV及可能受到的歧視[31]。
本研究通過多中心、大樣本調查對抑郁進行LCA,將MSM者分為無明顯抑郁、可能存在抑郁風險、可能存在輕微抑郁、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其中HIV及其預防相關知識對可能存在抑郁風險、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有影響;HIV預期污名化對可能存在輕微抑郁、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有影響,相關部門可考慮結合社交媒體針對MSM者的HIV相關知識及預期污名化進行干預,從而預防及控制MSM者抑郁的發生和發展。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沒有納入不使用Blued平臺的MSM者,結果可能產生一定的偏差;其次,本研究采用信息熵對研究對象進行分類,盡管在方法學上可行,但是在分類上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是本研究為針對MSM者的抑郁狀況施行精準干預提供了新思路,后續可開展多種心、大樣本的干預研究驗證本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作者貢獻:戴振威、司明玉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數據整理,結果的分析與解釋,撰寫論文;吳奕錦、陳旭、付佳琪、黃依漫、王浩、肖偉軍、于飛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米國棟、蘇小游進行論文的修訂,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蘇小游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