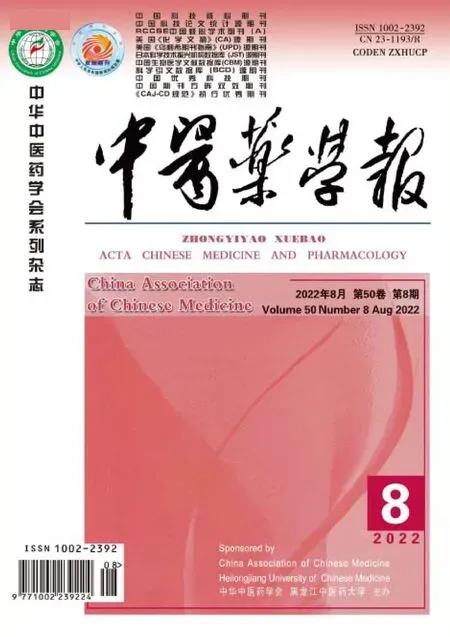基于《黃帝內經》探討“虛不受補”應對策略
陳俊煒,梁能幸,丁智聰,余尚貞,2*
(1.暨南大學中醫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2.暨南大學附屬江門中醫院,廣東 江門 529000)
養生與健康長壽,越來越成為當代人的生活追求,是實現《“健康中國2030”規劃剛要》的重要組成部分[1]。《黃帝內經》中談及的“法于陰陽,和于術數”為養生的最高境界,中醫的生理病理觀認為,人的衰老經歷了腎氣由盛轉衰的過程,《素問·上古天真論》超前地指出了當今社會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同時,人們“不知持滿,不時御神”的現狀,故“半百而衰”,疾病逐漸年輕化,亞健康困擾當代百姓,如糖尿病、高血壓等,但在為其運用補法時,往往不盡人意,甚至使癥狀加重,即所謂“虛不受補”的情況。《黃帝內經》沒有明言“虛不受補”之概念與含義,但可見于后世眾多醫家的典籍中,如張景岳的《景岳全書·雜·虛損》曰:“而有不能服人參、熟地及諸補之藥者,此為虛不受補”,陳士鐸筆下的《本草新編·十劑論》言:“愈補愈虛者,乃虛不受補”。但其中的“補虛之道”缺乏系統論述,故本文擬從《黃帝內經》的角度探討“虛不受補”的應對策略。
1 “虛不受補”的成因
廣義的“虛不受補”是指“虛人”服用補益藥之后起不到相應效果而且出現一些不良反應的一種狀態[2]。針對“虛不受補”的成因及緣由,眾多醫家學者從不同的維度解讀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觀點:一是虛實夾雜,辨證不準,處方用藥不當,持此觀點的現代學者居多[3-10]。二是脾胃失司,無力運化藥物[11-13]。三是補益時機不當[14-16]。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是特殊體質[17]、經絡不通[18]所致。以上觀點均有道理,但究其本質是沒有把握好“補虛”的陰陽之道,故“補不得法”“虛不受補”,故此需要“取法陰陽,和于術數”。從患者的角度看,“陰”的方面為脾胃失司、特殊體質、虛實夾雜等原因引起的藥物不耐受,醫者則需在此基礎上運用“陽”的方法,注重脾胃、緩補慢治、煎服調護、結合非藥物療法、順應四時等以平衡陰陽,正確把握補益的“法”與“度”。
而《黃帝內經》中對于補益的“法、度”高度濃縮在“法于陰陽,和于術數”一句中,針對此條文,結合所在的篇章《素問·上古天真論》、前后“上古之人”與“今時之人”對比的語境,歷代醫家通常注釋為養生的方法,如王冰曰:“夫陰陽者,天地之常道;術數者, 保生之大倫”。現代學者王成亞亦認為術數應為陰陽的下一層次[19],故大多理解為養生的方法[20-21],即“從宏大的陰陽變化規律中領悟出的治病養生的技術與方法”。而本文認為此“術數”貫穿于《黃帝內經》通篇內容,是一種治療思維的高度凝練,不單是養生之法,而《黃帝內經》中“虛不受補”的應對之策正是“和于術數”其中一種具象化的體現。
2 “虛不受補”的應對策略
2.1 注重脾胃,氣機和諧
脾胃為水谷生化之源,藥物進入人體后,需要通過脾胃運化成精微物質,才能作用于五臟六腑,如《素問·玉機真藏論 》曰:“五臟者,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臟之本也”。臨床上,應用中藥“補虛”即出現口舌生瘡或腹脹腹瀉,一般是“呆補”所致,反而阻礙脾胃氣機,如《靈樞·本神》云:“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臟不安;實則腹脹,涇溲不利”,脾胃升降功能失司,則運化無力,藥物不耐受、不吸收,如“清氣在下,則生飧瀉;濁氣在上,則生脹”(《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無論是吳鞠通[12]認為的脾胃虛弱所致虛不受補,還是吳澄[13]提出的“理脾陰法”用以辨治“虛不受補”均來源于《黃帝內經》中“脾胃為本”的思想[22],如“脾為孤臟,中央土以灌四傍”(《素問·玉機真藏論》),“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臟六腑皆稟氣于胃”(《靈樞·五味》), 在上述論述中,《黃帝內經》認為“脾胃”是藥物的運化之本,其中脾主運,胃主化[23]。從《黃帝內經》專門制定“治痿獨取陽明”的準則中,足以見得脾胃對“補虛”的重要性,如“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素問·痿論》),故此,脾胃運化功能是藥物“補虛”的基礎,《黃帝內經》亦從反佐的角度論證,“平人之常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素問·平人氣象論》)。脾胃之氣是實現人生理功能的重要基礎,故從《黃帝內經》論治“虛不受補”,首先應在用藥時注重脾胃的氣機升降,充分發揮脾胃運化之功效;臨證中,諸如平胃散、健脾丸之類,應用的就是健脾和胃、調整升降氣機之法,以健運、理氣為本,故能達到補而不滯。
2.2 用藥需緩,量及藥力
《黃帝內經》雖載方不多,而且大部分沒有具體藥物組成,但從其“十三方”的組方構造不難看出,“補虛”講究的是“簡、效、驗”,方不宜大,藥不宜多,即后世俗語中的“小劑救沉疴”,如二物合為丸,可治婦人血枯的四烏鲗骨一蘆茹丸。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所言:“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為故也”,認為治療藥物應“無使過之”“不可至劑”,從針對婦科疾患提出激進驅邪的治法看,“有故無殞,亦無殞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故需“衰其大半而止”。“補益”亦當如此,用藥需緩,量及藥力,慢病慢治,“補其大半而止”,“過度”則會“虛不受補”,如《素問·痹論》有云: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同理“藥物自倍,腸胃亦傷”,故需謹遵《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言: “補上治上制以緩”。
藥物治療的劑型同樣重要,當臨床上使用中藥湯劑內服而“虛不受補”時,改用丸散劑為其妙用,如《黃帝內經》中的烏鲗骨蘆茹丸、小金丹等。醫圣張仲景正是充分領悟及借鑒了《黃帝內經》“緩中補虛”之意,在其《傷寒論》及《金匱要略》中記載了大量藥方要求以藥丸為劑型服用,如治虛勞的薯蕷丸,治瘀血的大黃蟄蟲丸,治腎陽虛的腎氣丸等,即中醫認為“丸者緩也”,丸散劑大多為減毒的緩釋劑型,可平穩長久地釋放療效,尤其適合病后體虛,“虛不受補”之人。
2.3 煎服講究,調護有道

2.4 有形之藥與無象之藥結合
這里談的“無象之藥”具體指的是非藥物療法,人體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當遇到“虛不受補”情況時,藥物取不到相應的療效可以從非藥物療法考慮,平衡其陰陽,讓有形之藥與無象之藥結合。
非藥物療法,最經典的莫過于針灸,《靈樞》專門對針灸理論及方法做出了系統論述。經絡具有統籌全身氣血、平衡陰陽的作用,當藥物難以取效時,結合針灸以通經絡往往能取得良效,如《靈樞·經脈》言:“經脈者,所以能絕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 。現代學者黃小珍、粟勝勇亦認為“虛不受補”主要責之于經絡不通[18],針藥結合能增效減毒[26]。
功法鍛煉亦是重要一環,“運動養生觀”是《黃帝內經》“和于術數”的一個方面[27],“補虛”如同“健身增肌”一樣,既要加強蛋白質攝入,也要有相應的負荷鍛煉才能起到作用,在《素問·奇病論》中明確指出“導引”必不可少,是輔助治療的重要一環,“積為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黃帝內經》主要分為“外氣導引”和“導引”,兩者互相補充,即自體內修或醫師輔助外練。其中“外氣導引”,也稱“布氣療法”[28],指通過醫師使用特定手法,以“布氣”的形式作用于患者的經絡、腧穴中,起到相應的治療作用,即逐漸發展成現今的“推拿按摩手法”。“導引”,通過特殊的自我修煉功法平衡體內陰陽、通暢自身氣血以達防病治病的方法,而現今成為養生保健運動的統稱,如八段錦、太極拳、五禽戲等中醫傳統運動。在《靈樞·官能》中建議欲舒筋通絡、調和臟腑者宜導引行氣,“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
情志療法在《黃帝內經》中有十分豐富的論述,如《素問·上古天真論》中描述的“恬淡虛無”正是從情志入手以防病治病,其基礎是“形神一體觀”,如音樂調神、五志協調五臟亦是一種治療方法[29-31],體現的是一種系統對應、整體協調、取象比類的觀點,如《靈樞·邪客》言:“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神志和諧則五臟清靈、邪不可干,“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靈樞·本藏》),精神活動亦影響機體的健康,情志失常會使我們的臟腑氣機失調,影響臨床用藥,甚至“虛不受補”,如《靈樞·五變》云:“怒則氣上逆,胸中蓄積,血氣逆留”。《黃帝內經》中“形氣神”三位一體的觀點與現代醫學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不謀而合,早已實現從以病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突破,其中的精神心理療法對“虛不受補”的啟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心理暗示,臨證中常有“實則不虛”而自認為“虛證”的患者前來就診,此時《黃帝內經》的移精變氣,也稱“祝由法”,就能充分發揮作用,與西方的催眠、心理咨詢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毒藥不能治其內,針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素問·移精變氣論》),甚至不用“一針一藥”,亦能讓邪氣退散,“按摩勿釋,出針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素問·調經論》)。二是情志相勝,通過五志相克調節患者的情緒,亦能治病,如《靈樞·雜病》所言:“噦……大驚之,亦可已”。三是語言疏導,“補虛”的療效評價更多是患者的主觀感受,說理開導可以增加患者的信任度與配合度,以取得更好的療效,如《靈樞·師傳》言:“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簡而言之,情志療法是直接作用于人而非病,關鍵在于調暢臟腑氣機,氣機通暢,則補虛更易。
2.5 順應四時,無伐天和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32],“順應四時”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黃帝內經》中,相關的時間理論闡釋十分豐富,全書分多篇章論述。四時謹遵陰陽之規律,“虛不受補”不單是治療手段本身的問題,也有可能是補益時機的問題,故“順應四時”是應對“虛不受補”的重要策略。這里談“順應四時”,既指一日之四時,也指一年之四季。人源于自然,“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素問·寶命全形論》),人必然受到天地自然之影響,“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歲露論》),故人應四時而變化,“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素問·寶命全形論》)。學者任秀玲解析《黃帝內經》時指出人具有主動地調節適應自然的能力,名為“天人合一”[33]。現代醫學亦認為人有四時、四季的變化規律,如人隨生物鐘以應日夜變化,并應之休眠—覺醒[34];人在不同季節激素水平會發生輕微變化[35-36]。故相應的治療手段當順應自然變化規律,以達“天人相應”,即“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靈樞·逆順》)。
氣機變化在一日之四時有其固定規律,正如《素問·生氣通天論》所謂:“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若夜間胃氣受阻則夜不安眠,即所謂的“胃不和則臥不安”(《素問·逆調論》)。故施以治療手段時理應在平旦,即日間進行,在陽氣升發之際,讓針藥等充分發揮作用,“日西”而夜幕來臨氣門關閉時讓機體充分修養以運化日間的治療。
五臟在一年之四季亦有固定規律。《黃帝內經》指出的“五臟四季觀”,即五臟調控系統主動適應自然四季的陰陽變化規律,如《素問·咳論》曰:“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臟各以治時”,《素問·六節藏象論》言:“心者……通于夏氣。肺者……通于秋氣。腎者……通于冬氣。肝者……通于春氣”。故“補虛”的治療手段應從五臟入手,順應四季,春季應肝的“升發之象”,多用柔肝、緩肝之法;夏季應心的“君火之象”,多用益火養心之法;長夏應脾的“太陰濕土之象”,多用健脾燥濕之法;秋季應肺的“從革易燥之象”,多用潤燥益陰之法;冬季應腎的“封藏之象”,多用補腎溫陽益精之法。除此之外,《黃帝內經》認為經絡、脈象亦有四季的不同,如“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素問·脈要精微》),故治法不同,“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素問·診要經終論》)。
故此,補虛手段無論是內服中藥,還是外用針灸、功法鍛煉等治療手段,均需遵循“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之意以順應四時,即《靈樞·百病始生》所言:“毋逆天時,是謂至治”。若不從四時陰陽,往往會出現“虛不受補”,如《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言:“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茍疾不起”。簡而言之,本文認為從《黃帝內經》總結出的“順應四時”以應對“虛不受補”的具體解決方法為:一是內服藥物或者施以治療手段盡量在日間進行,夜間讓機體充分修養;二是治療手段盡量配合四季變化,“升藏有度”,以達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和陰陽消長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