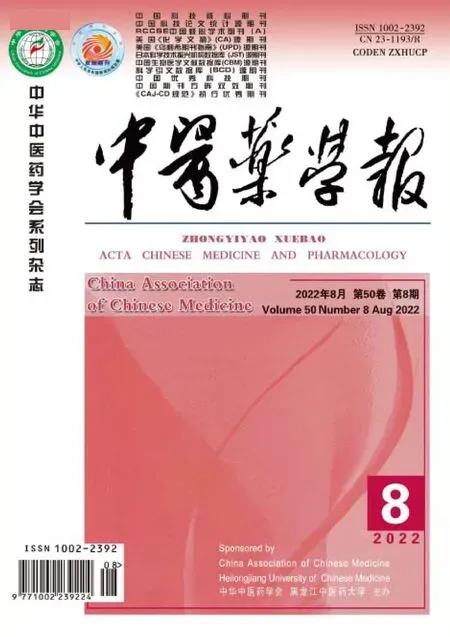腦腎腸軸研究進展
趙悅,牛若楠,馬雅鴿,張希,趙聲蘭
(云南中醫(yī)藥大學(xué),云南 昆明 650500)
腦、腎、腸都是人體的重要器官,研究發(fā)現(xiàn)一些疾病的發(fā)生、發(fā)展和痊愈不僅僅與單一的一個或兩個器官有關(guān),而是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近年來腸-腦軸、腸-腎軸、腎腦軸、腦-腸-腎軸[1]等相關(guān)學(xué)說先后被提出。本研究以“腦”and“腎”and“腸”為主題詞,搜索相關(guān)文獻,進行腦腎腸軸關(guān)聯(lián)分析,為防治腦腎腸軸相關(guān)疾病的研究和新的防治方案探索奠定基礎(chǔ)。
1 腦腎腸軸疾病
近年腦腎腸三者相關(guān)疾病的研究日益增多,見圖1,腸-腦軸、腸-腎軸、腎-腦軸、腦-腸-腎軸[1]等相關(guān)學(xué)說先后被提出,分別以“腎”并“腦”并“腸”為主題詞,知網(wǎng)搜索近10年相關(guān)中文文獻28篇,研究涉及腎病、抑郁癥、孤獨癥譜系障礙、腸易激綜合征、帕金森病、焦慮癥、老年性癡呆、肝性腦病、腦卒中等常見疾病,其中,腸易激綜合征、腎病、帕金森病研究最多。以“brain”and“kidney”and“gut”為主題詞,檢索近10年相關(guān)外文文獻233篇,涉及相關(guān)疾病依次為肝性腦病、糖尿病[2]、肥胖癥[3]、中風(fēng)[4]、高血壓[1]、腎病等。

圖1 腦腎腸相關(guān)疾病和中外文獻
查閱相關(guān)臨床資料,發(fā)現(xiàn)腎病、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腸道疾病相互之間有影響,一類疾病的發(fā)生往往會增加另兩類疾病的發(fā)病率。臨床研究表明在156例透析治療的終末期腎病病人中抑郁癥發(fā)病率為40.38%[5],在116例女性糖尿病腎病患者中,焦慮占25.86%,抑郁占37.07%[6],可知在腎臟疾病患者中焦慮、抑郁等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發(fā)病率較高。炎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會引起腎臟病變,如腎小球病變、腎小管間質(zhì)性炎癥、腎臟淀粉樣病變、IgA腎病[7]、膜性腎病等[8]。郝麗華等[9]發(fā)現(xiàn)焦慮、抑郁等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在IBD中很常見,并試探討腸道菌群在焦慮、抑郁與IBD之間發(fā)揮作用的機制。
腎病和腸道疾病均會增加患者患認知障礙的風(fēng)險。其中腎病引發(fā)認知障礙的機制與尿毒癥毒素、神經(jīng)營養(yǎng)因子關(guān)系密切,且炎癥、氧化應(yīng)激也對其有一定的影響。腸道疾病引發(fā)認知障礙的機制尚不明確。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表明[10]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者患認知障礙(cognitive disorder,CI)的幾率比普通人高,且腎小球濾過率(eGFR)下降與患認知障礙相關(guān),研究發(fā)現(xiàn)CKD會造成患者腦結(jié)構(gòu)異常,患者體內(nèi)毒素積累,導(dǎo)致神經(jīng)毒性、血腦屏障損傷、神經(jīng)炎癥、腦代謝功能障礙等。Merin等[11]的實驗發(fā)現(xiàn)腎選擇性切除大鼠表現(xiàn)出顯著的認知不良,記憶力、運動能力降低,探索性、驅(qū)動力降低以及情緒紊亂。CKD中神經(jīng)營養(yǎng)因子缺失也會導(dǎo)致學(xué)習(xí)、記憶能力下降,如腎臟產(chǎn)生的促紅細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具有減緩多種繼發(fā)性學(xué)習(xí)記憶障礙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腺嘌呤所致慢性腎衰小鼠學(xué)習(xí)記憶障礙與EPO表達的降低密切相關(guān)[12]。Hopkins等[13]的系統(tǒng)分析可知IBD患者表現(xiàn)出注意力、執(zhí)行功能、工作記憶方面的缺陷,這表明認知功能障礙是IBD的一種潛在的腸外表現(xiàn)。
由此可見,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腎病和腸病可能通過一些共有機制發(fā)揮作用,相互影響。收集相關(guān)研究資料,歸納出可能的共用機制,有腸道菌群、腸菌代謝物、免疫因子、生理活性肽、神經(jīng)系統(tǒng)、表觀遺傳、腎素-血管緊張素等。
2 腦腎腸軸疾病共有機制
2.1 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腎病及胃腸疾病的共調(diào)菌群
已有研究表明腎病[14]、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15]、腸道疾病[16]患者,其共調(diào)菌群也發(fā)生改變,收集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某些菌門或菌屬的豐度在三種疾病的發(fā)生發(fā)展中都發(fā)生變化,它們發(fā)揮協(xié)同或拮抗作用,共同參與腦、腎、腸疾病的進程。因此推斷,這三種疾病發(fā)病機制與這類腸道菌群有關(guān),可通過調(diào)節(jié)腸道菌群來實現(xiàn)同時對這三種疾病的調(diào)控和治療。相關(guān)腸道菌群的變化,見表1。實驗發(fā)現(xiàn)CKD患者腸道菌群放線菌門的豐度顯著升高,患者糞便中乳桿菌屬的豐度較健康對照組顯著降低;梭菌屬Ⅳ的豐度較健康對照組顯著升高[14]。早期CKD患者的腸道菌群放線菌門和變形菌門的豐度明顯高于對照組,擬桿菌屬、埃希氏菌屬、腸球菌屬、梭菌屬、克雷伯氏菌屬等也都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17]。糖尿病腎病患者腸道菌群放線菌門及雙歧桿菌屬豐度降低[18]。多種神經(jīng)、精神疾病也與腸道菌群密切相關(guān)。朱華等[19]研究發(fā)現(xiàn)阿爾茲海默癥(Alzheimer’s disease,AD)組擬桿菌屬豐度升高,梭菌屬豐度降低。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乳酸菌對精神疾病有改善作用,如具有抗抑郁作用的主要有乳桿菌屬、雙歧桿菌屬和腸球菌屬[20]。口服大腸桿菌K1會引起小鼠結(jié)腸炎、認知下降和抑郁[21]。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抑郁大鼠腸道菌群變形菌門和放線菌門相對豐度顯著降低,乳桿菌屬相對豐度顯著升高[22]。抑郁癥放線菌門豐度降低,擬桿菌門相對豐度增高,雙歧桿菌屬、乳桿菌屬相對豐度減少,而克雷伯氏菌屬、擬桿菌屬相對豐度增[23]。產(chǎn)前焦慮與腸道中梭菌屬細菌比例增加相關(guān);產(chǎn)后抑郁與變形菌門細菌比例增加相關(guān)[15]。另有研究發(fā)現(xiàn)[24]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腸道菌群結(jié)構(gòu)與健康人群相比存在顯著差異,如放線菌門的豐度顯著上升,擬桿菌屬等的豐度顯著降低。

表1 腦腎腸軸相關(guān)疾病患者中的共調(diào)菌群
腸道疾病無疑會伴有腸道菌群的改變,如脾虛型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diarrhoeal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D)小鼠擬桿菌門減少,變形菌門增多;乳酸菌屬減少,擬桿菌屬、埃希氏菌屬、克雷伯氏菌屬增多[26]。另有研究發(fā)現(xiàn)[27]炎癥性腸病患者腸道中腸球菌屬、擬桿菌屬、雙歧桿菌屬、乳桿菌屬、小梭菌屬數(shù)量顯著增多。結(jié)腸炎大鼠腸道中放線菌門、變形菌門豐度較高,埃希氏-志賀菌屬、擬桿菌屬豐度較高[25]。由此可見,腸道疾病無疑也會影響腦腎功能。
綜上可以得出,在菌門水平上,放線菌門、變形菌門在腎病、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腸道疾病中均有變化,在菌屬水平上,與三類疾病均有關(guān)的菌屬有擬桿菌屬、乳桿菌屬、梭菌屬、雙歧桿菌屬、腸球菌屬、埃希氏菌屬、克雷伯氏菌屬,其中克雷伯氏菌屬在腎病、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腸道疾病中均呈上調(diào)趨勢。
2.2 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腎病及腸道疾病的腸道菌群代謝物
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10,28]腸菌代謝產(chǎn)物也同時對腎病、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及腸道疾病有影響,如氧化三甲胺、硫酸吲哚酚、短鏈脂肪酸,這些代謝產(chǎn)物通過相應(yīng)的機制影響這三種疾病的進程。與三類疾病相關(guān)的腸道菌群代謝物,見表2。首先,腸菌失調(diào)會引起腸道疾病。臨床研究發(fā)現(xiàn)[29]口服連草瀉痢膠囊的結(jié)腸炎患者,TNF-α和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 oxide,TMAO)水平顯著降低。腸菌色氨酸代謝物吲哚類物質(zhì)對腸道起到重要的免疫保護作用,喂食吲哚的結(jié)腸炎小鼠,腸道炎癥減輕,腸道屏障被修復(fù)[30]。 短鏈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是膳食纖維經(jīng)腸菌分解發(fā)酵后的產(chǎn)物。近年來的研究表明SCFA可以調(diào)節(jié)腸腔水電解質(zhì)平衡,在修復(fù)腸黏膜受損組織、維持腸黏膜屏障的動態(tài)平衡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并與炎癥性腸病、腸易激綜合征、腸癌等有關(guān)[31],其發(fā)揮作用的機制需要更多的實驗來探索。周超等[28]的實驗得出SCFA中的丁酸可以通過穩(wěn)定腸道上皮HIF-1α誘導(dǎo)小鼠腸道發(fā)生自噬從而緩解小鼠結(jié)腸炎。

表2 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腎病及腸道疾病的腸道菌群代謝物
再者,腸透過性變高,細菌及其代謝物進入血液循環(huán),加重腎臟和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進程。Caroline等[32]發(fā)現(xiàn)血漿TMAO與腎小球濾過率(eGFR)呈負相關(guān),CKD患者血漿TMAO水平升高。硫酸吲哚酚(indoxyl sulfate,IS)可直接誘導(dǎo)腎小管管狀細胞凋亡,增加氧化應(yīng)激,降低抗氧化能力,與腎小管間質(zhì)損傷有關(guān)。而腸道菌群產(chǎn)生的腎保護性代謝物SCFA能夠減少腎損傷。三上大輔等[36]實驗發(fā)現(xiàn)SCFAs可以通過激活FFA2和FFA3來減輕人腎皮質(zhì)上皮細胞的炎癥而緩解慢性腎臟疾病。Meinitzer[33]的研究表明無碳水化合物吸收不良(carbohydrate malabsorption,CMA)的女性和男性血清TMAO濃度與抑郁癥狀嚴重程度呈正相關(guān),無CMA男性血清連蛋白(zonulin)水平與抑郁癥狀呈負相關(guān)。Ren等[34]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實驗發(fā)現(xiàn)躁郁癥(bipolar disorder,BD)患者較健康人尿液中的硫酸吲哚、三甲胺氧化物水平顯著升高。SCFA可通過調(diào)控TLR4、MyD88、TRAF6、NF-κB炎癥通路抑制脂多糖(LPS)誘導(dǎo)的小膠質(zhì)細胞的炎癥反應(yīng)[37]。
綜上可知一些腸道菌群的代謝產(chǎn)物在共同調(diào)控腎病、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和腸道疾病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目前已研究的對三類疾病均有作用的腸菌代謝物有TMAO、IS、SCFA。
2.3 腦腎腸軸中的免疫
收集歸納相關(guān)研究數(shù)據(jù),可知腎病、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腸道疾病的發(fā)生發(fā)展與白介素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轉(zhuǎn)化生長因子β(TGF-β)、IL-1β等免疫因子密切相關(guān),這些免疫因子在這三類疾病的發(fā)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見表3。

表3 腦-腸-腎相關(guān)節(jié)點及共軸免疫因子
腸道疾病的發(fā)生與炎癥直接相關(guān)。腸道是人體最大的免疫器官,小腸淋巴集合是發(fā)生粘膜免疫反應(yīng)的主要部位,病原體、營養(yǎng)物質(zhì)、共生菌群等都對粘膜免疫系統(tǒng)產(chǎn)生持續(xù)的刺激,產(chǎn)生先天免疫效應(yīng)。賈子君等[38]的實驗發(fā)現(xiàn)潰瘍性結(jié)腸炎患者血清中的TNF-α、IL-1β、IL-6、IL-8水平顯著高于健康組。實驗發(fā)現(xiàn)[39]炎癥性腸病小鼠在急性活躍期其促炎細胞因子IL-1β、IL-6、TNF-α表達水平增高,在組織消退期抗炎細胞因子TGF-β表達水平高于急性活躍期。
腎病與炎癥也密切相關(guān),Rapa等[40]的實驗發(fā)現(xiàn)IS與IEC-6細胞中TNF-α的水平、小鼠腹腔巨噬細胞參數(shù)呈正相關(guān)。IS還可上調(diào)信號轉(zhuǎn)導(dǎo)子和轉(zhuǎn)錄激活子3磷酸化,進而上調(diào)轉(zhuǎn)化生長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參與間質(zhì)性炎癥、腎纖維化,從而促進CKD進展[35]。黃偉等[41]的實驗表明腎衰泄?jié)釡赏ㄟ^對IL-2、IL-6水平的調(diào)控來上調(diào)T細胞亞群中CD4+/CD8+的比例,從而提高CKD患者的細胞免疫水平,延緩腎功能惡化。McKnight等[42]的實驗表明IL-1β在小鼠慢性腎臟病發(fā)病時促進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23(FGF-23)的產(chǎn)生,而FGF-23是腎功能障礙的早期生物標志物。
許多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與炎癥相關(guān),高魯?shù)萚43]發(fā)現(xiàn)重度顱腦外傷病人早期腸內(nèi)營養(yǎng)聯(lián)合益生菌治療,其IL-6、CD4+T細胞數(shù)量增加。周晶等[44]的實驗表明AD大鼠海馬組織促炎性細胞因子IL-1β、IL-6、TNF-α轉(zhuǎn)錄水平顯著升高,抑炎性細胞因子TGF-β轉(zhuǎn)錄水平顯著降低。補腎活血方可以使帕金森病(PD)模型小鼠神經(jīng)元數(shù)目增加,IL-6、TNF-α的表達下調(diào),從而抑制小鼠的神經(jīng)炎癥[45]。其作用機制可能為交感神經(jīng)直接支配和調(diào)節(jié)免疫器官、免疫細胞上的腎上腺素能受體的表達,而交感神經(jīng)系統(tǒng)(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SNS)的持續(xù)激活使得其信號轉(zhuǎn)導(dǎo)向促炎通路[1]。研究還發(fā)現(xiàn)自身免疫性腦脊髓炎小鼠血清和腦組織IL-1β、IL-6、TNF-α表達增加,而糞菌移植(FMT)小鼠血清和腦組織IL-1β、IL-6、TNF-α表達則降低[46]。蔣雪等[47]的研究發(fā)現(xiàn)腸道菌群與PD患者免疫細胞、炎癥因子相關(guān)。這些研究表明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可能通過腸道菌群影響免疫而影響疾病進程。其發(fā)揮作用的機制可能為腸道菌群影響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中免疫細胞功能、外周免疫細胞的活化,包括細胞免疫及體液免疫。
2.4 腦腎腸軸中的生理活性肽
腦腸肽是一些既存在于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又存在于胃腸道的胃腸激素。腦腸肽可將大腦的情感與認知中樞、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腸內(nèi)分泌系統(tǒng)、免疫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血清P物質(zhì)(SP)是廣泛分布于細神經(jīng)纖維內(nèi)的一種神經(jīng)肽。近年研究發(fā)現(xiàn)[48]P物質(zhì)與人類學(xué)習(xí)記憶能力有關(guān),并與焦慮癥、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的發(fā)病機理有關(guān)。何群芳等[49]通過實驗得出四神丸一定程度上能改善腎陽虛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相關(guān)腦腸肽血清血管活性腸肽(VIP)、SP、5羥色胺(5-HT)的水平。孫光曦等[50]實驗證明腦腸肽通過減少膠原產(chǎn)生,抑制細胞外基質(zhì)沉積和減少α平滑肌肌動蛋白表達改善腎臟纖維化。由上述可知腦腸肽在腎病、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和腸道疾病中均發(fā)揮作用。
2.5 腦腎腸軸中的神經(jīng)調(diào)控
交感神經(jīng)系統(tǒng)(sympathetic nervesystem,SNS)在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腎病和腸道疾病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交感神經(jīng)可直接支配腎血管系統(tǒng)和腎小球旁細胞,當交感神經(jīng)持續(xù)異常興奮,會增加尿白蛋白排泄和腎小球硬化。Jang等[51]的研究表明了去神經(jīng)支配有助于降低CKD患者的交感神經(jīng)活動,從而改善腎功能;在腎纖維化模型中,來源于腎神經(jīng)的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會通過α2腎上腺素受體引發(fā)腎臟炎癥和加重纖維化進程。此外,SNS還能通過腎元、腎血管和腎小球旁細胞的直接神經(jīng)支配調(diào)節(jié)水和鈉的平衡[10]。趙波等[52]研究得出炎癥性腸病的發(fā)病與IL-6、可溶性細胞間黏附分子-1(sICAM-1)水平升高、交感神經(jīng)功能增強、迷走神經(jīng)功能減弱有關(guān),IL-6、sICAM-1與自主神經(jīng)功能改變有正相關(guān)性。
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在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腎病和腸道疾病中也發(fā)揮重要作用。研究發(fā)現(xiàn)PD相關(guān)的α-突觸核蛋白在ENS中也有表達,說明ENS中的某些生物標志物與PD相關(guān)[53]。ENS能夠感知腸內(nèi)的機械和化學(xué)變化,并將信號傳達到自主神經(jīng)系統(tǒng),隨后自主神經(jīng)系統(tǒng)通過交感神經(jīng)、副交感神經(jīng)、迷走神經(jīng)等路徑影響對腎臟進行相應(yīng)的調(diào)節(jié)。實驗表明急性腎衰竭大鼠,其ENS神經(jīng)叢和神經(jīng)元數(shù)量減少[54]。腸道菌群也能影響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而影響疾病進程,如長雙歧桿菌可通過降低回腸肌叢神經(jīng)元的興奮性治療感染性結(jié)腸炎小鼠,并減輕其焦慮[1]。
由此可見,交感神經(jīng)系統(tǒng)、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均在這三類疾病的發(fā)生發(fā)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2.6 腦腎腸軸中的表觀遺傳
表觀遺傳是指不涉及DNA序列變化的基因表達和調(diào)控的可遺傳變化。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10],表觀遺傳因素在腎病、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腸道疾病的發(fā)生發(fā)展中發(fā)揮一定的作用。腸道菌群的代謝產(chǎn)物SCFA可抑制組蛋白去乙酰化調(diào)控基因表達,丙酸鹽、丁酸鹽可通過非競爭抑制作用,有效抑制組蛋白乙酰轉(zhuǎn)移酶和組蛋白去乙酰化酶,調(diào)節(jié)機體基因表達[10]。藤井良介等[55]研究日本中年人群中循環(huán)miRNA的表達水平與CKD之間的關(guān)系,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三種不同的miRNA的表達水平與eGFR正相關(guān)。腸菌可通過表觀遺傳修飾來調(diào)控大腦功能。王海洋等[56]的研究發(fā)現(xiàn)腸道微生物紊亂小鼠海馬的蛋白磷酸化修飾水平顯著改變,誘導(dǎo)抑郁障礙。此外,microRNA在大腸癌的發(fā)生發(fā)展中也起著重要作用[57]。
上文對腦腎腸軸相關(guān)生理作用和變化、相關(guān)疾病的聯(lián)系及相關(guān)因子進行了綜述,見表4,由此可見腦、腎、腸相互影響是通過相關(guān)指標進行的,見圖2,這些指標對相關(guān)疾病的調(diào)控有一定意義,是闡明疾病發(fā)生發(fā)展機制的主要基礎(chǔ)。本文歸納的相關(guān)作用途徑和因子主要有:(1)腸道菌群[14]及其代謝物[32]通過影響腸道屏障、機體免疫[40]影響疾病進程;(2)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將信號傳遞給大腦,交感神經(jīng)興奮增加,直接作用于腎臟和腸[43];(3)腸道菌群失調(diào),會引起腸上皮細胞表觀遺傳修飾異常,而這種異常能誘發(fā)腦病[56];(4)腦腸肽既作用于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又作用于胃腸道,并將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腸內(nèi)分泌系統(tǒng)、免疫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42,46];(5)腎會通過腎傳入神經(jīng)將信號傳遞到中樞,增加交感神經(jīng)興奮;(6)腎病會使體內(nèi)毒素積累增加,腎神經(jīng)營養(yǎng)因子減少,氧化應(yīng)激水平升高,炎癥,從而引起腦病;根據(jù)現(xiàn)有文獻可總結(jié)腦、腎、腸之間的相關(guān)因子,見圖3,其他還需進一步研究。

表4 腦腎腸軸相關(guān)疾病的聯(lián)系

圖2 腦腎腸軸相關(guān)指標關(guān)系圖
圖3可見,腦、腎、腸相互之間通過多種共有因子相互發(fā)揮兩兩及三者的相互作用。腦腸之間存在腦腸肽,這些肽可將大腦的情感與認知中樞、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腸內(nèi)分泌系統(tǒng)、免疫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如胃泌素(gastrin,GAS)、多巴胺(dopamine,DA)等。腸菌代謝物硫酸對甲酚(para-cresol sulfate,PCS)是一種腸源性尿毒素,可引起腎臟炎癥、全身低度炎癥和氧化應(yīng)激[58]。腎腦之間通過神經(jīng)遞質(zhì)、神經(jīng)營養(yǎng)因子、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tǒng)、交感神經(jīng)-腎上腺軸相互作用。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tǒng)(the 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是人體中最重要的體液調(diào)節(jié)系統(tǒng),腦存在RAS的所有成分,且AngⅡ/AT1-R、AngⅡ/AT2-R、AngⅣ/AT4-R、Ang1-7/MASR等成分與PD發(fā)病機制有關(guān),其中,AngⅡ/AT1-R與氧化應(yīng)激及炎癥反應(yīng),AngⅡ/AT2-R及Ang1-7/MASR與神經(jīng)保護、減輕氧化應(yīng)激及炎癥反應(yīng),AngⅣ/AT4-R與改善認知記憶功能、衰老、PD等相關(guān)[59]。

圖3 腦腎腸軸相關(guān)機制維恩圖
3 中醫(yī)治療及展望
中醫(yī)藥在治療腦腎腸軸疾病中遵循其特有的理論,腎屬五臟,小腸、大腸屬六腑,腦不屬于五臟六腑,屬于奇恒之腑。從整體觀的角度來看,奇恒指有規(guī)律的圓缺往復(fù)至永恒的動態(tài)平衡過程,因而可以說腦在腦腎腸軸中發(fā)揮了維持三者動態(tài)平衡的作用。神分屬于五臟而總統(tǒng)于腦,因而有腦藏五臟之說,在腦腎腸軸中表現(xiàn)為腦與腎的功能能夠相互滲透。此外,有腦髓臟腦室腑相互耦合[60]的說法,認為腦髓為臟屬陰,腦室為腑屬陽,相互之間遵循陰陽、表里、虛實的規(guī)律而互為影響。中醫(yī)的互藏、臟腑耦合等理論從整體論述了腦、腎、腸三者的關(guān)系,而本文從分子生物的層面,歸納了三個臟器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可能作用機制,如可通過調(diào)節(jié)三者共同影響的腸菌、代謝物,或調(diào)節(jié)相關(guān)炎癥因子、生理活性肽等來調(diào)控疾病,或在一種疾病發(fā)生時,對該疾病引起的并發(fā)癥進行預(yù)防,因此,可將中醫(yī)理論與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結(jié)合起來闡明腦腎腸軸和調(diào)控相關(guān)疾病。
中醫(yī)有腦-腎軸為命門之說,認為命門是一個與大腦及腎密切相關(guān)的器官,但在腦與腎之間存在一個連接,即神經(jīng)、內(nèi)分泌、免疫的網(wǎng)絡(luò)樞紐——下丘腦-垂體-腎上腺/性腺軸,使命門在人體得以發(fā)揮其在維持精神與生殖功能方面的作用。張潔等[61]探討了“恐”與腦及腎的關(guān)系,驚恐激活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和交感-腎上腺髓質(zhì)系統(tǒng),使海馬體、下丘腦中一氧化氮合酶活性增高,自由基過量,造成腦損傷和腎氣損傷,使得機體中的單胺氧化酶(MAO)降解,而單胺氧化酶參與許多神經(jīng)遞質(zhì)的代謝,導(dǎo)致單胺類神經(jīng)遞質(zhì)(5-HT、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的降解減少,引發(fā)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單胺類神經(jīng)遞質(zhì)及其代謝產(chǎn)物對心血管、神經(jīng)、內(nèi)分泌等組織系統(tǒng)有著廣泛的調(diào)節(jié)作用,并對睡眠、情感、情緒等生理活動產(chǎn)生重要影響。蔣希榮等[62]在腎腦相濟理論的指導(dǎo)下,得出電針療法可以通過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對絕經(jīng)期抑郁癥起到防治作用。許多基于中醫(yī)藥理論的防治腦、腸、腎相關(guān)疾病的方案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因此,綜合考慮各因子在腦腎腸軸中發(fā)揮的作用,將中醫(yī)藥理論融合進腦腎腸軸相關(guān)疾病的治療,結(jié)合中醫(yī)藥理論與現(xiàn)代藥理學(xué)研究,能夠為此類疾病的治療提供新思路,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