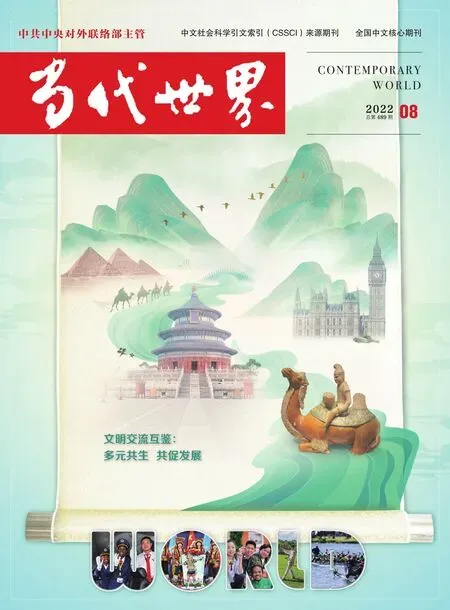全球發展倡議與中非發展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張 春

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疊加共振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出席2021年9月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全球發展倡議,推動整個國際社會對發展問題“再聚焦”,對可持續發展目標“再承諾”,對全球伙伴關系“再提振”,對國際發展合作“再激活”,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贊賞和普遍歡迎。全球發展倡議不僅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產品,更是中國在全球發展領域發揮引領作用的旗艦項目,對踐行“不讓任何人掉隊”理念、構建中非發展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
世界新動蕩變革期下的非洲發展困境
自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以來,非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低潮期,且這一低潮期可能持續較長時間:一方面體現在持續近20年的“非洲崛起”逐漸褪色并被新冠肺炎疫情所終結,另一方面體現為國際社會對非洲發展支持力度的大幅下降。
從內部動力看,在經歷了1994—2014年長達2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之后,非洲可持續發展遭遇重大挫折。一方面,非洲經濟持續增長的中長期態勢不容樂觀。考察冷戰結束后的非洲經濟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盡管在1995年和1996年非洲經濟有明顯增長,但“非洲崛起”很大程度上集中在2000—2014年間。自2014年起,非洲經濟先后遭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中美經貿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沖擊。特別是在疫情影響下,2020年非洲經濟出現半個世紀來的首次逆增長,增幅為-2.1%。2021年,非洲經濟增速恢復至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非洲2022年增速僅為3.7%。非洲發展銀行認為,到2024年以前非洲經濟增速都不太可能恢復到4%以上。如果以可持續發展目標來衡量,疫情事實上使非洲發展“不進反退”。例如,以2015年美元價格計算,疫情使非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倒退了10年:2020年為1564美元,僅與2010年水平(1531美元)相當。從減貧角度看,疫情使非洲過去20年的努力化為烏有,超過40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
另一方面,非洲發展的宏觀環境急劇惡化,資金缺口持續拉大。21世紀初“非洲崛起”的樂觀氣氛推動非洲多數國家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但自2014年起,日益嚴峻的國際收支平衡風險和快速上升的債務風險與疫情相疊加,使非洲發展的宏觀環境短期內難以改善。例如,非洲發展銀行在疫情暴發前估算,非洲基礎設施投資年度總需求在1300億—1700億美元之間,年度融資缺口在680億—1080億美元之間,其中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融資缺口約為每年260億美元。而疫情明顯放大了資金缺口:預計在2022—2024年間,非洲可能需要4840億美元用于應對疫情和實現經濟復蘇。財政收入下降使非洲各國債務風險迅速上升。2014年,非洲有30個國家存在債務風險,其中低風險國家11個、中風險國家14個、高風險國家僅5個;到2020年,面臨債務風險的非洲國家已增至38個,其中低風險國家1個、中風險國家16個、高風險國家15個,還有6個國家已經陷入債務危機。
從外部支持看,發達國家對非洲發展的支持自2014年起呈明顯下降態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OCEDDAC)成員國對非洲的發展援助曾經歷持續增長,但自2014年起開始下降,到2019年才恢復到2013年的水平(不考慮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而在疫情暴發后,2020年非洲所得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援助額并無明顯增長,其在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全球援助中所占比例事實上還呈下降態勢(見圖1)。
盡管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官方宣稱,其成員國在2020年共向全球提供1612億美元的對外援助,比2019年實際增長54億美元,增幅為3.5%。但這一增長主要體現為抗疫援助,共計約120億美元。這意味著,相比2019年,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的對外援助額事實上減少了66億美元。盡管缺乏援助非洲的細分數據,但結合圖1推測,情況不容樂觀。

圖1 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對非洲提供的發展援助,2008—2020年
發達國家在對非洲援助中有其虛偽性。一方面,對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可以發現,發達國家事實上大幅降低了對國際發展合作的貢獻。兩次危機的最大差異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西方引發的,無論是國內救援還是對外援助,救助對象都是西方自身;而新冠肺炎疫情屬于不可抗力,對外援助并非自救。因此,2008年時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提供的援助非常多;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除少數國家外,絕大多數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的對外援助都呈明顯下降態勢(見圖2)。

圖2 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提供的對外援助,2008年與2020年對比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通過協議鎖定疫苗,使非洲業已嚴峻的“免疫鴻溝”再度加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截至2022年3月底,盡管非洲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在世界各地區中最少,但其疫苗接種率也低得令人吃驚:每100人中接種疫苗劑次僅為25.4劑,與之相比,西太平洋地區則高達208.1劑,即平均每人都接種了兩針疫苗;就每100人中完成兩針疫苗接種的比例而言,非洲僅為12.35%,而西太平洋地區高達81.39%。雖然有觀點認為,非洲人是出于殖民歷史記憶對接種疫苗存在某種擔憂而導致接種率較低,但更關鍵的事實是,非洲難以獲得充足的疫苗。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發達國家往往通過與疫苗生產商簽署保密協議而提前鎖定疫苗產量,這不僅使真正可流通的疫苗數量大為減少,更哄抬了疫苗價格——因為各國鎖定疫苗的協議價格并不透明。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數據,截至2022年3月,由于經費及其他原因,非盟僅為整個非洲鎖定了4.86億劑疫苗,這一數量甚至比日本、英國等都要少得多(圖3)。

圖3 主要國家和地區利用協議鎖定疫苗(億劑)情況
全球發展倡議對非洲發展的重要意義
全球發展倡議是在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滯后且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背景下提出的,對面臨嚴峻發展困難的非洲地區尤為重要。通過與《中非合作論壇—達喀爾行動計劃(2022—2024年)》、《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非盟《2063年議程》及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有效對接,全球發展倡議可為非洲提供更為強勁的復蘇動能,促進非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和中非發展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第一,全球發展倡議可幫助非洲“加速行動”,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盡管國際社會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的熱情很高,但自2006年啟動落實以來,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沖擊下,各國的落實步伐明顯過于緩慢。因此,聯合國在2019年提出可持續發展目標“行動十年”計劃,呼吁國際社會加大行動力度以確保到2030年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疫情的暴發使實現“行動十年”計劃的條件不再充分。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場景模擬研究,即使是在疫情并不嚴重的普通疫情場景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前景也不樂觀。而當前的疫情顯然已超過普通疫情水平,達到了嚴重疫情即疫情長期持續、病毒持續變異的程度。因此,只有實行“加速行動”,采取包容性綠色增長的針對性干預,包括在國家治理、社會保障、綠色經濟和數字化等方面實現整合性政策,才可能有效緩解疫情沖擊,幫助各國重回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快車道。以可持續發展目標一(SDG-1)即全面消除貧困為例,疫情使全球貧困發生率重回12%左右。如使全球貧困發生率降至6%的水平,在采取“加速行動”的情況下到2030年可能實現這一目標,而如果不采取“加速行動”則要到2050年才能實現(見圖4)。由于非洲是全球貧困發生率最高的地區,因此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對非洲采取“加速行動”可謂“及時雨”。

圖4 可持續發展目標一的場景模擬
第二,全球發展倡議可有效整合中國的國際發展承諾,提升中非發展合作效率。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可使中國的發展合作與市場合作實現更為有效的平衡。在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努力中,中國的減貧貢獻占全球76%;目前,中國已提前10年實現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中國承諾努力促進國際發展,并與伙伴方共同制定了多項長期合作愿景,如2018年11月的《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2021年11月的《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等。在全球發展倡議提出之前,與重點促進市場合作的“一帶一路”倡議相比,中國的國際發展承諾系統性還不明顯。全球發展倡議提供了整合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的框架,并將推動發展合作與市場合作兩大支柱平衡發展。

在肯尼亞內羅畢馬薩雷,一名志愿者(右一)給學生們上課。
從非洲來看,這一平衡發展的作用會更為明顯。一方面,《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為中非全方位合作提供了中長期戰略指南,可使每屆論壇的3年行動計劃變得更加合理。另一方面,全球發展倡議為中非合作補足了發展合作的戰略框架。傳統上,中非合作包括政治、經濟、安全、人文及國際合作五個支柱,但無論是2006年的“八項舉措”還是2015年的“十大合作計劃”,以及2018年的“八大行動”和2021年的“九項工程”,發展合作都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以全球發展倡議統領中非發展合作,并成為中非合作的第六大支柱,將極大促進中非發展合作的深入推進。
第三,全球發展倡議可有效發揮中國資金的額外性和催化劑功能,緩解非洲發展籌資困境。全球發展倡議是在國際社會特別是非洲面臨巨大籌資困難的背景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通過統籌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資金,并提升其額外性和催化劑效應,可為緩解國際社會特別是非洲的發展籌資困難作出重要貢獻。額外性和催化劑都是國際投資的重要原則。前者指投資于其他投資者尚未進入或不愿進入的國家、部門、地區、資本工業或商業模式;后者指涌入商業投資者特別是當地投資者聚集的領域從而提升資本利用效率,也可能是通過其投資帶動其他投資者加入從而實現一種杠桿作用。
全球發展倡議強調堅持普惠包容,并強調重點推進減貧、糧食安全、抗疫、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其重點關注的脆弱國家多數位于非洲。換句話說,普惠包容和行動導向兩個方面,凸顯的是全球發展倡議對傳統援助方不愿關注的國家、地區和部門等方面發揮的額外性作用。
全球發展倡議強調的堅持發展優先、以人民為中心、創新驅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原則,凸顯了中國資金的催化劑作用,即通過促進既有國際發展努力、推動全球發展進程的協同增資,從而加快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落實步伐。同時,全球發展倡議的資金可與以“一帶一路”倡議為核心的市場合作相結合,形成“發展+合作”雙軌并行、相互促進的新型發展促進方法,發揮援助資金與市場投資的強大資本動員能力或杠桿作用。例如,無論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是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其杠桿功能都越來越明顯,撬動了大量的市場資金。此外,全球發展倡議通過為私人資本不愿或難以進入的項目注入前期啟動資本,也將極大地帶動私人資本進入,從而提升其催化劑效應,緩解非洲的資金困境。

中國專家組成員在布基納法索中西大區水稻示范區查看苗情。
中非發展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路徑
伴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也要從基本模塊抓起。以良好的中非發展合作為基礎,全球發展倡議將明顯加速推動中非發展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當然,這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將中非雙方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的發展愿景緊密結合,通過短期政策、中期戰略、長期愿景分階段落實,使中非發展命運共同體成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示范工程。
第一,將每3年一屆的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所制定的行動計劃作為中非發展合作的短期行動策略,不斷夯實中非發展命運共同體的基礎。盡管每屆論壇的行動計劃都存在差異,但其核心要素及結構大致是相似的。回顧自2000年以來歷屆論壇的行動計劃可以發現,貿易促進、投資驅動、減貧惠農、衛生健康、科技創新、綠色發展、人文交流以及和平安全都是核心要素。其中,減貧合作、公共衛生、技術轉移、綠色發展、人力資源等都是中非發展合作的傳統領域。盡管不同時期國際環境和中非發展優先次序存在差異,但對中非合作論壇的行動計劃而言,更多是依據不同的背景對優先次序作適當調整。隨著《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的制定和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今后的論壇行動計劃將擁有更為合理的邏輯,各行動計劃之間的相互銜接將更為順暢,中非發展合作效益將更為明顯。
第二,每10—15年作滾動式中期戰略規劃,特別是要實現《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與非盟《2063年議程》十年執行規劃的高水平對接。由于啟動規劃時間不同,《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啟動之際,事實上非盟《2063年議程》的第一個十年執行規劃(2014—2023年)即將結束,第二個十年執行規劃尚未制定。因此,短期而言,在推動《中非合作論壇—達喀爾行動計劃(2022—2024年)》落實的過程中,應密切關注非盟《2063年議程》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十年執行規劃的銜接問題,并根據第一個十年執行規劃的實現水平,及時調整《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的具體執行方案。
根據非盟2022年初發布的評估報告,到2021年底,非盟《2063年議程》的20個衡量指標中,僅2項目標的實現率超過80%,另有3項目標的實現率超過70%,實現率在50%—60%之間的目標有4個。換句話說,實現率超過50%的目標僅9個,不到總數的一半。更值得關注的是,與2019年的第一次評估相比,有4個目標出現了倒退,其中目標1和目標15倒退超過20個百分點,目標9的倒退幅度更是難以衡量(見表1)。目前看來,非盟《2063年議程》第一個十年執行規劃整體上將不能如期實現,因此其第二個十年執行規劃的使命很大程度上已經明確,中非合作到2035年的中期戰略應優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基礎相對較好且對非洲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的目標,包括目標3、目標10及目標13;另一方面則是基礎較差,但對非洲民生意義重大的目標,包括目標1、目標2、目標4、目標9及目標16。

表1:非盟《2063年議程》落實水平
第三,著眼中國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非洲第一個百年目標(非盟《2063年議程》)及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的高遠視角,考量非洲的長期發展愿景并作出靈活調整。由于中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非洲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均已設立,因此重點是聯合國發展議程的后續議程。首先,需要思考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聚焦群體的演變。21世紀以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一方面聚焦減貧或者說關注“窮人”,另一方面聚焦“性別”議題,主要是指“女性”群體。因此,界定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后續議程的聚焦群體就相當重要。目前主要有兩個候選群體,一是“年輕人”,二是“病人”。前者自“阿拉伯之春”后被廣泛關注,后者則因疫情而高度凸顯。其次,需要思考國際發展籌資體系的建設。中國已經并繼續為國際發展籌資作出重要貢獻,全球發展倡議便是最新例證。中國對整個國際發展籌資體系的貢獻仍在提升之中,有必要以中國貢獻推動升級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建設,即發達國家真正兌現其國民生產總值(GNP)0.7%對外援助的承諾;新興發展伙伴參照氣候變化的國別自主貢獻原則,設定對外援助的自主貢獻目標;而發展中國家或受援國則要設定自己的國內資源動員目標(見圖5)。如果升級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得到有效體現,中國貢獻特別是全球發展倡議的國際能見度也將大大提升。

圖5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2.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