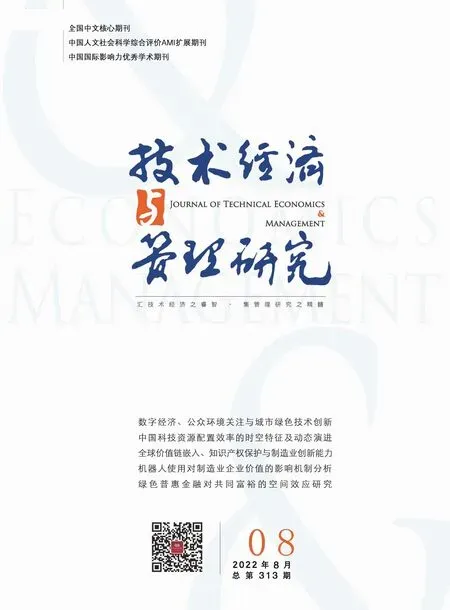產業政策視角下產業協同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劉 肖,金 浩
(河北工業大學,天津 300401)
一、引言
全球經濟呈現向“服務經濟”的轉型趨勢,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成為美國“再工業化”、德國“工業4.0”等再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重要引擎,并由于其發揮指揮和控制職能幫助跨國公司組織全球活動,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對成為世界城市網絡節點城市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1]。近年來,中央出臺《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 《中國制造2025》和《關于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等文件倡導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并促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合,以期通過兩業融合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做支撐。發達國家依靠服務外包和服務貿易的市場推動,為生產性服務業奠定良好基礎,政府僅需建設行業標準間接支持制造業服務化,制造企業服務要素占比提升已成為趨勢[2]。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體現為政府主導模式。目前,中國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耦合協調水平和產業融合均處于較低水平[3,4]。因而,探討如何激發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企業協同的積極性,以及如何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為企業間形成長期穩定協同關系提供有利條件,對推動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良性協同,培育具有競爭力的產業融合集群,發展“雙輪驅動”的內涵式經濟具有重要意義。
學者們普遍認同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之間具有相互補充、相關強化的動態協調關系[5,6]。一方面,學者們對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在產業層面的協同動因進行研究:Ciriaci&Palma[7]分析歐洲國家投入產出系統,指出制造業技術強度將會對知識密集商務服務業(KIBS)作為供應商的中間投入角色產生重要影響。郭凱明、黃靜萍[8]認為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具有高度互補性,制造業勞動率的提升有效拉動了生產性服務業需求,進而促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綦良群等[9]指出資源互補、風險分擔和利益共享是產業融合的內生動力,而政策、市場和技術是產業融合的重要外生動力。此外,資源要素基礎、技術基礎、產業關聯性、產業規制放松、技術創新和擴散、商業模式創新均是促進產業互動的重要因素[10,11]。另一方面,學者們發現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呈現臨近分布特征,并探究出現該現象的原因:Todd 等[12]指出具有相似知識需求的職業和知識共享會促使產業協同集聚。Sullivan&Strange[13]指出產業間外部性和產業協同集聚具有正向非線性作用,企業規模增加將促進產業協同集聚,但是搬遷成本過高將會阻礙企業選擇協同集聚。Diodato 等[14]指出價值鏈聯系和技能共享分別是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選址的動因,而勞動力和投入產出共享則是產業協同集聚的重要影響因素。此外,自然優勢、知識溢出、投入產出關聯、交易成本、城市規模都是協同集聚的決定因素[15,16]。
產業政策是政府利用有限資源協調產業結構轉型問題的重要手段,適宜的產業政策可以有效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17,18]。Rothwell&Zegveld[19]提出了較為經典和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分類標準,并將政策分為需求型、供給型和環境型政策。借助該分類標準,學者們探索了產業政策在不同領域的影響,黃永春等[20]指出新興大國實施需求政策有助于拉動企業趕超收益,并通過供給型政策推動創新要素集聚,而環境政策可以規范企業競爭秩序。韓超等[21]指出產業政策通過對資源進行配置影響企業績效,其中需求型政策有利于資源再配置。更多學者將法律監管和財政補貼等環境型政策作為政府調節手段重點研究。陸立軍、于斌斌[22]指出地方政府通過資金支持和搭建創新鏈平臺促進傳統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融合。Chakraborty&Chatterjee[23]發現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具有促進作用。韓瑩、陳國宏[24]指出政府可以通過制定適合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加強對企業的監管,利用獎懲制度彌補市場非正式契約不足,糾正企業機會成本傾向。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從產業關聯角度和集聚外部性視角對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互動關系和產業協同動因進行了有益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產業政策多用于新能源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探討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過程中多數文獻常將政府作為外生變量,并未考慮政府的重要作用。其次,產業協同研究多從靜態視角和宏觀層面進行研究,忽視了主體決策的動態性。為此,文章構建制造企業、生產性服務企業和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主體在產業協同過程中的演化均衡策略,并運用Matlab 數值仿真進一步研究各類產業政策對系統均衡的影響程度,以期為促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提供有建設性的建議。
文章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第一,在研究設計上,文章將政府作為內生變量,將制造企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納入同一研究框架,重視政府實施產業政策在產業協同過程中的作用;第二,在研究內容上,考察了系統各主體決策的影響因素,明確了何種產業政策對推動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更具效果,為企業管理和產業政策提供相關理論決策支持;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將演化博弈方法應用于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機制研究,充分考慮各微觀主體的群體性和策略選擇的動態性,豐富了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的研究成果。
二、產業協同演化博弈建模
1. 模型假設
第一,制造企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均是有限理性,不考慮其他約束條件,各主體學習、試錯和模仿進行隨機配對的多次博弈,并在過程中調整策略以追求最優收益。制造企業選擇策略為{積極協同,消極協同},制造企業選擇積極協同的概率為x(0≤x≤1),而選擇消極協同的概率為1-x。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策略組合為{積極協同,消極協同},其選擇積極協同的概率為y(0≤y≤1),而選擇消極協同的概率為1-y。政府的策略組合為{積極支持,消極支持},積極支持指政府實施產業政策,選擇積極支持的概率為z(0≤z≤1),而選擇消極支持的概率為1-z。x、y和z均是關于時間t的函數。
第二,參考Rothwell&Zegveld[19]、韓超等[21]的做法將政策分為需求型、供給型和環境型政策。結合實際情況,文章將產業政策聚焦于政府應用示范推廣、信息基礎設施和服務公共平臺建設、稅收優惠以及法律規制,分別代表了需求型、供給型、激勵環境型和懲罰環境型政策,各類政策執行成本分別為mD、nS、fT和hP,其中,m、n、f、h為不同政策的執行力度,且m,n,f,h∈[0,1]。若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積極支持產業協同,將會獲取產業協同收益V3。政府消極支持獲取收益E3,但在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條件下,政府將會獲取外部性收益bV3,其中b為外部性收益系數,b∈[0,1]。
第三,制造企業消極協同時獲取基本收益E1,選擇積極協同策略會付出協同成本C1,若實現產業協同將獲取協同收益V1。借鑒吳君民等(2021)的觀點,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有意愿協同時會簽訂合同預付定金以防違約,因而假設雙方均有意協同條件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背叛協同則會支付給制造企業定金K。制造企業積極購買生產性服務,能夠提高品牌聲譽W。借鑒汪明月、李穎明[25]的觀點,品牌聲譽W僅與制造企業行為有關,與其他主體行為策略無關。當政府積極支持產業協同時,政府采購產品和推廣宣傳為制造企業帶來額外協同收益mV0。若制造企業積極協同將會獲取稅收補貼r1fT。但如果制造企業違反合約,將會受到法律監管懲罰hP1。此外,當政府建設信息基礎服務設施和服務平臺改善服務供給質量時,制造企業也會降低協同成本a1nS。
第四,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消極協同時獲取基本收益E2,選擇積極協同策略付出協同成本C2,若實現產業協同將會獲取協同收益V2。若制造企業背叛協同將會獲取定金K。若政府積極支持產業協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受益于信息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的完善降低協同成本a2nS。若生產性服務業企業與制造業積極協同將會獲取稅收補貼r2fT,但如果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違反合約,將會受到法律制裁hP2。
2. 模型構建
根據模型假設可得到制造企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的支付矩陣,見表1 和表2。

表1 政府積極支持策略(z)時三方支付矩陣

表2 政府消極支持策略(1- z)時三方支付矩陣
第一,制造企業選擇積極協同戰略的期望收益Ux1、消極協同戰略的期望收益Ux2以及復制方程分別為:

第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選擇積極協同戰略的期望收益Uy1、消極協同戰略的期望收益Uy2以及復制方程分別為:

第三,政府選擇積極支持戰略的期望收益Uz1、消極支持戰略的期望收益Uz2以及復制方程分別為:

三、參與主體策略選擇演化均衡
演化過程穩定策略分析的目的是尋找各博弈主體和動態系統的長期均衡策略。文章首先分別分析制造企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演化策略的漸進穩定性,然后分析產業協同系統的演化穩定性。
1. 制造企業策略選擇穩定性
制造企業選擇協同策略概率對其穩定均衡策略的影響為:

命題1:x的概率隨著y和z概率的上升而增長,即當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傾向于協同,且政府偏向實施產業政策時,制造企業將傾向選擇積極協同策略。

命題2:當制造企業協同成本較低時,即滿足C1
根據命題1 和命題2 可知,當制造企業協同成本較高時,滿足條件C1>max{K+W+a1nS+r1fT+(V1+hP1+mV0)y,K+W+V1+(a1nS+r1fT+hP1+mV0)z},無論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采取何種決策,制造企業都傾向于選擇消極協同。當制造企業的協同成本較低時,即滿足C1 上述結果表明制造企業協同成本對制造企業的策略選擇具有較強影響,當制造企業的協同成本處于中間水平,生產性服務企業和政府的決策會對制造企業的策略選擇產生影響。 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選擇協同策略概率對其穩定均衡策略的影響可以通過公式(11)進行描述: 命題3:y的概率隨著x和z概率的上升而增長,即當制造企業傾向于選擇積極協同策略,且政府偏向于實施產業政策時,生產性服務業企業也將傾向于選擇積極協同策略。 命題4:當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成本較低時,即滿足C2 根據命題3、4 可知,當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成本較高時,滿足條件C2>max{K+V2+hP2+(a2nS+r2fT)z,K+a2nS+r2fT(V2+hP2)y},無論制造企業和政府采取何種策略,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都傾向于選擇消極策略。當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協同成本較低時,即C2 上述結果表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成本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策略選擇具有較強影響,當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協同成本處于中間水平,制造企業和政府的決策會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策略選擇產生影響。 政府選擇積極策略概率對其穩定均衡策略的影響可以通過公式(12)進行描述: 令F(z)=0,可得在以上三種情形下,所有的z均為穩定狀態,政府的策略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改變。在其他情況下,政府策略選擇需要考慮眾多因素的綜合影響。 在非對稱演化博弈中,僅需考慮E1=(0,0,0)、E2=(0,0,1)、E3=(0,1,0)、E4=(1,0,0)、E5=(1,1,0)、E6=(1,0,1)、E7=(0,1,1)、E8=(1,1,1)八個均衡點的穩定性,并根據李雅普諾夫判別法,對均衡點的穩定性進行判斷。不同參數假設會對協同策略的演化均衡產生影響,并主要包含以下三種情形: 情形1:若C1>K+W且C2>K,表示制造企業協同成本大于生產性服務企業背叛所支付的定金以及制造企業有意協同增加的商譽價值,同時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成本大于制造企業毀約的定金。在該情形上,僅有E1為穩定平衡點,對應的演化策略為(消極協同,消極協同,消極支持)。 情形2:若mD+nS+fT-(1-b3)V3>0,C1>K+W且C2>K,表示政府在實施政策獲取的產業協同收益V3和政府選擇不實施政策時獲取的收益bV3的收益差額不足以彌補政府積極支持的成本,制造企業協同成本大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毀約的定金以及制造企業有意協同增加商譽,同時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成本大于制造企業毀約的定金。在該情形下,Jacobian 矩陣的均衡點E1和E5的特征值均是負值,根據判別法,E1和E5為穩定平衡點,(消極協同,消極協同,消極支持) 和(積極協同,積極協同,消極支持) 為演化穩定策略。 情形3:若mD+nS+fT-(1-b3)V3<0,C1>K+W且C2>K,表示政府在實施政策獲取的產業協同收益V3和政府選擇不實施政策時獲取的收益bV3的收益差額足以彌補政府積極支持的成本,制造企業協同成本大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毀約的定金以及制造企業有意協同增加商譽,同時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成本大于制造企業毀約的定金。在該情形下,E1和E8為穩定平衡點,(消極協同,消極協同,消極支持) 和(積極協同,積極協同,積極支持) 為演化穩定策略。 各參數設定如下:C1=16,V1=30,C2=18,V2=25,V3=60,D=S=T=20,m=n=f=h=0.1,P1=8,P2=6,V0=5,a1=0.2,a2=0.6,r1=r2=0.5,b=0.4,K=1,W=1,x=y=z=0.5。 圖1反映了僅有需求型政策執行力度改變對產業協同系統策略的影響。在僅提高需求型政策執行力度時,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積極參與意愿最終都趨于0,最終達到穩定點E1,且伴隨需求型政策執行力度的加大,各博弈主體積極參與協同意愿趨向于0 的速度明顯加快。究其原因,需求型政策是通過鼓勵、引導制造企業增強其購買中間服務需求間接促進產業協同,當制造企業積極協同意愿無法在短時間內迅速上升時,對政府無法形成激勵反饋,政府積極支持意愿迅速下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也因協同成本等原因協同意愿具有下降趨勢。在政府實施需求型政策時,制造企業積極協同的激勵主要源于政府采購提供生產性服務的制造產品獲取額外收益以及作為產業融合示范點的品牌效益,因此制造企業協同意愿雖然因政策執行力度加強有微弱上升,但受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意愿影響,制造企業積極協同意愿會迅速下降。 圖1 需求型政策不同執行力度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圖2反映了僅有供給型政策執行力度改變對產業協同系統策略的影響,結果發現只有當供給型政策執行力度高于一定水平時,才能提高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積極協同的意愿。供給型政策執行力度n臨界值處于0.2~0.3 之間,當n小于該臨界值時,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積極協同意愿以及政府積極實施政策意愿都將收斂于0,最終系統趨向穩定點E1。伴隨政府供給型政策執行力度增加,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積極協同意愿以及政府積極支持意愿下降速度減慢。當n大于該臨界值時,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積極協同意愿以及政府積極支持意愿都將收斂于1,最終系統趨向穩定點E8。究其原因,政府加強供給型政策的執行力度,能夠大幅降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成本,并降低產業協同的交易成本,從而促進生產性服務的深度應用。因此供給型政策執行力度加大有利于提升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協同意愿。實施供給型政策時,政府前期受資金壓力的影響,積極支持意愿下降,伴隨企業積極協同意愿的提升,政府從產業協同中獲取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將會促進政府支持意愿提升。如果政府實施高強度的供給政策,資金壓力致使支持意愿下降,也會對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意愿產生一定的阻礙作用。 圖2 供給型政策不同執行力度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圖3反映了僅有激勵環境型政策執行力度改變對產業協同系統策略的影響,結果發現當激勵環境型政策執行力度達到一定水平時,即可提高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積極協同意愿。激勵環境型政策執行力度f臨界值處于在0.1~0.2 之間。當f小于該臨界值時,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積極協同意愿以及政府積極支持意愿都將收斂于0,最終系統趨向穩定點E1。當f大于該臨界值時,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積極協同意愿以及政府積極支持意愿都將上升并收斂于1,最終系統趨向穩定點E8。政府減免稅收補償了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協同成本消耗,伴隨政府補貼力度加大,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協同成本不斷降低,企業協同意愿更加強烈,高強度的激勵環境政策對企業協同具有積極影響。對政府而言,激勵型政策執行力度越強,限于財政支出壓力,前期政府積極支持意愿下降,但受企業協同意愿影響,后期政府支持意愿增長明顯。 圖3 激勵環境型政策不同執行力度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圖4反映了僅有懲罰環境型政策執行力度改變對產業協同系統策略的影響,結果發現當懲罰環境型政策執行力度達到一定水平時,可提高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積極協同意愿。懲罰環境型政策執行力度h臨界值處于0.2~0.3 之間。當h小于該臨界值時,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積極協同意愿以及政府積極支持意愿都將收斂于0,最終系統趨向穩定點E1。當h大于該臨界值時,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積極協同意愿以及政府積極支持意愿都將上升并收斂于1,最終系統趨向穩定點E8。說明當政府加強法律監管執行力度,對企業違約行為進行實質約束,有利于建設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從而促進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深度協同。 圖4 懲罰環境型政策不同執行力度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文章基于演化博弈理論,構建制造企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組成的產業協同演化博弈模型,對各方參與者的穩定策略進行分析,并利用Matlab 軟件進行仿真,分析各類政策不同執行力度對系統演化的影響,得到以下結論和啟示: 第一,政府積極實施產業政策對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協同策略具有積極影響,制造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積極協同策略對彼此的積極協同意愿具有強化作用。因而,政府應主動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各種便利條件,深度挖掘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動力,進而驅動產業協同。 第二,企業協同成本對博弈主體策略選擇具有重要影響,當博弈主體采取積極策略成本過高時,會選擇消極策略;而采取積極策略成本較低時,會選擇積極策略。而當博弈主體采取積極策略處于中等水平時,其他主體的協同意愿將會對其策略選擇產生重要影響。因而,一方面,通過穩健推進金融服務創新,積極吸引金融機構、民營資本和國外資本進入,提供更低成本、更便捷的金融服務,降低企業協同融資成本,并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另一方面,通過建設文化軟環境等方面的努力,降低各主體協同的交易成本。根據合同履約情況和法院判決等信息建立涵蓋各個行業透明、共享的“黑名單”制度,并利用信息技術即時發布相關信息,提高個體的違約成本。 第三,在各項政策中,政府在僅提高需求型政策執行力度時,對產業協同系統的有效支持較弱,且伴隨執行力度加大,對產業協同的不利影響也在增強。加強供給型政策執行力度有助于促進產業協同,但是須合理把控政策的執行力度。高強度的激勵型和懲罰型政策執行力度,將會促進制造企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政府積極參與協同。因而,政府優先考慮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發明專利權、商標權等無形資產的侵權行為加大懲治力度,建立有序的市場環境,逐步推動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此外,政府應該合理發揮稅收優惠的積極作用并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企業協同的積極性。2. 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策略選擇穩定性

3. 政府策略選擇穩定性

4. 產業協同系統策略的演化均衡
四、數值仿真
1. 需求型政策執行力度對產業協同演化行為的影響

2. 供給型政策執行力度對產業協同演化行為的影響

3. 激勵環境型政策對產業協同演化行為的影響

4. 懲罰環境型政策對產業協同演化行為的影響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