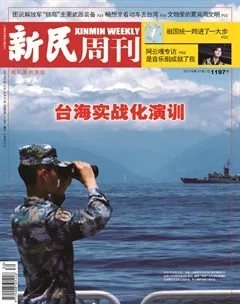夏天的滋味
姚謙

音樂制作人Music Producer游走于兩岸音樂界
今年7月意外失眠了幾次。
失眠早已經不再是我的困擾了,多年前家庭醫生定期的睡眠處方,讓我這些年來對于睡眠這件自少年起就擾人的事算是掌握好了,除了換季或調時差以外。但是入夏后的這兩周卻又讓我嘗到了不可控的失眠之苦,每次都是不預期的,入睡后不久在凌晨二三點醒來。這與早年失眠的節奏不同:當年是受困于入眠困難的焦慮,而現在是離清晨還遠的清醒。我想這跟醫生給我的處方沒有關系,因為入睡依然順利并且得到了休息,問題是在不該醒的時候醒了。我想這跟今年的高溫和夜晚降溫緩慢有關。
超高溫年年夏天都會發生,甚至近幾年會延續到初秋,我在面對高氣溫時節有一套安穩睡眠模式:我的習慣都是在睡前一個小時,預先把臥房的空調冷氣開足,先把室內溫降到20度左右,讓自己上床時觸碰到枕頭、被子和整個房間的空氣都是沁涼感,一解白天盛夏的壓迫,在一個微低溫的放松環境中上床;臨上床時就關上了空調。在過往的經驗里面,室外溫度會隨著入夜而從高溫緩緩降低,而臥房的溫度也從低溫中慢慢地回溫,當室內室外溫度達到協調時已經清晨,我也早已在踢開涼被中緩緩醒來,但這招卻在今年夏天算是徹底失靈了。特別是這二周多次天色仍黑中醒來,時不時滿身大汗被熱醒,縱然我再開空調,也失去了涼意的沁心感,而且已無睡意了;甚至自覺初老的身體,對于急速降低溫度感到不適。此時我唯一面對失眠的方法就是:起身干點別的事。
此時我唯一面對失眠的方法就是:起身干點別的事。
青年前的我是在臺灣南方度過,臺灣是亞熱帶天氣,童年時家里沒有空調,熱了就對著風扇吹,滿頭大汗也不擔心著涼,所以對盛夏高溫習之以常,不覺得被打擾或是厭煩;從小至今就是一個流汗達人,對于流汗我都有種放松的愉快感;只是成人后看別人眼中描述流汗發達者,有時是一種邋遢與狼狽暗喻,這讓我開始比較小心地處理自己在人前形象,怕一不小心就漏餡了:汗流浹背的真我狀態,幸好空調的普及。打開空調真是應付夏天最容易的事了,但是它也帶來了副作用,例如我的鼻子過敏的老毛病夏天也患;因為溫度一低,鼻子就不老實,老打噴嚏,在這疫情敏感之年,特別尷尬。
只是沒想到,今年7月的北京熱得不尋常,雖然高溫是預期中的不可免,但是今年的濕熱不散則不多見,像極了南方。幾次跟家人通話,家人說今年臺北反倒還好,因為今夏延續上半年的多雨,又有臺風助陣,所以沒有比往年熱。這不禁讓我想念起過往的北京夏天,再高溫也還是保留干爽的性格,有風!所有的熱意都是可以解決的,常常午后風一起就爽快地來場十分鐘大雨,痛快淋漓!晚上出門散步已經不怕地表反熱氣的蒸騰。可惜今年夏天,直到動筆寫著這篇稿子,都還沒有過黃昏公園的涼夏散步。
今夏對應氣候變化和能源危機,我的策略是:先強化了家中風扇設備,讓空間的氣流加強,不要過度依賴空調;這樣還算不錯地度過白天,但是夜晚還是失策了。雖然如此想想也不算太懊惱,反而在清晨3點起來看看書、聽聽播客,多了些安靜時光,大概五六點的時候,也許還可以回頭再睡個一小時。
想著這個夏天被復雜嚴實的疫情嚇得不敢出外,只能冒著冰鏈運送的風險,已經吃遍三省名種荔枝和不同地域四五種顏色的桃子。在不自由的盛夏夜晚,以冰涼果味抵御高溫。也許多年之后想起,半夜失眠看著書還有來自遠方的果香,將是2022年之夏的特別回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