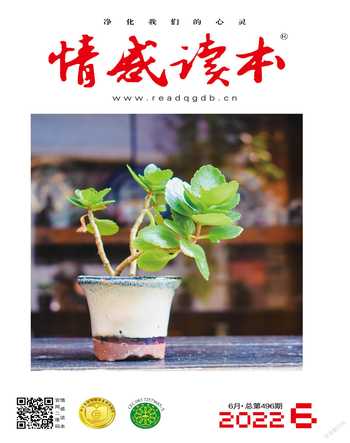你越來越能干了,父親卻老了
蔣瞰
我們覺得你掙錢不容易,不想花你的錢。你知道嗎?你現在能干了,而我們卻變得小心翼翼,你爸爸也是。
我們認識二十七年。我所記得的是,一看到我在畫畫,父親就不高興,哪怕老師告訴他“你女兒很有畫畫天分”,他還是自作主張幫我磨墨、鋪紙,嚇得我只有躲進廁所便秘。雖然后來鋼筆字還獲了個全國獎,但我至今沒弄明白,繪畫和書法差別在哪里。
年齡還在個位數時,他帶我去湖州大廈最高樓喝早茶,自己卻不吃,事后母親嘆息:你要寵女兒也不是這樣溺愛!至今我仍然喜歡上午十點去吃點心,可惜杭州并不多。
每天作業要簽字,只要發現有一個叉(尤其數學),他的臉色就會變得很難看,我小時候沒少吃過巴掌,動輒被打屁股,而我也奇跡般地從一個數學弱智到考150分滿分。
江南少雪,那年,上夜班的父親一見到積得厚厚的鵝毛大雪,立馬把我從床上拖起騎上自行車去花園拍雪景。多少張諸如此類隔夜的臉都被拍出了特寫效果,森友治的《家庭日記》不是贏得諸多追捧嗎,十幾年前我已擁有,只我一人未發覺。
對,我就是在這種既苛刻又寵溺的環境下被養大,現在流行說“女孩富養”,我覺得自己夠格;卻也不時有些諸如重男輕女、孤獨冷清的小陰暗窸窸窣窣爬出來。
而回憶,又豈是三言兩語能明細的,我不想再想下去。
父親這個人,從不曾流露過任何黏勁兒,不像母親會把想法直接說出來。你要回來,就回來,要走,就走,好像我的任何舉動在他看來都可以不動聲色地被應允。而我也因為他曾說過“要去就去北京”,誤以為父母是希望我遠走的,甚至一度覺得僅僅留在杭州,還是挺丟人的。
前天和朋友吃午飯,朋友是父親的下屬,她以為不方便,湊在我耳邊:“你爸爸好像不大情愿你出國?”我說:“是啊,這又不是什么秘密,他們總覺得這個姑娘太折騰了。”我又問:“你咋知道?”朋友說,有次在電梯里碰上,她以為是好事就恭喜我爸,結果他一個勁兒甩頭,一副“女大不中留”的無奈。
我突然覺得父親老了。
他開始婆媽,開始不介意變得細碎。
就說昨天。我的QQ簽名始終兩種,“在杭州”或是“不在杭州”,這次回來后,沒來得及改掉。他急了,一個短信發來:“你又不在杭州了?”
若要畫一個軸線來表達我們這對父女,我想應該是:天生喜歡男孩對女兒失望——自己的孩子沒法不愛——不爭氣給我給我們家族丟臉——很優秀讓我臉上有光——我們好像隔著很多。
而我,卻變得陌生,讓自己陌生,讓父母陌生,不知道我被這個世界怎么了,還是我把這個世界怎么了。
我跟一個一日三餐吃了五十多年米飯的父親講吃素,宣揚一天一頓主食的理論,期望他能和我一樣少吃一點。
我跟他講我又住了什么酒店,講有勞斯萊斯來接送的風光,他卻不吭一聲像是不想介入這種無謂的奢侈。
我跟他講同樣的職位,為什么人家的父親能幫子女搞定一切,而我卻什么都要自己爭取。
我跟他講,如果連這次,你都不愿意叫車來杭州把我的被子衣服運回家,我就當著你的面把東西全部從陽臺上扔出去。
不是炫耀,不是威脅,聽起來,卻那么殘忍,我說這些是為了什么?
說過后的大多時候,我沉默,我擺臭臉。
是過年在泰國,我朝母親發脾氣:“你們為什么從不說要吃什么,要玩什么,為什么都要依我?”母親哭了,她很直接地告訴我:“我們覺得你掙錢不容易,不想花你的錢。你知道嗎?你現在能干了,而我們卻變得小心翼翼,你爸爸也是。”
最后一句話刺痛了我。
這八年,我身上沾染了太多太多的戾氣和俗氣,而世上最愛我的兩個人對這一切卻選擇了忍耐甚至退讓。
我在腦海里繪制出天倫生活:前陽臺種花,后露臺摘果,上午做菜下午游泳,先看《新聞聯播》,二十七年雷打不動,再看電視連續劇——這幾年,他們越來越一致地追國產電視劇,有時還會說給我聽,感同身受的樣子,而我始終認為,開始看家庭劇,真的說明人老了。
我們吵吵鬧鬧,為的是:
我:“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啊,你怎么又忘了!”
母親:“你媽我年紀大了,忘記不是很正常嘛!”
我:“你把我的東西又放哪里啦,回到家就是找不到東西!”
母親:“你常年不在,你的東西當然都給你收好的啊,不是你一來,毛巾茶杯都給你準備妥當了嘛!”
我:“我們家怎么連個好的吹風機也沒有啊,這個不是用了二十多年啦!”
母親:“少用吹風機,會把頭發吹枯的,再說了,我們還不是為了節約,我跟你爸又不吹頭發的!”
我:“給你買了日霜晚霜,你怎么都不用啊!”
母親:“我想省著,要不送給你姨媽?她對我們家那么好!”
我:“爽膚水呢,家里怎么沒有爽膚水啊!”
母親:“在樓上你自己不看的啊!”
雞零狗碎。
是的,我帶母親把杭州的五星級酒店住了個大半,自助餐陪她吃到扶墻出,前幾天又買了衣服給她,自以為這就是對她好,是有面子的事,可是,和這些相比,母親更愿意得到一句軟語,一些順從。孝,順,往往“順”是主要的,你得順老人的意,這些我都是知道的,可是沖出嘴巴,還是一陣火辣辣。
不知是我缺席了他們的生活,還是他們缺席了我的蛻變。在這十年后再次共處的日子里,我感覺到他們小心翼翼地尊重著我那些不算習慣的習慣,尊重和保護著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女兒。(此段借鑒豆瓣蒂娜劉《我們缺席彼此最重要的十年》)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我想指望一下接下去的兩年,為歲月開一張方子。
方瑛摘自《每一個認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認真對待》(四川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