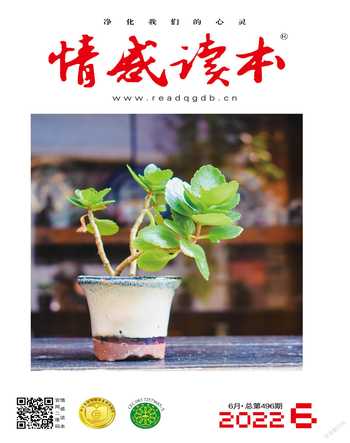下雨了,突然很想寫寫我媽
勾文君
我只知道,當我從老照片中看到結婚前的我媽——那個在洋氣的毛線帽、挺括黑色毛呢大衣襯托下的,白皙高挑、優雅年輕的女子——我是非常震驚的。
為什么突然想寫我媽呢?因為今天,杭州下了好大的雨。我媽說,她覺得最幸福的時刻就是,大人孩子都在家,倆孩子在方桌上寫作業,她坐在旁邊織毛衣,這時候,最好外面下著雨,雨下得越大越好。
這樣的畫面在我小學五年級之前,都是奢望。因為我爸在千里之外的部隊,不在家。直到現在我也不敢問我媽,那些年她是怎么過來的。只有記憶中零星的物件,可以勉強訴說一二——為了同時接送兩個孩子而被用木板加長、綁上藍底白花棉墊的自行車后座,因男主人常年不在家而多加了兩道門閂、又以原木抵住的木門……
我不怕下雨,因為我媽從不讓我們淋雨。北方的夏天,雨是不打招呼,說下就下的。有一回——我記得是初中時——下著雨,我媽來校門口接我。我坐在車座上,我媽推著車,邊走邊對我的一位女同學“抱怨”:“我們家這個,是個溫室里的花朵。”在此之前和之后,我無數次被同學說:“你媽對你可真好!”那時候的我一臉茫然——媽媽不是應該這么好的嗎?
是啊,那時候我以為,我媽為了讓我們吃新鮮的雞蛋,在自家的院子邊上養一窩雞——是理所當然的;我媽怕雞叫影響我午睡,每天中午手拿一瓢米坐在雞窩邊上,雞一叫就給一把米——是理所當然的;每天晚上,只要我倆還沒寫好作業躺好睡覺,我的警察老爸還沒“出現場”或者“行動”回到家,我媽就不會睡覺——是理所當然的……如今我因為偶有抑郁情緒,睡眠不好,第二天精神幾欲崩潰的時候,很想穿越回去問問我媽:你那時候困不困?累不累?你是怎么過來的呢?
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的確很早體會到媽媽的不容易,是從她微微佝僂的背上,還是從她偷偷吃的藥里,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當我從老照片中看到結婚前的我媽——那個在洋氣的毛線帽、挺括黑色毛呢大衣襯托下的,白皙高挑、優雅年輕的女子——我是非常震驚的。原來媽媽不是生來就是媽媽,只不過在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就已經是媽媽了。我認識我媽之后,再也沒見她買過、穿過那么時髦的衣服了。
我媽沒上過大學,所以她竭盡全力支持我們讀書。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媽不知道從哪里聽說《小學閱讀指南》的雜志,就去郵局給我們訂。那年月,整個清豐縣城,沒人訂這雜志。我媽央求郵政局的工作人員滿本子地翻,終于找到雜志的郵發代號。我媽向來勤儉持家,可是唯獨在給我們買書的時候,幾乎不看價格。她還讓我們放假時,閱讀各種經典的長篇小說。縣城的圖書館、私人的圖書館、名著多的書店,都是我們假期的常去之處。
十年后,我抱著自己幼稚的詩歌,從商學院轉專業到中文系。再后來,我成了一名語文老師,沒像小時候期待的那樣成為作家。但不管是在頂尖的學校做老師、在一流的平臺上課,還是如今做獨立教師,我一直在爭取更多的在文學世界里遨游的自由。總體而言,畢業9年來,表面看,我的狀態是鱷魚變壁虎——越活越抽抽,實際上,我越來越不用依賴外界去證明自己,越來越關注自己的內在成長了。在這個高度“內卷”的時代,我也算“反其道而行之”,并且逐步獲得精神上的舒展。
以至于兩年前,和作家畢飛宇老師第一次見面,聊到他們南大的知名校友,畢老師說:“你想去她那兒嗎?我給你寫推薦信。”我下意識地說:“我不要,做語文老師挺好的。”天地良心,我當時真的不是故作清高以求關注,偶像面前,我一萬個真心實意!因為熱愛,我懵懂但堅定地相信未來,相信青山不改,相信來日方長,相信未知的前路,尚有星辰和大海。這一切,都是我媽種下的種子。
我媽每天必看天氣預報。我上大學了,我媽不僅要看家里的天氣,還會看上海的;我弟也上大學了,我媽又把哈爾濱加入她天氣預報“勢力范圍”;我工作了,我媽要看哈爾濱、鄭州的。如今我在杭州,弟弟在北京,我媽的“天氣版圖”又變了。
我做語文老師,講過《詩經·氓》,有這樣的句子:“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我問我的學生:“復關”是個地名,作者為什么要讓女子“望復關”,還把自己的悲喜都寄托在能不能“見復關”上呢?大概因為她在乎的人在“復關”,所以這座城也顯得那么特別——哪怕只是望見了這座城,心里也能開出一朵花。就像陳奕迅歌里唱的那樣:“我來到你的城市”——我媽也是如此,她默默地把心分成幾半,日日關心著兒女的城市。
不年不節的,干嗎寫我媽呢?自己眼淚和著窗外的雨流個不住也就罷了,我媽讀了肯定也會哭。索性直接寫幾句給我媽吧——
趙建蕊同志,你好哇!
二十多年前,我偷看過你寫給我爸的信。那時,你選了一張海上巨輪的明信片,在一旁寫道:愿夫君是那遠洋的航船,為妻愿意做那船上升起的白帆。事實證明,你說的不對——你才不是白帆,你是咱家這艘航船的總指揮、總舵手!(這樣說,你大概不會追究我曝光你們夫妻陳年情話之罪了吧。追究也沒用,已經發出去了,而且,你現在打不著我!嘿哈!)
趙建蕊同志,謝謝你!
陽春摘自《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