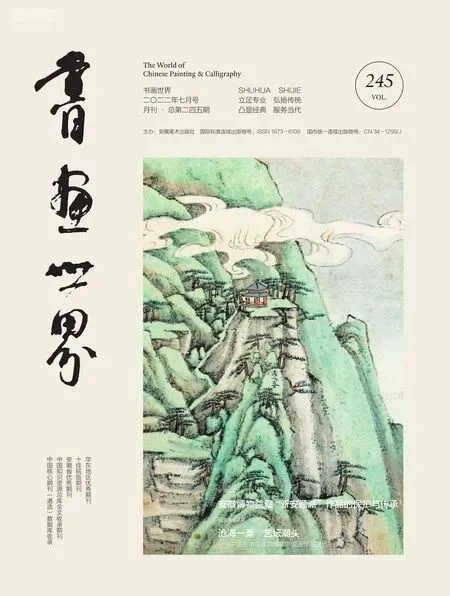從體象類物到時序評品:漢魏六朝書論中的微觀時間
文_李瓊玉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藝術學理論碩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漢魏六朝書論中,包含著微觀時間的觀念。在書論草創之初,書論家通過體象類物的方式賦予靜態的書體和筆觸以時間的動態感,經由感悟、構思、用筆力量和速度的經驗總結還原創作的時序,將技藝漸進等諸多因素促成的書家個性風格差異引入了史脈品評的范疇。這一時期對微觀時間的觀照,反映了時人對書法時間性特質的最初認知。
引言
時間性和空間性是中國書法的本質特征和核心概念,歷來為書家和書論家關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書學逐漸開始“空間轉向”,以宗白華先生對書法空間感的美學探討為先聲,邱振中、白砥、沃興華諸先生聚焦筆法、字法、章法的規律,推動書法形式研究方法體系的形成和完善,也引發了學界關于書法空間性和時間性的討論甚至爭議。實際上,盡管不少學者站在形式分析立場,但也未曾回避書法中的時間因素,就連張錫良先生的批判性文章也承認邱振中先生對書跡時間序列的觀照。
可見,時空二重性的交織,是書法研究中不可回避也無法割裂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書論肇始之時,就已經被提出。只不過,漢魏六朝書論家面對書跡,常抒發感想,或做經驗陳述,因而,其中的時間映象——靜態形體的時動意象、創作過程的時序表達,就顯得尤有趣味。此外,盡管此時的書論已初具梳理歷史脈絡的意識,但尚未見鴻篇巨制的宏大敘事,貫穿其間的是技藝的漸進和個性風格的史脈品評。因此,漢魏六朝書論中包含的時間觀念,更準確地說,是經由對微觀時間的書寫體現出來的。
現今來看,圍繞書法的時間特性,已有不少專論,或放眼宏觀,或精析法帖。學者們往往回到古典書論,尤其是在漢魏六朝書論中尋找理論依托,但都是間有引述,未做系統考察。雖然這一時期書論篇章真偽存疑,但畢竟可供參考。本文暫不涉辨偽,僅擇取經典案例,試梳理其中的微觀時間,探究其間觀念衍變的線索。
一、體象類物與靜態形體的時動意象
作為流傳至今的最早的書論篇章,崔瑗《草書勢》的字句對書學研究者來說已熟稔于心。“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以自然物象喻書法之美,是漢魏六朝書論的常見手法乃至程式,也呼應著文字創始“天垂其象,地耀其文”之地位的共識。這一點,通過崔瑗、許慎、衛恒的闡釋漸趨明晰,熊秉明先生稱之為“喻物派的書法理論”,甚為得宜。
對上述崔瑗的文字,潘運告先生進一步注釋說:“鳥獸將要‘飛移’,狡兔突然受驚將要‘奔馳’,給人強烈的時間藝術的動態感。”事實上,無論是以書跡“類”地之文,還是“體”天之象,漢魏六朝書論家都不自覺地將書法的靜態形體表述為動態的意象,注入流動的時間感。他們既面向新舊書體,也細致入微地體察獨立的筆觸。
鳥、獸、蟲、魚成為書論中的典型意象,當歸功于這一時期的頻繁使用:衛恒以其標舉古文,崔瑗、索靖、蕭衍摹狀草書,成公綏、王僧虔微舉隸體,蔡邕擬方篆勢,袁昂初涉評品。盡管庾元威記載的諸多書體多以鳥獸命名,但終究“雜體既資于畫”,與傳統的書法藝術不盡相合。伴隨著書法的自覺,為了凸顯藝術性的美感,書論家喻物很少用“蟲”“鳥”“馬”這樣寬泛的物種代稱,往往吸收神話傳說和當時的吉祥寓意,有“鸞鳳”“玄熊”“鵬羽”“騏驥”之說,有時也綴加修飾詞展現其張揚的面貌,諸如“狡兔”“鷙鳥”“騰猿”“驚鸞”。兼參漢賦鋪陳的筆調,摹寫這些動物的動態時大致沿兩條路徑:一方面,記錄完整的動作態勢,直抒其觀感,從“鳴鳳之游云漢”“鷹跱鳥震,延頸協翼,勢似凌云”“良馬騰驤,奔放向路”“玄熊對踞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諸句可見一斑;另一方面,側重描繪“蟲跂跂其若動,鳥飛飛而未揚”“若舉翅而不飛,欲走而還停”的瞬間。陳振濂先生指出:“不管是將奔將墜還是已奔已墜,都反映出運動過程在某一落點上的具體凝固形態以及足可向整個過程前后延伸的時間感覺。”在強化運動節奏的同時,這也營造了意猶未盡的想象空間。
擬書體多用鳥獸,山川草木偶爾穿插其間,表現其動態者,僅寥寥幾句。如索靖所言之草書“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又如成公綏所言之隸書“俯而察之,漂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它們與煙雨霧靄一道,被用作對筆畫形態的表述,在鐘繇、衛鑠、王羲之三人的技法傳習和理論承續中被多次重申。鐘繇善八分,“點如山摧陷,摘如雨驟”,極言筆觸之險峻淋漓,衛鑠《筆陣圖》、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后》都是其后緒:點“如山摧陷”的整體畫面被細化為“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的具象形態;而努筆如“萬歲枯藤”,則凝結著靜態時間的印痕,是“充滿生機的往昔的遺跡”。
“節奏化了的自然,可以由中國書法藝術表現出來”,蔡邕也曾說“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矣,陰陽既生,形勢出矣”。可以說,體象類物的時間性運動意象書寫,是對書論中“勢”之范疇的最初洞察。凡此數篇,大多本就是以“勢”命名。但這里的“勢”,是時間性的,“它的流動性、未完成性和開放性同樣在書法中是某種最重要的核心因素”。書作若要“盡形得勢”,心手調和甚為關鍵。因此,在漢魏六朝書論家對技法的討論中,手的節律和創作過程的時間順序,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
二、手的節律與創作過程的時序表達
書法創作的理論問題,正是在這一時期漸成體系,王僧虔《書賦》開篇之言,便理路清晰:“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于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靡深功。”寥寥數語,實則囊括了藝術創作活動從體驗、構思到傳達的全過程。
對于創作前豐富的內心活動,不獨王僧虔,蔡邕、王羲之亦有所感:作書應神情專注、開闊胸次、放縱情性,在沉靜的思考中,“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結思成矣”方可“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翰”,進而考慮技法的因素,關注筆畫的運行和手的節律在筆畫推移中的作用。
每一筆畫的完成,都是不可重復的運動過程。一畫之內,入筆須存筋藏鋒,“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收筆則要護尾隱跡。除此之外,疾勢、掠筆、澀勢等不同的筆畫,對應不同的書寫方法,巧思經營則如“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或“仰而后曳”。它們共同的規律是,通過左牽右繞的回顧,既保持相對獨立的勢態,又形成筆畫間的遞相映帶。其中經驗是,字中有點處,“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
提按之間,運筆節奏、力度各有異同,使書作呈現不同風格。趙壹對草書遲緩難寫之現狀的犀利批判,從書寫速度上揭示了書法的藝術化方向。針對具體的實踐,漢魏六朝書論家提供了參照和范例。衛鑠論執筆,“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此“緩”“急”應是指握筆力之松緊,與成公綏觀隸之“輕拂徐振,緩按急挑”、羲之所言“緩前急后”之意不盡相同。羲之還以“烏”字為例,認為點畫運筆要急,但橫畫運筆要遲。他們的標準是,摒棄過于平正而缺少變化的運筆,只有“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才可稱之為書法。
運筆之法,歷來被看作“非凡庸所知”的秘辛,通達其中奧義者甚少。對于作為個體的書家來說,技藝的嫻熟源于筆耕不輟的實踐和書寫經驗的不斷積累,加之書學師承、生平經歷等眾多因素,便形成了書家獨特的個性風格。
三、技的漸進與個性風格的史脈品評
虞和《論書表》、庾肩吾《書品》收王獻之取帚蘸泥書壁之事。庾肩吾感慨:“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天才與工夫的作用都被承認。盡管書史書論也往往樂此不疲地記錄天才的傳說,但更多地肯定投注于中的翰墨之功。庾肩吾就曾自述:“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

在時間的積淀中,年歲與書藝俱長。在漢魏六朝書論家看來,這可以從羲獻父子不同時期的書作中窺見。虞和認為,羲之早年之書,尚遜于庾翼、郗愔,在臨川時的手跡,并無可觀、可取之處,直至末年絕筆,方至妙境。陶弘景亦作如是觀,以其永和年間所書為佳。孫過庭“通會之際,人書俱老”的著名書學命題,觀念淵源應可上溯到此。
虞和還說過,“且二王暮年皆勝于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他對“古”和“今”的界定,是依據時間進行的先后對照。在此時的書家品評中,“與書家有關的時間因素在未經任何論證與推敲的前提下,很自然而默契地成為書法評論家對歷代優秀書家進行品評排位的首要選擇”。即使擬定的綱目中引入了不同的概念,但羊欣、庾肩吾、王愔都相對嚴格地遵循著這個秩序。
他們纂錄、品評書家,文字簡略但內容翔實,大多覆蓋了地域、職官、作品、師承。其中,個性風格的描述、比較與書法的藝術性最為契合。體象類物的手法,在這里仍被沿用,但受人物品藻的滲透,以人喻書的方式更為普遍。在系統地將書家納入史脈品評之前,鐘繇就已經無意中開始了這樣的嘗試,《用筆法》稱其善八分“來如游女之入花林”。引其端者,當推袁昂,“謝家子弟”“河洛少年”“大家婢為夫人”等喻,將身份、年齡各異的人物特征與書家書跡的格調一一對應。
依據歷史脈絡品評,書家個性風格和成就之間的高下之辨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衛恒整理《四體書勢》時就曾比較蔡邕與邯鄲淳,認為蔡邕尚缺精密熟練;羊欣首倡“肥”“瘦”,后蕭衍將其對照鐘繇與王獻之書風;承“筋”“骨”之說,羊欣又稱獻之“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結語
體象類物、手的節律、史脈品評,歷代書論中三種主要的論書體式,從漢魏六朝起交織演進。靜態形體的時間性運動意象、創作過程的時序表達、技的漸進與書家的個性,是此時書論家關注的重心,微觀時間的觀念便從這里呈現。他們在歷時性的揮寫中,將文字看作有生命的形象,以人的身體和性格反觀書法的風格。漢魏六朝書論中的微觀時間,暗含著書家個人的心態和經驗,也回應著人、書、自然之間和諧共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