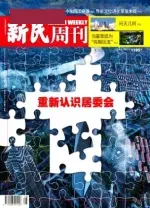天下靈犀一瞬間
何振華

滬上恢復“如常”的最初兩天,我沒去辦公室。在淮海路的那天上午,正愁著沒有一家方始營業的餐館可供堂食。周兵兄打來電話,問我是否在附近,說順道送一本他的新著給我,當然更想的是找個能坐下來的地方聊聊。我腦子里瞬間閃出一個去處,不遠有爿咖吧,往日我常去稍坐,我想,主人在,就是不營業,也不會拒一個好朋友于門外的。我發了一條微信過去,瞬間回復:“歡迎你來。”我當即發了定位給周兵兄。兩杯咖啡,店主為我們叫來兩份外賣簡餐,聊了兩個小時。
周兵兄是上海藝術研究所原所長。他的新著《一瞬間》,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春初版的一本攝影隨感集,裝幀雅致,讀來耐人尋味。
這本《一瞬間》圖文集,讓我想到玩攝影的朱厚澤那本《東張西望》。收羅在內、定格其中的畫面,于人于己,置身于任何時空,一躍入眼簾,它們的濃淡淺深,都會再次鮮活起來,都會讓人讀出各自心底的字里行間。
記錄昨天這“一瞬間”,就像周兵所講的,“時間會留下最真的人”。行走世間,腳步一直很快的人,并不錯過他視野里的僅有。珍惜和在意,不是單純的同義詞,而是任何一個人內心的天然節奏。
我對周兵兄說,想寫一篇讀后心得。這是真心話。他的《一瞬間》,與《嚴獨鶴文集》《唐大郎文集》,我都放在書桌上,隨手就能取過翻閱。而今,每每品讀嚴獨鶴、唐大郎這樣的耆宿當年的專欄隨筆,幾無一文超千字。斗轉星移,見微知著,我并不覺有隔世之感。我經常對身邊的文友說,自己的微信公眾號推文也好,自己平時發表的隨筆或時評也好,篇幅越短越好,一如平常言語,能一句話講清楚的,就不要講三句;一般文章逾千字我幾乎不看。新民晚報的《夜光杯》副刊緣何半個多世紀仍舊香溢誘人,恰恰就是它兩個整版的篇什,極少有冗文。周兵兄收入《一瞬間》的圖文,也有短小精悍之特點。圖出自其目之所及瞬間抓拍,每圖不過幾寸;文乃是其畫外之音發自胸臆,每每也就寥寥數行。亦莊亦諧,質而不俚;視野畢現,意蘊深遠。我無意摘抄書中佳圖佳文,相信讀者諸君定然與我有會于心,尤能與作者共鳴。
當今社會,手機拍照可以體現無數“一瞬間”的藝術、品質乃至思想,這本身就見證了任何一個所謂攝影家的成就,不是因為他手里的機器先進、駕馭的技巧先進,甚或所處的語境是否佳勝,恰恰還是因了一個最簡單也被可能存在的理論、起碼是做人的道理:常使胸中蔚朝氣,須知世上苦人多。從周兵兄的新作中,也能體味到這些滋味。
我曾說過,這個世道不缺作家藝術家,獨缺兀自于晝黑夜白而孜孜以忠實記錄、認真思考的行走者。回眸他們的回眸,前瞻他們的前瞻,你若真正發現他們心中的線條,你若真正走近他們淡入的光影,你似乎懂得了他們的價值之所在,那么,一切距離你所置身于這個當下的歷史包括了你自己的價值之所在,并不很遠。
先說這幾句題外話,是為了鄭重推薦周兵兄的這本新書。我還發現,藝術中國官方門戶網站如今遴選書中佳作并刊發了孫颙的序言。我不認識孫颙本人,但我知道他是個作家。他曾經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做過新聞出版局局長,當過作協黨組書記,有他的序文在前,我的個人理解,這本書的分量或曰要素,仍舊是在藝術、在品質、在思想。
本書主要討論日本學院里的魯迅研究傳統。這個研究傳統,包括認識魯迅的基本立場和思想史語境、主要觀點的確立與闡釋架構的形成及其方法論視角的演變,重點在于梳理學術傳承的內在理路,尤其關注那些構筑起具有其個人特色的“魯迅像”的代表性學者的研究。例如,竹內好那個充滿“贖罪的心情”而執著抵抗的文學者魯迅,丸山升那個片刻不曾離開中國政治過程的革命人魯迅,木山英雄那個穿越對死亡的深度思考而獲得新生的詩人之哲學的思考者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