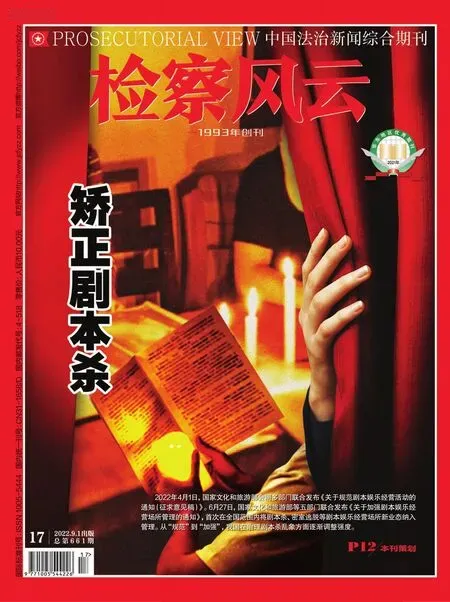“網絡暴力”治理
文/本刊記者 張程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網絡世界成為人們社交生活的重要場景之一,成為中國近10億網民表達觀點的高地。網絡世界的繁榮也帶來了網絡治理的難題。由于網絡世界的虛擬性、匿名性和便利性,使得部分人以為在網絡世界中可以為所欲為,“按鍵傷人”的網絡暴力事件時有發生。
近年來,網絡暴力引發的輿論事件屢屢沖上熱搜,如“女孩訂婚照被造謠成會所技師”“尋親男孩劉某某被網暴后自殺”“成都新冠肺炎確診女孩被網暴”等。如何治理網絡暴力行為,還網絡空間一片安寧,成為重要的社會議題。
“按鍵傷人”事件頻發
網絡暴力是全球性問題。1994年夏天,南非攝影師凱文·卡特把自己關在汽車里,用汽車尾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殺的前一年,他拍攝的作品《饑餓的蘇丹》引起轟動,次年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這張照片畫面中,一名蘇丹女童,即將餓斃跪倒在地,而禿鷹正在女孩后方不遠處,虎視眈眈,等待獵食女孩。作品得獎之后,遭受巨大爭議,引發了輿論風暴,批評的聲音說,他這是站在小女孩尸體上領獎。不堪網絡暴力的凱文·卡特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2019年,22歲的日本職業摔跤手木村花參加一檔電視節目后,在社交媒體上收到大量辱罵信息,持續數月。2020年5月,木村花被發現在家中自殺身亡。木村花在社交平臺留下的遺言是:“每天收到近百條意見,去死、惡心、消失吧,無法否認這對我造成了傷害。”
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網絡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微信、抖音、微博、B站等社交媒體的發展使得人人都能成為新聞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熱點事件或人物“一夜爆紅”“瞬間刷屏”的情況時有發生,在這網絡傳播環境下,網絡暴力事件也時有出現,通常會給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網絡暴力一旦發生,經常是圖文并茂的全方位攻擊,而且各種“咒人死亡”并殃及家人的無底線言論都會出現。
普通人無辜卷入網絡暴力、無力反抗甚至以性命自證的悲劇發生了一次又一次。2018年四川省德陽市一名年輕女醫生安某因在泳池與一名13歲男孩發生身體碰撞,隨后引發激烈沖突。幾天后,男孩的三名家人將安某的個人信息發布到網上,并配注帶有明顯負面貶損、侮辱色彩的標題、帖文和評論,引發廣大網民對其詆毀、謾罵,安某不堪壓力自殺。2022年1月24日在網絡上尋親的被拐男孩劉某某因不堪網絡暴力而自殺。2022年4月上海一女子因請外賣騎手長距離給父親送菜被網暴,后不堪壓力自殺。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開展的“青少年網絡安全研究”調查數據顯示,17.4%的青少年在上網過程中遭受過網絡暴力。

調查數據顯示,17.4%的青少年在上網過程中遭受過網絡暴力
需要提醒的是,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每個網民都應當尊重權利應有的法律界限,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如其言行不當,構成犯罪的,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2016年11月,中國留學生江歌在日本留學期間遭其室友劉某某的前男友陳某某殺害。2017年12月,陳某某被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判處有期徒刑20年。該案在國內網民中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評論。然而受害者卻因為一些網民的誤解變成了被網暴的對象。
自稱誤信網絡傳言的網民譚某某,通過其新浪微博賬號,發布系列與“江歌案”有關的文章及漫畫,侮辱江歌及其母親江某某。譚某某先后發布標題為《江某某自己克死女兒江歌,不能怨任何人》和標題為《江某某七百多天了還不安生,你想念你家鴿子就去買瓶敵敵畏就ok啦》的博文。在該兩篇文章的首部附上江歌遺照,在該遺照上添加的文字中有侮辱性字眼,“活該死你,江某某作惡克死你”等內容,并在文中以“賤婦”“可憐人有可恨處”等語言對江某某進行侮辱、謾罵。針對無端的網絡羞辱和謾罵,江某某以譚某某犯侮辱罪、誹謗罪向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提起自訴。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一審以侮辱罪判處譚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以誹謗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一審宣判后,譚某某不服判決并上訴。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譚某某得知江歌在日本被殺事件后,非但不表示同情,反而從2018年起通過網絡對原本素不相識的江歌及江歌之母江某某進行侮辱、誹謗,公然貶低、損害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侮辱罪、誹謗罪,依法應予數罪并罰。上海二中院裁定駁回譚某某的上訴,維持原判。
網絡暴力治理難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流量經濟”大行其道,一些不法分子,為了蹭熱點獲取流量,無底線無下限,不惜惡意歪曲事實,編造曲折離奇的失實信息誘導用戶關注和轉發,以取得流量最大化的效果。在這個過程很容易造成對當事人的負面影響。
除此之外,在商業領域,針對企業的網絡暴力事件背后總是隱約可見“網絡水軍”的身影。“網絡水軍”利用部分有影響力的網絡“大V”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將粉絲聚集,通過策劃鼓動網民、水軍造勢等方式攪亂輿論場。通過散布企業的不實信息,逼迫利益相關者支付巨額刪帖費用,令一些受害企業頭痛不已。
2021年6月,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作出安排,開展“凈網”集中行動,專項整治網上有害信息和不良內容,著力唱響網絡主旋律、弘揚網絡正能量。公安機關網安部門依托“凈網”系列專項行動,持續對“網絡水軍”相關違法犯罪依法開展偵查打擊。近3年偵辦相關案件600余起,抓獲嫌疑人4000余名,取得了初步成效。
關于網絡暴力犯罪的打擊,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關于辦理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為打擊網絡暴力行為提供了定罪量刑的依據。該司法解釋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46條第1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可構成誹謗罪;如果行為人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實施了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行為,主觀上故意,客觀上造成實際損害,情節惡劣的,以誹謗罪定罪處罰。《刑法》第246條誹謗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虛構的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行為。所謂情節嚴重,主要是指多次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捏造事實造成他人人格、名譽嚴重損害的;捏造事實誹謗他人造成惡劣影響的;誹謗他人致其精神失常或導致被害人自殺的等情況。
民有所呼,法有所應。網絡世界不是法外之地,近年來國家已經出臺了許多治理網絡空間問題的法律法規。2021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了對公民具體的人身權的保護條文。《民法典》總則的第五章第110條規定了自然人享有的生命權、名譽權等一系列權利;《民法典》第四編對人格權的內容做了詳細規定,第995條表明公民的人格權受到不法侵害的,可以要求造成損害的人承擔相應的責任。第四編第1024條規定了民事主體的名譽權受到保護,他人不得侵犯。涉及網絡暴力行為產生的后果,行為人在民法層面應承擔何種責任的問題在《民法典》中也有體現,其中第七編規定了不同種類的侵權責任及責任的承擔方式,主要有停止相關的侵害行為、彌補已造成的損失、向當事人賠禮道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規定,網暴他人有可能構成侮辱、誹謗、尋釁滋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犯罪。
除了國家層面的立法,近年來司法機關也非常重視網絡暴力問題的治理和打擊。2022年5月18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發布《上海市檢察機關關于服務保障本市復工復產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到,依法堅決整治網絡暴力和網絡黑灰色產業鏈,從嚴打擊通過電信網絡實施的詐騙和造謠、傳謠、侮辱、誹謗等犯罪,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凈化網絡空間。
隨著各項法律法規的完善,網絡空間的發展將越來越規范化,網絡暴力事件也有望得到規制,并逐步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