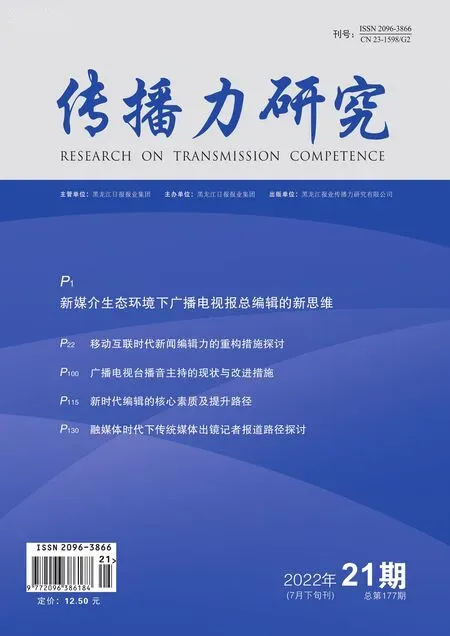傳統民俗媒介化賦能鄉村文化治理路徑研究
——以樂昌花鼓戲為例
◎黃詠楠 邱柔柔 黃瑩瑩 葉叢榕 李昕芮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6)
鄉村治理既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又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治理作為現代化治理的關鍵環節,其核心在“治”,不能停留在“辦”文化、“管”文化、“送”文化的老舊思路上。隨著“自治”在鄉村治理進程中地位逐漸提升,村民的主體性與在場感需要被進一步激發。而扎根于民間、生長于民間的民俗藝術以其在地性、接近性解決了治理主體的缺位,將“送”文化轉化為“種文化”。
本文將通過樂昌花鼓戲傳播案例,從媒介學視角,探討傳統民俗在鄉村文化治理中的作用路徑,并就其現狀提出發展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許多鄉村孕育了本土豐富的民俗文化,作為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的載體,其傳承和傳播至關重要。樂昌花鼓戲作為廣東省級非遺,具有原始生命力和不斷繁衍的文化滲透力。然而,在鄉村城市化發展進程中,花鼓戲的保育工作面臨人才流失、傳承斷層、創新乏力、傳播受阻等諸多困境。
民俗上,鐘敬文先生將其視為一個民族或者國家中的普通民眾所創造、享有并傳承下來的生活文化,國內關于民俗的研究多與此相似,主要聚焦其內涵與功能。李國江認為,民俗文化具有維持鄉村生活秩序的功能。在文化治理上,王志宏認為文化治理是通過文化進行治理以實現文化自身或者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強調文化治理對于經濟政治的作用,而葉鵬飛關注目前治理領域仍存在的問題及新時代鄉村群眾的文化需求問題。學界對鄉村文化治理的研究多傾向于從綜合性角度探討對于社會的影響。國內沙垚(2019)提出了鄉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轉向,指出該“媒介”的前端是文化和價值,后端是實踐和操作,所謂媒介化治理便是將媒介前端的精神落地,成為后端的實踐。
大多數以民俗文化鄉村治理功能為落點的研究,更傾向于民俗意義的歸納闡釋或經典理論的現實應用。本研究重在剖析傳統民俗在鄉村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機制,通過案例聚焦與實踐調查,明晰花鼓戲發揮治理功能的具體路徑,探究其與樂昌本地民風淳樸、文化繁榮、治理效能較高的聯系,并就其未來發展提出建議。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通過實地訪談結合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從原始訪談材料歸納發現,花鼓戲發揮文化治理功能是基于其作為傳統民俗的多方面特征被挖掘和傳播,從而成為一種適地性媒介,發揮其各項特征的具體作用,從而賦能鄉村文化治理。
研究對訪談資料中涉及到花鼓戲自身內容、形式、功能等特征因素進行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性編碼及飽和度檢驗,歸納出花鼓戲是通過發揮其何種方面的特征賦能鄉村治理。
范疇編碼與模型構建:
(一)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
將實地非結構化訪談的35 200字訪談記錄導入Nvivo11.0,基于扎根理論的“本土概念”原則,以開放的心態懸置個人“偏見”,將“關鍵詞”或“話題”創為節點,對文獻內容進行梳理和編碼。通過該階段工作,得到131個初始概念,形成對應的自由節點。對節點進行類屬化,得到31個關鍵性影響因素(如表1所示),這是位于從屬關系最底層的初級類屬,需要加以提煉概括。

表1 花鼓戲特征因素開放式編碼
(二)主軸編碼(Axle Coding)
軸心式編碼又稱為關聯式編碼,該階段主要分析探求上述31個關鍵性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本研究中,通過對開放式編碼中獲取的31個節點進行關聯,歸納提煉出8個二級節點,位于從屬關系的中間層,包括自身價值、內容特征、地域特征、形式特征、政府支持、服務民眾、社會氛圍、社會響應。

表2 花鼓戲特征因素主軸編碼
(三)選擇式編碼(Selective Coding)
選擇式編碼是編碼的最后一個環節,即三級編碼,是對二級編碼的進一步概括。通過深入思考和探究,將主軸編碼中的8個二級節點歸屬為三個主范疇,即“自身因素”、“政府因素”“社會因素”。

表3 花鼓戲媒介化治理因素選擇式編碼
(四)理論飽和度檢驗
基于開放式編碼中預留的初始訪談資料,隨機選取原始訪談資料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數據資料仍能反映花鼓戲特征因素分析框架中的3個主范疇,并且所選取的4條原始訪談資料不再能形成新的概念范疇與典型關系。因此,本次扎根理論編碼結果顯示的概念范疇已達到理論飽和。
三、研究發現
(一)自身因素:內容與形式高度契合鄉村生活實踐
花鼓戲作為鄉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其主體特征極大程度上促進了自身的傳播,因而,發揮規范價值觀念與優化民俗環境的作用,進一步賦能鄉村文化治理。編碼得出花鼓戲自身因素主要由自身價值、內容特征、地域特征、形式特征四個范疇構成。
內在表達上,花鼓戲融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與紅色文化、紅色精神于一體,如以“樂昌好人榜”廖聰濟三代守紅軍墓為題材改編的花鼓戲《守》,其自身價值在于高度吻合社會核心價值觀,起到引領價值導向作用。花鼓戲劇目內容本土化程度高,或作為當地優秀事跡傳播載體,或以生活化的題材和活潑化的講述形式呈現,緊扣民眾喜好和需求,注重情感互動,以受眾“在場”形式實現行為整合。
外在形式上,花鼓戲扎根本土文化實踐,受本土地域環境滋養,在職工文化廣場等開放式的鄉村舞臺、專業舞臺、監獄等地頻繁展演,嵌合本土多類型場域,深化本土認知。此外,花鼓戲從程式化的樣板戲逐漸發展為迎合民眾需求與時代需求的詼諧小戲、精致舞臺劇,迎合觀眾審美變化,多任用本土創作者,易于受眾接納。同時,花鼓戲與婚喪嫁娶等活動緊密結合,扎根本土社會文化實踐。
(二)社會因素:社會氛圍與社會響應的雙重作用
花鼓戲發揮其鄉村媒介化治理的作用,離不開民眾在民俗傳播中的在地性。花鼓戲本土演出內含情感表達與詼諧逗趣,與受眾緊密聯結,具備優化鄉村社會氛圍、激發社會響應的雙重作用。
花鼓戲通過獲得民眾情感認同,強化本土受眾參與。其在展演中表達出來的樸素價值觀與恒久公共價值大部分立足于本土文化環境,因此,更易于激發情感共鳴,縮短受眾的心理距離,從而促進受眾心情愉悅,豐富民眾日常生活。通過民俗表演實現主流價值觀的傳達,進而通過價值觀約束發揮穩定社會的作用。同時民眾也可通過這一媒介向政府反饋,比如,創編一些批評惡性官員的花鼓戲,實現良性的雙向互動,優化社會氛圍。
此外,調查中發現花鼓戲能夠帶來較好的社會響應,激發全民參與。花鼓戲在鄉村各地展演均獲得較好的反響,表明充分吸引受眾,鼓舞受眾充分參與價值反饋和意見表達。因此,在社會氛圍和社會響應的共同作用下,鄉村文化治理的效能不斷提升。
(三)政府因素:為民導向的決策支持
花鼓戲以媒介形態發揮鄉村治理的功能,離不開政府的參與,政府在花鼓戲的發展與傳播中擔任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政府為花鼓戲的傳播提供了資金支持、政策支持,為花鼓戲的發展傳播奠定了物質基礎。從與花鼓戲專家周麗萍的深度訪談中可知,樂昌政府在花鼓戲文藝展演的策劃、宣傳中同樣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政府可謂花鼓戲生存發展的重要支柱。
與此同時,花鼓戲本身的傳播又契合了當下時代的政策導向,它通過戲劇的故事性傳遞政府決策導向,如將部門工作總結公開的重要內容進行合理化展現。花鼓戲與政府存在雙向促進關系,花鼓戲作為政府“聲音”的傳播媒介,觸達鄉村人民,主推政策宣傳、規范民眾行為,而政府為花鼓戲的生存發展提供保障。
政府堅持以服務民眾為最終目標,因此,樂昌花鼓戲具有鮮明時代意義以及與人民主體性性特征。通過頻率高、范圍廣的展演,充分表征當地風土人情和時代發展機遇,營造良好社會氛圍,服務群眾對決策與時代發展的知情、參與等多方面需求,充分關注作為主體的民眾的作用與影響。
四、結語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論,對樂昌文化部部長、宣傳部部長、當地博物館館長、花鼓戲專業演員、花鼓戲業余表演者團隊、花鼓戲研究專家、樂昌民眾、花鼓戲觀眾、花鼓戲創作原型等不同身份的角色進行了專門訪談,最終歸納出花鼓戲作為媒介化治理的載體和中介,主要是借助自身、政府和社會三方面的特征因素促進了本土化傳播、本土化發展,從而在價值引導、民眾聯結、社會參與等多方面發揮作用,進而促進樂昌文化治理效能的提升。
通過傳統民俗媒介化賦能鄉村文化治理已成為文化振興與社會治理新趨向,傳統民俗的保育工作應得到充分重視,其傳承體系的更新、傳承路徑的探索亟待研究與實踐。只有促進其內核表達不斷深化、傳承形式不斷創新,加強與本土人民的聯結,適當融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決策導向,鏟除或轉化其內部的落后文化,才能更好地使其以媒介形態融入鄉村治理體系,發揮在地性、內生性等方面優勢,助力鄉村文化治理體系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