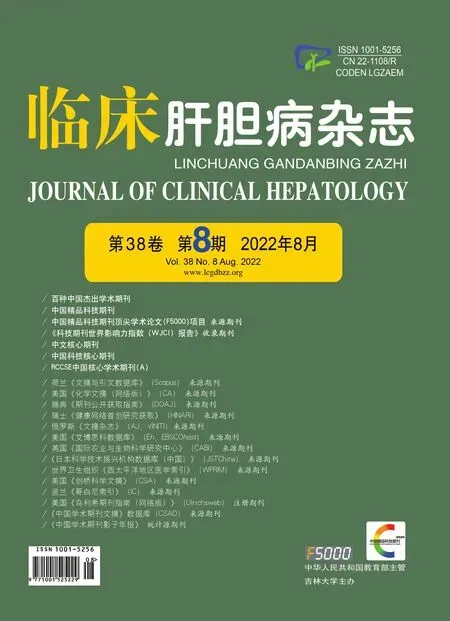衣殼組裝調(diào)節(jié)劑聯(lián)合核苷(酸)類(lèi)似物治療慢性乙型肝炎臨床試驗(yàn)中亟待解決的科學(xué)問(wèn)題
魯鳳民, 黃鴻鑫, 毛天皓, 陳香梅, 莊 輝
1 北京大學(xué)人民醫(yī)院 肝病研究所, 北京 100044;2 北京大學(xué)醫(yī)學(xué)部 基礎(chǔ)醫(yī)學(xué)院 病原生物學(xué)系暨北京大學(xué)感染病研究中心, 北京 100191
HBV感染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和原發(fā)性肝癌的主要病因。2021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1]顯示,全球慢性HBV感染者約2.96億人。我國(guó)自1992年開(kāi)始實(shí)施新生兒乙型肝炎疫苗免疫規(guī)劃管理,2002年實(shí)行乙型肝炎疫苗免費(fèi),2005年正式實(shí)施乙型肝炎疫苗免疫規(guī)劃,HBV新發(fā)感染大幅減少,其中5歲以下兒童HBV感染率已降至0.2%,全人群的慢性HBV感染率也下降至6.1%[2]。但我國(guó)既往慢性HBV感染者眾多,現(xiàn)仍有7000萬(wàn)例,其中亟需治療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2000~3000萬(wàn)例[3]。2016年5月,世界衛(wèi)生大會(huì)通過(guò)了“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衛(wèi)生危害”的全球戰(zhàn)略,要求將新發(fā)感染減少90%、死亡減少65%[4]。當(dāng)下我國(guó)每年HBV相關(guān)死亡約40萬(wàn)例,但CHB診斷率僅為22%,治療率為17%[5],距離世界衛(wèi)生組織提出的診斷率90%、治療率80%尚有很大距離。
現(xiàn)有的兩類(lèi)一線(xiàn)抗HBV藥物包括核苷(酸)類(lèi)似物(NUC)和聚乙二醇干擾素α(PEG-IFNα),均可有效抑制病毒復(fù)制,減緩疾病進(jìn)展和減少終末期肝病的發(fā)生。其中,PEG-IFNα主要通過(guò)免疫調(diào)節(jié)發(fā)揮抗病毒作用,經(jīng)過(guò)有限療程后,其HBsAg清除率約為10%,在優(yōu)勢(shì)人群中可有更高的臨床治愈率[6-8],但由于存在一定的副作用,限制了其廣泛的臨床應(yīng)用。NUC主要通過(guò)不可逆地阻斷HBV聚合酶(polymerase,P)介導(dǎo)的病毒RNA逆轉(zhuǎn)錄過(guò)程,顯著抑制HBV DNA復(fù)制以發(fā)揮抗病毒作用[9],加之口服方便、副作用較少,NUC在臨床上得到廣泛應(yīng)用。然而,停藥后反彈是NUC最大缺點(diǎn)[10],患者一旦開(kāi)始NUC治療,往往需要長(zhǎng)期甚至終生服藥,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患者的治療意愿。因此,目前亟需研發(fā)抗HBV新藥,以顯著提高CHB的治愈率。
近年來(lái),靶向HBV生命周期不同層面的直接抗病毒藥物(DAA)如進(jìn)入抑制劑、衣殼組裝調(diào)節(jié)劑(capsid assembly modulators,CpAM)、HBsAg釋放抑制劑、干擾共價(jià)閉合環(huán)狀DNA(cccDNA)轉(zhuǎn)錄及表達(dá)過(guò)程的RNA干擾,包括小干擾RNA和反義寡核苷酸等均已進(jìn)入不同臨床試驗(yàn)階段。其中,CpAM是截至目前進(jìn)入臨床試驗(yàn)階段較多的一類(lèi)在研藥物,但在以“安全停藥”為主要治療觀察終點(diǎn)的CpAM聯(lián)合NUC臨床試驗(yàn)中,幾乎所患者停藥后均發(fā)生反彈[11],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CpAM聯(lián)合NUC的用藥策略,以選擇適宜的臨床試驗(yàn)終點(diǎn)。
1 cccDNA與CHB的臨床治愈
近年來(lái),靶向HCV復(fù)制的DAA藥物成功治愈丙型肝炎,再次將“CHB治愈”推到聚光燈下。但與HCV基因組RNA在肝細(xì)胞質(zhì)內(nèi)通過(guò)快速自我復(fù)制維持慢性感染不同,以穩(wěn)定的微小染色體形式存在于感染肝細(xì)胞內(nèi)且有轉(zhuǎn)錄活性的cccDNA是HBV復(fù)制的源頭,也是維持HBV感染的關(guān)鍵。加之慢性HBV感染過(guò)程中普遍發(fā)生的HBV DNA整合[12],以及HBV的免疫逃逸[13],CHB的臨床治愈面臨著更大的挑戰(zhàn)。
盡管HBV基因組僅有3.2 kb長(zhǎng),但卻有2種病毒基因組形式:即松弛環(huán)狀DNA(relaxed circular DNA,rcDNA)和cccDNA。HBV進(jìn)入肝細(xì)胞后,rcDNA進(jìn)入細(xì)胞核并被修復(fù)形成cccDNA[14-17]。cccDNA在細(xì)胞核內(nèi)以微小染色體形式存在,可轉(zhuǎn)錄出病毒的全部mRNA,故有轉(zhuǎn)錄活性的cccDNA的持續(xù)存在,被認(rèn)為是HBV慢性感染得以維持和患者難以治愈的最主要因素[18]。除此之外,HBV DNA的復(fù)制有其獨(dú)特的逆轉(zhuǎn)錄過(guò)程,在細(xì)胞質(zhì)內(nèi)新合成的核心蛋白將前基因組RNA(pregenomic RNA,pgRNA)/P蛋白復(fù)合物包裹形成核衣殼,隨后P蛋白以pgRNA為模板逆轉(zhuǎn)錄合成負(fù)鏈DNA,再以pgRNA的5′端殘余為引物合成出長(zhǎng)度不一的互補(bǔ)正鏈,形成子代病毒rcDNA。期間,P蛋白要確保有3次正確的跳轉(zhuǎn)才能完成上述復(fù)雜過(guò)程[19]。肝細(xì)胞核內(nèi)的cccDNA池除了來(lái)源于新感染過(guò)程中進(jìn)入肝細(xì)胞內(nèi)的rcDNA,還可由感染肝細(xì)胞胞質(zhì)內(nèi)新形成的、帶有rcDNA的核衣殼直接入核并釋放rcDNA形成[14,20]。而病毒蛋白HBx對(duì)于形成有轉(zhuǎn)錄活性的cccDNA至關(guān)重要[21-22]。
我國(guó)學(xué)者[23]曾通過(guò)對(duì)CHB患者HBV耐藥病毒株動(dòng)態(tài)變化的分析,推測(cè)患者肝組織內(nèi)cccDNA的半衰期可能只有數(shù)月。cccDNA的較短半衰期帶來(lái)了通過(guò)NUC抑制HBV DNA復(fù)制阻止新病毒的產(chǎn)生,從而耗竭cccDNA實(shí)現(xiàn)乙型肝炎治愈的希望[24]。然而,在臨床實(shí)踐中,即使接受長(zhǎng)時(shí)間NUC治療,也僅有極少數(shù)患者血清HBsAg消失(伴有或不伴有抗-HBs陽(yáng)轉(zhuǎn)),實(shí)現(xiàn)臨床治愈(功能性治愈)。與之一致,2020年美國(guó)肝病學(xué)會(huì)年會(huì)報(bào)道一項(xiàng)來(lái)自10個(gè)國(guó)家(地區(qū))、25家醫(yī)院的國(guó)際多中心真實(shí)世界隊(duì)列研究[25],共納入初治CHB患者7697例,其中,5430例接受恩替卡韋(ETV),2267例接受替諾福韋酯(TDF)治療,結(jié)果顯示,ETV和TDF隊(duì)列的8年累積血清HBsAg清除率分別為1.69%和1.34%。此外,由于NUC的作用機(jī)制是競(jìng)爭(zhēng)性抑制P蛋白的逆轉(zhuǎn)錄活性,其往往難以完全阻斷cccDNA池的內(nèi)補(bǔ)充[26],導(dǎo)致停藥后病毒學(xué)復(fù)發(fā)和疾病反彈發(fā)生率較高,患者不得不長(zhǎng)期甚至終生服藥,給患者和社會(huì)帶來(lái)健康和經(jīng)濟(jì)雙重負(fù)擔(dān)。因此,對(duì)于長(zhǎng)期接受NUC治療的患者,安全停藥是一項(xiàng)無(wú)法回避的需求。
2 CpAM聯(lián)合NUC治療CHB臨床試驗(yàn)中需考慮的科學(xué)問(wèn)題
在研的CpAM類(lèi)藥物可分為2種作用類(lèi)別:Ⅰ型CpAM干擾病毒核衣殼的正常組裝,使之形成多種形態(tài)的非衣殼結(jié)構(gòu)[27];Ⅱ型CpAM則促進(jìn)結(jié)構(gòu)“正常”但無(wú)pgRNA/P蛋白復(fù)合物的空衣殼形成[28]。CpAM的上述作用均可抑制pgRNA的包裝[29-30]。此外,CpAM還有增強(qiáng)成熟核衣殼的非正常解聚和干擾rcDNA正確釋放入核以回補(bǔ)cccDNA的作用[31-33]。并且,由于HBV抗CpAM的潛在耐藥位點(diǎn)與NUC耐藥突變不重疊,預(yù)計(jì)對(duì)NUC耐藥變異株也有作用[34]。因此,已有的CpAM的臨床試驗(yàn)設(shè)計(jì)多與NUC聯(lián)合。有研究[35]顯示,相較于ETV單藥治療,CpAM與ETV聯(lián)合治療患者的HBV DNA和HBV RNA往往有更大幅度的下降。
目前,對(duì)于是從病毒學(xué)還是從臨床角度去定義“CHB治愈”尚缺乏一致意見(jiàn),并可能對(duì)新藥的臨床評(píng)價(jià)帶來(lái)一定的困擾。總的來(lái)說(shuō),僅僅是病毒學(xué)意義上的HBV cccDNA持久沉默或清除的CHB患者仍有較高的原發(fā)性肝癌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而以血清HBsAg陰轉(zhuǎn)(伴或不伴抗-HBs陽(yáng)轉(zhuǎn))為標(biāo)志的臨床治愈[36],則不僅是所有病毒學(xué)標(biāo)志物的完全陰轉(zhuǎn),包括肝癌在內(nèi)的相關(guān)肝病死亡風(fēng)險(xiǎn)也大為下降[37]。血清中HBV RNA病毒樣顆粒的發(fā)現(xiàn)為指導(dǎo)NUC治療的安全停藥提供了一定幫助,原因在于血清中的HBV RNA多為未完成逆轉(zhuǎn)錄的核衣殼內(nèi)包裹的pgRNA[38],NUC治療阻斷了逆轉(zhuǎn)錄過(guò)程,使核衣殼內(nèi)的pgRNA不再為P蛋白的RNase H活性所降解,并以HBV RNA病毒樣顆粒形式釋放至血循環(huán)[38]。因此,血清中HBV RNA檢測(cè)陽(yáng)性往往反映了患者肝組織中cccDNA仍在活躍轉(zhuǎn)錄,故血清中HBV RNA陽(yáng)性時(shí)的停藥往往提示更大的反彈甚至疾病復(fù)發(fā)風(fēng)險(xiǎn)[38-39]。但在CpAM治療時(shí),HBV RNA減少僅僅是藥物作用于靶點(diǎn)的重要證據(jù),并非代表cccDNA被清除或被靜默[11]。在HBsAg或乙型肝炎核心相關(guān)抗原(hepatitis B core-related antigen,HBcrAg)無(wú)明顯下降的情況下,以“安全停藥”為重要觀察終點(diǎn)的兩項(xiàng)CpAM臨床試驗(yàn)[40-41]中,幾乎所有患者均在停藥后發(fā)生了反彈,未能觀察到持續(xù)的治療效果,由于治療過(guò)程中出現(xiàn)ALT水平升高,研究暫停。
CpAM的藥理作用主要是干擾核心蛋白的正確組裝,使pgRNA/P蛋白復(fù)合物無(wú)法被有效包裹,從而使逆轉(zhuǎn)錄過(guò)程受阻;或引發(fā)已經(jīng)形成的成熟核衣殼易被拆解而穩(wěn)定性下降。而NUC則是在核衣殼內(nèi)競(jìng)爭(zhēng)抑制P蛋白以pgRNA為模板逆轉(zhuǎn)錄合成子代病毒負(fù)鏈DNA的過(guò)程。臨床上,二者聯(lián)用具有良好的協(xié)同作用,對(duì)rcDNA合成過(guò)程的抑制作用更加徹底;但由于二者均為通過(guò)干擾抑制子代病毒rcDNA的形成過(guò)程發(fā)揮抗病毒作用,當(dāng)與作用力超強(qiáng)的CpAM聯(lián)用時(shí),NUC可能將主要作用于逃逸了CpAM干擾作用的核衣殼內(nèi)的逆轉(zhuǎn)錄過(guò)程,僅僅發(fā)揮“堵漏”作用。或許不能期待在臨床試驗(yàn)的短療程條件下,CpAM+NUC兩強(qiáng)聯(lián)合實(shí)現(xiàn)“1+1≥2”的疊加效能。
此外,可以預(yù)見(jiàn)的是,核衣殼內(nèi)的pgRNA并非以無(wú)序狀態(tài)自由懸浮其中,更可能是以適當(dāng)?shù)姆绞健皯覓臁痹谔畛渲鴇NTP和一些未知宿主蛋白的衣殼腔內(nèi)。生物信息學(xué)分析[42]提示,在pgRNA上或許存在與構(gòu)成衣殼的核心蛋白結(jié)合的基序。也有研究[43]證實(shí),pgRNA的5′ε莖環(huán)結(jié)構(gòu)與核心蛋白相互作用,促進(jìn)衣殼的組裝。在CpAM作用下失去了正常結(jié)構(gòu)和殼內(nèi)空間的核衣殼內(nèi),pgRNA/P蛋白復(fù)合物是否能夠有效啟動(dòng)由P蛋白第63位酪氨酸引發(fā)的逆轉(zhuǎn)錄起始引物前3個(gè)脫氧核糖核酸的合成?隨后是否可以正常進(jìn)行首次跳轉(zhuǎn)以確保逆轉(zhuǎn)錄的精準(zhǔn)啟動(dòng)?如此多的不確定性提醒有必要探究聯(lián)合用藥下,NUC是否還能夠發(fā)揮對(duì)逆轉(zhuǎn)錄過(guò)程的有效競(jìng)爭(zhēng)抑制作用。若果真如此,兩者聯(lián)合的疊加抗病毒作用是否更容易碰到藥物效應(yīng)的天花板?期許兩強(qiáng)聯(lián)合加速cccDNA池耗竭的作用會(huì)不會(huì)難以成真?事實(shí)上,從既往報(bào)道的CpAM聯(lián)合NUC臨床試驗(yàn)研究結(jié)果來(lái)看,患者血清HBsAg或HBcrAg在短期治療后的確無(wú)明顯下降,也許提示聯(lián)合CpAM并未顯著加速NUC治療下的cccDNA耗竭或靜默,以至于幾乎所有患者在有限療程的聯(lián)合治療后均發(fā)生了停藥后的病毒學(xué)反彈[44]。目前比較確認(rèn)的是,在未來(lái)以安全停藥為觀察終點(diǎn)的臨床試驗(yàn)中,可能需要更長(zhǎng)時(shí)間的CpAM和NUC聯(lián)合治療以耗竭或靜默cccDNA池,提高安全停藥的可能性。此外,基于人肝嵌合鼠的動(dòng)物實(shí)驗(yàn)[45]發(fā)現(xiàn),CpAM與PEG-IFNα聯(lián)用能夠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PEG-IFNα誘導(dǎo)的肝內(nèi)干擾素刺激基因表達(dá),提示在未來(lái)對(duì)特定人群以臨床治愈為目的的臨床試驗(yàn)中,有必要考慮CpAM在與一線(xiàn)NUC聯(lián)用的基礎(chǔ)上,加用長(zhǎng)效干擾素,或與在研的免疫調(diào)節(jié)劑聯(lián)用,以提高臨床治愈率,減少肝細(xì)胞癌的發(fā)生(圖1)。

圖1 影響CpAM聯(lián)合NUC對(duì)抑制HBV DNA復(fù)制發(fā)揮疊加作用的可能機(jī)制及啟示
3 小結(jié)與展望
在本期發(fā)表的文章中,陳娟、黃愛(ài)龍從HBV cccDNA 的角度討論了慢性乙型肝炎的治愈問(wèn)題。除此之外,整合來(lái)源的HBsAg持續(xù)表達(dá)也是影響慢性乙型肝炎臨床治愈的主要因素。由于缺乏直接靶向cccDNA的抗病毒藥物,且整合的HBV DNA可持續(xù)表達(dá)HBsAg,通過(guò)調(diào)節(jié)宿主免疫清除感染及攜帶整合HBV DNA片段的肝細(xì)胞、或使之轉(zhuǎn)錄沉默,對(duì)于慢性乙型肝炎的臨床治愈尤為重要。這方面,高子翔等就一些關(guān)鍵細(xì)胞因子在CHB感染及治療中的研究進(jìn)展進(jìn)行了總結(jié)與討論;郭藝飛、張繼明對(duì)影響慢性乙型肝炎功能性治愈的因素特別是宿主免疫因素及其機(jī)制進(jìn)行了討論。在抗HBV新藥研發(fā)上,CpAM無(wú)疑是最受關(guān)注的一類(lèi),劉慧等系統(tǒng)闡述了CpAM 靶蛋白-核心蛋白的功能、CpAM 分類(lèi)、作用靶點(diǎn)及抗HBV機(jī)理及CpAM 臨床試驗(yàn)現(xiàn)狀等,并預(yù)期聯(lián)合治療可能是CpAM未來(lái)臨床應(yīng)用的最佳選擇。筆者團(tuán)隊(duì)認(rèn)為,現(xiàn)階段CpAM的聯(lián)合治療之路布滿(mǎn)荊棘,可能需要放緩步伐,優(yōu)先著手解決一些影響CpAM聯(lián)合NUC治療效果的相關(guān)問(wèn)題。這或?qū)?duì)CpAM的臨床應(yīng)用有更切實(shí)的預(yù)期與定位,使未來(lái)的臨床試驗(yàn)設(shè)計(jì)更為合理,并最終使CpAM類(lèi)藥物及早進(jìn)入臨床,使患者獲益。
近年來(lái),包括固有免疫調(diào)節(jié)劑、治療性疫苗、免疫檢查點(diǎn)抑制劑,以及單克隆抗體在內(nèi)的免疫調(diào)節(jié)劑均有長(zhǎng)足發(fā)展[46-49]。考慮到激活體內(nèi)特異性抗HBV免疫反應(yīng)在清除感染肝細(xì)胞及其cccDNA池、清除有轉(zhuǎn)錄活性整合HBV DNA肝細(xì)胞中的重要作用,未來(lái)的聯(lián)合治療或許是在更強(qiáng)的抗HBV DAA抑制病毒復(fù)制、靜默及清除cccDNA池和減少免疫抑制性的HBsAg水平的基礎(chǔ)上,再聯(lián)合免疫調(diào)節(jié)藥物,以誘導(dǎo)抗HBV特異性后天免疫,為CHB臨床治愈帶來(lái)更大希望。
關(guān)于多靶點(diǎn)聯(lián)合治療,目前看來(lái)似應(yīng)綜合考慮如下幾點(diǎn):(1)安全性;(2)療效;(3)多靶點(diǎn)藥物的相互作用及其與患者因其他疾病而用藥物的相互作用;(4)成本效益比;(5)患者的經(jīng)濟(jì)承受能力,即可及性等。我國(guó)CHB臨床治愈(珠峰)工程項(xiàng)目最新研究[50]結(jié)果顯示,對(duì)于NUC治療下達(dá)到HBV DNA檢測(cè)不到、HBsAg≤100 IU/mL的患者,聯(lián)合PEG-IFNα治療后,臨床治愈率可高達(dá)55.3%。因此,未來(lái)如出現(xiàn)比現(xiàn)行NUC(ETV、TDF和TAF)更強(qiáng)效、低耐藥的DAA藥物,再聯(lián)合一種比PEG-IFNα更強(qiáng)效的免疫調(diào)節(jié)藥物,也許能夠獲得更高的臨床治愈率。總之,多種潛在的聯(lián)合治療策略仍有待深入研究。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xiàn)聲明:魯鳳民、莊輝擬定寫(xiě)作思路并最終定稿;陳香梅指導(dǎo)文章撰寫(xiě)并修改文章關(guān)鍵內(nèi)容;黃鴻鑫和毛天皓負(fù)責(zé)文獻(xiàn)檢索并參與起草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