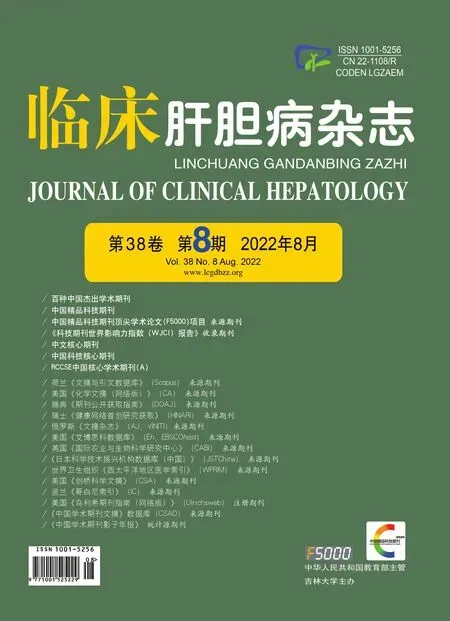肝細胞癌微波消融術后遲發性膈疝1例報告
王曉棟, 張玉蓉, 朱曉寧, 鄭 丁, 汪 靜
西南醫科大學附屬中醫醫院 肝膽病科, 四川 瀘州 646000
微波消融(MWA)已成為目前早期或不適合手術切除的肝癌患者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膈疝是其較為罕見的并發癥。現將1例高齡肝細胞癌(HCC)患者經MWA術后并發遲發性膈疝,腹腔鏡下行右側膈疝回納及膈肌修補術治療后恢復良好的病例報道如下。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性,70歲,2018年5月14日因“發現乙型肝炎肝硬化4年余,肝區占位3個月”入本院,3個月前門診MRI檢查發現肝右后葉S5與S8交界處占位(圖1a),診斷為HCC。入院后完善術前檢查,AFP 163.1 ng/mL,PLT 59×109/L;肝功能:ALT 91 U/L、AST 53 U/L、GGT 102 U/L;心電圖:竇性心動過緩、心前區R波增高、提示V4~V6導聯早期復極;胸部CT示:雙肺多發結節及纖維灶;雙肺多發肺大皰;縱隔淋巴結少許腫大,主動脈弓少許鈣化,左心室增大;胸椎退變、側彎。掃描層面示:肝硬化,脾大。考慮患者年齡大,肝硬化失代償,血小板水平低,病灶較小,且患者不愿行手術切除,故在局麻下經超聲引導行肝腫瘤MWA術(圖2)。在超聲引導下,先行確定病灶位置及進針路線,進針時先經正常肝組織部分后再進入腫瘤病灶,進針深度7 cm(肝內4 cm),超聲確認針尖到達對側病灶后,開始消融,功率為50 w,時間6 min。手術順利,未發現相關并發癥及其他不適。術后1、3、6個月行常規影像學隨訪均未發現腫瘤復發。2019年1月隨訪MRI發現肝S7段小結節影(圖1b),考慮系腫瘤復發,故再次在CT引導下行肝腫瘤MWA術,功率為40 w,時間12 min,手術順利,2個月后影像學隨訪未見異常(圖3)。

注:a,2018年5月門診,S5與S8交界處占位(白色箭頭);b,2019年 1月隨訪,S7占位(白色箭頭)。圖1 MRI檢查結果Figure 1 MRI images


注:a,術前; b,術中; c,術后。圖2 超聲檢查結果Figure 2 Ultrasonic images


注:未見膈疝影像學表現。圖3 2019年3月隨訪CT檢查結果Figure 3 CT images in March 2019
2019年4月14日,患者因“突發右上腹部劇烈疼痛”再次入本院,疼痛呈脹痛樣,進食后加重,無惡心、嘔吐、心慌、胸悶,無畏寒、發熱、肛門停止排氣、排便等不適,腹部CT(圖4)示:右側膈肌欠連續,結腸肝曲突入右側胸腔內,考慮膈疝可能性大;右肺炎癥,右側胸腔少量積液;心包少量積液。排除相關手術禁忌后,行腹腔鏡探查術發現右側膈肌有一直徑約4 cm缺損,橫結腸肝曲及部分大網膜疝入,疝入的橫結腸水腫明顯(圖5),未見壞死,立即行腹腔鏡探查+右側膈疝回納+膈肌修補+小切口輔助橫結腸修補+右側胸腔閉式引流術,將疝入胸腔的網膜及結腸回納入腹腔。術后患者恢復良好出院,2019年11月、2020年5月及2021年8月影像學隨訪均未見明顯異常(圖6)。


注:a,疝入胸腔的橫結腸(白色箭頭);b,疝入的橫結腸組織經過腹腔并壓迫肝臟(白色箭頭);c,橫結腸疝入右側胸腔(白色箭頭)。

注:橫結腸經膈疝直接侵入右胸腔(白色圓圈)。圖5 腹腔鏡術中所見Figure 5 Laparoscopic surgery image


注:a,2019年11月復查CT;b,2020年5月復查MRI; c,2021年8月復查MRI。
2 討論
肝癌是一種臨床常見的惡性腫瘤,其中80%以上為HCC,是世界諸多地區癌癥相關死亡的主要原因[1]。目前治療方案主要以外科治療為主,結合局部消融、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放射治療及全身治療等多種手段綜合治療[2-3]。近年來,以射頻消融(RFA)、MWA為代表的局部消融方案在肝癌治療中得到廣泛應用,被認為是小肝癌、不適合手術切除或化療失敗患者的替代療法[4]。
MWA是一種通過微波對生物組織的加熱效應引起腫瘤組織發生變形和凝固性壞死的技術,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與RFA相比無顯著差異[5],且相對于RFA具有速度更快、消融范圍更廣、同時消融多個病灶以及術中患者痛感更輕等優勢[6]。目前報道的MWA主要并發癥包括出血、氣胸、腸穿孔和膽道損傷等[4],MWA術后膈疝是較為罕見的并發癥,其發病率為0~0.31%[7],目前僅見英國1例報道[8]。
HCC患者MWA術后膈疝的發生機理目前尚不清楚。既往文獻[9-11]報道的RFA術后膈疝病例的病變大多位于肝右葉第7、8或5段,本病患者病灶位置位于S5與S8交界處,臨近膈肌,提示病灶臨近膈肌是HCC患者MWA術后膈疝發生的重要條件。筆者團隊前期研究[12]發現,消融術后膈肌穿孔可能與消融治療期間間接熱損傷、晚期肝硬化等因素有關。分析本例患者MWA術后膈疝的發生原因:(1)由于反復行消融治療,局部熱損傷易引起膈肌炎癥反應并逐漸發展為纖維化,最終削弱膈肌纖維,導致膈肌遲發性穿孔[10]。本例患者前后行2次MWA治療,不排除術中由于間接熱損傷造成膈肌損傷的可能。(2)肝硬化晚期,肝臟進行性縮小,膈肌和肝臟之間的空間相對增大,膈肌穿孔的概率亦升高。本例患者處于肝硬化失代償期,肝體積未見明顯縮小,追溯病史,該患者在發現膈疝之前有腎結石病史,伴下腹部劇烈疼痛,不排除橫結腸疝入胸腔和劇烈腹痛時腹內壓增高有關,從而誘發膈疝的產生。
膈肌損傷或膈肌穿孔無臟器疝入時缺乏特異性臨床表現和影像學特征,初期通常難以發現,故其延誤診斷率較高。當發展為膈疝時,可表現為腹痛、胸悶氣促、呼吸困難、惡心嘔吐等,同時影像學檢查提示一側膈肌抬高,膈面模糊,膈肌欠連續,胸內有大小不等的圓形透光區或液平,胸腔內可見胃泡或腸襻影,患側膈面上方出現氣泡或致密影,心臟和縱膈向健側移位等[13]。總結既往報道[12]可見,肝癌消融術后并發膈疝多為遲發型,時間間隔跨度大,更增加預測和診斷術后膈疝發生的難度。本例患者發現膈疝時分別與其2次MWA手術間隔11個月和3個月,但考慮膈肌穿孔的部位,筆者認為與第1次手術相關性更大。患者CT檢查表現為右側膈肌欠連續,結腸肝曲突入右側胸腔內,與既往報道[12]膈疝的影像學表現一致,故認為其為MWA術后遲發性膈疝。
對于消融治療后繼發膈疝患者的治療,由于其多伴有不同程度腸梗阻、腸壞死或嚴重呼吸困難,常因呼吸困難、急性上腹痛等癥狀于急診求醫,起病急,病情重,嚴重者可危及生命,建議能夠耐受手術者均應及時行外科修復手術治療,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均得到證實,且對提高患者生存率至關重要[14]。對于無癥狀者,可長期臨床隨訪觀察,一旦出現癥狀,盡快手術干預。本例患者癥狀明顯,診斷明確,及時進行腹腔鏡下手術治療,術后恢復良好。
綜上所述,HCC患者MWA術后繼發膈疝是一種罕見并發癥。隨著消融技術在臨床不斷開展,膈疝的發生率可能將越來越高,但由于其缺乏特異性臨床表現,如果臨床醫師對此認識、警惕不足,極易導致失治誤治。因此,在對鄰近膈肌的肝腫瘤行消融治療時,應注意避免損傷穿刺路徑局部膈肌導致膈肌穿孔。同時,應設計出避免膈肌熱損傷的方法,例如控制消融范圍、采用人工腹水或經腹腔鏡消融等方式[15]。術后隨訪監測應關注患者有無腹痛、呼吸困難、腸梗阻、胸痛和胸腔積液等癥狀,同時注意觀察膈肌的完整性,以早期識別、及時干預,減少死亡風險。
倫理學聲明:本例報告已獲得患者知情同意。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王曉棟、張玉蓉負責課題設計,資料分析,撰寫論文;朱曉寧、鄭丁參與收集數據,修改論文;汪靜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