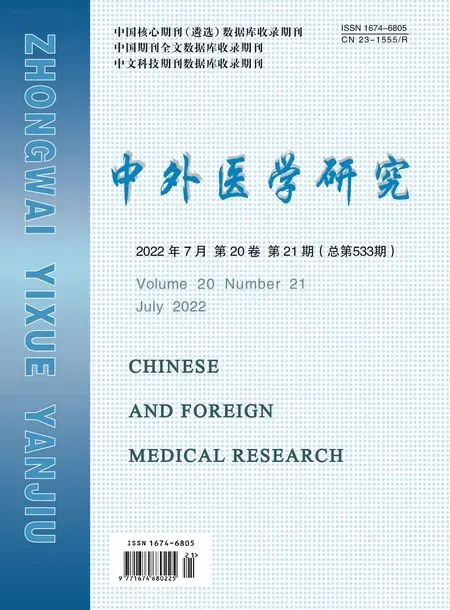早期機械通氣在高血壓腦出血術后并發癥防治中的作用
王恒福 萬鵬飛 魯健 王洪艷
高血壓腦出血(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HICH)在我國屬于高發病率、高致殘率和高死亡率的典型三高疾病。導致高死亡率和高致殘率的原因除了腦出血本身對腦組織造成的原發性和繼發性損傷外,并發癥也是改變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如血壓劇烈波動引起的再出血、肺部感染、低氧血癥、消化道出血等[1-3]。特別是高血壓腦出血術后72 h內的圍手術期,在麻醉復蘇、神經功能恢復過程中和應急狀態下,患者更容易出現劇烈的血壓波動、呼吸功能紊亂、低氧血癥及誤吸等并發癥,誘發患者病情惡化,甚至危及生命,影響手術效果及患者預后。在臨床工作中發現這些并發癥的中心環節或多或少均與呼吸、循環功能穩定與否相關。查閱文獻發現,目前國內一些學者已經對早期機械通氣在高血壓腦出血患者治療中的應用進行了研究[4-5],但大多都在患者出現明顯機械通氣適應證后,作為搶救措施應用,很少作為預防治療措施應用。修文縣人民醫院采用術后麻醉復蘇前即行機械通氣結合鎮靜、鎮痛以穩定呼吸功能和暢通呼吸道為中心環節的預防性治療方案,明顯降低了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改善了患者的預后。現將2020年1-12月采用該方案治療的45例患者資料與2018年1月-2019年12月采用傳統常規方案治療的72例患者資料進行對比分析,得出了積極的結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8年1月-2020年12月修文縣人民醫院手術治療的,符合納入標準的高血壓腦出血患者117例,
男68例,女49例;年齡43~77歲,平均(63.5±5.4)歲,有效回訪6個月。納入標準:(1)入院時CT檢查提示基底節或腦葉腦出血,出血量≥30 ml,高血壓腦出血分級為Ⅱ~Ⅳ級;(2)既往有高血壓病史;(3)順利實施手術及相應治療,病歷資料完整;(4)年齡18~80歲。排除標準:(1)合并嚴重其他系統或器官疾病,影響預后評估;(2)確診為動脈瘤、動靜脈畸形、“煙霧病”、海綿狀血管瘤等腦血管疾病及瘤卒中;(3)GCS評分3~5分;(4)因家屬自請出院等原因中斷治療。其中2020年1-12月采取術后延遲麻醉復蘇、早期機械通氣結合鎮靜鎮痛治療的45例患者為觀察組;按相同標準收集的2018年1月-2019年12月采用術后常規麻醉復蘇及治療的72例患者為對照組。觀察組,年齡43~75歲。對照組,年齡46~77歲。兩組年齡、性別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術前臨床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本研究經修文縣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所有患者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兩組術前臨床資料比較
1.2 治療方法
1.2.1 手術方法 兩組均在氣管插管全麻下,根據頭顱CT提示定位血腫位置,避開重要功能區,于顳部或額顳部以血腫為中心,取顳部“馬蹄形”或額顳部“弧形切口”開顱,顯微鏡下經顳中回、顳上回或外側裂入路清除血腫,人工硬腦膜減張縫合修復硬腦膜,常規放置引流管,根據術中腦組織塌陷情況,決定是否去骨瓣減壓。對血腫破入側腦室有急性腦積水或中腦導水管及第四腦室有積血梗阻者,行側腦室置管外引流術。
1.2.2 術后處理 對照組術后常規麻醉復蘇,按中華醫學會編著《臨床診療指南-重癥醫學分冊》有創機械通氣適應證:(1)經無創氧療患者病情無改善或繼續惡化;(2)意識障礙,氣道保護能力差,存在窒息風險;(3)存在多臟器功能不全(上消化道大出血、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等);(4)呼吸功能嚴重異常,呼吸頻率>35~40次/min或呼吸頻率<6~8次/min;(5)嚴重的低氧血癥或呼吸性酸中毒:持續 2 h 平均 PaO2<50 mm Hg充分氧療后仍無改善,PaCO2進行性升高,pH值動態下降[6]。行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后應用機械通氣治療。觀察組:術后不立即進行麻醉復蘇,麻醉狀態下帶氣管插管,利用移動呼吸機維持呼吸功能,送入神經外科重癥監護室,立即行預防性行機械通氣穩定呼吸功能。兩組均根據呼吸功能具體情況采用合適的通氣模式,如患者出現躁動或血壓控制困難時靜脈泵入鹽酸右美托咪定0.2~0.3 μg/(kg·h)鎮靜,必要時加用芬太尼0.7~1.5 μg/kg或持續靜脈泵注丙泊酚0.3~0.4 mg/(kg·h),使患者維持在淺鎮靜狀態(刺激有反應,不刺激無活動)。兩組術后均送NICU病房監護及治療,常規予控制血壓、營養神經、脫水降顱內壓、抗癲癇、維持水、電解質平衡、改善微循環等治療,必要時抗感染治療,控制PaO2≥80 mmHg,防止腦組織缺氧性損害;兩組患者術后均按常規嚴格控制血壓。術前收縮壓為150~220 mmHg(1 mmHg=0.133 kPa) 患 者, 術 后 降 壓 目 標 為130~140 mmHg;術前收縮壓 >220 mmHg 患者,術后降壓目標為150~160 mmHg;常規監測動脈血氣分析、血常規、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電解質等實驗室指標;術后6、24、72 h均常規復查頭顱CT,之后根據患者病情變化情況決定是否復查頭顱CT。對再出血且有手術指征者,行二次開顱再次清除血腫并去骨瓣減壓術。術后24 h開始口服(胃管注入)降壓藥物,以口服降壓藥控制血壓為主,必要時靜脈用藥輔助,同時行胃腸營養支持,必要時腸外營養支持。
1.3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1.3.1 并發癥情況 (1)再出血:術后兩次CT所示血腫體積(CT軟件測算血腫量),分別與基線CT比較,血腫體積超過1/3,視為再出血。(2)肺部感染:體溫≥37.3 ℃、咳嗽或痰多;血常規白細胞、中性粒細胞升高,降鈣素原和C反應蛋白升高;胸部CT提示肺部感染病灶;痰培養有病原菌生長。(3)收縮壓≥180 mmHg:血壓升高(收縮壓≥180 mmHg)需醫療干預,血壓才能控制在可接受范圍。(4)低氧血癥:動脈血氧分壓<50 mmHg,動脈血氧飽和度<90%,指末端氧飽和度監測<90%,鼻導管或面罩氧療不能改善。(5)消化道出血:大便或胃液隱血陽性。
1.3.2 預后指標 (1)神經功能評分:兩組術前和術后1周均采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評分)評分評定神經功能損傷及恢復情況。NIHSS包括意識水平、視野、凝視、上肢運動、面癱、下肢運動、感覺、共濟失調、構音障礙、語言和忽視癥等維度,總分0~42分,評分越高神經功能損傷越嚴重。(2)術后1個月格拉斯哥預后評分(GOS),5分:恢復良好,可有輕度缺陷,但恢復正常生活和工作;4分:輕度殘疾,可基本獨立生活;3分:中度殘疾,神志清醒,日常生活需要部分幫助;2分:重度殘疾或植物生存狀態,僅有最小反應(如隨著睡眠/清醒周期,能睜眼)日常生活需要完全幫助;1分:死亡。GOS評分3~5分為恢復滿意,1~2分為恢復不良。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2.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并發癥比較
觀察組低氧血癥、收縮壓≥180 mmHg、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再出血發生率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并發癥情況比較[例(%)]
2.2 預后比較
兩組術前NIHS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術后1周NIHSS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觀察組術后1個月GOS評分1~2分1例,3~4分33例,5分11例;對照組術后1個月GOS評分1~2分12例,3~4分45例,5分15例。觀察組術后1個月預后滿意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預后指標比較
3 討論
在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的救治中,并發癥的防治在患者的預后影響因素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常見的并發癥如術后再出血、神經源性肺水腫、肺部感染、低氧血癥、消化道出血等,一旦出現常誘發多器官功能衰竭,導致患者病情惡化,使其致死率、致殘率增高[7-8]。以術后立即在鎮靜鎮痛的狀態下早期行機械通氣,保障患者呼吸道的暢通、呼吸功能和生命體征的穩定,使患者平穩度過圍手術期,作為防治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術后并發癥的中心環節,進行研究。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低氧血癥、收縮壓≥180 mmHg、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再出血發生率均低于對照組(P<0.05);觀察組術后1周NIHSS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觀察組術后1個月預后滿意率高于對照組(P<0.05)。有研究顯示,術后再出血、低氧血癥及上消化道大出血均是影響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9-10]。
首先是術后血壓控制不良和再出血。有研究發現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術后血壓控制欠佳(收縮壓>180 mmHg)時再出血的相對危險度可達13倍[1-3]。文獻[11]發現,將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血壓平穩降至140 mmHg以下,可改善神經功能預后。還有研究發現,開顱血腫清除術后6 h內再出血率占比高達36%,6~24 h內再出血率占比為34%,明顯高于48 h的3%和3~6 d的1.6%[9-10]。因此,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術后72 h內維持正常平穩的血壓,在預防術后再出血中有重要意義。而引起術后血壓急劇波動的因素多見于:(1)常規麻醉蘇醒過程中麻醉藥物的降壓作用快速減弱,引起反射性血壓升高;(2)吸痰刺激所致的劇烈咳嗽;(3)顱內增高所致腦組織灌注不足,引起腦組織缺氧性損害,導致的應激性血壓升高;(4)患者神智和神經功能恢復過程中的頻繁躁動引起血壓升高;(5)麻醉復蘇后腦出血、手術刺激及術后術區疼痛刺激所致的應激性血壓升高。所以術后在麻醉狀態下,移動呼吸機輔助呼吸帶管入NICU病房立即行預防性機械通氣,在保障呼吸功能安全下,使用鎮靜鎮痛治療,最大限度降低以上因素的發生概率,使患者于安靜狀態下于緩慢復蘇,平穩度過圍手術期,有利于血壓的控制,從而降低了術后再出血的概率。
其次是低氧血癥。造成低氧血癥的原因主要有:(1)神經源性肺水腫。文獻[12]報道腦出血患者并發神經源性肺水腫的發病率為10%~20%,雖然其病理生理機制目前尚無定論,但臨床上經常并發于蛛網膜下腔出血、創傷性顱腦損傷、癲癇、腦卒中等急性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的急性期。研究提示氧合指數下降和血乳酸含量升高與神經源性肺水腫的發生有關[13]。表現為肺間質或肺泡液體滲出而導致的肺功能障礙,可產生嚴重的低氧血癥,引起腦組織及機體其他器官發生缺氧損害,這些損害又會通過加重機體應激性反應加重神經源性肺水腫,形成惡性循環,引起患者病情惡化,影響預后。(2)呼吸抑制。腦出血患者因腦組織的損傷,顱內高壓、腦疝等原因常常引起呼吸功能紊亂,術后早期麻醉藥物后遺效應、鎮靜鎮痛藥物的應用都會引起呼吸抑制引起低氧血癥。(3)呼吸道梗阻。大量腦出血及腦疝患者常出現的舌后墜,喉咽部肌肉麻痹引起梗阻性呼吸困難,導致低氧血癥。(4)肺部感染。腦出血患者早期常因嘔吐誤吸、呼吸道分泌物清除不及時或清除困難導致肺功能障礙,而致低氧血癥。術后保留氣管插管暢通了呼吸道,防止了誤吸,方便了呼吸道分泌物的清理,早期機械通氣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呼吸抑制造成呼吸功能障礙,有效防止了低氧血癥,避免了機體的無氧呼吸導致高乳酸血癥的發生,降低了神經源性肺水腫的發生率。必要時采用呼氣末正壓通氣模式可有效地治療神經源性肺水腫,從而改善了患者的預后。
再次是消化道出血。腦出血患者急性期有近30%發生應激性消化道出血。輕癥者僅潛血試驗陽性,重癥者可加重急性期患者的全身性應激反應,甚至休克,加重腦組織缺血缺氧,誘發患者病情惡化,嚴重影響預后[14-15]。陳晴晴等[16]對314例住院急性腦出血患者的臨床治療進行了回顧性分析,也發現導致患者出現繼發性消化道出血的危險因素包括神經功能損傷嚴重程度、圍手術期收縮壓升高及劇烈波動、既往有冠心病和飲酒史。早期的機械通氣穩定了呼吸功能,防止了低氧血癥,有利于降低腦組織的缺血缺氧性損害而加重神經功能的損傷,有利于防治胃黏膜缺氧性損害所致的消化道出血,同時也有利于冠心病的病情穩定,因而降低了消化道出血率。結合鎮靜鎮痛,有利于血壓的控制,也有利于防止血壓的劇烈升高引起的消化道出血。
綜上所述,由于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術后72 h內,病情處于極不穩定狀態,病情變化極為復雜而快速,是嚴重并發癥發生的高危時期。本研究提示高血壓腦出血術后不立即麻醉復蘇,于神經外科重癥監護病房,早期機械通氣結合鎮靜鎮痛,使患者緩慢平穩復蘇。以穩定呼吸循環功能為中心環節,為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原發性疾病的治療和各種并發癥的防治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內環境或條件,有利于降低并發癥發生率和改善患者的預后,在臨床上具有一定的推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