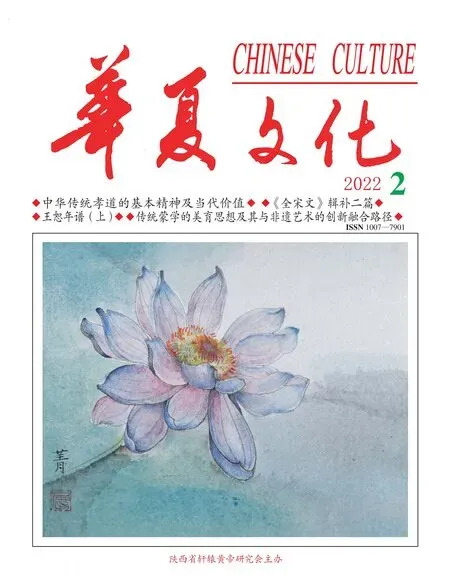從認知角度看《說文解字》“示”部字
□劉 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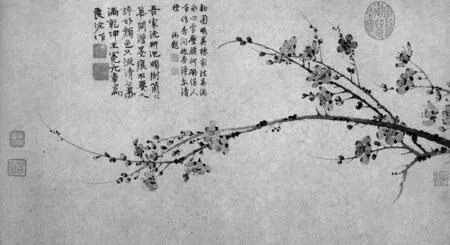
《說文解字·示部》共收字67個,示部作為540個部首之一,目前學界對其研究較少。據現有資料,對示部字的研究大多是以祭祀文化為著眼點,比如樊楊梅《從〈說文解字·示部〉看中國先民的神崇拜文化》等。有些文獻是從文字學本體出發來研究示部的字形或字類,比如李昕皓《〈說文解字〉形聲字溯源——以示部等部為例探究》。從認知角度研究《說文解字》“示”部的文獻迄今未見。本文主要運用認知語言學的范疇、隱喻、轉喻、意象、圖示的概念來闡釋《說文解字》“示”部字的編排、字形和釋義等問題。
《說文解字》“示”部所體現的認知基礎是古人對于自然現象以及天災人禍的集體心理反映。“示”解釋為“天垂象,見吉兇,所以示人也”,上天垂下征象,使人們可以預見吉兇禍福。當科學誕生后,我們才知道一切征象其實是自然現象的結果,而古人卻把這些自然現象與人的體驗聯系起來,通過想象認為是神靈干預世間萬物以及人的生死禍福。這種集體心理反映投射于現實就形成了以崇敬神靈為主的祭祀習俗。
一、“示”部字體現的范疇思想
(一)經典范疇思想的體現
范疇的概念在人類活動中屢見不鮮,大致的意思類似于領域、范圍、類別(參見劉德臨:《說文解字力部字蘊含的認知語言學概念》,載《中國民族博覽》2020年第16期)。依據范疇而建立的兩大理論為亞里士多德的“經典范疇理論”和維特根斯坦的“原型范疇理論”。這兩個理論并不完全矛盾,它們都有自己的解釋角度,并可相互補充。范疇總包含一定的成員。經典范疇理論認為“范疇內的成員都是相對獨立的個體,界限分明,并且全部成員都能共享某些特征”(王寅:《認知語言學探索》,重慶出版社2005年,第122頁)。《說文》整體編排體現了經典的范疇思想,“示”部下67個字在字形上都是以“示”為部首的成員,“示”就是所有成員共享的特征,并且每個字的字形都不相同,界限分明。往下還可以根據字義所描述的事物屬性分為更小的類別:祭祀目的、祭祀對象、祭祀名稱、祭祀方法、祭祀用品、祭祀地點、祭祀過程等等。這種事物屬性是更小范圍成員的共有特征。當然,以上根據事物屬性劃分字類是后人總結為之,盡管并不完全精準,但許慎在編排上也有意把有相似屬性的字編排在一起,如依序排列的“祜”“禮”“禧”“填”“祿”“褫”“補”“祥”“祉”“福”“祐”“祺”“祗”“禔”十四個字因均是祭祀目的而排列在一起;“齋”“禋”“祭”“祀”“祡”“禷”六個字因講祭祀之禮而排列在一起。
(二)原型范疇思想的體現

二、“示”部字體現的隱喻與轉喻機制
“隱喻”和“轉喻”都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隱喻指從一個認知域投射到另一個認知域的認知方式(參見陸儉明、沈陽:《漢語和漢語研究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55頁)。“轉喻”指用一個認知域內的某個概念指代另一個認知域內的某個概念(《漢語和漢語研究十五講》,第358頁)。隱喻突出“相似”關系,轉喻突出“聯想”關系。如果說隱喻是認識世界時一種心理現象的投射,那么轉喻更像是人類用思維表達世界的一種手段或方式。
(一)隱喻的體現

從構成部件上分析,隱喻可分為“零部件式”和“腳手架式”。“零部件式”隱喻的整體字義是對構成部件意義的簡單疊加,“零部件式”在其他部首有相關體現,但是在“示”部字表現不明顯,而“腳手架式”在“示”部運用卻非常普遍,“腳手架式”隱喻就像樓房蓋成后撤去腳手架,概括來說是“整體意義大于部分之和”(《漢語和漢語研究十五講》,第357頁)。如“祭”“禷”“祏”“祠”“礿”“禘”“祼”“祓”等字的構成都是“示”部加上某一突出要素,其構成部件合起來的整體意義要大于構件意義之和。如“祏”從部件組配上可理解為石室祭祀,這種祭祀活動包括眾多要素,至少涵蓋了石室中祭拜的人、石室祭祀禮儀、祭祀物品以及石室里的神主牌位等內容。但“祏”這個字舍去了這些要素及細節,相當于撤去了祭拜的人、祭祀禮儀等蓋房子的“腳手架”,在字形上只抓住“祭祀”和“石室”兩個突出要素,從而概括了整個意義。概括是思維上的體現,這些字的部件構成體現了古人概括事物的思維過程,即用突出、顯著的特征來隱喻整體的事物或行為,如果不經歷這樣的過程,字的意義也很難從構造上體現。
(二)轉喻的體現

三、“示”部字體現的意向圖式模型
“意象圖式”是指人類在與客觀世界進行互動性體驗過程中反復出現的常規性樣式,它們主要起意象性抽象結構的功能(《漢語和漢語研究十五講》,第180頁)。正如術語包含“意象”和“圖式”兩個概念,“意象”體現人類基于身體體驗的心理表征,就如人對一個客觀事物或情形采取的角度不同,凸顯的心理意象不同,從而形成的心理印象就有所不同。“圖式”則突出意象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它是人們從體驗中抽象出的一種認知模型,根據這種認知模型,在遇到相關情形時就會用這種既定的認知模型加以衡量并做出相關判斷。
(一)意向的體現
“意象”涉及“物象”和“背襯”兩個概念。“物象”是一個意象中凸顯的部分,“背襯”是一個意象中不凸顯的相關背景。如“祿、禠、祥、祉”《說文》皆“福也”,“禎,祥也”“福,祐也”“禛,以真受福也”,都表達了幸福的含義,但每個字凸顯的角度并不相同,這是根據不同的身體體驗,依據不同的角度來突出幸福的意義。比如上文“祿”字,右邊部件“錄”表示井鹿盧的形象,進一步突出汲水灌溉,可保豐收的物象,“禎”字的“貞”本義為卜問,突出由卜問求得吉祥幸福的物象,“禛”字的“真”強調以真誠的情意感化神明而得福的物象,“福”“祐”“祉”等都突出神靈的降福和幫助,這些物象的背襯都是古人希望通過祭祀神靈獲得福佑的美好心愿。從這些對“福”義的造字可以看出在認知還未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古人借神明佑護來驅除心理上對自然現象的恐懼感,從而得到“福”。
(二)圖示的體現
圖式可以通過人們的經驗和信息加工組織成常規性的認知結構,可以較長期地儲存于記憶之中。比如上文表示“福”義的幾個字的意象也可以理解為“通過某種對神靈虔誠的行為就可獲得福佑”的圖示,這樣的圖示經過古人長期的實踐和體驗被長久地固定、儲存在集體潛意識中,構成古人獨有的祭祀文化。再例如表示祭祀方式的幾個字“祭”“祡”“祼”禡”。“祭”表示以手持肉;“祡,燒祡焚燎以祭天神”表示焚燒牲體來祭祀天神;“祼,灌祭也”表示以酒灌注在地上的祭祀(參見張菁:《〈說文解字〉中與祭祀文化相關的漢字研究》,山西大學文學院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禡,師行所至,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表示軍隊下馬祭祀天神。這些字的物象是有差別的祭祀方式,背襯的是一切虔誠的祭祀行為。轉換成圖式就是“通過某種祭祀方式來虔誠地祭祀天神”。
四、結語
《說文解字》“示”部字不僅體現了古人崇敬神靈的祭祀文化,也體現了古人造字時的認知機制。“認知科學”雖然是20世紀才興起的研究領域,但“認知”本身并不是現代社會所獨有的產物,它從人類開始思考時就一直存在。語言可以體現一個民族從古到今的思維方式,通過與語言相適應的文字同樣也可以推斷或模擬出一個民族對世界的思考和認知機制。可以說,從文字出發,是探索中華民族思維方式和認知機制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