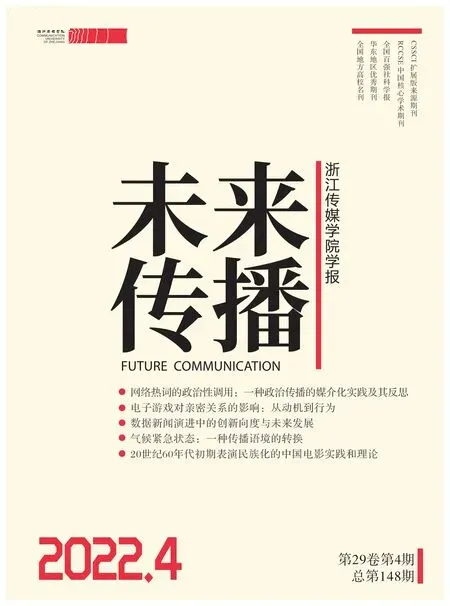解讀青年文化癥候:“躺平”模因的感覺結構分析
章文宜,莫少群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蘇南京210097)
語言作為人類獨有的符號系統,表達人的思想情感、實現人際交往,同時也是人們表達自我、知曉他人、認知世界的工具。當下的網絡流行語如一面鏡子折射了青年的社會生活交往,折射著青年文化的新興風格和特征,蘊涵著青年的時代體悟和情感訴求。“躺平”是2021年“現象級”的青年網絡流行語。所謂“躺平”,就是癱倒在地,不再雞血沸騰、渴求成功了。躺平源于一位草根博主發布在百度貼吧“中國人口吧”里面名為《躺平即是正義》的帖子,該帖作者講述了自己兩年多沒工作的躺平生活,且非常“低欲望”地生活著,努力保持身體的健康和思想上的自由思考。[1]一時間,該博主的躺平理念迅速引起青年群體特別是90后、00后的效仿和附和,在網絡上掀起關于“躺平”“躺平學”“躺平主義”的話語敘事。
有主流媒體對于“躺平青年”主張的“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維持最低生活欲望,堅決抵制成為資本收割的‘韭菜’”等消極心理予以批判,更有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李鋒亮直言“躺平態度極不負責,不僅對不起父母,還對不起努力工作的納稅人”[2]。有學者指出,躺平是“‘喪文化’‘佛系文化’為代表的‘頹廢型’青年文化的延續,是青年面臨社會難題而群體性焦慮的文化反映。”[3]作為一種新的青年亞文化癥候,“躺平”話語不斷地被復制、模仿、傳播、再造,并引起在文化感知、社會結構、現實矛盾等不同層面的深刻討論。作為青年的話語實踐,“躺平”不僅是青年亞文化中簡單的娛樂化用詞,它與青年的生活體驗和社會結構有著緊密的關聯。本文將引入“感覺結構”的理論框架,以“模因”概念為分析工具,深挖“躺平”如何作為一個話語符號和意義單位在互聯網平臺流行和擴張,探究“躺平”話語背后的感覺結構,并探尋“躺平青年”與中國社會結構性因素的互動關系。
一、理論資源:感覺結構與網絡模因
(一)作為理論框架的“感覺結構”
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一直思考文化與社會的關系。他在《電影序言》(1954)第一次提出,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1)該概念國內有兩種翻譯:感覺結構或情感結構。倪偉(《漫長的革命》譯者)、王爾勃(《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使用“感覺結構”進行翻譯,馬中紅的論文《2020 亞文化熱詞:詞源、意義及情感結構》、楊擊論文《情感結構: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論遺產》中使用“情感結構”,為了統一本文采用感覺結構這一翻譯。,認為“它與總體性的共同經驗相關,不能被分割概括,要在鮮活的生活經驗中去把握”[4]。文學、電影、藝術作為當時社會共同經驗的載體,通過電影文本分析感覺結構是把握時代經驗的重要研究方法。在《漫長的革命》中,雷蒙德·威廉斯把感覺結構描述為解決方案中的社會體驗,是特定歷史時刻的文化、情緒和感覺。他認為:“感覺結構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帶來的特殊的、活的結果。”[5]他提出,每一代人都擁有屬于自己這一代人的感覺結構,時代和人們經驗感知的變化會連帶感覺結構發生變化。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威廉斯進一步完善了感覺結構的定義,將它與主導的意識形態分離,認為感覺結構是“溶解流動中的社會經驗”[6],不同于已經沉淀出來、可以直接使用的社會意義,認為它是來自大眾的、尚未定型的新興文化相關的整體性的生活體驗。可以看出,感覺結構是威廉斯分析文本和社會的工具,它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整體的社會文化,并體察到在主流文化之外,游離著代表一部分社會群體“共同體驗”的新興文化。
很多中外學者以“感覺結構”為基礎,分析了在互聯網技術背景下的文化形式和社會關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傳播學院教授茲茲·帕帕查理斯(Zizi Papacharissi)將社交媒體視為一種感覺結構,“是一種講述故事、創造意義的軟結構,為網絡和公眾情感提供了質感、調性、話語性和敘事形式”,并認為柔軟的、網絡化的感覺結構幫助人們講述“我們是誰”“我們想象我們可能是誰”的故事。感覺結構打開并維持了可以講故事的話語空間。[7]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數字傳播系副教授曹洵將“自我矮化”這種整體性的社會經驗看作一種在線的感覺結構,認為“草根”“屁民”“屌絲”的走紅反映了底層群眾對現實困境產生的身份焦慮。[8]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傳播學碩士生導師馬中紅以情感結構(感覺結構)理論分析了2020年亞文化熱詞背后青年使用的內在情感動因,認為時下中國青年擁有與父輩不同的情感結構,使得他們對社會事件、公共議題呈現更多的娛樂化和戲謔性的態度。在媒介化平臺上碎片式、分散式的青年話語經由青年不斷重復、改造、創新,引起更大范圍的情感共鳴和身份確認,成為青年群體文化和社會感知。表面是混雜的青年亞文化新現象,內在有自己的文化軌跡。由此,本文將體現出新一代青年共享式經驗的網絡流行話語稱為青年的感覺結構。
(二)作為分析工具的“模因”理論
1976年,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一書中首先提出“模因(meme)”的概念,道金斯認為:“如同基因作為人類遺傳進化的基本單位,模因是文化進化和傳播的最小單元,人們通過復制和模仿進行人際傳播實踐,其本質是一種復制因子。”[9]互聯網傳播環境下,“模因被用來描述文本、圖像、語言的移動或以其他單位內容呈現的特定思想在快速吸收后傳播”[10]。模因最本質的特征是成功地實現了復制和傳播。任何信息經歷了廣義上的“模仿”過程,可以被稱為模因。控制論學者弗朗西斯·海拉恩(Francis Heylighen)詳細劃分了模因成功復制傳播的四個階段,包括同化、記憶、表達、傳播[11],網絡流行語是在語言傳播過程中競爭生存下來的強勢模因,通過簡明扼要的語言表達,易于人理解、接受并同化進入記憶階段,通過人際交往進行個人表達和擴散傳播。紐約佩斯大學傳播學助理教授薩布萊維茨(Marcella Szablewicz)認為,模因既反映也塑造著流行文化,是人們態度、思想、心態的表達,強調其表征文化和政治信息功能[12],這與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反映特定歷史時期文化、思想、情緒、經驗的感覺結構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于威廉斯而言,詞語的變遷秘密地記錄著一切社會轉型過程。他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感覺結構概念以后的20年間不斷豐富其內涵,感覺結構是他理解和研究社會變遷的重要理論方法,“其1985年出版詞典《關鍵詞》對文化與社會重要詞語概念的梳理和記錄,也向后人展示著透過詞語研究人類經驗的轉變是文化研究的可靠路徑”[13]。當下的網絡模因文化是青年對社會轉型的深刻體驗,通過對網絡文化模因的復制、傳播、擴散規律的把握和研究,可以感知新時代青年的感覺結構。由于感覺結構是一個抽象度比較高的理論概念,而“模因”作為研究網絡流行語的傳播規律和意義表征的理論工具,不僅具有操作性強的優點,且強調使用者共同創造和共享的文化體驗,這與感覺結構理論強調的通過文本研究新興群體的社會經驗不謀而合。本文以微博話題“躺平青年居家圖鑒”“躺平是年輕人的正確選擇嗎?”“拒絕躺平的86歲科學家”等青年關于躺平討論的語料為文本分析庫,將“躺平”作為網絡文化模因,分析其傳播邏輯和意涵網絡,再借助感覺結構理論,分析“躺平”模因隱含的青年社會感知及這種感知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網絡模因下躺平文化的多維審視
“模因作為文化的基因,通過非遺傳的方式、特別是通過模仿將一些思想加以傳播并相傳下來。”[14]可見,模因是流行的文化單位,網絡模因由互聯網參與者傳播、模仿、改造,并在過程中創造共享性的文化體驗,其流行與復制的速度決定模因的繁殖和傳播能力。利昂·G.希夫曼(Leon G. Schiffman)指出,模因是人與人之間傳遞的文化信息,一方面在微觀上形成網絡文化的擴散,另一方面還在宏觀上形塑社會心態。他進一步提出模因的三個維度以分析當代的數字文化,即內容、形式、姿態。[15]內容是指模因文本傳達的思想與意識形態,形式是指模因傳播的載體或表達的形態,姿態即模因表達者的立場或話語傾向。“躺平”模因作為網民生產、創作、傳播的網絡流行語,其符號意義為參與的網民共享,并利用拼貼、解構、挪用、再造等方式擴大本文指涉范圍,獲得廣泛的民眾參與,擁有了強大的網絡關注,體現了網絡模因文化的內在屬性。下文將“躺平”作為典型的網絡模因,借由希夫曼提出的內容、形式、姿態三個維度,來分析其核心意涵、傳播策略和話語傾向,為更好地把握其隱含的感覺結構作鋪墊。
(一)表達焦慮無力的核心意涵
2017年“喪”文化盛行時,“葛優躺”系列表情包走紅,它源于1993年情景喜劇《我愛我家》里葛優飾演的紀春生眼神空洞、生無可戀地癱躺在軟皮沙發上的動作,網友借此進行復制傳播,展演喪文化。2021年的“躺平”有類似的喪文化基因,但更多源于對流行語“內卷”一詞的回應或延展。
“內卷”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名詞,學術應用中常用作“內卷化”,國內學者黃宗智用“農業內卷化”來說明勞動的密集化帶來單個勞動日報酬的遞減,表現為沒有發展的增長。[16]網友將“內卷”用來形容當下過度低效的競爭,過剩的人力投入到有限的資源爭奪中。熱詞“996”“007”“末位淘汰”“非升即走”投射了各行各業的職場內卷壓力,“躺平”模因則是對過度競爭、嚴重內卷的一種抵抗。“內卷”是因,而“躺平”為果,隨即在網絡上形成強烈的輿論共振。
分析“躺平”模因的文本,發現其話語表達有兩重邏輯:一是主動的躺平,諸如在微博“躺平青年居家圖鑒”話題下,有網友表示“不買房買車,不生娃結婚,不社交應酬,一個人宅居躺平過活”,表達了青年主動降低生活訴求,以低姿態面對消費主義和社會競爭,不爭不搶,減少娛樂,回歸悠閑穩定的慢生活的內心價值取向。躺平者選擇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環境對個體的規訓;另一種是被動的躺平,“天道并不酬勤”“你奮斗的終點敵不過別人的起點”“社會險惡,先躺為敬”“躺平是等死,不躺平是猝死”等話語反映了青年在城市叢林競爭中的無力感,認為努力無法改變現實,不如躺平休息。這種被動的“躺平”心理源于對外在社會壓力的感知和自身社會地位提升的恐慌。新華社于2021年5月30日報道了86歲老科學家趙煥庭每天凌晨4點起來工作,每天工作10到12小時的視頻,希望借此激勵年輕人不要“躺平”,要“持續奮斗”。“躺平族”表示:“老科學家在需求第五層,即實現自己人生價值,我們在第一層,給老板打工解決生存問題。”“科學家確實偉大,可我只是普通垃圾啊!”[17]面對主流媒體的教育引導,躺平青年無動于衷,認為個人奮斗也無法改變社會地位的躍遷。“躺平”敘事有“犬儒主義”玩世不恭的懈怠之感,被外界認為是一種不務正業或者自我放逐,但“躺平”實際蘊涵著擁有較少社會資源的青年對社會壓力的無奈感知,對現實的焦慮無力是“躺平”模因進行意義共享的基礎。
(二)依靠戲仿拼貼的創作形式
形式層面重點考察“躺平”模因在互聯網空間的媒介表達形態和文本呈現結構。“躺平”模因作為用戶生產內容,具有典型的網絡文化傳播特性。傳播形式有玩笑段子、惡搞圖片、表情包、漫畫、帖子、歌曲等,媒介形態包括文本、視頻、音頻,傳播敘事策略則是戲仿和拼貼。
戲仿(parody)是戲謔地模仿。丹·哈里斯(Dan Harries)認為,戲仿將原文本的文本要素或語境要素進行轉換,并帶有諷刺脈動,對其再語境化以創造一個新文本。[18]一種文化產品或文化實踐帶著某種挑釁或諷刺意味,對另一種文化產品或實踐進行不動聲色的模仿是戲仿。在互聯網強調平等、重構經典的文化創作氛圍中,青年戲仿文化愈發興盛。很多“躺平”話語是對經典歌詞或者名言警句的戲仿,比如“躺平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是一群人的躺平”是對歌曲《葉子》中“孤單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是一群人的孤單”的仿擬。而“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放棄”“世界那么大,誰愿躺平。世界那么小,只能躺平。”“條條大路通羅馬,而有的人就生在羅馬”等躺平模因的延展話語,多以出人意料的結局和轉折,對名言警句進行解構,戲謔地抵抗著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奮斗觀念。還有通過對影視劇人物形象進行加工制作,成為躺平族的形象代言人。葛優躺倒的畫面成為躺平族戲仿創作圖片的主要素材。從圖1可以看到畫面中空洞無力的眼神,躺倒在沙發上慵懶懈怠的身體形態惟妙惟肖地傳達了青年躺平的姿態,配上“生命不息,躺尸不止”的夸張文字表述,傳達出青年對生活失去信心的懈怠感。
拼貼一直被用于亞文化研究領域,“是一種即興創作或改變的文化過程,客體、符號或行為通過拼貼到不同的意義系統和文化背景中,獲得新的意味”[19]。亞文化研究經典著作《亞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Themeaningofstyle)的作者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認為,青年打破日常符號系統規則,將不同的“商品符號拼貼在一起,以抹殺或者顛覆原有的直接意義”,踐行著“符號游擊戰”的顛覆性實踐,[20]并造成了日常語義系統的斷裂和失調。當代網絡中的惡搞歌曲、網友自制表情包、二次創作視頻都屬于拼貼的表達形式。特別是用戶生產的表情包(如圖2),將躺平的動作和躺平的價值觀點拼貼在一起,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臺廣泛流傳。不同于社交系統提供的官方表情包,網友通過挪用、拼貼多種文化符號,在重新編碼解碼的二次創作中享受著自我制造的“躺平”文化和敘事快感,并通過“一言不合就斗圖”的形式參與社交狂歡,以生動的“躺平”表情包表達對現實內卷化的不滿和憤懣。

圖1 網民制作的“躺平”圖片 圖2 網友制作的“躺平”表情包
戲仿、拼貼的文本表現手法都符合當下媒介碎片化傳播的特性,更易于情感的表達和釋放。帶有反諷意味的戲仿話語、惡搞圖片、表情包等語言模因快速繁殖,突破青年圈層在整體網絡空間中病毒式傳播。自嘲為打工人、社畜、屌絲的青年在躺平文化的氛圍中宣泄負面情緒,以只言片語的表意實踐在社交空間傳播著躺平族的共享性體驗,為“躺平即正義”的思想觀念爭取網絡話語權和現實社會的關注。
(三)作為戲謔姿態的情感溝通
“‘姿態’指代說話者與文本、文本語言代碼以及其他潛在說話者之間的關系。”[8](154)模因在網絡平臺流傳推廣,經由躺平青年群體,通過媒介平臺的接合作用,以自我矮化的表達框架,向主流文化進行戲謔式的情感性溝通。
青年從“呱呱墜地”到進入社會,一直受到主流價值觀的引導教育,諸如“知識改變命運”“只有通過艱苦奮斗,才能獲得美好生活”等。但上完大學、留在一線城市打拼的青年,要面對的社會現實是居高不下的房租、極度激烈的就業上崗競爭、嚴格的戶籍積分制度……現實社會的巨大生存壓力和網絡時代的原子化生活讓青年在城市感到愈發孤獨和飄零,而“躺平”模因給予青年一個情緒的出口,以自我矮化的戲謔姿態嘲諷自身的生活焦慮和現實苦悶。如著名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所言:“媒介話語傳播的實質在于意義、快感和身份的流通。”[21]青年通過調用網絡媒介空間的“符號資源”和“符號權力”來表達身份認同和建立群體歸屬。如“一時躺平一時爽,一直躺平一直爽”等口號富有煽動性,能激發更多獨居青年關于自身社會處境的情感想象和情緒流動。在虛擬空間尋求情感互動、文化認同和社會聯系是青年網民繞不開的路,而“躺平”模因實現了青年的符號意義互動和身份認同,對社會壓力擁有共同情感體驗的青年們借此建立網絡“聯結”,形成相互撫慰的情緒氛圍。“躺平族”在不斷擴大的非理性聲浪中抱團取暖,在由共同語言標識構建“聯結”的新部落中獲得情感聯系。另一方面,當躺平青年用戲謔化的方式反諷現實,以自我嘲諷形成浩然聲勢,也是在呼喚主流價值觀的教育引導者轉換角色,傾聽青年的心聲和社會感知。面對躺平撲面而來的情感宣泄,有批判“躺平”可恥的代際認知差異,也有主流媒體如《光明日報》發文稱“年輕人選擇‘躺平’,也是在傳遞信號”[22],或有媒體重新闡釋“躺平”的意蘊內涵,認為青年中的“語言躺平族”并不妨礙他們奮進,早晨的鬧鈴未響之前他們已經醒來,整裝待發。[23]盡管主流價值觀對躺平族的情感訴求回應呈現多元層次,但“躺平”模因促進了代際對話以及主流文化與青年亞文化的情感溝通。
三、“躺平”模因盛行隱含的感覺結構
“躺平”文化的傳播突顯了網絡文化模因的特性,即網絡個體將單元化的信息通過參與、創造、分享成為群體共享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體驗一方面是個體私人化的、帶有獨特個人烙印的,另一方面也經由網絡模因的復制擴散而傳播發酵,成為群體的社會認知體驗,它不是個體感覺的總和,而是社會總體性的感知體驗,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狀態。正是這種對社會感知的共同性,形成青年網民傳播“躺平”模因的現實基礎。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說:“每一代人以自身的方式對世界作出反應,并同時進行改造,把自己對社會的感知塑造成一種新的感覺結構。”[8](158)他將感覺結構定義為“溶解流動中的社會經驗,并通過新的語義形象表現出來(如文學、藝術、語言、建筑)”[6](142)。在互聯網的傳播環境下,年輕一代的感覺結構通過青年創造的文化符號進行社會感知的共享,即通過網絡模因文化實現意義生產、身份認同和情感溝通。可以說,網絡模因將青年一代的感覺結構進行了符號化的表征,而感覺結構是新興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雙向互動。理解和認知新時代青年的感覺結構,需要回到其產生的社會物質基礎。當下青年的感覺結構代表著新興的、非化約的社會意識,并與主導文化和主導意識形態形成張力和對抗。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提出,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使命是將個體生活與社會歷史放在一起認識,使“環境中的私人困擾”上升為“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議題”。[24]感覺結構理論恰好能實現個體感知與社會結構議題的勾連。通過分析“躺平”模因隱藏的感覺結構,幫助我們解讀新型亞文化癥候背后的社會結構問題,挖掘“躺平”主義的心理結構特征和社會矛盾根源,從而理解和應對“躺平族”的時代訴求。
(一)社會壓力下的軟性抵抗
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感覺結構,但感覺結構的生成不只是代際替換使然,感覺結構的分化和社會結構的分化有很大的關系。雷蒙德·威廉斯認為:“一種新的感覺結構的興起是同一個階級的崛起有關,在另一些時候這些階級的崛起又與階級內部出現矛盾、沖突、分裂有關。”[6](144)中國正在經歷社會的轉型,高速的城鎮化進程,大量的鄉鎮人口流入城市,成為城市的新移民。這些新移民來到大城市求學、就業、創業,懷揣扎根現代都市的夢想,但社會的多重壓力讓他們自稱“打工人”“社畜”,越來越意識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呈現出“喪”的社會心態,這種心態的一個突出表現是“躺平”。居高不下的房價、競爭內卷的職場、醫療教育資源的緊張、生娃育兒的高昂成本以及物價的上漲都成為青年必須承擔的社會壓力和現實困難。主流價值觀多引導青年努力奮斗,關于生活中的矛盾、沖突、斷裂、異化等負能量要么不被呈現,要么消失在關于和諧、美滿、幸福、夢想、成長等主導敘事話語之中。對于主導敘事的過度完美,很多青年選擇用戲謔的方式進行抵抗。
英國伯明翰學派認為,那些被“風格化的儀式抵抗”有可能形成一股強勢的社會力量,而青年亞文化的“儀式抵抗”需要通過“風格”來實現。“風格被看成是一種令人矚目的癥候,代表了更廣泛、更普遍的、被掩蓋的不滿情緒”[25]。當下很多青年宣稱不戀愛、不結婚、不生子,用“社會險惡,先躺為敬”“世上無難事,只要肯躺平”等價值觀顛覆傳統觀念,形成與主流文化相悖的消極文本。一方面,這是青年網民對傳統奮斗價值體系的懷疑和否定,他們不接受主流意識形態類似“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等規范化、“雞湯化”的訓誡,以“躺平”的戲謔姿態,反諷現實社會的壓力和強調自我社會身份的弱勢。但戲謔的抵抗恰巧印證了青年現實生活中處于資源弱勢甚至無權地位,“躺平”模因是一種作為話語方式的軟性抵抗。另一方面,“躺平”文化的盛行,說明年輕一代想要創造與父輩不同的社會感知和文化結構。他們比父輩更容易獲得物質享受和數字化娛樂產品,對通過“狼性競爭”等高強度的工作而獲得物質財富的必要性表示懷疑。沒有社會財富、權力、資源,也無力改變社會環境,就降低自我的物質需要,以低欲望的生存心態應對社會的多重壓力,以躺倒的消極姿態拒絕上進,以惡搞、自嘲的方式與嚴肅、正統的說教文化和父輩觀念相區隔,以帶有道德自裁意味的自我展演對主流價值觀進行邊緣式的抵抗。
(二)階層固化感知中的隱憂和無奈
網絡模因能夠快速傳播和流行的表象背后是其耦合著一種社會現實,折射出一種社會心態。“躺平”模因映射了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弱勢青年群體對中國社會階層固化的焦慮和無奈。階層固化表現為社會流動滯化,社會流動分為水平的代內流動和垂直的代際流動。水平方向的階層固化表現為依靠個人努力、才華、能力等后致性因素,很難實現社會地位和階層躍遷,而垂直方向的階層固化表現為家庭背景和繼承遺傳等先賦性因素在教育、就業、升遷、財富累積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大,社會中上層的權力、地位在代際之間不斷復制和世襲,使得社會流動受阻。[26]先賦性因素影響的增強,后致性因素的式微是階層固化的首要原因。剛進入社會的青年如美國文化批評家保羅·福賽爾(Paul Fussell)所言:“那些剛來的、精力充沛、不斷追求上進的人,在攀登社會階梯的戰斗中已經汗流浹背了,卻突然吃驚地發現,通向被上層社會完全承認和接受的門仍然是關著的。”[27]社會階層固化的趨勢為想要依靠個人努力實現社會地位上升的青年設置了障礙,很多青年放棄奮斗,選擇“躺平”。
再者,戶籍管理制度是制約青年實現階層跨越和社會流動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充沛的勞動力,很多農二代青年跟隨父母腳步,離村進城打拼,并想在城市留下來。但戶籍制度的存在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很多農二代青年在二元結構下,承受了城市住房、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歧視性擠壓,很難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由此,戶籍制度為階層固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構成了無形的推力,將農二代青年推出城市、遣回鄉村,形成被動躺平的狀態。
最后,網絡媒介關于階層固化的焦慮信息傳播,渲染了青年對社會流動滯化的感知。媒介技術把公眾的日常生活無限度地卷入網絡社會之中。社交媒體不僅是媒介技術的延伸,還是社會互動關系的投射。“媒介化過程中滲透著媒介邏輯,使得網絡社會的物理空間、心靈空間和社會空間都發生了位移和融合”[28]。社交媒介習慣用“青年焦慮”的框架敘事,并將青年日常關注的社會議題和情緒反饋都做了放大性呈現。以社交平臺作為主要信息獲取渠道的青年,逐步陷入社交媒體建構的“階層固化”的信息繭房。勤勞、奮斗、拼搏等價值觀念會被排除在“躺平”敘事形成的媒介“過濾氣泡”之外。加之“躺平”話語不斷地在社交媒體快速復制和傳播,形成了奮斗無望的群體性隱憂,并讓部分青年認為“共享的現實”是中國當下的“全部現實”,而聽不到其他青年群體的聲音,在自我艱辛和身份焦慮的主觀意識中不斷加深對階層固化的認知和隱憂。
(三)現實剝奪感下的防御性悲觀
新興的“躺平”文化是青年理想被現實擊碎而產生相對剝奪感后,采取的防御性話語策略和自我保護措施。1970年,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泰德·格爾(Ted Robert Gurr)提出“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認為“社會中的個人都有價值期望,而社會擁有滿足大眾價值期望的價值能力,當社會變遷導致社會價值能力小于個人的價值期望時,人們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29]。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發展,改革紅利逐步被稀釋,全社會的經濟增速也有所放緩且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容樂觀。據《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2020年新冠疫情的沖擊下中國財富基尼系數上升到0.704。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1%的居民占總財富的比例也從29.0%上升至30.6%。[30]財富分配的不平衡讓青年感到強烈的被剝奪感,加之“高房價、強內卷、低收入”外顯了社會結構矛盾,讓很多青年認為努力奮斗也難以實現自己價值期望,不如選擇降低期望值的心理狀態,即防御性悲觀。1986年,美國韋爾斯利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朱莉·諾雷姆(Julie Norem)和南希·康托(Nancy Cantor)提出防御性悲觀(defensive pessimism)的概念,“指那些在過去的情境中取得過成功,但現在面臨相似的情境設置了不現實的低的期望水平并反復思考各種可能的后果”。我國學者袁愛清和邵培仁認為:“防御性悲觀是弱勢群體在利益表達時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采取的心理策略,是基于自我保護的話語表達機制。”[31]
不同于宣泄憤怒的非理智性破壞力量,“躺平”模因以防御性的話語姿態,用自我嘲諷的框架表達內心對于社會壓力的不安和焦慮,但有時這份不安和焦慮也會轉化為前進的動力。以職場壓力為例,剛步入職場的青年缺少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很難實現階層躍遷。從而容易出現對有限的資源進行無序低效的競爭,致使職場內卷化。青年群體無限的努力其實是內部沒有意義的自我消耗,于是部分青年用“躺平”發出拒絕內卷的宣言,降低個人職業晉升欲望。“我只想躺平,完成每天任務,做個咸魚”“躺平人,躺平魂,躺平都是人上人”等話語意在建立躺平族的情感防御機制,在主動污名化自我中尋找“天涯淪落人”,以悲觀無為的心態扮演社交角色,獲得壓力的紓解和喘息,與平凡的自己和解之后獲得動力,更好地工作和生活,是不同于主流價值觀的新興價值選擇。其次,“躺平”作為一種在線的感覺結構,以防御性悲觀的策略性表演為青年爭取網絡話語權,以消極的弱者姿態進行底層敘事。在“躺平”模因的傳播復制中,將個體情緒表達轉變成網絡集體行為,形成引發官方話語和青年話語互動討論的媒介事件,以促進國家和社會思考,傾聽青年壓力,提高社會價值能力,降低青年的被剝奪感。
四、余論:感覺結構與社會結構雙向建構
雷蒙德·威廉斯認為:“新的一代人以自己的方式對它所繼承的那個獨一無二的世界作出反應。”這種反應會追溯和吸收前人生活體驗中的一些連續性,但是“又對組織進行多方面的改造”,以不同的方式感覺他們的生活,將這些反應創造性地加以塑造形成他們新的感覺結構。[5](57)這種感覺結構被視為與主導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新興的生活體驗,是經由大眾主體間意識與社會結構互動而產生文化結構。感覺結構是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的概念,是用來研究文化與社會的重要方法論。肖恩·馬修斯(Sean Matthews)認為,這個概念主要用作考量社會型構過程中各種新出現的元素,用于分析社會或文化的變遷。[32]本文從威廉斯的感覺結構出發,分析了青年新興的“躺平”網絡模因文化,解讀當下青年關于社會的共同體驗,并借由“躺平”文化的感覺結構,分析探索了其背后的社會結構問題。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它的變動和興起反映了社會結構中的某些因素的流動和變化。社會結構包括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就業結構、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方面的變化。[33]社會結構彼此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結構性矛盾復雜而宏觀,對“躺平”模因的感覺結構分析實現了微觀感覺與宏大結構的融合,并且我國的社會結構變動還伴隨著現代化、全球化的整體過程,出現“躺平”的感覺結構并非我國孤立的社會感知,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也在經濟轉型期出現類似的情況。日本學者大前研一認為,整個日本進入“低欲望社會”,在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社會結構出現了低消費、少夢想、無干勁的低欲望青年。[34]還有英國的“尼特族”、美國的“歸巢族”等,這些以青年的“頹喪”“無欲”為核心的社會體驗和中國的“躺平”青年有著類似基因的感覺結構,但其背后的社會結構矛盾存在異質性。針對中國本土出現的“躺平”文化分析,除了感知它的模因傳播邏輯,分析它感覺結構的內涵意蘊,還要深刻理解到感覺結構背后是更為復雜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一些青年感知到社會結構因素對自身發展的限制,包括城鄉二元體制帶來的戶籍差異和住房、醫療、教育、公共服務的不均衡,青年陷入高房價、低收入、強內卷、少流動的結構困境之中,從而導致部分青年形成了強焦慮、多悲觀、少奮斗、低欲望的感覺結構。“躺平”模因的出現和流行是青年用短小精辟的話語,反諷社會現實和自身處境,是他們對社會結構性矛盾的話語抵抗,表現出他們對于生存狀態的焦慮和對社會結構僵化的不滿。而且,“躺平”模因具有“喪文化”家族基因,同譜系的“喪文化”熱詞諸如“佛系青年”“積極廢人”“985廢物”“小鎮做題家”等不斷涌出,廣為流傳后又逐漸消失,詞語的外在形式雖然不斷變化,但其意蘊表達有著內在的同構性。
亞文化研究中用“同構”的概念來“描述一個群體的價值觀與生活風格之間象征性的一致”,也就是說亞文化群體“調用的物品和符號都和亞文化關注焦點、活動、群體結構以及集體的自我形象有著同構的關系。”[25](113-115)“喪文化”光譜中的流行語是青年對社會現實矛盾的經驗感知,其調用的話語符號和內在價值取向存在同構關系。它們折射出青年存著與主流價值觀相抵抗的感覺結構并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只要造成青年感覺結構的社會根源和社會結構不發生變化,青年的感覺結構也將在很長的時間保持穩定。社會結構以及其自身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青年不斷興起的異形同構的感覺結構,社交媒體上復制傳播的網絡模因也在不斷重復和強化著青年的感覺結構。這也在提醒我們,不能將“躺平”文化簡單地視為媒介噪音或對青年的價值觀進行道德審判,而要重視、傾聽青年關于現實的苦悶和訴求,分析他們的感覺結構,并從社會結構層面著手改變社會的困境,激發當代青年的實干精神,為青年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
針對“躺平”青年的關鍵性政策包括:一是穩步推進城市住房體系改革,貫徹房住不炒政策,降低一、二線城市的房價,加大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應量,降低城市新移民、農二代城市購房的門檻。二是增強青年就業保障體系,出臺青年靈活就業的社會保障政策,加大對青年創業的扶持力度,提高最低收入標準保障青年勞動收入,加大政府再次分配在收入調節中的作用。三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減少因為城鄉戶籍差異導致的社會醫療、教育、購房等不公平現象。以此為青年的感覺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良性互動創造更多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