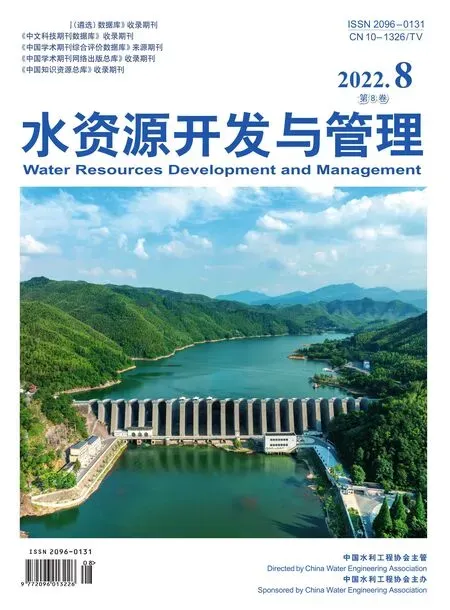基于綜合指數法的城市水安全評價
周 雙 何懷光 李 娜
(湖南省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湖南 長沙 410007)
20世紀70年代,水安全問題開始受到關注。90年代以來,世界水資源論壇等[1]呼吁關注水資源保護和管理、水與可持續發展,水安全問題逐漸成為研究熱點。“水安全”一詞來源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資源環境承載力原理、危機管理理論等[2-3],體現的是人口、經濟、自然、社會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城市水安全體現的是城市涉水綜合系統的健康或可持續狀態。
水安全評價研究是“水安全”問題研究的熱點,其中水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最為關鍵[4-5]。目前,水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多基于水貧困指數[6](資源、途徑、利用、能力、環境)和DPSIR概念模型[7](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確定。也有部分學者進行了創新,如史正濤等[8]將水安全分為水安全支持子系統、水安全協調子系統、防洪子系統;邵東國等[9]從城市重要性、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環境安全等維度建立了水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張蕾等[10]從資源、社會、經濟、環境4個方面構建了南京市水安全評價指標體系。但隨著城市發展變化,這些指標體系研究存在指標體系冗雜、指標不全或代表性不夠等問題,影響了評價結果的客觀性。基于此,本文將綜合考慮水安全概念內涵、當前經濟社會現狀及發展趨勢、民眾關注焦點及國內水安全相關規劃,從城市涉水綜合系統中梳理、篩選出最能表征城市水安全狀況的指標,并采用綜合指數法開展城市水安全評價,為城市水安全管理提供參考。
1 城市水安全評價方法
基于綜合指數法的城市水安全評價基本思路為:首先選取合適的評價指標,建立水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同時征求專家意見確定不同層次的指標權重和分級閾值,再利用指數型函數實現指標值的標準化,最后根據水安全指數模型計算地區水安全指數,同時確定水安全指數分級標準,對水安全的評價結果進行直觀判斷。
1.1 指標體系構建及權重確定
城市水安全指標體系包括目標層、準則層和指標層。目標層即區域城市水安全;結合水安全概念內涵,參考國內水安全相關規劃,聚焦水災害規避、水源供給保障、水資源高效利用、水生態環境保護、水監管服務等影響城市水安全的核心要素,將城市水安全分為防洪安全、飲水安全、用水安全、河湖生態安全、涉水事務監管安全5個準則層,利用頻度統計、理論分析、專家咨詢等方法,將準則層進一步細化為31項具體指標,其中正向指標25項,反向指標6項;指標層具體包括防洪安全指標5項,飲水安全指標6項,用水安全指標7項,河湖生態安全指標7項,涉水事務監管安全指標6項。
指標權重指單項指標對總目標的貢獻程度,是反映各指標在評價體系中地位的重要系數。目前,確定指標權重的常見方法有德爾菲法(專家打分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層次分析法(AHP)等。由于本研究評價指標數量較多,且指標大多貼近涉水管理實際情況,權重賦值需要在有經驗的專家指導下進行,因此本文選取德爾菲法(專家打分法)確定各個指標權重。根據經驗并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分析提出對于指標權重的初步意見,并征求相關專家意見最終確定指標權重。城市水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城市水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續表
1.2 指標標準化及閾值確定
為消除指標不同量綱對指數計算的影響,須對指標進行歸一化處理(即指標標準化)。指標標準化的常用方法為直線型功效系數法,即將指標數值變化和指標評價值的關系作直線關系處理。但實際上指標數值變化對城市水安全影響的規律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存在與邊際效益遞減原理相似的特點。因此,本研究借鑒邊際效益遞減原理,對兩者關系作出更為客觀與符合實際的處理,即采用指數型功效函數實現指標的標準化處理,以便更好地反映客觀實際,提高評價結果的準確性。
標準化計算公式:
Im=e-f(x)
(1)
對于正向指標:
(2)
對于逆向指標:
(3)

本研究指標閾值分為上限值、下限值和控制值。絕大部分指標設置上限值和下限值,對于正向指標,指標值越大越好,反向指標反之。對于萬元GDP用水量、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指標則只設置相對控制值,其中萬元GDP用水量和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測算值低于控制值為優,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測算值高于控制值為優。參考國際、國家相關標準,結合國家或地區相關規劃,并咨詢相關專家,確定了評價指標閾值(見表1)。根據指標上限值和下限值,利用式(1)~式(3),實現指標標準化。
1.3 水安全指數評價標準
水安全綜合指數由防洪安全、飲水安全、用水安全、河湖生態安全、涉水事務監管安全5個分指數組成。首先對單項指標權重和無量綱數值進行加權計算得出各分指數,然后將分指數進行加權求和得出水安全綜合指數,具體公式為
(4)
(5)
式中:WSI為區域水安全指數;Wi和Wj分別為單個指標權重及WSI分指數Xi的權重;Xi為防洪、飲水、用水、河湖生態、涉水事務監管各項分指數。
參考省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提出水安全評價標準,將指標得分按0~1分為5個等級。水安全綜合指數和分指數評分值大于0.8的為“安全”;在0.7~0.8(含)之間的為“較安全”;在0.6~0.7(含)之間的為“基本安全”;在0.4~0.6(含)之間的為“較不安全”;小于等于0.4的為“不安全”。城市水安全評價標準見表2。

表2 城市水安全評價標準
2 城市水安全評價實例
2.1 研究區概況
邵陽市位于湘中偏西南、資江上游,屬于衡邵干旱走廊湘資分水嶺核心地帶。總面積20824km2,下轄3個市轄區、6個縣、1個自治縣,代管2個縣級市。全市分屬湘江、資水、沅江和柳江流域,其中資水流域面積占全市總面積的70.8%。2019年常住人口730.24萬,地區生產總值2152.48億元。全市多年平均地表水資源量為160.60億m3,2019年降水量為1566.5mm,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為94.12%,污水處理率為94.64%。
2.2 實例計算
本研究采用2019年基礎數據,數據主要來源《湖南省統計年鑒》《湖南省水利統計年鑒》《湖南省水資源公報》《邵陽市水資源公報》《湖南省水安全戰略規劃(2020—2035年)》以及水利、生態環境等部門的基礎資料。運用所建立的指標體系和水安全指數模型,對2019年邵陽市水安全狀況進行評價,利用指標標準化值和式(4)、式(5)進行計算。邵陽市水安全評價結果見表3。

表3 邵陽市水安全評價結果
2.3 結果分析
評價結果顯示,2019年邵陽市水安全綜合指數為0.6562,處于“基本安全”狀態,反映出全市水安全形勢不太樂觀,特別是用水安全、飲水安全和涉水事務監管安全方面還存在一定的短板。具體分析如下:
a.防洪安全分指數為0.7004,處于“較安全”狀態。該指數在各分指數中排名靠前,主要是由于堤防達標率(0.8374)、山洪溝達標治理率(0.7873)指標表現較好,主要短板是水庫病險率(0.5232),原因為全市小型水庫數量眾多,建設時間較早、技術標準偏低,水庫運行存在較大安全隱患,急需加強病險水庫綜合治理,增強水庫抵御各類自然災害的能力。
b.飲水安全分指數為0.6304,處于“基本安全”狀態。其中供水安全系數(0.4220)、城市管網漏損率(0.2942)和規模化工程服務人口比例(0.2886)得分較低,原因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飲水需求不斷增大,而相應的供水工程及配套管網未及時跟進,導致供水能力相對不足,此外,城市管網明顯老化、漏損問題突出。建議加快推進規模化供水工程建設,加強供水管網維護,增強城市供水保障能力。
c.用水安全分指數為0.6043,處于“基本安全”狀態。其中萬元GDP用水量(0.5100)、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0.4957)、大中型灌區骨干工程完好率(0.4639)、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0.3872)等得分較低,反映出全市農業用水和工業用水效率水平較低,節水意識相對較弱,節水措施不夠完善,需加強各行業節水力度,提升全市整體用水效率。
d.河湖生態安全分指數為0.7163,處于“較安全”狀態。在各項分指數中表現較優,表明全市較為重視河湖生態保護和治理,且取得了初步成效。各項指標中,河湖水域空間保有率(0.5239)得分較低,下一步需嚴格落實河湖管控要求,加強水域岸線保護,提升河湖生態安全水平。
e.涉水事務監管安全分指數為0.6019,處于“基本安全”狀態。其中水利投資占財政投入比例(0.0976)得分最低,表明當地財政對水利建設重視程度不夠;水利人才結構達標率(0.4826)、重要水管理事項有效實施率(0.5107)等指標表現也較差,反映出部分縣(區)人員老化現象突出、專業性人才緊缺,監管能力相對薄弱。需進一步加大財政資金投入力度,加強人才引進和培養,提升基層監管能力和水平。
邵陽市地處湖南省西南部,屬于衡邵干旱走廊地區,水資源相對緊缺,經濟欠發達,水資源監管能力相對薄弱,評價結果“基本安全”狀態與實際情況基本相符。
3 結 語
本文基于水安全概念及內涵,聚焦影響城市水安全的核心要素,建立了包括防洪安全、飲水安全、用水安全、河湖生態安全、涉水事務監管安全的城市水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并以邵陽市為例進行評價研究。結果表明,邵陽市水安全處于“基本安全”狀態,其中飲水安全、用水安全和涉水事務監管安全方面短板突出,需加強病險水庫治理、推進規模化供水工程建設、加強各行業節水力度、強化資金和人才保障等;該指標體系能有效反映城市管理現狀,且與已有指標體系相比,指標代表性和有效性顯著增強,其評價結果與實際情況基本相符。
但該研究也存在一定問題:權重設計采用德爾菲法,存在一定主觀性;實證研究缺乏多年數據支撐,結果預警性不足。后續可結合系統動力學仿真模型,利用歷史數據開展水安全趨勢分析和預判,提高模型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