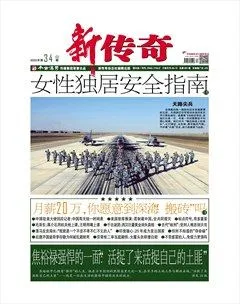住在“云端”,什么感覺
“像是來到了高山上,被云霧包圍了。”住在超高層住宅的頂層,是一種小眾選擇。這就像是居住在“云端”之上——它既有常人難以體會到的居住樂趣,也伴隨著諸如恐高、氣壓差、火災逃生困難等潛在風險。
“像是來到了高山上,被云霧包圍了。”在一個大霧天,一名住在56 層的32 歲武漢業主,這樣形容自己站在窗邊的感受。那天,待到霧氣散去,她再俯瞰遠處的東湖,像是看一個小池塘。
在中國,超高層建筑指的是高度超過100 米的民用建筑。而住在超高層住宅的頂層,是一種小眾選擇。這就像是居住在“云端”之上——它既有常人難以體會到的居住樂趣,也伴隨著諸如恐高、氣壓差、火災逃生困難等潛在風險。
自2020 年以來,國家已經連續4 次發布“限高令”,各地已有的超高層住宅或許會成為“絕唱”。那么,究竟什么樣的人會選擇住在超高層?住在超高層建筑的頂層,會是一種怎樣的體驗?人為什么會迷戀更高的地方?

陳牧南家從窗外看出去的風景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住在東莞最高住宅樓的陳牧南。他住在“東江之星”小區的50 層頂層,生活在約150米的“云端”。
可以看到別樣的風景
東莞很少有霧,但每當大霧來臨的時候,陳牧南家的窗外會變得一片空白,站在地面上的人即使抬頭,也看不到樓頂。人在這個世界上,像消失了一樣。
陳牧南說:“站在50 層向外看,窗外全是云,層次分明,感覺云離你很近。夏天的黃昏有時是紅色的,有時是黃色的。雷雨天的時候這種拉近的距離感更明顯,烏云壓得很低,雷噼里啪啦地砸在你面前,那種感覺很震撼。如果沒有讓人感到安全的門窗做壁壘,應該會感到恐懼。”
在陳牧南家,有三個房間能看到江景。他把其中一個房間拆了,改成一個小餐廳。一家人吃飯的時候,面向東江,邊看江邊吃飯的感覺很不錯,跟二三十層看到的江景不一樣。住在50 層還有一個好處,比較私密。所以,他把洗手間都換成透明玻璃了,可以一邊在浴缸里泡澡,一邊欣賞外面的風景。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樣的視野。因為隨著高度的上升,有人有恐高癥,這是一種本能。陳牧南說,前不久,有一個租客來看這里的房子,一聽是50 樓,都沒敢進來看房,覺得太高了,有點兒害怕。
高層的困境:停電、風和火災
剛搬過來的時候,陳牧南多少還是有點兒不適應。一開始坐超快速電梯,從負幾層一下子到50 層,一瞬間上到100多米,氣壓的變化讓人感到耳鳴。不過他很快就適應了。
比起氣壓差,住在高層最怕的就是電梯停電。陳牧南說,有一次,電梯因停電暫停使用一個小時。剛好是早上七點半到八點半的時候,他從50 樓一直走到1 樓后,腿都軟了。更恐怖的是,一個47 樓的業主居然點了一份外賣,那個外賣小哥硬是從1 樓一直爬了上去。
高層,風也會很大。夏天的時候,風會直接往臉上吹。陳牧南買的房子是東南朝向的,夏天的風吹起來不用空調,買一個搖椅,在陽臺上搖一搖,就能睡著。住在頂樓不同方位的人對于風的感知也各有不同,有的鄰居覺得一年四季風都很大,不敢開窗。
關于火災,住在高層的人提及便會覺得恐怖。陳牧南說,他住的小區每一戶都是精裝交付的,每一層都有一個消防水管。但如果真的發生火災,消防車也到不了那么高的樓層。不過,他覺得生活中的極端情況很少,即使住在二樓也會有意外發生,這些是個人控制不了的,也就不去想了。
在高層,“能站在盒子外看世界”
陳牧南說,其實,在都市文化中,像香港、紐約、巴黎,人們都去很高的樓上班,也住很高的樓,這是一種對身份地位的共識。“我曾經也認為去很高的地方,是一種高學歷、高收入的象征或炫耀”。
但是,陳牧南說,東莞不是這樣的,人們即便是有錢,好像也不喜歡住高層。越有錢的人越要去買別墅,住在地上接地氣。“但對我們家來說,其他樓層都被人買了,只有47 樓和50樓兩個選擇。那我為何不選頂樓呢”?
陳牧南和他的妻子都是對高處風景比較向往的。去旅游,他們一般會挑最高的酒店住。他們住過日本萬豪酒店的六十多層,在空中眺望風景的體驗讓他們感覺很好。除此之外,他也喜歡小眾的東西,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住在50 層,也是奔著這個想法去的。他覺得高層是一個小眾但又有潛力的選擇。
“住在高層讓我能夠從更高的角度去思考人生。這段時間,我總是透過小餐廳的窗戶看著東江,思緒天馬行空,這是屬于我的放空時間。我有一個很舒服的沙發,我喜歡坐在上面看窗外地上的路。這個角度給了我一個在事物框架外去看待它的思維。我看到的是全景,就好像有一種超然物外的感覺。我現在35 歲,遇到了人生困境。當我迷茫的時候總會走到窗邊眺望一下。看著夜里星星點點的燈,深吸一口氣,整個人都放松了。有時候我還會抱著孩子、躺在搖椅上搖一搖。在高層,好像能夠站在盒子外看世界。”陳牧南說道。(應受訪者要求,陳牧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