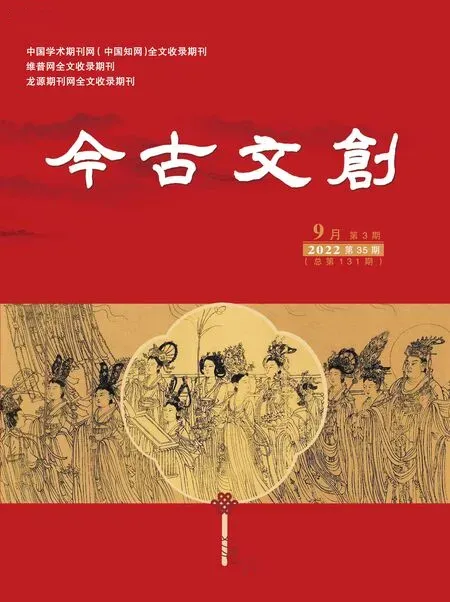論姜夔詞中 “ 幽澀 ” 之美的形成與呈現
◎趙子璇
(延安大學 陜西 延安 716000)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名高詞壇。學界對姜夔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姜夔詞本身“清剛醇雅”的藝術特征及音樂特征研究、姜夔詞建立的新的審美規范及其詞序在詞史上的意義與價值研究、對姜夔詞的評論及其反映出的具有時代意義的詞學觀念研究。歷代詞學家對姜夔詞有推崇有批評,但其詞反復被后世詞學家推為楷模加以學習或是推為范例進行批評就表明姜夔詞的創作風格自有其開創性與代表性,但總體看來,姜夔詞的藝術特征和美學價值在學術界存在被固化的趨勢。研究者大多聚焦于對其詞清空騷雅、清剛疏宕特征的分析,很少有研究者談及姜夔詞的“幽澀”,因此,對姜夔詞此種特質的分析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幽澀”之釋義
評價姜夔詞有“幽澀”特質見于譚獻《篋中詞》:“蓮生古之傷心人也。蕩氣回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譚獻,晚清詞學家,他在繼承張惠言、周濟的詞學思想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詞學體悟與時代風尚提出“柔厚說”“潛氣內轉”“一波三折”等一系列詞學主張。彼時的同光詞壇,浙西詞派學習姜夔之清空卻未注意到其幽澀,于是愈流于浮薄淺滑,譚獻“幽澀”之美的詞學主張正是針對其時浙西詞派浮薄空疏之弊病提出的。如《篋中詞》中所說:“浙派為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錄乾隆以來,詞慎取之。”
要了解“幽澀”一詞的意義,則要分別了解“幽”與“澀”二字的意義。《說文》:“幽,隱也。”段玉裁注:“隱,蔽也。”《爾雅·釋言》:“幽,深也。”《玉篇》:“幽,深遠也”“幽,微也”“幽,不明也”。《說文解字詁林·續編》:“《說文》無‘澀’字,《止部》:‘澀,不滑也。從四止,色立切。’即‘澀’字。”可見“幽澀”一詞指一種不流于俗的隱匿而深微的美感。遲寶東在《譚獻的詞學思想》中總結道:“譚獻所謂‘幽澀’指的就是詞中情思所表現出的一種含蓄蘊藉、幽微深隱、拗折盤旋的姿態之美。”
此外,還應厘清“幽澀”與“清空”“質實”的關系,唯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幽澀”之義。邱世友在《馮煦的詞論》一文中認為姜夔詞的清空與幽澀本是矛盾的,但卻統一著,白石詞的高妙便在于他的詞作是這兩種詞學特征矛盾而統一的存在。其實,幽澀與清空并不矛盾,因為清空與質實相對。張炎說:“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味。”質實是由于堆垛實字、辭句研練所致的文氣不暢,而質實和前文定義的幽澀卻并無關系,因為幽澀并不意味著文字堆砌與辭句過分晦澀,而是情感深沉蘊藉、筆致曲折有韻味。因此,幽澀應該是清空更深一層的呈現。清空是重事物的神理而不重事物自身,頗有些像《詩人玉屑》中說的“言用勿言體”“言其用而不言其名”,如描繪月亮是寫出月亮的精神情態,冷月的重點不在月而在冷,“冷”又是詞人心境的外化,這種感情表現的“一波三折”再加上詞人填詞時的深婉筆法,清空容易走向幽澀的境界。
二、“幽澀”之形成
姜夔詞“幽澀”的形成是復雜的,涉及他在詞學上的繼承與創新,也涉及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作為詞人的姜夔有著對時代、文字與生命、情感的敏感,才不落窠臼,終為南宋一大家。
(一)江西詩風的陶染
南宋一代,江西詩派衣被甚廣。“楊萬里、陸游皆傳山谷一脈,范成大晚學蘇、黃,姜夔則初學山谷,晚年則否。”可見江西詩派理論對姜夔詞風的形成有著較深的影響力。江西詩派詩人受黃庭堅影響深遠,黃詩章法回旋曲折,務去陳言,力撰硬語且聲律奇峭,姜夔學習江西詩派重思理、寄托、新意的內蘊,詞之結構深復,詞意轉折頻繁,甚多熔鑄典故。葉嘉瑩在《唐宋詞十七講》中說:“把江西詩派作詩的方法用到詞里邊去的,就是姜白石。”吳熊和《唐宋詞通論》也說:“以江西詩風入詞,合黃、陳與溫、韋、柳、周為一體,這種作法就是姜夔的首創,并使他的詞形成和加強了騷雅的特點。”
論“章法回環曲折”,姜夔詞多有曲折頓宕的結構。例如《醉吟商小品》:“又正是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鞍去。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春歸時節,細柳千縷呈現暗黃色,此時此景讓詞人回憶起那年分別地也是春歸時節細柳暗黃的暮鴉啼處,像是“剪輯”進來一組回憶。“夢逐金鞍去”就完全落到人與情的事情上,言女子的魂夢相隨,“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又轉為男子視角,臨行前要女子莫再叮嚀,所有情意寓于琵琶聲中。全詞三十字,視角轉折三次,結構多轉折可見一斑。又如《暗香》:“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何遜而今”是由往昔到如今,“但怪得”又是一個轉折,寫人衰老不堪對花而花卻香氣襲人,在與梅花有關的今昔對比中表現感情,今與昔的轉換造成了曲折的結構。《琵琶仙》也極見文字回環曲折之功,用“又還是”“奈愁里”“想見”等詞回環勾連,形成今昔對比、情景錯落的深復結構。
論熔鑄典故而務去陳言,姜夔善于巧妙化用典故,頗有“點鐵成金”的意味。姜夔在《白石道人詩說》中說:“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詞人也很好地實踐了自己的理論,比如《浣溪沙》:“剪燈心事峭寒時”暗用“何當共剪西窗燭”典故,《鷓鴣天》:“知是凌波縹緲身”化用《洛神賦》中語。《齊天樂》:“豳詩漫與”連著化用《詩經·豳風·七月》與杜甫的“老去詩篇渾漫與”。《永遇樂·次韻辛克清先生》更是全詞用了十一個典故但毫無堆砌艱澀之感,一首詞用如此多典故,這種互文性使讀者對詞人情感有更深一層的揣摩,也使詞作本身有了更豐富的內蘊。
論“拗折”而力撰硬語,《凄涼犯·綠楊巷陌》一詞便很好體現了江西詩派用“拗折”句對姜夔詞風“幽澀”的影響,龍榆生《詞曲概論》分析此詞聲韻:“在整個上片中沒有一個平收的句子,把噴薄的語氣,運用逼側短促的入聲韻盡情發泄。后片雖然用了兩個平收的句子(即歌、約),把緊促的情感調節一下;到結尾再用一連七仄的拗句,顯示生硬峭拔的情調。”
綜上,在江西詩派的影響下,姜夔詞的回環婉曲、用典天然、拗折不俗皆作用于詞中情感表達的幽澀。
(二)詞體語言的創新
詩詞所使用的語言是語言中最要求精約、字句凝練的語言,要通過極少的詞句去表現內蘊豐富的情與事,所以要追求更加豐富的藝術手法。修辭的作用不僅在于把要表達的事物形象可感化,也在于使文字抽象藝術化。詞人運用修辭使得詞語與詞語之間形成詩意的搭配,這種搭配常常表現出作者瞬間而私人的感覺,語詞之間顯出更詩意的跳躍,雖不直接表達意思,但往往極富新意,澀且不俗,如現代詩中不受制于客觀事物的秩序而用別種語法或語義去表達詩人獨特感受的詩行。
如《探春慢》中的“梅花零亂春夜”在白石筆下,“梅花”與“春夜”之間,有“零亂”一詞就顯得尤其有新意——梅花零亂使得春夜零亂,最終歸于詞人心緒零亂,但這樣的零亂沒有直接被描繪出來,而是使用移情、比擬等修辭手法使詞句形成“陌生化”的感覺,回避正面陳述,但這更推動了詩意的表達,更富渲染力。又如《念奴嬌·鬧紅一舸》:“翠葉吹涼,玉容銷酒,更灑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玉容銷酒”用擬人的手法形容荷花紅暈的顏色,更妙的是寫荷香,不寫人嗅到香氣,卻寫“冷香飛上詩句”,極為俊逸巧妙,富有意趣。這種“隔”一層比直接敘述更富情致。《暗香》中的“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揚州慢》中的“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中的“香冷”“寒碧”“吹寒”“冷月”都采用通感手法,突破語言局限,極富藝術感染力。姜夔寫“冷”的感覺既有視覺上的“碧”,也有嗅覺上的“香”,更可貴的是這些句子都是有詞人感受的先后順序的,竹外疏花先是帶來“香”,靠近水面有寒氣,“香”就慢慢冷卻,而這冷因“碧”這種冷色調顯得更冷。“吹寒”,“冷”的時間被“吹”拉長而成為“寒”,夜雪初霽后先感受到冷,目及波心的水中月,自然是“冷月無聲”。《卜算子·吏部梅花八詠》中的“花下鋪氈把一杯,緩飲春風影”“惆悵西村一塢春”,《驀山溪·題錢氏溪月》中的“一亭寂寞”,《漢宮春·次韻稼軒》中的“秋風一榻”等皆獨具新意,在姜夔的筆下,春風有影,影能入酒而飲,春的量詞是“塢”,寂寞的量詞為“亭”,這些句子是符合語法規則的,但不是事物之間正常的搭配,這需要詞人對字詞進行創新性推敲,更需要詞人的情感附于事物上,才使景上染情之色彩,表面上無理、抽象,但細細品味便覺很貼近個人的直接感受。語詞搭配上表現出新穎與陌生,使文字抽象化、藝術化,以致營造出詩意的空間,不俗的語言體現出的是詞人情感表達的私人化,詞人將物“著我之色彩”,語詞上的雅澀自然會帶來情感表達的幽澀,此種美學價值不可忽視。
(三)個人情感的冷卻
徐復觀在《中國文學精神》中《釋詩的溫柔敦厚》一篇中說:“‘溫柔敦厚’都是指詩人流注于詩中的感情來說的……不遠不近的適當時間距離的感情,是不太熱不太冷的溫的感情,這正是創作詩的基盤感情。因為此時可把太熱的感情,加以意識地或不意識地反省,在反省中把握住自己的感情,條理著自己的感情。”而敦厚則是“富于深度、富有遠意的感情,也可以說是有多層次,乃至是有無限層次的感情。”如此看來,姜夔的詞可謂“溫柔敦厚”,他把無限復雜而紛涌的感情用理性“條理”著,然漸理漸深,逐漸“冷卻”,以至于詞人用情極深卻由于理性的冷卻而不易被讀者看出,就形成了情深蘊藉的幽澀感。
王國維批評姜夔詞“隔”,歷來有很多的解讀,有的認為姜夔有人格狷潔的士大夫精神,而王國維時代是士大夫精神沒落的時代,自然會以“矯飾”批評他,有的認為姜夔“熱中”,寫詞時隱藏真我逃避感情,少用正面表達而使用“私立象征”使詞意顯得曖昧,但王國維的“不隔”卻要求詩人自然流露與詩心純凈……諸類解釋都有合理性。然《白石道人詩說》中強調詩之高妙,如礙而實通的理高妙、寫出幽微的想高妙等都表明姜夔其實是有意營造“幽澀”感的,這大概是姜夔自人生體會與時代美學而得出的創作經驗。白石一介布衣寄人籬下,才高而終究未能科舉進身,他是自卑的,但人在排解自卑時又常常體現為自尊,所以他對自己的諸多感受不愿直抒,因此很多詞作表現得有“隱衷”而不濫情。“由人生境界懸隔而來的不易懂,實包含了透徹骨髓臟腑的不隔,而不只是普通所說的不隔。”姜夔詞所謂的“隔”很大一部分是在他沉浸于人生的痛苦卻又在無意識地逃避痛苦的矛盾過程中形成的,這種矛盾心態使他認為“寫出幽微”的詞是節制而深刻的,是高層次的美學表現,而宋代士大夫主流審美也正表現出精致、內趨的性格,這明明是透徹骨髓臟腑的不隔。如《淡黃柳》一詞看似是詠柳詞,但詞中身世漂泊之感和家國之哀結合在一起,詞人面對空城蕭條,角聲嗚咽更覺衣物單薄,又回憶起合肥戀情,雖有“鵝黃嫩綠”,但已“看盡”,面對凄涼景無心飲酒,但“怕”字又表明趁春強樂之意,即便如此春也會一瞬而過只留下“池塘自碧”,多種情感凝結卻全詞寓情于景,落筆虛處卻足夠深沉矜持。
三、“幽澀”之呈現
姜夔詞力求語言不落俗套、結構回環婉曲,讀起來有雅澀的特點,表達上的澀感加深了詞人情感表現的幽深,姜夔的“幽澀”得以成為一個整體——情感之幽造成語言之澀,語言之澀又加深了情感之幽。姜夔詞的幽澀之美最終呈現為情感表現的雜糅深遠,這些情感表達的雜糅深遠在詞中經過詞人理性地冷卻表現出“一波三折”的情態。
閱讀姜夔詞,總有縹緲復雜的體會,一首詞中姜夔所要表達的不是單一的情感,而是將各種情感糾結于一處,理性地用意象絲絲抒發出來。他寫國事興亡常用比興寄托,借意象或典故手法完成藝術化處理,使詞意耐人尋味。寫戀情時也在寫身世,感情更顯深沉,所以姜夔感懷身世之作較多,因為在所有題材的作品中他都可以抒發身世之感。如《點絳唇·丁未冬過吳松作》雖文字簡省,但詞人與陸天隨、寒士與高士、清苦與超然等意味相互交織,悲愴藏于景物中卻付之言外,有避世之意,通過雁燕意象,自況漂泊無定,“清苦”“商略”寫山雨欲來的陰沉黃昏,憑欄懷古覺往事不可追含傷今之情,雜糅的“哀感”用諸多意象一波三折地表達出來,傷懷殊深。
姜夔還總在詞的最后化情為景作結,如《鷓鴣天·正月十一日觀燈》結拍“沙河塘上春寒淺,看了游人緩緩歸”表現觀燈之落寞,《解連環》結拍“念唯有、夜來皓月,照伊自睡”表現詞人用情之深,其實,不論是此處,還是相思血沁綠筠枝、淮南皓月冷千山等情景,皆表現用情之深遠,但深情皆寓于典中景中便是一波三折的呈現,這種“一波三折”也可看作《白石道人詩說》中的“語貴含蓄”。詞中之“景”如影視中的一組“空鏡”,具有暗示、隱喻、引起聯想的藝術效果,由此所表現出的感情,深刻而不憤不激,含蓄不盡,深具“幽澀”高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