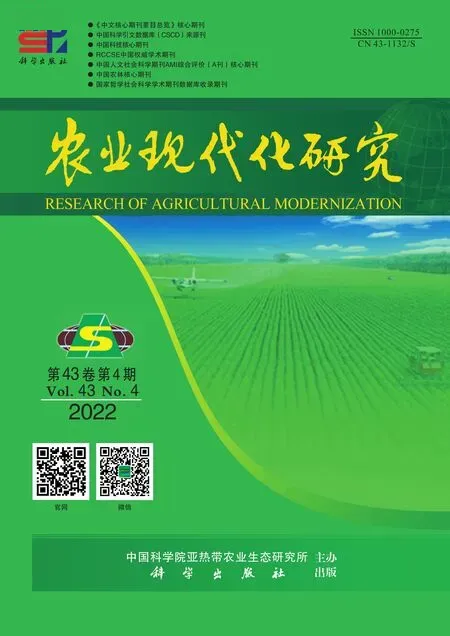農業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運行機制與實施路徑
劉某承,蘇伯儒, ,閔慶文, *,李文華
(1.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
從世界各國現代化歷程來看,“鄉村衰落”是伴隨城市發展的普遍現象[1],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城鄉差距擴大、鄉村衰落也是我國當前在快速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問題[2]。2017年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開啟了全面建設現代化鄉村的新征程。如何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具有重要意義[3]。中國5 000多年的游牧和農耕歷史衍生出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勞動人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發展并世代傳承了具有豐富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完善的傳統知識與技術體系、獨特的生態與文化景觀的農業生產系統[4],可為民族文化豐富、生態脆弱且重要、經濟落后地區的鄉村振興提供經驗和智慧。
已有研究表明,導致鄉村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快速城鎮化、人口外遷、產業結構單一和農村環境污染等[5-7]。眾多國內外研究者針對如何實現鄉村振興展開了一系列研究,如Zhou等[8]分析了土地整治助力鄉村文化、人才、生態、產業和組織振興的驅動機制;Yang等[9]研究探討了鄉村旅游對農村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Xue等[10]研究表明,可持續的農村教育對于鄉村振興具有關鍵作用。
現階段,關于如何實現鄉村振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工程等方面。同時,大量研究表明,農業文化遺產在遺產地對鄉村振興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傅志強和黃璜[11]研究表明,農業文化遺產可為第一產業、農產品加工業和旅游業有機融合發展提供良好基礎;陳茜[12]從分布地域、蘊含價值等方面分析了農業文化遺產與鄉村振興的緊密聯系;閔慶文和曹幸穗[2]認為農業文化遺產蘊含的生物、技術、文化“基因”對于鄉村振興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農業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的運行機制如何,農業文化遺產蘊含的資源如何助力鄉村振興尚待進一步探討。鑒于此,本文基于農業文化遺產資源稟賦,分析農業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的資源基礎;根據農業文化遺產蘊含的獨特資源,探討其助力鄉村振興的運行機制,明確其助力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研究結果可以為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振興與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
1 農業文化遺產及其保護途徑
200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起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保護倡議,旨在保護和傳承具有突出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等多種功能價值的傳統農業系統及其景觀、生物多樣性、知識和文化[13]。
我國是最早參與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工作的國家之一,2005年“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 被FAO列為首批GIAHS保護項目,現擁有18項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數量位居各國之首。同時,我國于2012年在全球率先開展國家級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挖掘與保護工作,截至目前農業農村部共發布6批13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分布在153個縣(市、區)。
復合性、活態性和戰略性是農業文化遺產的三大特性[14]。“動態保護”是基于農業文化遺產特性的內在要求。動態保護有三層含義,一是發展與保護結合,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不能像古建筑一樣封閉式保護,而應當促進遺產地居民與外界的交流,通過發展生態旅游等產業,避免遺產地貧困狀況加劇;二是多方參與,當地農戶既沒有獨立保護農業文化遺產的能力,也沒有獨立保護的積極性,政府、企業、社區等應當共同制定多方參與機制。三是變中求穩,在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不能變化過快,不能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完全摒棄原有的農耕方式與民俗信仰,遺產地在發展產業時不能忘記保護的初衷,避免遺產地徹底淪為商業景區。
2 農業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的資源基礎
農業文化遺產是一種“活”的遺產,現如今依然發揮農業生產等功能[15]。截至目前,23個國家和地區的65項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系統以可持續方式供應多種產品和服務,為億萬小農保障糧食和生計安全[16-17]。
2.1 農業文化遺產系統蘊含鄉村振興所需的生物資源
古代先民們在農業文化遺產上千年的發展歷史中選育出了大批質量上乘、品質極佳的優良作物,與現代技術融合后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如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中曾種植過20多種傳統水稻品種,生長有6種鯉魚,5種其他魚類,保育有較高的水稻品種多樣性與田魚遺傳多樣性[18],其農田邊界保育有較高植物多樣性及與之相共生的AMF群落[19]。浙江紹興會稽山古香榧群的香榧籽油能選擇性降低油脂,具有極高的藥用價值,其假種皮也是高級芳香油的極佳原材料[20]。
我國部分地區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間存在嚴重的“爭地矛盾”,農業文化遺產具有豐富的農作物品種,在為人類提供高產優質的糧食作物的同時,還提供了多種經濟作物與工業原料,不僅能保障遺產地糧食安全,還能促進當地第一產業全面發展。
2.2 農業文化遺產系統蘊含鄉村振興所需的技術資源
農業文化遺產所蘊含的適應當地獨特自然和社會條件的傳統栽培技術、種植模式和水土資源管理方法在千百年的人工選擇中長盛不衰,通過改善系統內部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達到提升農產品質量與生態系統功能的目的。
江西崇義客家梯田的村民常用間種套作、農田冬翻和燈火滅蟲等古老方法防治農田害蟲,肥料主要為人畜糞尿、火土灰和枯餅等農家有機肥,部分地區還施用牛骨粉,秋收后雞、鴨等家禽散養在田間,其糞便與秸稈共同發酵,增強土壤肥力[21],還提升了稻谷內在品質[22]。四川郫都林盤農耕文化系統的水旱輪作制度是流傳千年的傳統耕種制度,其主要分為傳統二元輪作(稻—菜)模式和傳統三元(稻—菜—菜)輪作模式,這兩種模式的地下水補給量分別為539.1 mm和469.2 mm,遠高于現代三元(菜—菜—菜)輪作模式(177.5 mm)[23]。此外,還有浙江慶元香菇文化系統蘊含的“剁花法”香菇種植技術、內蒙古敖漢旱作農業系統的旱作農業技術、福建安溪鐵觀音茶文化系統孕育的烏龍茶制作技術等眾多古代先民們遺留下來的農業技術瑰寶。
現代耕作技術通過長時間連續耕種和無節制使用農藥化肥來提高農作物產量,這不僅會加劇農田水土流失,還會導致農田肥力急劇下降,最終陷入“土壤肥力越喂越貧”這一惡性循環。遺產地農戶在上千年的實踐經驗中,逐漸總結出多種環境友好型耕作方式,使農業文化遺產在保證一定農作物產量的同時,可以盡量減少對耕地未來生產潛力的透支。
2.3 農業文化遺產系統蘊含鄉村振興所需的生態資源
現代農業的集約化發展使得農業面源污染等生態問題愈發嚴重[24]。已有研究表明,農業文化遺產獨特的景觀格局與水土資源利用模式,使其具有更高的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能力。如浙江紹興會稽山古香榧群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86.14萬元/(hm2·a),遠高于我國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平均水平[20]。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作為一個有機生態整體,其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遠高于桑園生態系統和魚塘生態系統提供的價值之和[25]。
還有研究者探析了農業文化遺產生態系統服務供給水平較高的生態學機理。如稻魚共生系統中魚的排泄物會降低甲烷排放[26];由于草魚的捕食行為,稻飛虱數量減少45%,水稻根部的紋枯病菌會被田魚食用,從而降低紋枯病發生概率[27];而且魚的糞便中N素形態主要為銨態氮,易于水稻吸收[26],可以減少氮肥施用量。
國外關于農業文化遺產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位于南美洲的古臺田農業系統能提供眾多獨特的生態系統服務:一是氣候調節服務,有效保護農作物免受夜間霜凍;二是養分持留服務,古臺田農業系統的部分土壤長期或間歇性位于水面之下,能提高磷的可用性[28]。
同時,由于現代農作物品種單一化導致了農田生物多樣性銳減[29],病蟲害加劇[30]等生態問題,而農業文化遺產地被喻為中國良種活態基因庫,保育了豐富的農業生物多樣性,有效解決了這些問題。現代農業科技正高速發展,但農業文化遺產中流傳千年的生態學機理仍值得去探索。
2.4 農業文化遺產系統蘊含鄉村振興所需的文化資源
農業文化遺產為鄉村振興發展保留了深厚的文化積淀,包括語言、集體記憶、價值觀、社會組織、民俗與節慶、傳統知識與技術、信仰與禁忌等,反映在契合當地氣候、環境與資源條件的建筑文化、飲食文化和服飾文化,符合當地自然條件反映生物生長物候節律的農事歷法,能夠推動遺產地資源可持續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生計方式、理念和行為模式,以及其他協助人類形塑集體記憶的物質和非物質遺存等[31]。
鄉村民俗文化是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農業文化遺產上千年的發展中,誕生出了眾多人民喜聞樂見的民俗傳統、博大精深的農耕文化和深邃飽滿的精神產品[32]。四川郫都林盤農耕文化系統位于四川盆地西緣是川西農耕文化的發源地,緊貼“胡煥庸線”及羌、藏與漢族的民族交融線。據郫都黨史地方志辦公室編著的《郫縣民俗集萃》顯示,郫都共保留有74條日常生活民俗、128條經濟民俗、117條民間信仰、176條民間文藝與游樂和23條民間科技等。
3 農業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的運行機制
農業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包括農業生態系統維持食物生產韌性的可持續性,農業多功能維持當地居民生計安全的可持續性,集體記憶傳承集體價值觀念并穩定社會組織結構的可持續性,以及獨特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維持系統穩定的可持續性。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遺產地可以充分利用農業文化遺產的生物資源、技術資源、生態資源和文化資源,通過產品增值、鄉村旅游實現產業振興、人才振興與生態振興,通過文化驅動實現文化振興與組織振興(圖1)。
3.1 產品增值驅動
農業文化遺產所蘊含的獨特的生物資源以及“天人合一”的綠色生產理念,能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高質量”和“多元化”需求,這為遺產地產品的品牌化和高端化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
農業文化遺產具有突出的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價值的獨特品種資源,例如云南紅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統的紅米,內蒙古敖漢旱作農業系統的小米,以及相關茶葉、香菇、楊梅等經濟作物,是農業文化遺產地通過產品增值驅動鄉村振興的基礎。遺產地的政府、企業和農戶需要注意收集、復壯和推廣這些傳統品種資源,保護優勢品種資源;通過體現遺產地產品自然特色、地域特色、加工工藝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的品牌和營銷規劃,塑造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遺產地品牌;同時探索相關農產品的資源整合以及后續加工產品的開發,延伸產業鏈。
遺產地獨特產品的價值提升不僅能驅動遺產地的產業振興,還能幫助遺產地實現人才振興。研究表明,鄉村人口向城鎮遷移并不單純因為收入差距的問題,即使在同等收入水平下,由于城鎮地區發展前景更好,遺產地農戶也可能會離開家鄉去更發達的城市謀生。因此遺產地的產業振興能幫助人們看到發展的機會,進而吸引具備一定知識技能的高素質人才回鄉創業就業,為鄉村振興提供人才保障。同時,農產品增值能幫助遺產地轉變產業結構,摒棄污染密集型產業與高耗能產業,保護遺產地的青山綠水,進而實現生態振興。
3.2 鄉村旅游驅動
產業單一化是鄉村經濟衰敗的重要原因。我國的眾多農業文化遺產大多分布在傳統農業地區,具有生態良好、環境優美、民風淳樸、文化多樣等特點。同時,除了農業文化遺產系統本身之外,遺產地還具有其他諸如山水、技藝、民俗、節慶等物質形態或非物質形態的豐富的旅游資源,受到了很多旅游者的青睞。遺產地可憑借其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推出眾多極具特色的旅游產品,開發集休閑度假、生態保健、文化感知和商務談判為一體的旅游產業,同時積極宣傳當地優質農產品和文化產品,推動遺產地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吸引優秀青年人才回鄉就業。
一般而言,農業文化遺產地可以通過三種鄉村旅游發展模式來驅動鄉村振興。一是農業景觀型—資源帶動市場模式。多數農業文化遺產都具有一定的景觀和觀賞價值。其發展的關鍵在于資源,需要在自然景觀資源的基礎上挖掘人文景觀資源,通過主體資源與輔助資源、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的配合,構成持續機制。江蘇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集森林、水域和農田為一體,其獨特的垛田景觀與豐富的景觀元素吸引了眾多海內外游客前來觀賞游玩。旅游業極大地促進了興化當地的經濟發展,2013年間,超過100萬游客前來觀光游覽,累計收入4.2億元,比2012年增長7.7%,同時新增300個就業崗位[33]。
二是農業技術型—市場帶動資源模式。農業文化遺產系統本身所蘊含的適應性技術和傳統知識本身就是一種十分寶貴的旅游資源,但其發展的關鍵在于市場,要打造研學市場,促使“到處看看、隨便聽聽”向“學習知識、體驗文化”的轉型。如浙江青田歸國華僑楊小愛女士研發農遺餐,建立農遺主題酒店,打造方山谷農遺文化園,通過接待小學生割稻、插秧和放魚苗,帶領他們走進農遺,了解農遺,感受稻魚共生系統的魅力。這類模式不僅帶動了當地旅游業發展,還能吸引企業家、海外華僑、優秀青年等回歸家鄉,建設家鄉,促進了遺產地的人才振興。
三是農業遺址型—節事活動帶動模式。一些農業文化遺產地存在一些早期的農業遺址,具有較高的歷史學價值。其發展的關鍵在于節事創意,通過深挖地方文脈,將活態的展示形式與靜態的遺址資源相結合,鼓勵社區農戶參與。云南紅河通過當地文化產業繁榮帶動旅游業發展,依托哈尼梯田流傳千年的歷史文化,推出了一批與遺產地“土司文化”和“稻作文化”等緊密聯系的文化節日,打造了以節事活動為主體的旅游路線。
但作為一種新型的旅游資源, 農業文化遺產還具有脆弱性和瀕危性的特點,其文化傳承還存在傳統與現代的背離、文化傳承的代際失衡等問題。旅游開發是一把雙刃劍,在推進農業文化遺產的鄉村旅游中應注意文化傳承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融合,使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文化得以正常傳承和發展。
3.3 農耕文化驅動
文化多樣性保護是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點。農業文化遺產的文化積淀有助于了解和繼承歷史記憶,保存傳統知識和技術,傳承鄉土集體價值觀,促進民眾的文化自覺;有助于保護鄉村文化的多樣性,進而使其各項功能良好發揮;有助于有效保存文化資源,為休閑農業、鄉村旅游和農業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資源基礎。
農業文化遺產蘊含的優秀傳統文化可傳承鄉風文明,促進鄉村治理,進而驅動遺產地鄉村振興。中國農民的主要形態是以小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馬克思將小農的特點概括為安于現狀、聽天由命、平均意識濃厚等[34]。小農對市場波動與自然災害的抵抗能力較弱,致使其看待事物難免有局限性。現代的鄉村管理方式可能難以達到“自治、法治、德治”的目標。然而,農業文化遺產蘊含的鄉風文化弘揚真善美,傳遞正能量,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度契合,提倡村民尊老愛幼,誠信友善,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識與道德意識,在鄉村管理中因勢利導、順勢而為。部分遺產地的一些古老村規仍然流傳至今,在基層管理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如云南紅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統的“刻木分水”制度,有效解決了農戶的用水糾紛。分水時,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牽頭,組織大家商議好每戶的用水量,然后再根據用水量在堅硬耐用的橫木上刻下凹槽,將其放在分水口處,開口寬則分到的水多,反之則分到的少,村里還會專門安排“趕溝人”巡視分水渠,保證渠道暢通。
4 農業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的路徑
目前,我國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所在地具有一些顯著特點:基礎設施薄弱、經濟發展落后;生物資源豐富、生態系統脆弱;傳統知識豐厚、技術體系完善;文化資源富集、鄉村景觀優美;人口數量較多、人才資源短缺。農業文化遺產地應當針對上述特點,充分利用資源優勢與“后發”優勢,實現“五個振興”。
4.1 推進三產融合發展
實現遺產地產業振興,促進當地一二三產業融合是關鍵。遺產地在產業融合發展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應將農業文化遺產生物、技術、生態和文化四大資源,與現代技術手段、先進營銷理念和網絡輿論宣傳等有效結合,因地制宜構筑遺產地獨有產業體系,延長農產品價值鏈條,增加農產品附加價值,幫助農民實現生活富裕。
江蘇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融合其資源稟賦與人文歷史,憑借遺產地生態環境優良、文化資源豐富等優勢,打造“天下第一垛”鄉村生態旅游示范區,以生態旅游為契機,大力宣傳興化龍香芋、興化香蔥等生態農產品,開發垛上農民畫等文旅產品,積極推動遺產地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福建尤溪聯合梯田發揮萬畝梯田、萬畝果園、萬畝竹林資源優勢,著力發展食用菌、優質稻、竹產品等優質產業,建立“聯合梯田”品牌體系,與企業聯合推出“食米”文創品牌、“農旅優品”系列品牌等,助力當地產業振興。
4.2 積累優秀人力資本
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可為鄉村振興積累人力資本,鄉村振興可為遺產保護提供政策便利。遺產地應以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為契機,鼓勵年輕人留鄉創業,以故鄉情懷為紐帶,吸引企業家、海外華僑、優秀青年等回歸家鄉,建設家鄉,在保護農業文化遺產的同時實現鄉村振興。實施人才振興的重要路徑是提高農民謀生技能,遺產地可培養農遺技藝傳承人,在保護農業文化遺產的同時,增加了村民的謀生手段。
2017年返鄉大學生劉海慶在內蒙古敖漢旗成立了小米生態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一方面帶領當地農民創業致富,另一方面摸索如何保護敖漢旱作農業系統,他還帶領合作社社員在村內舉辦大型文化活動,喚醒當地民眾對農業文化遺產的文化記憶。除此之外,青田縣歸國華僑金岳品,紅河縣帶領村民創業的郭武六等都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
4.3 促進農耕文化繁榮
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保障,對于農業文化遺產包含的鄉村民俗文化,應秉著揚棄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保留在基層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村規民約,摒棄陳規陋習,幫助實現鄉風文明,助力鄉村治理新體系的建設。隨著現代社會高速發展,一些傳統民俗文化正逐漸流失,遺產地可將傳統農耕文化保護與鄉村文化振興相結合,通過發展鄉村文化旅游宣揚農業文化遺產傳承的優良農耕文化,同時喚醒村民們心中的文化記憶,引導村民向善向美,助力鄉村文化振興。
四川郫都林盤農耕系統蘊含的傳統農耕文化形成了血緣—親緣—地緣的差序格局,這種由血緣和親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逐漸演變成傳統社會組織,這些組織自成體系,維持社會生產穩定與社會安全穩定,在文化傳承與教化上有著明顯的優勢和當代價值。同時,川西平原作為東西移民的交融地,東西移民帶著各自家鄉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習俗匯聚于此,共同融入巴蜀文化中,創造了當地的文化繁榮。
4.4 保護良好生態環境
在構建新經濟發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傳統高耗能產業將會被逐漸淘汰,綠色產業具有廣闊發展前景。遺產地應牢牢把握后發優勢,將農業文化遺產的傳統耕作技術、水土資源利用模式與現代農業科技相結合,發展具有農遺特色的生態農業,在為人類提供高產優質農產品的同時,能有效保護遺產地生態環境與生態系統功能,美化鄉村生活環境。2013年以來,貴州省黔東南州從江縣建立3.8萬畝稻—魚—鴨養殖示范點,舉辦稻田養魚、養鴨技術培訓,引導村民合理開挖漁溝、種植稻谷、施用有機肥。建立綠色立體病蟲害生物防治體系,科學掛放誘蟲板,提升稻魚鴨產品品質。同時,充分利用傳統田魚苗培育資源,增加傳統稻魚鴨養殖過程中的科技含量,提高魚苗的成活率
農業文化遺產大多處于偏遠閉塞區域,生態環境良好,生態資產豐厚,生態系統服務供給水平較高。遺產地可嘗試與周邊地區建立區域生態補償基金,在為周邊地區提供大量生態系統服務的同時,獲取一定的經濟報酬。然而,關于農業文化遺產生態系統服務評估的研究較少,尚沒有一套針對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評估體系,農業文化遺產蘊含的生態價值仍不明晰,這使得在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時,缺少理論依據。
4.5 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
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是實現組織振興的重要途徑。基層黨組織擔負著教育黨員、管理黨員和監督黨員的職責,是組織群眾、凝聚群眾和服務群眾的重要力量。2018年1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要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成堅強戰斗堡壘。能否建立健全基層黨組織,關系到鄉村振興戰略能否成功實施。
在建立健全基層黨組織的同時,要充分發揮傳統社會治理的積極因素,堅持法治、德治、村民自治相結合的治理結構,倡導農業文化遺產中利用行之有效的鄉規民約,構建新型鄉村社會治理體制。貴州省黔東南州從江縣加榜鄉的“垃圾銀行”制度屬于基層自治的典型范例,對于一些原先亂丟亂棄的垃圾,村民都按照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進行分類,村里會派專人上門收取這些垃圾并向村民支付費用,這一基層管理制度有效扭轉了垃圾亂扔現象。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5.1 結論
農業文化遺產對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遺產地通過農產品深加工、綠色食品認證、塑造遺產地品牌等方式延長農產品價值鏈,通過構建農業景觀型、技術型、遺址型旅游發展第三產業,進而實現遺產地三產融合發展、高耗能產業轉型與人才積極回流,最終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和生態振興;同時,遺產地可通過傳承鄉風文明、保護農耕文化多樣性等方式,促進鄉村黨組織建設與新型治理體系的構建,最終實現鄉村文化振興和組織振興。
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產業振興是基礎,人才振興是關鍵,文化振興是靈魂,生態振興是支撐,組織振興是保障。農業文化遺產作為一座生物、文化、技術“基因庫”,憑借其傳承千年的資源稟賦,可以有力推動遺產地的文化傳承、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最終建立起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現代化農村,并為世界農業農村的振興工作貢獻中國智慧。
5.2 政策啟示
1)加強農業文化遺產價值評估研究。農業文化遺產價值評估研究分為價值體系構建與評估方法研究。在價值體系構建方面,應緊扣農業文化遺產的復合性、活態性和戰略性等特點[14],發掘核心價值,建立一套統一有效的價值體系;在評估方法研究方面,應充分借鑒業已形成的自然資源資產價值評估方法、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方法,著力解決評估結果“虛高”等問題,幫助人們客觀認知農業文化遺產價值。
2)建立農業文化遺產地生態補償機制。過去我國區域間生態補償標準主要通過協商博弈[37]、受償意愿[38]等確定,缺乏生態學依據。應加強生態系統服務供給—流動—消費聯級模式在生態補償實踐中的應用,加強生態補償機理研究,探尋補償標準、補償方式對生態補償效益的影響,積極探索多元長效補償機制,架起從“綠水青山”通往“金山銀山”的橋梁,為鄉村振興與農業文化遺產保護提供資金支持,促進遺產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3)實施農業文化遺產鄉村振興系列工程。實施農業文化遺產的文化振興工程,以傳統農業文化保護與傳承為重點開展農村生態文化建設,強調社區居民在文化保護中的作用,提高民眾的文化自覺;注重文化適應,注意保護特定的、對區域可持續性和社區發展有益的傳統文化和社會組織方式。實施農業文化遺產的生態振興工程,總結并推廣農業文化遺產系統在生態關系調整、系統結構功能整合等“軟”關系方面的微妙處理,充分發揮農田、草地、水域、森林、濕地等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同時避免一些負面效應的產生,如面源污染、溫室氣體排放和農藥化肥的過量使用等。實施農業文化遺產的產業振興工程,在保護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農業文化遺產獨特的品種資源、文化資源和景觀資源,將生態環境保護與綠色農業發展有機結合,將農業文化宣傳展示與休閑農業發展有機結合,打造農業文化遺產的獨特品牌,有效帶動遺產地農民的就業增收,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4)實施農業文化遺產振興鄉村的示范工程。根據區域和類型分布,總結農業文化遺產振興鄉村發展的典型模式;從區域優勢、成本效益、參與程度等角度,分析各種模式的適用性與可推廣性;引入新科技提升傳統農作技術和農作模式,推廣以低碳、循環、綠色為核心的高效生態農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