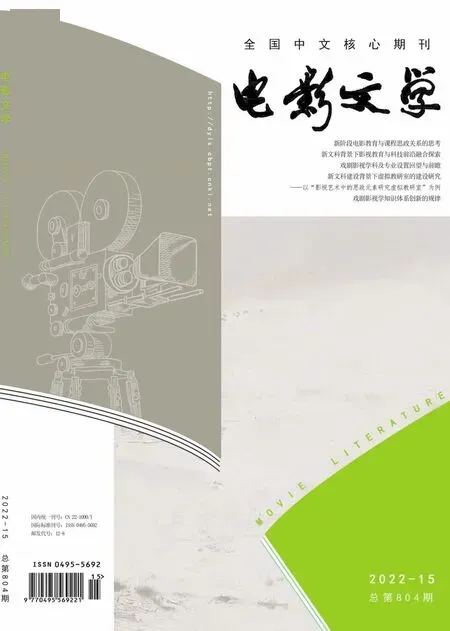楊荔鈉電影的個體關注與詩意生成
王 樾
(山西應用科技學院文化傳媒學院,山西 太原 030062)
楊荔鈉,中國內地女導演,獨立紀錄片代表人物,1972年生于吉林,曾經是一名話劇團演員。楊荔鈉1999年執導了個人首部紀錄片《老頭》,完成了從演員到導演的身份轉變。《老頭》記錄的是北京城里一些整天坐在樓下聊天的老頭和他們的平凡生活,在長達三年的記錄里,楊荔鈉的攝影機幾乎隱形,與拍攝主體形成了融洽的記錄關系,她也展現出了出色的紀錄片創作能力。《老頭》獲得了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浪潮優秀獎、法國真實電影節評委會獎等多個國際獎項。此后,楊荔鈉陸續執導了《家庭錄像帶》(2000)、《一起跳舞》(2006)、《老安》(2008)、《我的鄰居說鬼子》(2008)、《野草》(2009)、《來自青島的野生藥材》(2009)等多部紀錄片。
2013年,楊荔鈉開始涉足故事片創作領域,執導了劇情電影《春夢》。該片起用非職業演員,采用手持攝影和同期聲的創作方式,使得整部影片呈現出紀錄片的風格特色,也體現出楊荔鈉在故事片創作領域的獨特審美。《春夢》獲得了第50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配角提名,以及第3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別關注獎。2019年,由楊荔鈉自編自導,郝蕾、金燕玲等人主演的故事片《春潮》在網絡平臺上映,該片承續了《春夢》對國內中年女性的影像雕塑,并延伸至三代女性的代際相處之間,以富有詩意的鏡頭描繪了兩代母女的親情暗涌,關注代際的鴻溝之間個體的情感表達。今年5月,繼《春夢》《春潮》之后,楊荔鈉女性三部曲的第三部《媽媽!》(原名《春歌》)登陸內地院線,講述了患有老年疑心病的85歲母親和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65歲女兒之間的生活,展現出了母愛的頑強力量,該片由吳彥姝和奚美娟主演。此外,2020年,楊荔鈉導演了紀錄片《少女與馬》,記錄了六位少女騎手和她們的馬伙伴之間的青春故事。縱觀楊荔鈉的導演生涯,在獨立紀錄片時期,她的鏡頭記錄的最多的對象是平平無奇的老人,記錄他們坐在樓下聊天、在公園里跳舞,也記錄了他們的情感世界。她關注的是普通的個體以及他們無法掌控的平淡的抑或是戲劇般的人生。
在紀錄片的創作中,楊荔鈉表現出了強烈的現實關注性。在故事片的創作中,我們又得以窺見她善于使用意象以營造出詩意氛圍的創作手法。本文將從楊荔鈉導演的紀錄片與故事片創作兩大方面,來探究她的創作維度與審美旨趣。
一、記錄:時代變遷中個體的生存狀態
楊荔鈉是國內最先開始使用DV進行紀錄片創作的導演,在DV成為一種“個人寫作的工具”的技術更新下,獨立紀錄片的創作在變得更加簡便的同時,也與被拍攝群體形成了更加緊密的關系。在楊荔鈉的紀錄片中,我們可以看見中國獨立紀錄片初興時的種種創作傾向與記錄觀念,楊荔鈉也在數十年的記錄生涯中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拍攝模式。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楊荔鈉的鏡頭對準的多是老年群體,以及在他們身上所承載的歷史記憶。《老頭》是一部在國內紀錄片領域頗具創造性的作品,這部影片記錄的是老人們每日聚集在家門口的空地上聊天的場景。他們大多光著上半身或穿著棉白上衣,以及黑色的褲子和布鞋,一眼望去分不清樣貌。他們構成了一個“老頭群體”。這些從工廠退休的老頭們每日無事,每天下午兩點鐘準時下樓,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閑聊。影片的開頭,鏡頭以固定鏡頭呈現了一對老年夫妻之間的日常拌嘴,以妻子對“老頭”三言兩語的抱怨呈現了老年人的生存現狀:在工廠工作期間全年無休,退休后生活驟然空虛。隨著鏡頭轉向了在樓下聊天的老頭們,群體性的特征隨之顯現。我們發現,很難在老頭群體中辨認出剛剛與妻子拌嘴的老頭了,他們擁有著一致的行為模式、外貌特征,聚集在一起。每個人都在說話,又似乎每個人都在聽他人說話。語言在這個群體中并不以溝通性作為主要功能,作為觀眾的我們時常聽不清老人之間的對話。老頭們在下午兩點陸續來到這片空地,又在五點左右陸續離去,形成了一道城市景觀。當老頭們散去后,鏡頭對準了一個獨自拄著拐杖前行的老頭,他以十分緩慢的速度顫顫巍巍地移動,此時個體的年齡性頓顯。從群體到個體的鏡頭呈現方式,凸顯了群體的重要性——他們在以熱鬧的聚集與無意義的閑聊來對抗時間的流逝。
《老頭》的拍攝周期長達三年,在此過程中,楊荔鈉與拍攝群體形成了彼此熟悉的朋友關系,也逐漸形成了一種交友式記錄方式。長鏡頭與同期聲的表現方式讓影片最大限度地還原了老頭們的日常生活,他們有時獨自躺在床上喃喃自語,個體的孤獨性以席卷般的方式籠罩了鏡頭內外。楊荔鈉曾表示,在拍攝《老頭》的過程中,老頭們的生活便是她的生活。楊荔鈉的創作在進入式體驗的拍攝狀態下,在極大程度上體現出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契約精神,即“解構掉了一種精英化的拯救意識,面對小人物,表現出謙卑的姿態”。當楊荔鈉以及她的鏡頭以平等的姿態進入老頭們的生活時,老頭們也沒有了對于介入式鏡頭的防備,在對著鏡頭傾訴時也更加自然,他們的焦慮與痛苦更能被觀眾理解與感受。當老頭們說出“等著吧,等著冒煙吧,沒別的可想了”“活一天算一天吧”這樣的話時,老年人的生活與心理狀態讓人產生了時間維度上的考量。畢竟“老年”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人生階段。這些生活在北京城的老年人為首鋼建設貢獻了一生,這是屬于他們的時代使命。當我們終有一天從所屬的時代浪潮中退場時,所將面對的又與他們有何不同?楊荔鈉所關注的并非是時代中的具體事件,而是在時代的變遷下個體的生存狀態。換言之,老頭也即是我們,是每一個終將老去的人。在鏡頭的瑣碎記錄之下,我們對于生命的無常有了更多的思考——給予老人更多的關愛,便是給予了他們對抗個體孤獨的力量。在影片的最后,有的老人“回家了”,老頭們懷念那些逝去的朋友,繼續著他們的聊天。聊著,他們便存在著。鏡頭也繼續對老頭們無言地長久凝視,記錄他們,便是記錄我們。
2008年,楊荔鈉的《我的鄰居說鬼子》和《老安》兩部紀錄片問世。《我的鄰居說鬼子》通過小區里經歷過二戰的老人們口述對于侵華日軍的回憶,呈現出普通百姓對于戰爭的個體經驗與帶有個人感受的講述。這部紀錄片中采用了訪談式的拍攝手法,導演的聲音有時在片中出現,作為提問人而存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被隱去,只保留老人們的講述。影片通過剪輯將大段的講述打散并進行重組,在紀錄片的視覺觀感上帶給觀眾更易于接受的觀影體驗。
拍攝《老安》時,距離《老頭》已經過去了十年。楊荔鈉延續了對于老年群體的關注,將鏡頭轉向了在天壇公園跳舞的老人們,并選擇了其中一位九旬老人老安的故事進行拍攝。老安在跳舞的過程中,認識了一位舞伴小魏,二人產生了好感,在生活中互相幫扶照顧。影片在記錄二人日常生活的過程中,遇見了一場戲劇性的變故:老安生病住院后,經常去探望他的小魏卻突然不再出現。出院后,老安得知小魏因突發腦出血去世了。老安經歷過悲痛后又回到了天壇公園,認識了新的舞伴,繼續他的生活。在拍攝《老安》之前,楊荔鈉對于在公園中跳舞的老頭群體已經有了一段時間的跟蹤拍攝,并選擇了老安與小魏的故事作為這一部的主要拍攝對象。與《老頭》相比,《老安》在主題上更加突出了人的生命意志和欲望。創作者在拍攝過程中經歷的小魏的悲劇為紀錄片增加了戲劇感。但拍攝主體老安的日常與樂觀的心態,降低了紀錄片中紀實性與戲劇性之間的矛盾感,人物本身由自身閱歷所形成的豐富的層次性為整部影片帶來一種真誠而平和的敘事狀態。對老安的生活細節的描摹以小魏的離世作為時間結點,在此前后,記錄對象的精神面貌與情感狀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十年前面目模糊的“老頭”成為如今具有清晰個人性格與價值取向的老安,楊荔鈉在持續的記錄下關注到了個體人生的獨特性。同時,此時楊荔鈉的記錄鏡頭已經代表她本人成為被記錄人物的“傾訴對象”。小魏在世時對著鏡頭訴說著自己在與老安的故事中所經歷的委屈,而這些個體的情感困境在小魏離世后以一種影像的姿態被永久地記錄了下來,成為影片觸及個體情感生活時所記錄的一個隱秘的角落,個體的價值也在記錄中被顯現出來。當觀眾因為小魏的離世而震驚心痛之余,片中的老安卻已經有了新的舞伴,開始了新的生活——二者都是真實的表達,在這兩種“真實”之間,《老安》也形成了其在紀錄片領域的獨特創作呈現。
楊荔鈉的紀錄片在20世紀90年代初誕生,被稱作“中國式的‘直接電影’”。“直接電影”是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的紀錄片流派,主張紀錄片拍攝過程中攝影師作為旁觀者而存在,主創不干涉、不控制、不介入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視采訪、燈光、解說等為一種破壞行為。《老頭》中比較明顯地體現了“直接電影”的風格,但到了《老安》,顯然地,楊荔鈉并不排斥在記錄過程中融入采訪,反而以提出問題的方式來推動記錄的產生。正如楊荔鈉所說,在拍攝《老頭》期間,她不知道那是在拍紀錄片,更遑論類型表達。而到了《老安》,屬于她的創作意識已經形成。相比于對于類型規則的復刻,楊荔鈉更加關注的是個體人物本身。無論是尋找舞伴的老安,還是讓人遺憾的小魏,都將自己的生活呈現出來,共同構成了生活本身的樣貌。《老安》所表達出的個體命運之無常與堅韌,與《老頭》一脈相承。
二、故事:紀實風格下的詩意表達
2013年,楊荔鈉嘗試涉足故事片領域,起用非職業演員完成了《春夢》,該片演員薛紅獲得了第50屆臺北金馬影展最佳女配角的提名。《春夢》是一個關于國內中產階級家庭的故事。養尊處優的太太方蕾和丈夫結婚多年,身體的欲望逐漸被忽略,無法得到滿足的她轉而去夢境中尋求安慰,現實生活中女兒卻遭遇了意外。夢中的男子成為方蕾的心魔,她轉向宗教尋求解脫。盡管是一部故事片,但《春夢》帶有明顯的紀實風格,特別是前半段劇情中方蕾對于自我欲望的探索,在男人符號化的不在場的當下,中產階級日常的無聊萎靡呈現在我們面前。影片以夢境的方式對女性的身體與欲望進行直接展示。春夢,一場旖旎夢境,夢中有英俊的男子,能夠撫慰在枯燥日常中焦慮寂寞的方蕾,她在這場春夢中無法自拔。而當她試圖尋求現實的解脫時,夢中之人卻逐漸猙獰,這一場女性主體的“聊齋”,在人“鬼”之間,讓整部影片呈現一種現實與虛構之間的詩意性。
《聊齋志異》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中國古代志怪小說,也被認為是有著詩意敘事的詩化小說。“詩化小說落墨不在人物性格上,而是著墨于人物情感的表現,心靈中剎那間的感悟。”在貼近生活的故事背景下加入一個想象中的奇幻空間,在一虛一實間,人物情感得到強烈抒發,由此產生“作者滲透于作品中的既內斂而又十分強烈的情感意緒”,并被受眾所感受到。《春夢》同樣有人“鬼”愛戀的情節,繼承了這種詩意的敘事方式,奇幻想象下是對現代人生存方式與生活現狀的真實刻畫。方蕾的身體欲望沒有得到老公的重視,外部對女性身體與欲望的壓抑使她只能逃遁到虛擬空間中去尋求排解,卻由此造成了女兒的意外,家庭關系走入了更逼仄的現實困境。從巫婆到道士,再到尋求佛教的救贖,方蕾在利用宗教爭奪自我欲望合理性的過程中,逐漸由無意識的被動走向有意識的主動。我們可以感受到影片中涌動的強烈的個體情感,方蕾的鮮活的生命狀態成為時代中個體的真切畫像。當現實越發苦悶,個體向夢境尋求慰藉;而當夢境開始干擾現實,被粉飾的現實立刻被撤下了華麗的絨布,露出了干癟的內核。《春夢》呈現出一種復雜而迷人的氣質:它既是身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既是寫實的,又是超現實的。
在對方蕾日常生活的呈現上,影片加入了許多作為時代背景的細節。當她和女兒開車時,有乞討者帶著來歷不明的孩童乞討;當她在商店購物時,背景音是遭遇車禍的路人因無人幫助而死去的新聞;當她在做家務時,窗外響起了陣陣警笛聲;當她想和老公親密接觸時,老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平板電腦的切水果游戲上……盡管影片沒有提及某一個具體的社會事件,但處處傳遞了一種緊張與不安感,觸及到時代的精神與道德剖面。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方蕾的欲望代表著中產階級的焦慮與不安,衣食無憂并不能讓她獲得精神上的安定之感。方蕾所面臨的是時代的欲望與恐懼。方蕾把夢境當作安身之所,影片也在夢境中完成了超現實性的表達,象征著自由的馬匹與流動的水,這些充滿詩意性的意象是精神的棲息之所,也是影片詩意生成的重要途徑。
2019年上線流媒體的《春潮》進一步強調了對意象的使用,聚焦中國社會家庭關系中遭遇的情感困境。《春潮》的故事發生在由三個女性組成的家庭關系中。紀明嵐、郭建波與郭婉婷這兩對母女關系架構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在巨大的裂痕下無法探尋到合理的理解與溝通的渠道。影片呈現了一種無法調和的原生家庭中的親子關系,整體氛圍是較為壓抑的,敘事空間集中在狹小的兩室一廳內。以手持攝影去還原一種真實的生活狀態,盡可能地減少劇情片的造型感,因此,《春潮》同樣呈現出一種樸素的紀實感。同時,影片很善于在細節之處使用意象表達,在有限的空間內彌漫出詩意性。例如,郭建波兩次在花盆里埋下東西,體現了她剛強外表下的柔軟內心和對于美好事物的期待。被郭婉婷驚嚇的粉紅色的鴿子,象征著被施加精神暴力的無助個體;最為重要的是影片中多次出現的水的意象。影片以水代表夢境空間,其實是對《春夢》中超現實夢境空間的延續。當郭建波因為母親的言語暴力而崩潰大哭時,她在廚房把水龍頭打開,在巨大的水流聲中將崩裂的自我與現實分隔開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春潮》中的水正如《春夢》中的夢境一樣,是自我暫時逃避現實的寄身之所。在影片的結尾,攝影師以手持攝影的方式跟蹤水的流淌,“在潮水段落,所有的水都是實實在在地從門縫、階梯、馬路上流淌出來的”。郭婉婷追逐著水流一路奔跑,最終跳入湖中嬉戲。此時的水流象征著個體來到世間時所經歷的母親的產道,跳入湖中的舉動象征著個體回到了母體子宮,寓意著自然所賦予的母子關系,萌生了一種誕生自現實之中的詩意。此外,影片還有諸多隱晦的意象和隱喻,最終大多以簡單、樸素的現實主義手法加以展現出來。
楊荔鈉的故事片創作在極大程度上借鑒了她拍攝紀錄片的經驗,二者形成了一種審美維度上的延續。她的故事片并不追求奇巧的劇情,沒有刻意營造的矛盾與轉折,劇情是生根于現實生活的。她的故事片另辟了一條既現實又隱喻的蹊徑去書寫一些無解的難題。《春夢》中的方蕾在尋求佛教解脫時卻對英俊的小和尚動了情欲;《春潮》中紀明嵐與郭建波無法緩和的母女關系以一方的離去而告終……楊荔鈉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些問題都是沒有答案的。而她所要做的也并不是尋求一個最優解法,只是呈現。換言之,她的故事片同樣是另一種形式的記錄。在虛構的情節中融入當下的真實,在虛構的人物中融入個體的感悟。楊荔鈉的詩意,最終體現在以“真”來刺破她所建構的現實主義文本幻象,呈現生活的本來樣貌。
結 語
楊荔鈉作為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在紀錄片創作領域記錄了許多“老頭”的生活,而轉向故事片時,男性角色卻從她的敘事中缺席了,人們常把她的故事片與當代女性導演的女性意識表達聯系在一起。除卻性別意識之外,楊荔鈉在兩種電影類型領域中一以貫之的美學觀念也是十分值得關注的,她從未放棄對個體處境的關注,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一直在她的作品中散發著柔和的光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