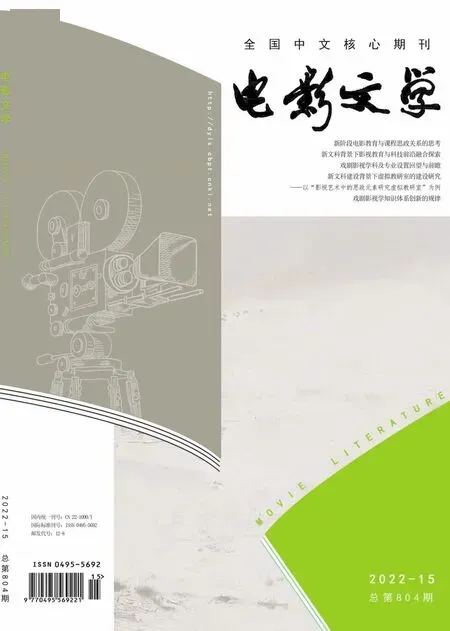論諾蘭電影語義悖論的發展、機制與價值
許五龍
(黃岡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北 黃岡 438000)
克里斯托弗·諾蘭是當今好萊塢最炙手可熱的導演之一,他不僅樹立了自己獨特的影像風格,并且影響了整個好萊塢乃至整個電影世界,他的名字成為當代電影界令人矚目的現象級符號。國內對諾蘭電影的研究大多數以單部電影為研究對象,而且主要集中在敘事技巧、人物塑造、影像語言、主題思想等方面,但是鮮有從語義悖論的角度對克里斯托弗·諾蘭的電影進行研究。目前僅有黃賢春博士在其論文《論電影中的語義悖論》中初步考察電影藝術中語義悖論的發展、邏輯基礎和現實生成的原因,對于諾蘭電影的語義悖論現象也只是提到了《盜夢空間》這部電影。
悖論是指通過有效推理而導致了必然矛盾的認識現象,語義悖論是指在“本質上包含語義學概念”的悖論。電影語義悖論現象早已有之。1985年上映的《回到未來》和1992年上映的《終結者》都講述了有關時空穿越的故事,然而穿越者卻與幾十年前的人物擦出愛情火花甚至共同孕育了未來人類的領袖,這樣,語義悖論現象也就出現了。當主人公回到未來后,即出現了無法理解的“此人非此人”的現象。1999年沃卓斯基兄弟拍攝的《黑客帝國》使得電影語義悖論現象從時空穿越模式走向平行空間模式,它不再依托時間旅行這樣的情節,而是在電影內部創造一個平行空間,使一個系統中包含另一個系統的結構,而外部系統中的信息或者規則又影響到內部系統本來的運行法則。進入21世紀后,諾蘭導演的許多電影,如《記憶碎片》《致命魔術》《盜夢空間》《星際穿越》都出現更為復雜的語義悖論現象,使電影中的語義悖論發展到更為成熟的階段。本文從語義悖論的視角切入,分析諾蘭電影中語義悖論的發展歷史、形成機制與藝術價值。
一、諾蘭電影中語義悖論的發展歷史
諾蘭電影中語義悖論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在諾蘭的早期電影中存在大量的第一人稱視角的語義悖論,并且這些現象呈現出一種無意識、自發的狀態。在《記憶碎片》中,諾蘭通過黑白與彩色的對比,以及交叉敘事的手法區分了過去完成時與現在進行時兩個不同的系統。當泰迪解開謎題后,真相指向于男主人公因為自己的病癥而失手殺死了自己的妻子,男主人公知道泰迪只是利用他的病癥來幫助他不斷地除去死對頭后,一氣之下殺死了泰迪,但是此時坐在車中的主人公卻在照片上面,以及自己的文身上面寫下了警察泰迪是兇手的線索,從而企圖逃避自己殺死妻子的事實。這里就出現了一個語義悖論,當男主角再次醒來后,會繼續按照自己身上的文身來尋找殺死自己妻子的兇手,但是文身所留下的線索所指向的內容,是主人公的主觀印象所創造的線索來引導的,而不是真實發生的事情,這就形成了“我見非我見”的語義悖論。
在《致命魔術》中,第一人稱語義悖論更具有新奇性。影片中,諾蘭不再是通過交叉敘事手法來構筑兩個不同系統,而是通過情節設置來構筑外部系統。影片中的外部系統是兩位魔術師的世紀對決,以及他們的恩怨情仇,而內部空間存在著多個,即每一場魔術都可視為一個內部系統。在魔術世界中,由于一切都是受控的,魔術師往往通過自己的手法令觀眾受控于自己,令觀眾看到不可思議的一幕,而這一幕是真實的同時又是由魔術師控制而形成的,因此觀眾在魔術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會打上一個“非”的烙印,于是出現了“我見非我見”的悖論。影片中由科學家發明的復制機可以對人本身進行完全的復刻,因此魔術師安吉爾便利用這個機器來克隆自己從而完成魔術。而安吉爾為了避免克隆后的自己進入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外部系統當中去,他設置了機關使得每次魔術表演完,會有一個自己掉入水箱中淹死,而這也使得影片中的內部系統形成一個閉環,具有穩定性和封閉性。在外部環境中,與安吉爾互為宿敵的伯登便變成了一個不可計量的變量因素,他帶有外部系統所塑造的情緒誤入了魔術后臺看到了安吉爾掉入水中淹死,也就打破了內部系統原有的穩定性和封閉性,那么電影中的語義悖論也就產生了:當伯登含冤入獄后,安吉爾其實并沒有死去,那么也就出現了“我死非我死”以及“我殺非我殺”的悖論。
在諾蘭的后期電影中,語義悖論的形式逐漸發展成了第三人稱視角。影片《盜夢空間》講述了一個經驗老到的造夢團隊進入他人夢境,從他人的潛意識中盜取機密,并重塑他人夢境的故事。影片設置多重夢境,每一層夢境與上一層夢境之間都形成了一個羈絆關系,影響其信息傳遞和因果聯系,這也就為悖論的出現構成了一個“此在”的現象,而這個承載悖論的媒介也就不再受其本身控制。影片中男主人公柯布的亡妻瑪爾頻繁出現在主人公的行動中,但是這個人物并不是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生命體,她既不屬于夢境的控制者們,也不屬于被盜夢團隊所控制的人物,而只是男主角因情感因素而導致的執念從而形成的潛意識,因此瑪爾作為一個干擾者在所在夢境中所形成的干擾并不受人物瑪爾本身所控制,這就是所謂的“此人非此人”。
電影《星際穿越》講述了一隊探險家利用他們針對蟲洞的新發現,超越人類太空旅行的極限,從而開始在廣袤的宇宙中進行星際航行的故事。當處于高維度的庫伯在宇宙中向低維度的墨菲傳遞信息時,畫面中便出現了兩個庫伯,一個是在宇宙中流浪的庫伯,一個是還未來到航空中心的庫伯。盡管觀眾看到的是兩個同時出現的庫伯,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在宇宙中流浪的庫伯出現在了更高維度,他自身呈現出了一種不受控的狀態,因而在電影中被墨菲稱之為“幽靈”。因此出現在更高維度的庫伯并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庫伯,而是更高維度的生物通過某種方式將庫伯的意識進行了一個“無意識”的投射。與《盜夢空間》不同的是,庫伯的出現并不是以“干擾者”的身份,而是以“協助者”的身份幫助墨菲找到拯救地球的方法,“庫伯”的出現呈現出了一個“此在非此在”的悖論。
二、諾蘭電影語義悖論的生成機制
波蘭數學家和邏輯學家塔斯基對對象語言和元語言做了區分,從而指出了悖論的來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在語義悖論問題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時,我們的語言被稱為對象語言,而當我們在討論一種語言時,我們使用的語言便被稱為元語言。借用這一方法分析諾蘭電影,我們會發現,對象語言和元語言的套層結構是諾蘭建構其獨特的語義悖論的邏輯基礎。
如《致命魔術》中復制機的設定就體現出語言層次上的套層結構。在魔術師安吉爾向觀眾表演魔術節目“我死了”中,魔術師的表演活動是這一情節的元語言,而節目內容“我死了”則成為對象語言;而當另一位魔術師闖入,即作為一個外部系統的因素闖入內部空間后,“我死了”這一對象語言就變成了元語言,這種套層結構是其產生語義悖論的重要方法。
相對于早期作品,諾蘭的后期作品中呈現出一種有意識的、自發性的主動創造狀態。在《盜夢空間》中,可以看到當亡妻瑪爾作為干擾者出現在夢境當中時,主人公所處的夢境即為元語言,而主人公自己的潛意識則為對象語言。在這一情節當中,元語言本身與對象語言之間并不構成一個表達關系,也就不會出現套層,但是諾蘭刻意令潛意識里面的瑪爾出現在了主人公所出現的夢境當中,強行將元語言和對象語言構成聯系,此時的對象語言處在其元語言的層次當中形成套層結構,從而導致其悖論的產生。
對諾蘭電影而言,僅止于分析其元語言和對象語言之間所具有的套層結構顯然是不夠的,如果深入分析其電影會發現,內在真實情感支撐和外在反常規敘事相融合的創作手法為諾蘭電影中的語義悖論構成提供了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或者說,真實塑造與虛擬呈現是諾蘭電影建構語義悖論的重要策略。
諾蘭電影首先表現為對于某種真實性的塑造,反映出他對于“人”本身的價值思考,這種方式形成了一個序列化的發展狀態,從早期的《追隨》《記憶碎片》等對人類內心的個體化反思到后期的《蝙蝠俠》《星際穿越》等對反人類行為的討論。這種真實性的塑造為諾蘭電影中的人物和情節提供了某種合理化和形而上的主題追尋,進而對電影中帶有的悖論性情節提供了內在的情感支撐。心理學家楊姍姍在《心理學九型人格》一書中指出:“人是非常復雜的,很少有人具有單一的某種人格特征,在某種類型的人格中可能混雜著其他類型的特征。”電影《盜夢空間》中,作為團隊領導者的柯布除了顯現出領導者的人格特征外,還顯現出一種浪漫主義者身上所特有的對愛情的負面情緒。弗洛伊德認為,“潛意識的存在雖然不為人所察覺,但卻支配著人的一生”。柯布因為自己當年的私欲導致妻子的精神失常和墜樓身亡讓他心中飽含愧疚,隨之而形成的潛意識成為他每一次行動的“干擾者”。浪漫主義人格使柯布呈現出的愧疚這一情緒更具有其合理性,潛意識所代表的人類內心的真實性也表現出了諾蘭對于人類心理的最真實的表達訴求。
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其小說《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曾表達了人類的憂慮:人們會漸漸愛上工業技術所帶來的娛樂和文化而不再思考。電影《致命魔術》中,諾蘭就表達出對全新科技所導致的人類社會的改變的憂慮。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爾特認為,“外延符號(能指和所指)又構成了內涵的能指,這種內涵的能指(即包括外延能指和外延所指的外延符號)再和內涵的所指一道,共同構成內涵符號”。影片中,安吉爾使用的作為外延符號的特斯拉發明的復制機構成了“科技”內涵的能指,而波登的作為外延符號的雙胞胎魔術構成了“原始生命”內涵的能指,而科技和原始生命展現了諾蘭對于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彼此斗爭的隱喻。當科技和原始生命意味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時,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也就變成了電影中內涵符號的所指,進而可以看到諾蘭通過復制機和雙胞胎完成了對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的符號表達。
然而在諾蘭的電影中,他對內在情感真實性的表達并沒有立足于現實主義,而是采取非常規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時空。在《記憶碎片》中,諾蘭沒有使用現實主義常用的傳統線性敘事,其敘事方式并不符合麥茨的八大段理論。盡管電影中有主觀插入鏡頭,但是電影的整體結構并不符合麥茨所指出的兩種非時序組合段中的任何一種。諾蘭在線性敘事結構下在影片的中間進行分割,然后又將后半部分的戲進行倒敘,前半部分的最后一場戲與后半部分的第一場戲又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一個環形結構。這使得電影中的敘事形成了多級系統,為這部電影中的語義悖論現象的產生提供了基礎。在諾蘭的影像中,他往往會創造一種新的宇宙和人物世界觀,通過對時空的重構來展現出非傳統的影像世界,這種表達形式也逐漸形成了諾蘭電影中的層級結構,為語義悖論現象提供了溫床。在《星際穿越》中,諾蘭將整部電影的故事環境置于宇宙中,他并沒有立足于人類當下對于宇宙的理解,而是利用當代量子力學提出的假設去呈現宇宙。諾蘭借助物理學家索恩的理論將時空翹曲等物理法則融會在電影當中,從而呈現出了一個超越真實的宇宙世界。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曾說過:“人類如果想描述現在已知的宇宙,必須跨越現實的存在,進入高維空間,只有那時,宇宙中的許多結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星際穿越》正是利用對于五維空間的一個呈現來改變了時間和空間的線性構造,將時空進行了重構,從而形成了差異化的系統,而各級系統之間也就為語義悖論現象的形成提供了基礎。
三、諾蘭電影語義悖論的藝術價值
諾蘭電影語義悖論的藝術價值,首先表現在多學科融合下的藝術創造。黃賢春博士在《論電影中的語義悖論》中認為,影片中的語義悖論的產生與電影藝術的復雜性發展相關,“在電影語義悖論生成過程中,電影組織規則的變化主要涉及神話、科學和哲學系統”。
首先,無論是《記憶碎片》中的短期失憶癥、《致命魔術》中的復制機、《盜夢空間》中的盜夢、《星際穿越》中的量子力學,這些在電影中形成語義悖義現象的較為重要的情節點一方面呈現出新穎性和虛擬性,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某種現實性與合理性,比如短期失憶癥對應的是失憶癥,復制機對應的是克隆技術,盜夢對應夢境理論,時空穿越對應的是當代量子物理中的某些假說。可見,語義悖論得以形成的情節點是將電影內容高度復雜化的結果,例如科技與神話的結合、魔術與科技的結合等。諾蘭通過悖論性的構成將電影中的藝術系統、神話系統和科技系統等多學科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內容奇觀。與其說諾蘭通過這些新鮮的理論來將電影內部構成了不同的系統,進而產生了語義悖論現象,倒不如說這些理論其實是與語義悖論現象之間具有某種高度匹配的關系,這也就使得電影與科學乃至其他更多學科產生進一步的交融,大大增加了電影本身的新奇性和深刻性。
其次,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系統,其悖論性不僅在于與科技系統和神話系統相結合所帶來的新奇性,而且要呈現出合理性和有意義,要表現出“人”的內涵所在,將“人”這一主題與電影中的悖論現象相結合從而達到某種效果。例如在《盜夢空間》中,柯布所呈現出的浪漫主義人格為瑪爾的出現提供了一種合理性;而《星際穿越》中,庫伯所體現出人本身親情的力量也為庫伯出現在高維度地區呈現出一種合理性。在這些情節當中,諾蘭不僅是結合了科技層面,更是結合了心理學等學科。
諾蘭電影語義悖論的藝術價值還在于其對藝術性和商業性做了完美的結合。諾蘭電影通過語義悖論現象將邏輯哲學引入電影當中,使觀眾在思考電影悖論時感受邏輯哲學帶來的魅力。此外情節上的跌宕起伏和結構上的復雜化,也給觀眾錯綜復雜的感覺,既消除了觀眾在觀看藝術電影時所產生的疲憊感,也打破了觀看商業電影時的同質感現象,平衡了電影在藝術與商業之間的關系,使電影藝術性和商業性做了完美的結合,這也正是他的電影取得口碑與票房雙贏的秘密所在。
幾乎所有電影語義悖論現象都是在后現代語境下產生的,無論是早期的《回到未來》和《終結者》,還是諾蘭的電影中,語義悖論都是在某種非傳統的影像呈現方法中萌生的。然而語義悖論與后現代的影像方式之間并沒有出現必然的關系,且并非所有的后現代的呈現方式都如同諾蘭的電影一樣帶來口碑與票房的雙贏。例如中國導演陳正道的作品《催眠大師》和《記憶大師》都借鑒了諾蘭《盜夢空間》中對于夢境和記憶的運用,但是在口碑上卻呈現出一種兩極化的現象,反觀諾蘭的《盜夢空間》則完成了對于電影票房和口碑的雙贏狀態。陳正道的作品盡管利用了夢境或記憶這些元素,但是并沒有產生相對應的悖論現象,整個夢境與現實生活呈現出一種脫離的狀態,令整部電影缺乏整體性。而《盜夢空間》中加入了一個干擾元素,將整部電影中的夢境與現實形成了一種聯系,而這種聯系是諾蘭刻意形成悖論性的結果。
在電影藝術的發展進程中,電影語義悖論從產生到走向成熟,諾蘭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他不僅深化了語義悖論的影像創作手法,而且把它發展成為一種美學特征與影像風格。諾蘭電影中的語義悖論的邏輯基礎在于他善于通過對時空關系的拆解從而達到一部電影中同一空間內產生不同的系統,且系統內外之間形成一個規律性的差異。而電影本身則剛好是通過其符號化的表達和對于現實的真實塑造來獲得的一種人為構建的空間,使得人物在這些空間內部不斷地活動或互相影響,來造成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悖論。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本身的呈現方式就被允許有某種不合理性,也就是為何諾蘭可以隨意搭配或運用元語言和對象語言從而產生語義悖論。早期的語義悖論現象并不是電影創作者手中的武器而更像是創作者在肆意發揮想象力時無意間放出的野獸。電影語義悖論現象為世界電影的發展開拓一種全新的可能性,而諾蘭通過有意識的創造藝術悖論大大增加了其電影中的新奇性和深刻性,并且逐漸消除了好萊塢傳統電影的同質化創作所帶來的傷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